孔子與官書制度(下)——孔子對(duì)書籍傳播的歷史貢獻(xiàn)
劉光裕
(山東大學(xué) 新聞傳播學(xué)院,山東濟(jì)南250100)
經(jīng)學(xué)傳記是一家之學(xué)的集體著作——兼談官書三特征與產(chǎn)生集體著作的必然關(guān)系
六經(jīng)的經(jīng)學(xué)都由經(jīng)文與傳記兩部分組成。如《詩(shī)經(jīng)》之305篇詩(shī)作,如《春秋》之魯國(guó)十二公編年史,如《周易》之六十四卦象與卦辭、爻辭,這些都是經(jīng)文,也稱本經(jīng)。傳記是對(duì)經(jīng)文的解釋。舉例如,《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此為經(jīng)文。《公羊傳》解釋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此為傳記。再如,《詩(shī)經(jīng)·周南》第一篇《關(guān)睢》,這詩(shī)作是經(jīng)文。《毛詩(shī)》解釋說:“《關(guān)睢》,后妃之德也,風(fēng)之始也,所以風(fēng)天下而正夫婦也。”此為傳記。對(duì)經(jīng)文的解釋,無論是口頭還是文字,古人稱“傳”或“記”,也稱“傳記”。對(duì)經(jīng)學(xué)來說,經(jīng)文與傳記都重要,兩者缺一不可。經(jīng)文如果沒有傳記,如《詩(shī)經(jīng)》經(jīng)文就是一部古代詩(shī)歌集,又如王安石稱《春秋》經(jīng)文為“斷爛朝報(bào)”,就只有史料價(jià)值與文獻(xiàn)價(jià)值,而不具有儒家意識(shí)形態(tài)的意義。東漢桓譚說:“經(jīng)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太平御覽》卷610)從“王正月”到“大一統(tǒng)”,從《關(guān)睢》到“后妃之德”,說明經(jīng)文的思想意義是由傳記賦予的。經(jīng)學(xué)作為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思想體系,都是通過傳記對(duì)經(jīng)文的解釋而產(chǎn)生的。儒家經(jīng)學(xué)以此為特征,區(qū)別于諸子,也區(qū)別于世界上其他思想家的著作。經(jīng)學(xué)的歷史演變?nèi)鐫h學(xué)演變?yōu)樗螌W(xué)之類,最終取決于傳記內(nèi)容的演變;經(jīng)學(xué)作為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性質(zhì),概取決于傳記。經(jīng)文雖為“周官之舊典”,可是孔子對(duì)經(jīng)文的解釋是民間著述,所以在西漢獨(dú)尊儒術(shù)以前,經(jīng)學(xué)一直是民間學(xué)說,儒家也與諸子一樣是民間學(xué)派。
據(jù)漢以來文獻(xiàn)記載,傳記都由孔子弟子傳于后世。如認(rèn)為商瞿傳《易傳》①《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淄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子夏傳《毛詩(shī)》②《漢書·藝文志》:“毛公之學(xué),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xiàn)王好之。”又,《經(jīng)典釋文》:“徐整曰:‘子夏授高行之,高行之授薛倉(cāng)之,薛倉(cāng)之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shī)故訓(xùn)傳》。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xiàn)王博士。’”,子夏傳《公羊傳》《谷梁傳》③徐彥《公羊傳疏》載《何休序》引載宏曰:“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于子平,平傳于子地,地傳于子敢,敢傳于子壽。至漢景帝時(shí),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谷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還有曾參傳《孝經(jīng)》等。商瞿、子夏、曾參都是孔子著名弟子。學(xué)界公認(rèn),傳記歸根結(jié)底源于孔子教授弟子時(shí)對(duì)經(jīng)文的解釋,沒有孔子當(dāng)年講經(jīng),就沒有傳記。那么,這些傳記的作者是誰呢?是否就是孔子?若不是孔子又是誰?如《易傳》,自漢至魏晉的幾乎所有著名學(xué)者都說是孔子作。④舉例如:《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系辭》《說卦》《文言》。”《漢書·藝文志》:“孔氏為之《彖》《象》此外,魏晉以來大都認(rèn)為,《左傳》的作者為左丘明,《公羊傳》的作者為公羊高,《谷梁傳》的作者為谷梁赤作,《毛詩(shī)》的作者為子夏或毛弘或毛萇,如此等等。宋代歐陽修最早指出《易傳》“非一人之言”(《〈易〉童子問》),否認(rèn)《易傳》為孔子作。大致從宋代開始,逐漸發(fā)現(xiàn)傳記都不是某一個(gè)人的文字,于是產(chǎn)生了是否“偽作”的長(zhǎng)期爭(zhēng)執(zhí)。總之,傳記的作者問題由來已久,兩千多年懸而未決。
凡書籍都有作者,討論作者與作者問題是書籍史或出版史的份內(nèi)之事。經(jīng)學(xué)傳記都是先秦古書。可是,后人所見傳記都是漢代人整理并公諸于眾后傳下來的本子;它們?cè)跐h代以前傳承了二三百年的本子(口傳或文字),因?yàn)閺奈垂T于眾的緣故,漢代就見不到了,漢代以后根本無法見到,無以為據(jù)。在我國(guó)書籍史上,漢代以前是漫長(zhǎng)的官書時(shí)期。官書與漢以來書籍相較有三大特征,這就是:不準(zhǔn)公眾傳播,作者不署名,書無定本。官書時(shí)期的學(xué)術(shù)著作受官書三特征的影響,凡經(jīng)長(zhǎng)期傳承,最后不能不演變?yōu)闊o名氏集體著作。可以說,有官書三特征,必有無名氏集體著作。傳記在官書時(shí)期傳承了二三百年,不能不受官書三特征影響與制約。因此,討論經(jīng)學(xué)傳記這類先秦古書的作者問題或著作權(quán)性質(zhì),首先要注意官書三特征與產(chǎn)生無名氏集體著作的必然關(guān)系。弄清了這個(gè)關(guān)系,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不然的話,只能再一次回到上千年懸而不決的爭(zhēng)論中去,不會(huì)有什么結(jié)果。對(duì)傳記來說是如此,其它先秦古書大致也是如此。不過,人們對(duì)官書三特征早已陌生,它與無名氏集體著作的關(guān)系又是諸多因素糾結(jié)在一起的復(fù)雜問題,三言兩語說不清,且從作者不署名講起。
秦漢以前,作者不署名作為一種歷史傳統(tǒng),最初源于官書,后來又被經(jīng)籍與子書所繼承。余嘉錫《古書通例》有“古書不題撰人”一節(jié),說之甚詳。清初學(xué)者章學(xué)誠(chéng)最早發(fā)現(xiàn)先秦作者不署名,他在《文史通義·為公篇》反復(fù)講一個(gè)觀點(diǎn)就是:“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jù)為己有也。”他說“古人”不將作品(“文辭”)“據(jù)為己有”,意思就是作者不署名,此言不虛。不過,他認(rèn)為不署名的原因是出于作者“為公”之心,無非是復(fù)古史觀的臆測(cè)而已,并無事實(shí)根據(jù)。商周以來,政治上為君權(quán)至上;經(jīng)濟(jì)上是無所不包的國(guó)有制;文化上實(shí)行幾無遺漏的全面壟斷,就是史官文化。官書都是官府典籍。史官文化從壟斷典籍的需要出發(fā),將官書中作品一律規(guī)定為君王所有或國(guó)家“公有”,不許視為作者“己有”。如果允許將作品視為作者“己有”,等于將作品視為貴族私有,必將危害官書制度的鞏固,所以是史官文化決不允許的。將官書中作品視為君王所有或官府“公有”,這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頗為一致,也與公田之外沒有私田頗為相似,這些在西周是普通平常之事,并不奇怪。在出版學(xué)看來,作者署名的根據(jù)是什么?這根據(jù)就是將作品在名義上或精神上視為作者所有。官書中作品不許視為作者“己有”,說明作者沒有署名的根據(jù),也就是沒有署名權(quán)。可見,官書作者不署名的真正原因不是別的,是因?yàn)樽约簺]有署名權(quán)。如果作者是因“為公”而不署名,其中一個(gè)必要前提是作者享有署名權(quán);而官書作者是因?yàn)樽约簺]有署名權(quán)而不署名,所以與“為公”毫不相干。須知官書作者的身份是“王官”,他們撰寫作品是奉王命,循職守;
《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魏晉易學(xué)名家王弼、韓康伯說:“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見
《周易正義卷首》,《十三經(jīng)注疏》本)他們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賞賜,是爵祿(因?yàn)樽髌凡荒芄妭鞑ィ髡邔懽鞲挪灰悦麨閯?dòng)機(jī))。如前所說,官書作者是壟斷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可能也不需要反對(duì)將作品視為君王所有或國(guó)家“公有”,這也是不將作品視為作者己有的觀念得以長(zhǎng)期存在的一個(gè)原因。經(jīng)籍與子書都不是官書,可是官書傳統(tǒng)是書籍領(lǐng)域的唯一歷史傳統(tǒng),人們只能繼承這個(gè)傳統(tǒng),包括繼承不將作品視為作者“己有”的傳統(tǒng)觀念,故而經(jīng)籍與子書的作者也不署名。
先秦作者概不署名,說明先秦作者對(duì)作品沒有署名權(quán);沒有署名權(quán)的根源在官書制度,不在作者方面。
在我國(guó)古代,作者署名萌生于戰(zhàn)國(guó)后期,到漢代才漸漸成為社會(huì)習(xí)尚,大致以漢代為界,由作者不署名演變?yōu)樽髡呤鹈臍v史過程看,作者在作品上署名,首先取決于社會(huì)觀念將作品在名義上或精神上視為作者所有,簡(jiǎn)單說是將作品視為作者己有。自漢代開始建立了這樣的社會(huì)觀念,我國(guó)作者從此享有作品的署名權(quán),因而都在作品上署名。與此同時(shí),又逐漸形成了與這種社會(huì)觀念相適應(yīng)的道德準(zhǔn)則,以維護(hù)作者署名的真實(shí)性不受損害。漢代以前因?yàn)橐恢蔽茨芙⑦@樣的社會(huì)觀念,所以作者概不署名。今天所說著作權(quán),其核心就是作者對(duì)作品享有署名權(quán);作者對(duì)作品的其它權(quán)益,都是在署名權(quán)基礎(chǔ)上派生出來的。我國(guó)自漢代建立的將作品視為作者己有的社會(huì)觀念,以及與此適應(yīng)的道德準(zhǔn)則,與今天所說著作權(quán)的核心——署名權(quán)完全一致,僅因?yàn)椴皇欠梢?guī)定的權(quán)利,故稱“著作權(quán)觀念”,以示區(qū)別。
在我國(guó)書籍史上,漢代開始建立著作權(quán)觀念是古代書籍文明的重大進(jìn)步,具有里程碑意義。至今有人仍舊認(rèn)為,先秦作者不署名是“為公”,漢以來作者將作品視為“己有”是道德退步,這是與書籍文明背道而馳的錯(cuò)誤觀點(diǎn)。無論在著作界還是讀書界,著作權(quán)觀念之有無,亦即作者署名與否,都是具有重大影響的頭等大事。例如,在沒有著作權(quán)觀念(作者不署名)的社會(huì)中,作者可以無條件地、任意地利用或使用他人作品,其中概不存在“竊為己有”與“篡改”之類問題,僅此便知著作權(quán)觀念決非無足輕重。在漫長(zhǎng)的官書時(shí)期,因?yàn)闆]有著作權(quán)觀念(作者不署名),再加不向公眾傳播與書無定本,這些深刻影響了作者觀念、讀者觀念以及著作方式,從而形成一種與漢以來截然不同的特殊著作環(huán)境,再通過作者及其著作活動(dòng),最終影響作品特別是學(xué)術(shù)著作的著作權(quán)性質(zhì)。下面,分別予以說明。
其一,影響作者觀念。作者不署名與不向公眾傳播這兩項(xiàng),決定作品不可能成為作者獲取名利的工具,因而作者頭腦里的名利觀念也無從產(chǎn)生。作者不署名得以長(zhǎng)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書籍尚未公眾傳播,在實(shí)現(xiàn)公眾傳播以前,作者不署名必將繼續(xù)存在。鑒于作者的自我意識(shí),包括作者的責(zé)任觀念、榮譽(yù)觀念、道德觀念等,無不源于將作品視為作者己有(作者署名),所以在建立著作權(quán)觀念以前,作者的自我意識(shí)不可能完全自覺,與作者意識(shí)相互依存的讀者自我意識(shí)也不可能完全自覺。由此可知在漢代以前作者與讀者的區(qū)別是模糊不清的,兩者間不存在像漢代以來那種涇渭分明的界限。
其二,影響讀者觀念。不將作品視為作者己有的社會(huì)觀念決定讀者頭腦里的書籍作者,一概沒有真假之別,與此相聯(lián)系的“偽作”觀念也就無從產(chǎn)生。因此,道德領(lǐng)域也不可能產(chǎn)生反對(duì)“剽竊”“篡改”之類旨在規(guī)范作者活動(dòng)的道德準(zhǔn)則。受作者不署名的影響,讀者只關(guān)心作品本身,不知道也不關(guān)心作者是誰,對(duì)作者問題從來不聞不問。讀書界產(chǎn)生偽作觀念以及社會(huì)上重視作者問題的時(shí)間,只能在著作權(quán)觀念產(chǎn)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其三,影響著作方式。不準(zhǔn)公眾傳播的官書,都在相對(duì)固定的狹小范圍內(nèi)世代傳承,如醫(yī)書在醫(yī)官范圍世代傳承、天文書在天官范圍世代傳承,如此等等。對(duì)官書來說,一是在相對(duì)固定的狹小范圍內(nèi)世代傳承(不向公眾傳播),二是不將作品視為作者己有(作者不署名)。因此,凡有舊作可用,就不必另撰新作;凡撰新作,大都利用舊作,對(duì)舊作做修訂改造的工作。總之,著作活動(dòng)以修訂舊作為常規(guī),非必要不另著新篇。作者修訂舊作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對(duì)已有的單篇作品,做重新選擇、編次的工作,《詩(shī)》《書》皆屬此類;另一種是對(duì)舊作內(nèi)容做增刪、改造或吸收、整合的工作,學(xué)術(shù)著作大都屬于此類。
由此可見,受官書三特征影響的作者觀念、讀者觀念與著作方式,與漢代以來迥然有異,因而形成一種與漢代以來截然不同的特殊著作環(huán)境,時(shí)刻制約作者及其著作活動(dòng),從而影響作品特別是學(xué)術(shù)著作的著作權(quán)性質(zhì)。
為何特別強(qiáng)調(diào)影響學(xué)術(shù)著作的著作權(quán)?所說學(xué)術(shù)著作,是與同為官書的典章文獻(xiàn)相對(duì)而言。官書中的學(xué)術(shù)著作,著名者如《內(nèi)經(jīng)》《本草》《周髀》《九章》等,漢代稱“方技”“數(shù)術(shù)”。這類著作與典章文獻(xiàn)相比,后者常常被諸侯私自毀滅,前者一般不會(huì)。悉心傳承這類著作,完全符合執(zhí)政當(dāng)局的利益。這類著作的傳承者是專業(yè)技術(shù)官員。對(duì)這些技術(shù)官員來說,傳承這類著作就是傳承一家之學(xué);這一家之學(xué),又是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據(jù),無不視若生命,或比生命更重。因此,這類著作與典章文獻(xiàn)很難傳于后世不一樣,它們傳承時(shí)間大都特別長(zhǎng),往往數(shù)百年或上千年傳承而不佚失。此外,典章文獻(xiàn)理應(yīng)保持歷史原樣,不可隨意修改。與此不同,學(xué)術(shù)著作在千百年或數(shù)百年傳承過程中,為了適應(yīng)社會(huì)發(fā)展與科技進(jìn)步,必須不斷修訂;若不修訂,就不能與時(shí)俱進(jìn),將失去生命力。當(dāng)年有能力修訂這類著作的人,只有著作的傳承者——專業(yè)技術(shù)官員。著作修訂以后仍供他們自己使用(不用于公眾傳播),所以除偶爾需另著新篇外,大都以修訂舊作為常規(guī),對(duì)舊作做增刪、改造或吸收、整合的工作。這樣不斷修訂的結(jié)果,必將導(dǎo)致以下兩個(gè)結(jié)果。
結(jié)果之一,導(dǎo)致有些作品成為古典名著。學(xué)術(shù)著作不斷修訂的過程,就是不斷豐富、完善、提高的過程,也是不斷從幼稚走向成熟的過程。作品通過多次修訂,積累成果,凝聚智慧,其中有些終于登上學(xué)術(shù)頂峰,像《周髀》《九章》《內(nèi)經(jīng)》《本草》等公諸于世時(shí)遂成古典名著。有些人不知古典名著的上述經(jīng)歷,不知它們是華夏先人千百年心血與智慧的結(jié)晶,常常以為它們是莫名其妙地突然降臨的,或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結(jié)果之二,導(dǎo)致它們必然成為無名氏集體著作。學(xué)術(shù)著作在長(zhǎng)期傳承過程中必須不斷修訂,已如前述。在修訂著作時(shí),官書時(shí)期特殊著作環(huán)境中一些因素,如作品無真?zhèn)沃畡e,作文無名利之念,特別是沒有著作權(quán)觀念與定本觀念,必然對(duì)作者及其著作活動(dòng)產(chǎn)生重大影響。首先,因?yàn)闆]有著作權(quán)觀念,作者(修訂者)可以無條件地、任意地使用或利用他人的作品。“無條件”,指無需征得他人同意,無需做任何說明;“任意”,指增、刪、抄、改之類,悉聽尊便。作者這樣做,因?yàn)樯袥]有著作權(quán)觀念,完全符合社會(huì)道德。作品經(jīng)過這樣多次修訂后,作者不能是一人,必定是不同時(shí)代的許多人;作者概不署名,所以必然成為無名氏集體著作。其次,因?yàn)闆]有定本觀念,凡修訂,必定將舊作留存的文字,與修訂者新增的文字,以及吸收整合其它作品的文字,這些不同時(shí)代、不同作品的文字都混合在一起,不加區(qū)分。修訂一次,就混合一次;修訂多次,就混合多次。最后,這類著作傳承到漢代公諸于眾時(shí),作品中不免留下多次混合的痕跡,諸如觀點(diǎn)前后矛盾,文字前后重復(fù),全篇結(jié)構(gòu)不統(tǒng)一,混用不同時(shí)代的專門詞語等。公諸于世前多次修訂留下的這類痕跡,用漢代以來“一人一作”的標(biāo)準(zhǔn)衡量,都是不可原諒的常識(shí)性錯(cuò)誤,所以一旦被文獻(xiàn)學(xué)家發(fā)現(xiàn)就驚呼“不是一人一時(shí)之作”!殊不知官書時(shí)期的作品,因多次修訂而成為“不是一人一時(shí)之作”是合乎規(guī)律的正常現(xiàn)象,這不是“偽作”的憑證,這是歷經(jīng)多次修訂的可靠證據(jù)。
前面,從官書三特征形成的特殊著作環(huán)境,說明長(zhǎng)期傳承的學(xué)術(shù)著作因多次修訂而必然成為無名氏集體著作。現(xiàn)在,再將這過程歸納為以下四點(diǎn)。
其一,在官書時(shí)期,書籍因?yàn)椴荒芄妭鞑ザ鵁o法成為社會(huì)傳播工具,學(xué)術(shù)著作受此影響而不能流布于社會(huì)公眾間,它們?cè)谙鄬?duì)固定的狹小范圍內(nèi)世代傳承。其中,王官之學(xué)在疇官家族范圍內(nèi)世代傳承,而私學(xué)中學(xué)說在師徒范圍內(nèi)世代傳承。
其二,在相對(duì)固定的狹小范圍內(nèi)傳承的學(xué)術(shù)著作(口說或文字),凡經(jīng)長(zhǎng)期傳承,必須不斷修訂;若不修訂,就不能與時(shí)俱進(jìn),將失去生命力。這類著作的修訂者,就是著作的傳承者。
其三,凡修訂著作(口說或文字),以下四個(gè)因素必然影響并制約修訂者(作者)及其著作活動(dòng):一,作品無真?zhèn)沃畡e;二,作文無名利之念;三,沒有著作權(quán)觀念(作者不署名);四,沒有定本觀念(書無定本)。
其四,著作(口說或文字)經(jīng)歷這四個(gè)因素制約下多次修訂,最后傳承到漢代公諸于眾時(shí),必然成為無名氏集體著作,亦即“不是一人一時(shí)之作”。這類作品的作者包括歷代參加創(chuàng)作與修訂的所有成員,所以是一個(gè)特殊的作者群體。這類作品的著作權(quán)屬于這特殊的作者群體,概不屬于任何個(gè)人。
在上面四點(diǎn)中,第一點(diǎn)、第三點(diǎn)是既定的客觀因素,第四點(diǎn)是必然結(jié)果,導(dǎo)致這必然結(jié)果的關(guān)鍵是第二點(diǎn),即凡經(jīng)長(zhǎng)期傳承必須不斷修訂。
經(jīng)學(xué)傳記作為學(xué)術(shù)著作,既然在官書時(shí)期傳承了二三百年,長(zhǎng)期處于由官書三特征形成的特殊著作環(huán)境,最終不能不演變成為無名氏集體著作。這一點(diǎn),只要在傳記中找到不斷修訂的證據(jù),亦即“不是一人一時(shí)之作”的證據(jù),大致就能確定。可是,經(jīng)學(xué)傳記在漢魏以來似乎都有了作者,如認(rèn)為《易傳》的作者是孔子,認(rèn)為《左》《公》《谷》的作者是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等。既然有了有名有姓的作者,而且作者是一人,都與我們所說無名氏集體著作有矛盾,這個(gè)問題不解決,我們無法繼續(xù)討論下去。
實(shí)際上,漢魏以來,不只是經(jīng)學(xué)傳記都有了作者,其它先秦古書也都有了作者。既然先秦作者不署名,先秦古書為何到漢魏以來都有了有名有姓的作者呢?這些“作者”是怎樣得到的呢?揭開這個(gè)謎,不能不涉及漢魏以來社會(huì)上針對(duì)先秦古書的“被作者”思潮。
傳承到漢代的先秦古書,因?yàn)樽髡卟皇鹈木壒剩蠖疾恢酪膊豢赡苤雷髡呤呛稳耍@是完全正常的現(xiàn)象。可是,因?yàn)闈h代開始建立了著作權(quán)觀念,人們所見漢代以來書籍都有一人為作者,有些人以為先秦古書也是這樣的“一人一作”,于是想方設(shè)法給不知作者的先秦古書包括傳記、子書與官書都按上一個(gè)“作者”,這就是所謂“被作者”,詳見拙作《簡(jiǎn)論官書三特征》。[1]“被作者”的出發(fā)點(diǎn)是為先秦古書找一個(gè)作者,然而置主客觀條件于不顧,再加求功心切,因而采用猜測(cè)、比附之類幼稚辦法給先秦古書硬按上一個(gè)所謂“作者”。具體方式不一,茲舉兩例。
例證之一,西漢還不知作者的《本草》,東漢開始有了作者。
《本草》是古老官書之一,《漢書》三次記“本草”,意思是藥物學(xué)或藥物學(xué)這一類作品,都不涉及作者是何人。①《漢書》三次記“本草”見:一,《郊祀志》“本草待詔”;二,《平帝紀(jì)》載征召“方術(shù)、本草及五經(jīng)、論語、孝經(jīng)、爾雅教授者”。三,《樓護(hù)傳》記樓護(hù)“誦醫(yī)經(jīng)、本草、方術(shù)數(shù)十萬言”。從這三次所記,西漢時(shí)“本草”的含義有二:一為藥物學(xué),如“本草待詔”;二為藥物學(xué)這一類作品,如樓護(hù)所誦“本草”。“本草”的含義指稱藥物學(xué)一類作品,這類作品的作者必定有許多人,決不是一人。可是到東漢,鄭玄就說《本草》是神農(nóng)作;到晉代,皇甫謐又說是歧伯或伊尹作。鄭玄或皇甫謐給《本草》按上的這個(gè)“作者”,未經(jīng)考證,沒有根據(jù),無非是在權(quán)威崇拜心理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一種猜測(cè)而已。
例證之二,以書名中的人名為作者。
傳記以書名中的姓氏為作者,子書以書名中的諸子為作者,都是以書名中的人名為作者。歷史上的事實(shí)是,先有以人命書,然后才出現(xiàn)以書名中的人名為作者。先秦古書原來只有篇名,沒有書名;它們的書名都是到漢代以后才有的,原因是它們要在公眾間傳播了,非有書名不可。漢代常見的命書方式是以人命書,像西漢劉向以子命書便是。我們從劉向校定的子書看,他以學(xué)派為準(zhǔn),把同一派的作品,包括疑似同一派的作品,都編入這一派的書中。②例如,劉向《晏子敘錄》說:“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jīng)之義。又有復(fù)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fù)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jīng)術(shù),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fù)以為一篇。凡八篇。”再如,劉向《列子敘錄》說書中有些篇章,“不似一家之言”。由此可知?jiǎng)⑾蛐W訒詫W(xué)派為準(zhǔn),為了保存資料,“不敢遺失”,他將“疑后世辯士所為”或“不似一家之言”的作品,也編入這一派的書中。劉向校定的子書,其實(shí)是學(xué)派的文集,或?qū)W派的集體著作。他雖然以子命書,然而不認(rèn)為子書是諸子一人所作,不認(rèn)為書名中的諸子就是作者。由此可見,劉向以子命書,他沒有把書名中的人名(諸子)與作者等同起來,也不認(rèn)為子書是諸子一人的作品。劉向以后,經(jīng)東漢到魏晉,以書名中人名為作者才流行起來,主要對(duì)象就是傳記與子書,《左》《公》《谷》以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為作者皆為此類。用這種辦法給傳記或子書按一個(gè)“作者”,除了同樣是一種猜測(cè),另外還是一種不科學(xué)的比附。漢代人所撰作品若以人命書,以書名中人名為作者大致是對(duì)的,可是將這種辦法,用于傳記、子書這類先秦古書就不對(duì)。
“被作者”作為書籍領(lǐng)域一種錯(cuò)誤思潮,興起于漢魏間;大致官書在先,再及傳記、子書;到唐代,《隋書·經(jīng)籍志》將子書都錄為某子“撰”③例如,《隋書·經(jīng)籍志》稱:“《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莊子》二十五卷,梁漆園吏莊周撰”等。,從此登峰造極,幾成定論。現(xiàn)在看來,“被作者”是我國(guó)校讎學(xué)在幼稚階段所犯最大錯(cuò)誤,后果之嚴(yán)重,始料不及。“被作者”的要害不僅是弄錯(cuò)作者,更是篡改了先秦古書的著作權(quán)——將集體著作篡改為某“作者”的個(gè)人著作。這樣篡改了著作權(quán)以后,只要在先秦古書中發(fā)現(xiàn)那個(gè)所謂“作者”死后才出現(xiàn)的人物、事件或詞語之類(文獻(xiàn)學(xué)這類發(fā)現(xiàn)并不難),這些就都成為有人篡改或作假的證據(jù),該古書因此就變成了“偽作”。宋代以來,“被作者”的先秦古書都是這樣輕而易舉地被打成“偽作”,釀成千古冤案。清初以來,文獻(xiàn)學(xué)家不斷發(fā)現(xiàn)古書作者不署名,以及子書不是諸子一人所作等。這些新發(fā)現(xiàn)等于宣告“被作者”是一個(gè)偽命題,客觀上是一個(gè)騙局。可是,古書辨?zhèn)握呱钚挪灰桑识麄兎磳?duì)“偽作”的崇高熱情只能事與愿違,實(shí)際上變成了抹黑先秦文化的一場(chǎng)欺世盜名的游戲。
從“被作者”的錯(cuò)誤可知,討論經(jīng)學(xué)傳記這類先秦古書的作者問題,要注意以下兩點(diǎn):其一,官書時(shí)期的學(xué)術(shù)著作因長(zhǎng)期傳承而不斷修訂,最終不能不演變?yōu)闊o名氏集體著作;其二,不可胡亂套用漢代以來的“一人一作”模式。“被作者”的錯(cuò)誤,首先源于套用漢代以來的“一人一作”模式于先秦古書,不知先秦學(xué)術(shù)著作大都是無名氏集體著作。這個(gè)慘痛教訓(xùn),是以諸多先秦古書被打成“偽作”為代價(jià)換來的,理當(dāng)記取,不可忘記。
針對(duì)“被作者”之荒謬,余嘉錫《古書通例》指出:“傳注稱氏,諸子稱子,皆明其為一家之學(xué)也。”[2](P184)他認(rèn)為傳記以姓氏命書,子書以諸子命書,都不是指稱作者,都代表一家之學(xué),他的看法是對(duì)的。為何代表一家之學(xué),容后再說。下面,以《春秋》三傳《左》《公》《谷》為例,主要引用四庫(kù)館臣的話,說明傳記在公諸于世以前都經(jīng)過多次修訂。
《公羊傳》,據(jù)說最初由孔子弟子子夏傳給公羊高。公羊高,戰(zhàn)國(guó)時(shí)齊人,生平不詳。《四庫(kù)全書總目》卷26“公羊傳”條說:“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jīng)師,不盡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于兩楹之間’二句,《谷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于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證(按:高,即公羊高)。”四庫(kù)館臣一再說《公羊傳》“不盡出于公羊子”。換句話說,就是《公羊傳》的作者不是一人,而是許多人。我們前面說過,官書時(shí)期的學(xué)術(shù)著作因長(zhǎng)期傳而必須不斷修訂,最后必然演變?yōu)闊o名氏集體著作,亦即“不是一人一時(shí)之作”,《公羊傳》就是一個(gè)例證。
《谷梁傳》,據(jù)說最初由孔子弟子子夏傳給谷梁赤。谷梁赤,戰(zhàn)國(guó)時(shí)魯人,生平不詳。《四庫(kù)全書總目》卷26“谷梁傳”條說:“《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為后師。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谷梁既同師子夏,不應(yīng)及見后師。又‘初獻(xiàn)六羽’一條,稱谷梁子曰。傳既谷梁自作,不應(yīng)自引己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為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于蜀。其人亦在谷梁后,不應(yīng)預(yù)為引據(jù)。”四庫(kù)館臣發(fā)現(xiàn)“沈子曰”“尸子曰”都是谷梁赤以后的人,說明該作品在谷梁赤以后有人修訂過。根據(jù)“谷梁子曰”這種語氣,這話必定是谷梁赤以外的人留在作品中的。這些說明,《谷梁傳》曾經(jīng)一些人修訂;究竟多少人修訂,概不可知。《谷梁傳》的作者包括歷代參加創(chuàng)作與修訂的所有人,故而它的作者是一個(gè)特殊的作者群體。谷梁赤或許是這作者群體中的一員,然而更多成員全然不知。由此看來,《谷梁傳》不是谷梁赤或其他人的個(gè)人著作,它是無名氏集體著作。
《左氏傳》,據(jù)說最早由左丘明傳于后世。左丘明,春秋后期人,大致與孔子同時(shí)。四庫(kù)館臣發(fā)現(xiàn),《左氏傳》“哀公五年”載有“子思曰”一段話。子思(前489—前402),姓孔名伋,孔子之孫,比左丘明晚兩代。“子思曰”這段話,必定是左丘明死后另有人加進(jìn)去的。《左傳》書中許多“君子曰”,有些學(xué)者以為是左丘明以外另有人加進(jìn)去的。史學(xué)家顧頡剛認(rèn)為,今本《左傳》經(jīng)過七種途徑的“改造”①顧頡剛認(rèn)為,今本《左傳》是對(duì)《左氏》原書改造而成,改造之途徑有七:一,本無年月日而勉強(qiáng)為之按插者;二,本為一時(shí)事,再分插入數(shù)年中者;三,將《國(guó)語》中之零碎記載加以修改并作一篇者;四,受西漢時(shí)代影響而加入者;五,受東漢時(shí)代影響而加入者;六,在杜預(yù)作《注》后加入者;七,《左傳》本有而后人刪之者。詳見顧頡剛講授、劉起釬筆記《春秋三傳及國(guó)語之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版,第59-83頁。。所謂“改造”就是修訂,“改造”者為何人,概不可知。如果《左傳》最初真的是左丘明作,它的歷代修訂者或“改造”者姓甚名誰,人數(shù)多少,都不知道。在《左傳》的特殊作者群體中,左丘明只是一員而已,更多成員一無所知,所以《左傳》為無名氏集體著作無疑。
從有關(guān)《左》《公》《谷》的以上考證,可知它們?cè)陂L(zhǎng)期傳承過程中經(jīng)過多次修訂,最后到漢代公諸于眾時(shí)遂成為無名氏集體著作。其它傳記也與《春秋》三傳一樣,都是無名氏集體著作。
那么,為何認(rèn)為這些傳記都是一家之學(xué)的集體著作呢?這是因?yàn)閭饔浽跐h代公諸于眾以前一直在師徒間世代傳承;凡是世代師徒相傳的學(xué)說,都是一家之學(xué)。
在官書時(shí)期,書籍因?yàn)椴荒芄妭鞑ザ鵁o法成為社會(huì)傳播工具,故而私學(xué)中的學(xué)說不能不靠門弟子傳于后世。而傳記的“口耳相傳”,足以證明它們?cè)诠T于眾以前一直在師徒范圍內(nèi)傳承。章太炎《國(guó)學(xué)講演錄·經(jīng)學(xué)略說》認(rèn)為,“《詩(shī)》無所謂今古文,口授至漢,書于竹帛”。章學(xué)誠(chéng)說,《易傳》“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于藝文,皆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學(xué)也”①章學(xué)誠(chéng)《文史通義·言公上》。。“田何而上,未嘗有書”,意為《易傳》從孔子弟子商瞿到西漢初年的田何,一直是口傳。《春秋》三傳中《公》《谷》在漢以前也是一直口傳。學(xué)說的口耳相傳,必定是師徒相傳;不是師徒關(guān)系,無法口耳相傳。經(jīng)學(xué)傳記多數(shù)靠口傳,已如前述。此外,《左傳》是少數(shù)錄為文字者之一。東漢范升說,《左傳》“出于丘明,師徒相傳”②《后漢書》卷36《范升傳》。。可見錄為文字的《左傳》,與“口授”的《公》《谷》一樣也是“師徒相傳”。
根據(jù)“師徒相傳”這一點(diǎn),可以判斷傳記的歷代修訂者的身份,不會(huì)超出同門師徒這個(gè)范疇,四庫(kù)館臣說是“傳授之經(jīng)師”也是對(duì)的。當(dāng)年,一家?guī)熗街粋饕环N傳記,《左》《公》《谷》《齊》《魯》《韓》《毛》等分別在各自師徒關(guān)系中傳承,通常是后學(xué)修訂師輩傳下的作品(口說或文字)。不過,像《谷梁傳》的“尸子曰”,尸佼是法家,法家不可能成為儒家傳記的修訂者,所以“尸子曰”當(dāng)為某谷梁后學(xué)所引。既然歷代的修訂者概出于同一師門,他們雖不是同時(shí)代人,然而遵循同一師說家法,故而可以判斷傳記的內(nèi)容為一家之學(xué)。
歸根結(jié)蒂說,傳記最初源于孔子講經(jīng)。可是,孔子所講經(jīng)義,經(jīng)弟子后學(xué)不斷修訂改造而傳承到漢代時(shí),早已不是孔子當(dāng)年所講原樣,早已演變?yōu)閿?shù)量很多而彼此相對(duì)獨(dú)立的一家之學(xué)。對(duì)后代研究者來說,可以認(rèn)知的不是孔子當(dāng)年所講原樣,而是由此演變而來的一家之學(xué)。與傳記的一家之學(xué)相比,古老官書如《周髀》《九章》《本草》《內(nèi)經(jīng)》都出于疇官的一家之學(xué),它們因?yàn)閭鞒袝r(shí)間特別長(zhǎng),在千百年傳承中轉(zhuǎn)輾于不同疇官之手,最終成為不同一家之學(xué)的綜合體。傳記的一家之學(xué)源于民間私學(xué),傳承時(shí)間相對(duì)較短,大都是單一的一家之學(xué)。
從著作權(quán)考察,傳記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個(gè)人的著作,它們是一家之學(xué)的集體著作。從傳記是集體著作看,以為它們是包括孔子在內(nèi)的任何個(gè)人的著作,都與事實(shí)不符。歐陽修稱《易傳》“非一人之言”,其實(shí)所有傳記都“非一人之言”,因?yàn)樗鼈兪羌w著作。從傳記是一家之學(xué)看,它們的作者都是一個(gè)特殊群體;具體一點(diǎn)說,是以一家之學(xué)為界限的、跨越不同時(shí)代的特殊群體。不同的經(jīng)學(xué)傳記,出于不同的作者群體。誠(chéng)然,孔子不是傳記的作者,然而是這些作者群體的始作俑者與關(guān)鍵人物。誠(chéng)然,傳記書名中的姓氏不是作者,然而可能是該作者群體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一個(gè)成員。這樣說并不矛盾,事實(shí)就是如此。
孔子“述而不作”的原意——兼談書籍尚未公眾傳播對(duì)作者行為的影響
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③《論語·述而》。“述”與“作”的含義,古今差異不小。在先秦,“述”的本義是遵循、訓(xùn)釋、解釋等意思。如《說文》:“述,循也。”禮《說文》:“作,起也。”《廣雅·釋詁》:“作,始也。”漢以后稱“作”,多為“著作”之“作”,或“創(chuàng)作”之“作”,限于文字作品與精神產(chǎn)品。先秦稱“作”不以精神產(chǎn)品為限。例如,《呂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車,倉(cāng)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所作,當(dāng)矣。”可見在先秦,不論物質(zhì)產(chǎn)品、精神產(chǎn)品還是社會(huì)制度,都可稱“作”。
“述而不作”之“作”所指是什么?要注意“述”與“作”兩者,都與“信而好古”聯(lián)系在一起。孔子所“信”之“古”是什么?他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④《論語·八佾》。“吾從周”表示他對(duì)西周禮樂制度的敬仰與崇拜。“信而好古”之“古”,就是西周禮樂制度。“述而不作”之“作”是禮樂制度之“作”,其中包括有關(guān)禮樂制度的精神產(chǎn)品。孔子“述而不作”的原意大致是,遵循、訓(xùn)釋周公的禮樂制度,而不是自己另外創(chuàng)始什么制度。這樣的意思,與“信而好古”一致,也與“吾從周”一致。如前所說,孔子對(duì)六經(jīng)所做工作是利用原有篇籍而賦予新解釋。這種工作稱為“述而不作”,完全符合“述”“作”的原意。
到秦漢年間,“述”與“作”的含義有所變化。由河間王劉德整理問世的《樂記》說:“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shí)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明、圣者,述、作之謂也。”《樂記》詮釋的“述”“作”,代表秦漢年間儒家學(xué)者的理解,與孔子原意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就聯(lián)系而言,其一,《樂記》所講“作”,仍舊是禮樂制度之“作”。其二,《樂記》所講“述”,仍是遵循、訓(xùn)釋、解釋等意思;所講“作”,仍是創(chuàng)始或興起的意思。以上兩點(diǎn)與孔子原意一致。就區(qū)別而言,其一,孔子“述而不作”,推崇的對(duì)象是西周的周公,不包括孔子自己;《樂記》中“作者之謂圣”的“作”,已經(jīng)包括孔子在內(nèi)。其二,孔子的“述”本是夫子自謂,《樂記》“述者之謂明”之“述”,已將孔子排除在外。如《樂記》孔疏說:“述”指“子夏、子游之屬”。
現(xiàn)代社會(huì)稱“作”,是“著作”之“作”或“創(chuàng)作”之“作”,與孔子所稱“作”不一樣,也與《樂記》所稱“作”不一樣。那么,假如從現(xiàn)代所稱“作”考察,孔子有沒有自己的“著作”或“創(chuàng)作”呢?下面,列舉上世紀(jì)三位學(xué)者的看法,供參考。
其一,哲學(xué)史家馮友蘭說:“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般儒者本來都是如此。不過孔子雖如此說,他自己實(shí)在是‘以述為作’。因其以述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他是儒家的創(chuàng)立人。”[3](P277)其二,歷史學(xué)家范文瀾說:“《論語》載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事實(shí)上述與作是分不開的。他講解古書,絕不能不摻入自己的意見,這個(gè)意見正是作而非述。”[4]其三,文化史家柳詒徵說:“《易》《春秋》則述而兼作。世謂孔子‘述而不作’,蓋未讀《十翼》及《春秋》也。”[5](P236)
上面三位學(xué)者,或說“以述為作”,或說“述與作是分不開的”,或說“述而兼作”,都認(rèn)為“述”與“作”結(jié)合在一起。他們的意思大致是,孔子的著作存在于他給弟子講學(xué),特別是口授弟子的經(jīng)義之中;其中,“贊《易》,修《春秋》”則更多表現(xiàn)為他的著作。20世紀(jì)中國(guó)史學(xué)界,無論批孔還是尊孔都認(rèn)為孔子有著作;否認(rèn)孔子有著作者,大概只有編輯史與出版史。
孔子作為思想家與著作家,不能不向社會(huì)傳布自己的思想與學(xué)說,這樣必然碰到使用何種傳播工具,怎樣使用傳播工具,以及利用何種傳播方式等問題。這類問題如何解決,首先取決于客觀的社會(huì)條件,而不是個(gè)人意愿。這是因?yàn)閭鞑スぞ吲c傳播方式任何時(shí)候都不屬于個(gè)人而屬于社會(huì),它們必然由社會(huì)提供,人們只能在此基礎(chǔ)上發(fā)揮自己的能動(dòng)性。因此,不論古代還是現(xiàn)代,傳播工具與傳播方式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必然影響并制約人們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從官書時(shí)期的特定社會(huì)條件看,主要是書籍尚未公眾傳播,還有作者不署名,這兩項(xiàng)必然對(duì)孔子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產(chǎn)生重大影響。為此,我們討論兩個(gè)問題。
第一個(gè)問題,孔子講解經(jīng)義,為何“口授”而不錄為文字?古今學(xué)者一致認(rèn)為,孔子給弟子所講經(jīng)義是“口授”,而沒有錄為文字。那么其中原因何在?《史記》《漢書》都說,孔子講《春秋》經(jīng)義,因?yàn)槠渲杏信u(píng)時(shí)政的內(nèi)容,“不可以書見”,故而口授。不過,孔子講《詩(shī)》經(jīng)義沒有批評(píng)時(shí)政,同樣不錄為文字,可見批評(píng)時(shí)政并不是孔子不錄為文字的主要原因。再進(jìn)一步看,儒家傳經(jīng),除經(jīng)文有文字,傳記大都口授到漢代才錄為文字。不僅如此。在漢代以前,師徒間口授學(xué)說并非儒家獨(dú)有。章學(xué)誠(chéng)說:“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①章學(xué)誠(chéng)《文史通義·言公上》。從“口耳之授”到“著之竹帛”的時(shí)間,大致以漢代為界。在先秦學(xué)術(shù)界,師徒間口授學(xué)說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其中必有深刻原因。民國(guó)前后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先秦學(xué)術(shù)盛行口授的原因是簡(jiǎn)牘繁重,使用不便。與紙書相比,簡(jiǎn)書繁重為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可是,簡(jiǎn)牘另有兩大優(yōu)點(diǎn):一是書寫文字與繪制圖畫,無不可用;二是制作不難,價(jià)格不貴,貴族以外的布衣也用得起。在漢代,簡(jiǎn)牘繁重依然如故。可是,傳記在漢代紛紛從口授錄為文字,著于簡(jiǎn)牘,這個(gè)事實(shí)可以證明簡(jiǎn)牘繁重,并不是先秦學(xué)術(shù)盛行口授的主要原因。
離開了社會(huì)傳播,孤立地討論孔子為何口授經(jīng)義而不錄為文字,先秦學(xué)術(shù)為何盛行口授而不利用文字作品,這類問題無法解決,或許只能是個(gè)謎。
對(duì)思想家或著作家來說,他們的學(xué)說要向社會(huì)傳播是既定的,是不可改變的,可以變更的是傳播的方式與渠道,或利用書籍(文字作品),或通過“口授”(口耳相傳)。如果書籍(文字作品)可以將學(xué)說傳布到社會(huì)公眾間,若是這樣再盛行“口授”(口耳相傳),就完全違背常理,也完全違背常識(shí)。由此看來,口授之盛行必定與書籍的作用如何密切相關(guān)。以前,人們從不懷疑先秦書籍的作用,總以為它們與漢以后書籍的作用是一樣的,其實(shí)大謬不然。從書籍的社會(huì)作用看,漢以前書籍與漢以后書籍有何不同?簡(jiǎn)單地說,后者是傳播工具,前者不是。漢以前書籍為何不是傳播工具?因?yàn)樯形垂妭鞑ァR话阏f,凡書籍都可以成為傳播工具或媒介工具。但是,書籍只有公眾傳播才能成為傳播工具,才能發(fā)揮傳播工具的巨大作用;不向公眾傳播的書籍,不能成為傳播工具,僅僅是一種記錄文字的載體,這種不能成為傳播工具的書籍作用是有限的。書籍的作用如何,首先取決于是否公眾傳播,這一點(diǎn)被人們完全忽略了。官書作為君王的政治工具,作為貴族特權(quán)等級(jí)的標(biāo)志,從來不準(zhǔn)公眾傳播,故而從來不是傳播工具。受官書傳統(tǒng)的影響,官書時(shí)期的書籍都不能成為傳播工具,僅僅是記錄文字的載體,這種書籍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國(guó)書籍到漢代才在公眾間流通與傳布,從而成為傳播工具。所以,孔子從未見過成為傳播工具的書籍,他頭腦里對(duì)書籍作用的認(rèn)知,與漢以來人們的認(rèn)知相差甚遠(yuǎn)。從資料看,孔子作為思想家與教育家家從未正面談?wù)摃淖饔谩Kv過“文獻(xiàn)”對(duì)考證夏禮、殷禮的作用,這“文獻(xiàn)”的含義除了典籍文字,還指賢者口傳。①《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xiàn)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按:楊伯峻注:“《論語》的‘文獻(xiàn)’包括歷代的歷史文獻(xiàn)與當(dāng)時(shí)的賢者兩項(xiàng)。”考證古禮要靠口傳資料,說明書籍的作用還不大。孔子以后的墨子,最早宣稱書籍具有超越時(shí)間空間的巨大傳播作用。墨子這些高論,漢代以前應(yīng)者寥寥,原因也是書籍尚未成為傳播工具,所以他的超前意識(shí)無法成為社會(huì)共識(shí)。
討論孔子為何將經(jīng)義“口授”弟子而不錄為文字,以及先秦學(xué)術(shù)為何盛行“口授”而不利用書籍,首先要注意的一個(gè)問題就是,他們身處官書時(shí)期,必須面對(duì)書籍不能公眾傳播這個(gè)客觀現(xiàn)實(shí)。不能公眾傳播的書籍無法成為傳播工具,只是一種文字載體,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例如,早就錄為文字的《左傳》在先秦社會(huì)上一無所聞,說明錄為文字對(duì)擴(kuò)大傳播范圍、提高傳播效率等沒有什么作用,可見當(dāng)年書籍(文字作品)的作用很有限。所以對(duì)經(jīng)學(xué)來說,除了防止記憶差錯(cuò)或其它原因不得不錄為文字者,如經(jīng)文等,將口授的經(jīng)義都錄為文字是不必要的。再?gòu)膶W(xué)者傳播學(xué)說的要求看,因?yàn)槭苤朴诓荒芾脮鳛閭鞑スぞ撸麄冎荒軐W(xué)說傳授給弟子,通過弟子再向社會(huì)擴(kuò)散。在此情況下,老師“口授”弟子不只是一種教學(xué)方式,也是學(xué)說的傳承方式。將學(xué)說向弟子“口授”(口耳相傳)的作用,未必不如文字,有時(shí)優(yōu)于文字。像解經(jīng)的傳記由老師口授弟子,不只比文字方便靈活,還有利于弟子后學(xué)的發(fā)揮創(chuàng)造。從學(xué)說傳承的生命力看“口授”與錄為文字,前者為《公》《谷》,后者為《左傳》,前者如果不是比后者更具生命力,至少不比后者差。由此看來,孔子“口授”經(jīng)義而不錄為文字,以及先秦學(xué)術(shù)盛行“口授”,都是受制于書籍(文字作品)不能公眾傳播這個(gè)客觀現(xiàn)實(shí),無可奈何,不得不如此。
話得說回來,“口授”的作用僅限于師徒之間,不能超出門弟子這個(gè)范圍。因此,當(dāng)歷史發(fā)展到書籍可以公眾傳播的時(shí)候,書籍作為傳播工具的巨大作用得以發(fā)揮出來;與此相比,“口授”的局限性必然暴露無遺。在此情況下,要向社會(huì)傳播學(xué)說的學(xué)者憑常識(shí)就能判斷:必須棄“口授”而利用書籍(文字作品)。這就是一直“口授”的傳記到漢代紛紛錄為文字的原因所在。章學(xué)誠(chéng)說:“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我國(guó)古代學(xué)術(shù)從先秦“口授”到漢代錄為文字,幕后主導(dǎo)這場(chǎng)歷史變革的最大因素,不是學(xué)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書籍(文字作品)面向公眾傳播。
我們?cè)購(gòu)膫鞑シ绞娇础翱谑凇迸c書籍(文字作品)的區(qū)別,前者是人與人之間面對(duì)面的直接傳播,后者是利用傳播工具的間接傳播。與直接傳播相比,間接傳播因?yàn)槔脮蚱渌鼈鞑スぞ撸梢猿綍r(shí)間、空間的限制,故而信息傳播的范圍廣,速度快,效率高。所以,書籍是推動(dòng)人類文明進(jìn)步的重要力量。
漢代以前書籍尚未公眾傳播這個(gè)客觀現(xiàn)實(shí),決定孔子或其他思想家向社會(huì)傳布學(xué)說時(shí),因?yàn)闀荒艹蔀閭鞑スぞ叨鵁o法從事間接傳播,只能主要利用面對(duì)面的直接傳播,即口頭宣傳。直接傳播的先決條件是要靠人,故而思想家必須依靠門下弟子,別無它法。總之,孔子與其他先秦思想家要將學(xué)說布于社會(huì),傳于后世,除了靠自己外,必須靠門弟子,因而門弟子數(shù)量越多越好。如果沒有門弟子,學(xué)說難以布于社會(huì),更無法傳于后世。例如《春秋》傳記之一《鄒氏傳》,據(jù)《漢書·藝文志》載它在西漢初年有書十一卷,可見已錄為文字,然而因?yàn)椤盁o師”很快就失傳了。同為《春秋》傳記的《公》《谷》并無文字,一直靠口傳,然而代有師徒,數(shù)百年長(zhǎng)盛不衰。與錄為文字的《鄒氏傳》因“無師”而失傳相比,《公》《谷》的長(zhǎng)盛不衰可以證明,師徒關(guān)系對(duì)傳承學(xué)說的作用,遠(yuǎn)比錄為文字重要。在書籍尚未公眾傳播的社會(huì)上,思想家的學(xué)說必須靠師徒關(guān)系傳于后世。有師有徒,學(xué)說才能傳承,才能保持生命力;無師或無徒,學(xué)說就失傳。因此,師徒關(guān)系成為思想家學(xué)說賴以傳承并賴以發(fā)展之不可或缺的載體,世代“師徒相傳”就是這樣必然地產(chǎn)生的。在長(zhǎng)期師徒相傳的過程中,原為老師創(chuàng)立的學(xué)說(口說或文字)不能不被弟子后學(xué)修訂改造,最終演變?yōu)橐患抑畬W(xué);而一家之學(xué)的著作必定是集體著作。
總起來說,一,口授而不錄為文字;二,世代“師徒相傳”;三,一家之學(xué);四,集體著作。這四者看似互不相干,實(shí)際上彼此聯(lián)系,它們都是書籍尚未公眾傳播的產(chǎn)物。孔子與戰(zhàn)國(guó)諸子及其弟子后學(xué),他們?cè)谶@四個(gè)問題上為何不約而同,十分一致?這個(gè)原因就是因?yàn)樗麄兌忌钤诠贂鴷r(shí)期,必須接受書籍尚未公眾傳播這個(gè)共同因素的制約,故而必須如此,也只能如此。
到了漢代,因?yàn)闀梢栽诠婇g傳播了,人們開始利用書籍作為傳播工具從事間接傳播,促使學(xué)術(shù)界紛紛放棄“口授”而利用書籍(文字作品),作者為文字作品甘愿傾注一生心血,以期自己隨文字的傳布而揚(yáng)名于世。于是,師徒關(guān)系逐漸演變?yōu)橐越膛c學(xué)的關(guān)系為主,它不再是思想家學(xué)說賴以傳承并賴以發(fā)展之不可或缺的載體。書籍作為傳播工具的巨大作用被人們認(rèn)識(shí)并掌握以后,口授的作用相形見絀,望塵莫及。在此情況下,“口授”只是作為師徒間一種教學(xué)方式繼續(xù)存在,學(xué)術(shù)界數(shù)百年“口耳相傳”的歷史就此結(jié)束了。書籍成為傳播工具以后,一家之學(xué)遲早要突破門弟子的范圍而融入社會(huì),從而被公眾掌握,一家之學(xué)很快演變?yōu)楣娭畬W(xué)。新的一家之學(xué)仍將產(chǎn)生,然而像傳記那種師徒相傳二三百年的一家之學(xué)不能再有了,一家之學(xué)主宰我國(guó)學(xué)術(shù)的歷史就此結(jié)束了。與此同時(shí),無名氏集體著作也隨一家之學(xué)一起走向歷史的終結(jié)。鑒于公眾傳播必然要求作者署名,誕生有名有姓的大著作家、大科學(xué)家的時(shí)代從此來臨。
凡此種種,都說明書籍(文字作品)公眾傳播與否,對(duì)人們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的影響非常重要。
第二個(gè)問題,孔子與諸子作為思想家為何都開門辦學(xué)?先秦私學(xué)中師徒為何結(jié)成一體,形成利益共同體?孔子一生開門授徒,門弟子三千。他先在魯國(guó)一面辦學(xué),一面從政;五十五歲開始,帶領(lǐng)弟子周游列國(guó);六十八歲返回魯國(guó),與弟子一起著書,至七十三歲去世。在此可注意兩點(diǎn),一,孔子著書已是晚年,離去世只有五六年;二,孔子著書,著于文字者只有經(jīng)文,經(jīng)義都口授弟子,并不錄為文字。既然是晚年才著書,又不將經(jīng)義錄為文字,說明面對(duì)書籍不能公眾傳播這個(gè)客觀現(xiàn)實(shí),他不指望通過書籍作為媒介工具向社會(huì)傳布學(xué)說,他主要通過包括周游列國(guó)在內(nèi)的口頭宣傳(直接傳播)擴(kuò)大社會(huì)影響。孔子以后,戰(zhàn)國(guó)諸子也都開門授徒,他們門弟子數(shù)量也都很多。例如,墨子、孟子的弟子常有“數(shù)百人”,道家田駢有“徒百人”,農(nóng)家許行有“徒數(shù)十人”,等等。那么,孔子與其他先秦思想家為何都開門授徒辦教育呢?這樣不約而同,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共同受一種客觀因素的制約呢?在此,先將孔子與西漢揚(yáng)雄作一比較。
揚(yáng)雄(前53—18),西漢著名思想家,一生未為大官,立志“求文章成名于后世”,重要著作有《法言》《太玄》《方言》等。①《漢書》卷87下《揚(yáng)雄傳》:“雄三世不徙官。……以耆老久次轉(zhuǎn)為大夫,恬于勢(shì)利乃如是,實(shí)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用心于內(nèi),不求于外,于時(shí)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矣,而桓譚以為絕倫。……雄以病免,復(fù)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shí)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xué),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時(shí)人大司空王邑、納言嚴(yán)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yáng)雄書,豈能傳于后世乎?’桓譚曰:‘必傳,顧君及譚不及見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將揚(yáng)雄與孔子相比,至少有三點(diǎn)不同。第一,孔子開門授徒,有三千弟子;揚(yáng)雄沒有開門授徒,去世前只有一個(gè)弟子——侯芭相隨。第二,孔子帶領(lǐng)眾多弟子從政,并周游列國(guó);揚(yáng)雄在長(zhǎng)安閉門謝客,“人希至其門”。唐代詩(shī)人盧照鄰說:“寂寂寥寥揚(yáng)子居(按:“揚(yáng)子”即揚(yáng)雄),年年歲歲一床書。”(《長(zhǎng)安古意》)第三,孔子到晚年才著書,孟子也是到晚年才著書;揚(yáng)雄一輩子埋頭著書,很早就立志“求文章成名于后世”。這三點(diǎn)說明,同為思想家的揚(yáng)雄與孔子,他們所走道路并不一樣。揚(yáng)雄走的是著書揚(yáng)名的道路。這里要提的問題是,孔子能否也像揚(yáng)雄那樣走著書揚(yáng)名的道路呢?
揚(yáng)雄所以能走著書揚(yáng)名的道路,首先取決于西漢社會(huì)為他提供了兩個(gè)客觀條件。其一,書籍(文字作品)已經(jīng)在公眾間傳播。這證據(jù)便是,揚(yáng)雄死后四十多年,他的著作“大行”于世。其二,作者已經(jīng)在作品上署名。這證據(jù)便是,揚(yáng)雄頭腦里產(chǎn)生了“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著作動(dòng)機(jī)。在揚(yáng)雄以前,司馬遷早已公開了自己著書揚(yáng)名的觀點(diǎn)。要是沒有這兩個(gè)客觀條件,揚(yáng)雄把文章做得再好也無法靠埋頭著書而名揚(yáng)全國(guó)。這兩個(gè)客觀條件,漢代以前概不存在。例如,戰(zhàn)國(guó)末年流布到秦國(guó)的韓非《孤憤》《五蠹》抄本上,作者仍未署名。①《史記·韓非列傳》:“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亦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之書也。’”從李斯告知秦王“此韓非所著之書”,可知作者沒有署名。戰(zhàn)國(guó)后期的書籍領(lǐng)域,在子書帶領(lǐng)下悄悄發(fā)生許多變革,然而一直到戰(zhàn)國(guó)末年,不向公眾傳播與作者不署名仍舊未見根本改觀。因此,孔子或諸子如果也像揚(yáng)雄那樣埋頭著書,所著書不能流布社會(huì),湮沒無聞,這樣他們無法成為具有社會(huì)影響的思想家。
漢代以前的社會(huì),因?yàn)闀形垂妭鞑ヅc作者不署名的緣故,揚(yáng)雄那種著書揚(yáng)名的道路從來不存在,人們頭腦里連這種想法也不可能有。孔子與諸子要做思想家,他們必須開門授徒辦教育,而且門弟子數(shù)量越多越好,所以師徒關(guān)系成為思想家學(xué)說賴以傳承并賴以發(fā)展之不可或缺的載體。于是,在私學(xué)師徒之間,不能不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特殊關(guān)系。一方面是弟子依賴?yán)蠋熥觽魇趯W(xué)說;另一方面又是老師依賴弟子傳承學(xué)說,并發(fā)揚(yáng)光大。這種相互依賴的特殊關(guān)系,促使師徒雙方以傳承師說為中心,抱成一團(tuán),結(jié)為一體,最終形成一個(gè)利益共同體。孔門儒家的師徒關(guān)系是如此,諸子的師徒關(guān)系也是如此。
教育史最早發(fā)現(xiàn)先秦私學(xué)的師徒之間存在這樣一種特殊關(guān)系。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guó)教育通史》說:戰(zhàn)國(guó)年間,“學(xué)派林立,私學(xué)比春秋更為昌盛,儒墨法名農(nóng)諸家都有私學(xué)。……各學(xué)派都有自己的信仰,以私學(xué)為中心,結(jié)成政治集團(tuán)”[6](P162)。像孟子常常帶領(lǐng)“數(shù)百”弟子“傳食于諸侯”,②《孟子·滕文公下》:“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這樣的師徒關(guān)系稱為“集團(tuán)”,或不為過。與儒家相比,墨家?guī)熗礁墙M織嚴(yán)密。先秦私學(xué)中師徒雙方,抱成一團(tuán),結(jié)為一體,這是事實(shí)。不過,既以傳承師說為宗旨,或許稱為“文化集團(tuán)”更好些。師說,是將師徒雙方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利益共同體的紐帶;維護(hù)或強(qiáng)化師說的生命力,是這紐帶繼續(xù)發(fā)揮作用的關(guān)鍵。因此,師說在傳承過程中,弟子后學(xué)必須不斷修訂。若不修訂,因此師說失去生命力,無法成為聯(lián)系的紐帶,他們的利益共同體也將解體。明乎此,再看經(jīng)學(xué)傳記在師徒相傳過程中演變?yōu)橐患抑畬W(xué)集體著作,也就不難理解了。
官書制度在西漢初年宣告結(jié)束,書籍從此開始面向公眾傳播,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隨著利用書籍作為傳播工具的人越來越多,漢代以前師徒間那種相互依存、相互依賴的特殊關(guān)系失去了繼續(xù)存在的理由,故而兩漢產(chǎn)生了有別于先秦私學(xué)的新型師徒關(guān)系。這件事再次提醒我們,傳播方式特別是傳播工具的變革,不只改變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也改變?nèi)穗H關(guān)系。
[1]劉光裕.簡(jiǎn)論官書三持征——不準(zhǔn)公眾傳播、作者不署名、書無定本[J].濟(jì)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1,(3).
[2]余嘉錫.余嘉錫說文獻(xiàn)學(xu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馮友蘭.新原道[M]//馮友蘭學(xué)術(shù)論著自選集.北京:北京師范學(xué)院出版社,1992.
[4]范文瀾.中國(guó)經(jīng)學(xué)史的演變[M]//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79.
[5]柳詒徵.中國(guó)文化史(上卷)[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
[6]毛禮銳,沈灌群.中國(guó)教育通史(第一卷)[M].濟(jì)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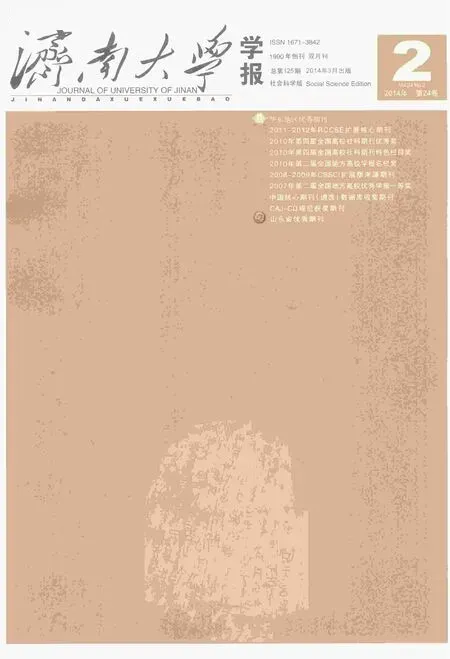 濟(jì)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年2期
濟(jì)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年2期
- 濟(jì)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大學(xué)生對(duì)國(guó)內(nèi)旅游景區(qū)認(rèn)知差異研究——以東部地區(qū)某大學(xué)為例
- 縣級(jí)學(xué)生資助中心的政府規(guī)制缺陷及其完善
- 可控與非可控——現(xiàn)代漢語方式狀語的語義類研究
- 試論我國(guó)農(nóng)村中小企業(yè)規(guī)范文化軟資源開發(fā)
- 新生代農(nóng)民工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能力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
- “實(shí)體一站式政府”與“網(wǎng)絡(luò)一站式政府”研究綜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