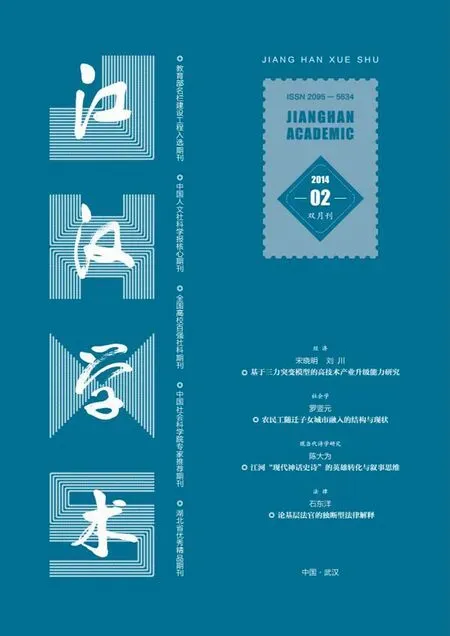對我國媒體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反思與重構
李廷軍
(江漢大學 教育學院, 武漢 430056)
20世紀初,歐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亞洲部分國家和地區逐漸出現了一種新型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媒體素養教育的適應性也不同,在不同發展階段所選擇和確定的媒體素養教育的目標也存在差異。這些都隱含一定的價值取向,不同媒體素養教育價值取向也代表了媒體素養教育者對各自國家媒介與公眾等環節關系的不同反思。因此,明確媒體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有助于認識我國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和本質。
自1990年代末以來,媒體素養教育開始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至今已十年有余,并儼然成為學界的一個顯性話題。在中國當前語境中,非本土媒體素養教育在我國本土化過程中,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面臨的最大困境無疑是過于嚴格的保護主義價值取向的沿襲。因此,拋棄傳統“純粹”保護主義取向,超越媒體素養教育的困境,建構一種“超越保護主義”的媒體素養教育,還有待于學者們給予足夠重視并作進一步研究。
一、“純粹”保護主義:我國媒體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現狀反思
1.制度層面:存在一定的政治保護壓力
政治制度是“指統治階級為實現其階級統治而采取的統治方式、方法的總和,它包括國家政權的階級實質、政權的組織形式、國家結構形式以及為保證國家機器運轉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1]。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與我國相去甚遠,其政治制度多為多黨輪流執政的資產階級共和制。經濟上,西方國家基本實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經濟。因此,大多西方國家的媒體素養教育最初直接來源于國家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其動機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保護主義。“從上個世紀70 年代以來,諸如‘反對性別政治’和‘種族政治’等‘身份政治’內容和‘意識形態’內容被加入了這種政治保護主義的范疇。相應地,大眾媒體要為男性至上主義或種族主義負主要責任。而通過媒體素養教育過程中的媒介分析,這種有關大眾媒體的性別偏執、種族偏執和意識形態偏執可以得到克服或矯正。”[2]其實,這種基于政治保護的媒體素養教育亦被許多其他西方國家順理成章地看作是一種消除錯誤信仰、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工具,其主要目的在于發展受眾獨立思考的能力,能夠挑戰社會上偏頗的意識形態。應該說,政治保護主義是某些國家開展媒體素養教育的主要動機和行動,推行起來也頗為不易,因為其明顯有違現代意義上的媒體素養教育的初衷。
我國有著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的政治、歷史、文化和教育背景。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政治體制的原因,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全體國民對新聞媒體不能有絲毫懷疑,有關媒體教育幾乎停滯不前,甚至還有倒退。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甚少涉及政治體制和媒體制度改革,因此,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根本無暇顧及這場由國外引入、由民間學者發起的媒體素養教育運動。在世紀之交,我國即使勉強引入和開展了媒體素養教育,也是如履薄冰,時刻擔心觸碰雷區。對此,有學者尖銳指出,“在中國的語境下,從事媒介素養教育會承擔更大的風險,……我們的學生已經接受了多年的政治教育,媒介素養會不會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社會教化?……我們在媒介素養教育中,是否應該強調沉默,強調聆聽他人的技能?……我們推動個人、社會運動組織、社區活動中有效使用媒介,但所有的這些實踐相對于日益強大的、依賴于市場、在中國還包括國家政權的媒介組織,是否太微弱了?……”[3]這些問題確實值得廣大媒體教育工作者們思考。
事實上,在現有媒體制度和政治體制下,我國公民已習慣了疏于對媒體建構社會現實的功能進行思考,從而對媒體的商業化傾向和政治教化傾向缺乏認識。可以說,我國的媒體使用者是很好的媒體信息接受者,但并不是很好的分析者、辨別者、評判者和利用者,由此導致媒體素養普遍不高。據一項權威研究發現,“在目前中國,無論是對媒介信息的批判思考、還是對媒介生產的積極介入,均處于偏弱水平,其影響因素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值得深入探究”[4]。這是因為,中國媒體素養教育理論研究與實踐的主要資助來自政府,這樣更便于官方對該教育項目的控制,避免越軌行為。同時,“盡管媒介素養強調政治參與,但在中國,可供人們選擇的參政行為有限,職責性、公民性、制度性的參與,與絕大多數人無緣,即使那些最激進的行動者也不例外”[5]218。因此,無論是作為一場社會運動,還是作為一個研究主題,在我國開展媒體素養教育即會受到一定的制約,會面臨種種壓力。
(二)文化層面:精英思維傾向頗為嚴重
媒體素養教育起源于英國,究其原因,無外乎是當時社會精英出于對大眾媒體的本能抵制而采取的一種文化保護。當前,我國與媒體教育有關的、相對重視技能的“信息技術教育”(teaching with media)早已進入中小學課程體系,但真正與媒體教育相關的、側重于文化的“媒體素養教育”(teaching about media)卻遲遲未能正式進入該課程體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媒體素養教育重技能、輕文化的傾向和仍處于起步階段的事實。即使涉及到文化考量,媒體素養教育也是采取一種精英文化取向、主流文化取向和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精英思維。
媒體素養本質上是個文化問題。所謂文化,關涉的是思想、價值觀、信念和趣味,它們才是媒體素養的核心和媒體素養教育的永恒主題。同時,媒體素養教育理應針對社會普通公眾,但是眾多學者仍然立足于精英教育來確立媒體素養教育的目標。若以這種文化取向和思維看待其他非主流文化,則不難發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大眾文化幾乎已經成了‘自由’和‘個性’的代名詞,它意味著反叛權威、精英和擺脫傳統的束縛,拒斥諸如真、善、美、圣等終極價值或人類永恒的崇高目標對人的感性世界的制約,它依靠追求時髦和不斷更新來尋找自身的價值”[6]。若將這種“文革式”的思維和觀點運用于媒體素養教育,必然會產生嚴重后果。我們不僅應該主動地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主導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主流文化,也應該以包容的態度去關注、甄別、引導和欣賞諸如搖滾文化、大話文化、涂鴉文化、惡搞文化、博客文化、微博文化、山寨文化以及草根文化等形形色色有價值的亞文化風景。
(三)價值層面:“妖魔化”媒體傾向依然存在
英國媒體素養教育學者巴扎爾格特在回顧英國媒體素養教育的發展時,曾批評早期“免疫式”媒體素養教育是“災難的開端”,因為“責難媒體”的媒體素養教育連帶地產生了“否定”媒體的誤解。而“否定”媒體的思維在所有國家媒體素養教育理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7]受英國媒體素養教育運動的啟發,美國的媒體素養教育運動也一直伴隨著“道德恐慌”和對媒體信息、媒體受眾等概念的簡單化理解。大衛·帕金翰對此評價道:“美國的媒體素養研究經費經常來自于精神健康領域的資金,這意味著這些問題主要被視作是病理學上的問題。”[8]由此可見,受眾在道德失范的媒體信息面前是多么無能為力,他們迫切需要基于道德保護、文化保護、健康保護以及政治保護的媒體素養教育。
目前,我國的大眾媒體也一度出現了“去政治化”傾向,幾乎都在如何“經營”媒體上做文章——因為有一些媒體因為追逐利益而越來越低劣化。于是,“我國學校和社會對青少年媒體接觸行為的關注,仍集中在對媒介負面影響的抵御和防范上。部分高校開學時為防學生過度迷網而禁止新生帶電腦入學,以及一些中小學禁止學生帶手機上學的做法,都說明了社會和學校對青少年的日常媒介行為的焦慮心態”[9]。這表明,越來越多的家長、老師,甚至教育機構片面認識、夸大了媒體的負面影響,他們對大眾媒體,特別是對基于網絡的眾多新媒體采取了“抵制”、“否定”甚至“妖魔化”的價值判斷。與此相對應的是,由這種取向出發的媒體素養教育往往局限于對青少年媒體行為的片面約束、抵制和保護。事實上,我國大多數教育工作者和媒體管理部門還簡單停留在媒體受眾是媒體被動的受害者,他們會被媒體的強大效果一擊即倒的傳統觀念上,因而會更傾向于“媒體罪惡觀”的教育,即在媒體素養教育中,充斥著拒絕式、對立式和預防注射式的思考,以及只靠常識的思考,從而使媒體與媒體受眾處于互為對立的角色。這和西方早期“免疫式”媒體素養教育所采取的“抵制”取向幾乎如出一轍。
實際上,媒體素養是一個包涵多重維度、多重要素、相互交融的復雜能力結構和素質結構,要求我們要有多重批評標準,并且把這些標準有機結合起來去把握和判斷。而且,媒體素養教育作為一項價值性很強的教育活動,有關文化、審美、道德等標準的價值尺度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忽視這些價值標準的存在,必然很難企及媒體文本的價值真諦,也難企及媒體素養教育本身的價值真諦。當前我國的媒體素養教育所表現出的“抵制”媒體、“妖魔化”媒體的取向,無疑過于簡單、機械、淺薄和粗暴,從而在價值判斷時往往陷入了諸如“好與壞”、“正面與負面”以及“留與棄”這樣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中。
(四)教育層面:灌輸式教學尤為普遍
在引進西方媒體素養教育理念之初,卜衛就曾警告說,“在媒體素養教育中,教師不應以自己的體驗代替學生的體驗,不能以自己的判斷代替學生的判斷”[10]。然而現實情況卻是,“我國一貫主張媒體輿論和思想的引導,在教育上,始終還是師道尊嚴,以灌輸訓解為要,耳提面命為豪,在這樣的狀況下,媒體素養教育的話語很容易消融于固有的勸說指導傳統中,成為家長、教師調教孩子的又一個上好理由。……最終的結果無非是又增加了一個對學生進行灌輸式教育的機會,離提高學生素質的根本目的相差甚遠”[11]。而且,不少教授媒體素養課程的教師仍然相信他們可以教給學生“正確價值觀”、“正確知識”和“精英品味”以及相應的能力。因此,大多數文章或教材局限于教授“知識”,但缺少對一些關鍵問題的反省:這些知識是誰建構的?為誰建構的?為了達到何種目的?這些問題的實質在于,“個人的批判自主權和賦權沒有被放到應有的重要位置上。如果主流或傳統的教育學沒有任何改變的空間,比如,沒有大規模的教育改革,那么在這種情景下,僅僅靠媒介素養教育來挑戰教育制度可能收效甚微”[5]202。
西方媒體素養教育的發展過程不斷提醒人們,媒體素養教育的對象在接受媒體素養教育之前并非對媒體一無所知。在我國,正如陸曄教授指出,“盡管從未冠以媒體素養之名,但是長期以來,由于中國大眾傳播媒體的喉舌功能,普通民眾對媒體文本的解讀、認知、理解,一直是他們間接參與社會政治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領域。除了有組織地對重大政治事件的新聞報道和評論進行學習之外,公眾在新聞使用上,業已形成相當深刻的領悟力。無論知識階層還是普通百姓,對‘文以載道’歷史傳統都有著來自民間的深厚理解,因此尋找媒體文本的‘弦外之音’,多年來從來就是公眾媒體使用的目的之一”[12]。事實上,我國媒體使用者在媒體化生存過程中,也早已積累了基于切身感受的、豐富的媒體體驗和媒體素養,雖然這種媒體素養帶有某種自發性和樸素性。介于此,用灌輸式的說教去替代學生關于媒體識讀的“批判性自主”體驗,恐怕只能適得其反。
二、“超越”保護主義:我國媒體素養教育價值取向的理論重構
(一)不再需要“保護”嗎?
首先,無論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文化霸權的抵制,還是對我國媒體市場化運作中出現的不良現象的應對,抑或是對不良意識形態的消除和對“身份政治”的矯正,媒體素養教育都是一種調適人和媒體之間不諧關系的相對有效的途徑和方法,是我們對社會和媒體中出現問題的積極思考和主動作答,即存在一定的保護色彩。顯然,面對媒體的負面影響,面對人與媒體關系的種種不適,完全放手、放任自流的態度和方式顯然是不可取的。譬如,在Web2.0的世界里,“很多‘業余者’用他們的電腦在網絡上發布各種各樣的東西:漫無邊際的政治評論,不得體的家庭錄像,令人尷尬的業余音樂,隱晦難懂的詩詞、評論、散文和小說。……在博客里,人們恬不知恥地公開了自己的私人經歷、性生活、人生渴求、生活所缺甚至重新活一次的想法”[13]。在這樣一個世界,人人都應該有一種自我“保護”意識,正確處理好自己與媒體的關系,以免使自己在這樣一個精英消解、草根為王的時代成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其次,我國的媒體素養教育,應該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繼承、弘揚和保護。我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雖不免有其糟粕,但終以海納百川、地承萬物的氣魄和精深博大、兼容并蓄的親和力,在當代彰顯出超越時代及地域的文化熏陶和保護價值。然而,深具諷刺意味的是,當下我國一邊是網絡惡搞的盛行,一邊卻是書籍閱讀率的一再下降和“淺閱讀”現象的日漸普遍。據悉,“我國民眾每年人均閱讀圖書僅有4.5本,遠低于韓國的11本、法國的20本、日本的40本、以色列的64本”[14]。而且,“很多人根本無法忍受一星期或幾天不看電視的日子,卻可以對幾個月不讀書泰然處之”[15]。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提倡傳統文化教育、提倡“文學文化”教育,提倡“對包括《紅樓夢》這樣的經典文學巨著,無論是原拍、戲說,還是翻拍,不看最好,少看次之,而要多讀、多讀、再多讀”[16],對于我國媒體素養教育的開展和社會民眾媒體素養的提高,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再次,我國當前的大眾文化,雖然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越來越受到諸如“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等媒體文化的威脅,發展環境并不容樂觀。而且,在新媒體環境和參與式文化中,諸如對個人隱私、知識產權、文化的侵犯和信息安全的失范、信息犯罪、信息污染等弊端也導致了媒體道德觀念的紊亂和淪喪。因此,我國的媒體素養教育,本能地有著文化保護、道德保護和政治保護等歷史使命。當然,這種保護,并不是對包括大眾文化在內的非主流文化趕盡殺絕,而是有褒有貶,有打有壓,有收有放,是一種理性而有序的保護。
(二)媒體“賦權”的涵義與價值
一般來說,“賦權(Empowerment)”廣泛涉及“公民參與”、“協同合作”和“社群意識”等概念,具有多層次性(個人、團體、組織及社區)、多面向性(人際、社會、行為、組織及社區)、草根性(涉及由下而上的改變)和動態性(是一段進程而非處于一個穩定狀態)等典型特征[17],對現代公民教育和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卜衛認為,“賦權是指一個過程,學生們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批判地運用存在于他們直接經驗之外的知識和方法,目的是加深他們對自身和世界的理解,……賦權的核心問題是尋找那些可以消除社會不公正和減少權力不平等的方法”[18]10。她進一步強調,“媒介素養教育的目標應該包含個人的層面,即發展對媒體的批判性自主權,以及社會層面的,即提高發聲的能力,這最終將有利于發展一個更為民主的社會”[18]12。事實上,作為“超越保護主義”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價值取向,“賦權”在我國還具有一些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1.“賦權”的超越“保護”指向
英國大衛·帕金翰博士認為,“賦權”是與“絕對保護”相對的一個概念,是“超越保護主義”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價值所在。他還認為,教育者對大眾媒體的態度應該變“堵”為“導”,應以青少年為中心,尊重他們既有的媒體知識和媒體體驗,引領青少年根據自身利益對媒體信息做出明智選擇,尤其是要鼓勵、“賦權”青少年參與媒體制作,以增進他們對傳播的本質和新媒體技術的認識。因此,這種新的媒體素養教育已不再是一種被動的保護主義策略,而是一種培養青少年對大眾媒體進行批判分析的對話過程。[19]事實上,20世紀末媒體技術的革命性發展,新媒體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的媒體生態和人們的媒體觀念。這時的參與式文化也蓬勃發展起來。相應地,媒體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必須有所改變,先前被動的保護主義取向已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應該是一種主動“探索”、“賦權”取向,即從被動的“防御性保護”逐步走向主動的、賦權式的“進攻性保護”,即所謂的“超越保護主義”。
2.“賦權”的“參與”指向
媒體素養教育所強調的“賦權”,“不僅是對媒介的回應,也是對主流教育學的回應。這其中潛藏著自下而上的對媒介生產機制、媒介社會功能的反思和對一般意義上知識生產的精英立場的反思。媒介參與式現代社會公民權利的組成部分,旨在促進公平的社會表達和多樣化的信息流動,因此所有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的對價值觀、文化形態、生活方式的操控都值得警惕”[5]477-478。因此,開展媒體素養教育,“如果以賦權為目標,以參與者的文化經驗為基礎反省主流文化并發展改變社會的行動,那么,就一定要采用參與式方法,而不是以往的灌輸式教育”[18]21。事實上,“參與”式方法的實質,與提倡網絡面前人人平等的互聯網精神有著天然的契合。受教者運用各類媒介的“參與”行動是在演練如何“參與”公共空間的民主生活,就是讓受教者在“參與”中學習如何利用媒介發出自己的聲音。
3.“賦權”的“批判性自主”指向
美國教育理論家亨利·A·吉魯克斯認為,“賦權也是一種批判性思維和行動的能力。這個概念具有雙重指向,既是對個人而言,又是對社會而言。個人的自由和天賦能力必須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但個人能力又必須與民主緊密相連,這是因為社會改善一定是個人充分發展的必然結果。激進教育家把學校看作是社會形式,這些形式應當培養人們具有思考、行動、成為主體和能夠理解其思想所承擔義務的限制的能力。……而當今主流的教育哲學想要的卻是教育人們去適應那些社會形式,而不是批判地質疑它們。”[20]由此可見,“賦權”具有研討、協商、對話和行動的特征,它不能容忍將特定的文化價值觀、政治價值觀或意識形態強加于人。其目標顯然不是培養簡單的批判技能,而是建立人的批判自主權,以促成個人的解放。
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批判教育學的代表人物保羅·弗萊雷就曾指出,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具有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的社會公民,也就是塑造能夠在一個民主社會中發揮領導作用的、能動的政治主體。媒體素養對批判性的要求決定了媒體素養教育既是批判性自主思維的養成教育,又是積極的行動教育,因此,其在本質上是一種更為開放的、更為民主的教育。當前,針對我國媒體素養教育中的“灌輸”傾向,我們不僅應該強調媒體素養教育理論的批判性自主思維,更應該在實踐上強調“賦權”的批判性自主行動。這種思維和行動是媒體素養教育需要“賦權”最重要的理由,同時也是現代媒體素養教育最根本的特征。針對當前諸如“媒介有多壞,受眾有多傻,現在就看精英如何出來教育他們別上當受騙”的種種議論,有學者告誡我們,媒體素養教育“本質上是反對媒介和文化對人的操控,但不能從一種操控轉到另外一種操控;媒介素養教育是一個個人解放的過程,不能造成新的文化壓迫”[5]203。由此可見,媒體素養教育的目標不僅應該包含個人層面,即發展對媒體的批判性自主權;還應該包含其社會層面,即提高個人在媒體上的發聲能力。
三、結 語
平心而論,我國這十多年來的媒體素養教育研究和實踐探索是十分艱苦的,也是難能可貴的。伴隨這些探索的時代背景是,“中國社會目前正在進行著一次巨大的工業化、城市化變革,這場以‘時間遷徙’和‘空間遷徙’的方式同時進行著的變革,把西方國家持續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進程壓縮在短短的數十年間內完成。與此對應的是,短短的十多年之內,西方媒體素養教育流變過程中歷時態的多種價值取向在中國大陸幾乎是共時態地涌入研究者的視野,由于對有關媒體素養理念、目標、實踐形態和社會意義等各維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間尚缺乏較為一致的價值取向和理論起點,從保護主義的道德防范立場,到對媒體市場化商業化的意識形態批判;從對公民社會的認同,到強調主流意識形態控制;從技術決定論的樂觀主義,到哀嘆大眾文化泛濫的悲觀主義……這些,比Hobbs概括的美國圍繞媒體素養的七大爭論,要更加莫衷一是”[12]。
但是,媒體素養教育遵循自由、平等、民主等基本價值觀,對于我國每一位生活在當代的公民,尤其是青少年,接受“媒體啟蒙”已經成為其成長過程中的必要和必需。我們不能過分地強調媒體素養教育的中國特色,否則就根本沒必要開展、也無法開展。或者說,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地方。我們總不能等到我國的政治體制、媒體制度以及文化建設較成熟時才開展媒體素養教育,而應該在條件還不太成熟時積極創造條件啟動之。當前,不管何種紛爭,有一點已然達成了共識:應拋棄傳統的“純粹”保護主義取向的媒體素養教育,代之而起的是,建構和開展一種“超越保護主義”的媒體素養教育。
以“賦權”作為媒體素養教育的價值取向,具有借助媒體啟發人們擺脫蒙昧的操作意義,能夠啟蒙受教者個人的權利意識,引導他們以批判思維解構媒介,從而理解自身的社會處境,學會利用媒介維護自身利益,積極主動地爭取個人的自由幸福以及社會的民主公正。這正是培養現代公民的一條正途。正如卜衛所說“‘賦權’其實是媒介素養教育的最重要的理由,同時也是現代媒介素養教育的最根本的特征。”“賦權”取向體現了“超越保護主義”媒體素養教育從集權到分權再到賦權的權力轉移的發展過程:媒體使用權及參與權從成人、教師的手中逐漸下放,最后再由新媒體直接分散、賦權給媒體使用者;權力的轉移也反映了傳播活動從傳者中心向受者中心、教育活動從“教師中心”向“學生中心”的轉移。這種轉移,在網絡時代往往又會產生文化民主化的結果:創作者與觀眾、生產者與消費者、專家與業余者之間的傳統區隔一時轟然坍塌。這樣的結果,反過來又對媒體素養教育的開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張永桃.當代中國政治制度[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1.
[2] Buckingham.D.Media Education in the UK: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1).
[3] 陸曄,卜衛,李月蓮,等.媒介素養的國際發展與本土經驗[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7).
[4] 周葆華,陸曄.從媒介使用到媒介參與: 中國公眾媒介素養的基本現狀[J].新聞大學,2008(4).
[5] 陸曄.媒介素養:理念、認知、參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6] 王艷,張彭松.大眾文化及其本質[J].理論界,2006(2).
[7] 邱偉.臺灣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踐困境[J].東南傳播,2007(1).
[8] Buckingham D.Children Talking Television:The Making of Television Literacy[M].London: Falmer press,1993:10-11.
[9] 高校禁止新生帶電腦入學,80后不能沒有網?[EB/OL].(2007-10-14).[2013-09-08].http://q.sohu.com/forum/10/topic/349791.
[10] 卜衛.論媒介教育的意義、內容和方法[J].現代傳播, 1997(1).
[11] 仇加勉.超越保護主義:文化反哺視角的媒介素養教育[J].現代傳播,2007(4).
[12] 陸曄.媒介素養的全球視野與中國語境[J].今傳媒,2008(2).
[13] 安德魯·基恩.關于互聯網弊端的反思:網民的狂歡[M].丁德良,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1.
[14] 第七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發布[EB/OL].(2010-04-28).[2013-05-14].http://www.gmw.cn/content/2010-04/28/ content_1105804.htm.
[15] 高德勝.道德教育的時代遭遇[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43.
[16] 王旭明.建議少看多讀《紅樓夢》[EB/OL] .(2010-09-03).[2013-08-12].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02f740100lvza. html.
[17] Dalton James H,Maurice J Elias,Abraham Wandersman.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M].London:Thomson Learning,2007.
[18] 彭少健.2008中國媒介素養研究報告[C].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
[19] 秦學智.帕金翰“超越保護主義”媒體教育觀點解讀[J].比較教育研究,2006(8).
[20] 亨利·A·吉羅克斯.跨越邊界:文化工作者與教育政治學[M].劉惠珍,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