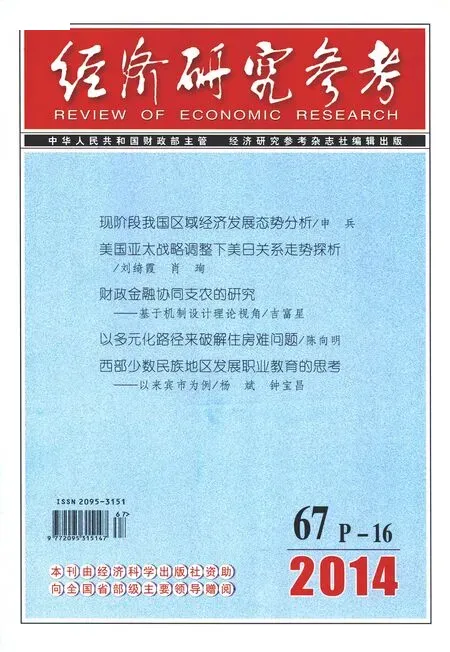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下美日關系走勢探析*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劉綺霞 肖 珣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下美日關系走勢探析*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劉綺霞 肖 珣
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增強并逐步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國為制約中國實力的崛起,實施了包括“重返亞太”、“亞太戰略再平衡”等內涵的亞太戰略調整,意圖在亞太地區重新塑造其領導下的新秩序,而美日關系成了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上的重要環節。本文闡述了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時代背景、布局和內涵、實施途徑,重點分析了在亞太戰略調整視野下美日關系的戰略博弈,即美日同盟所進行的新一輪戰略性調整以及所面臨的困擾因素,并就其對中國的影響進行了剖析。
美國亞太戰略調整;重返亞太;美日關系;走勢
一、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新布局
(一)亞太戰略調整的時代背景。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后的一段時期內,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實力奠定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把國際恐怖主義視為主要威脅,將其戰略重心轉移到中東,集中大量軍事、財政力量反恐,從而忽視了亞太地區的力量平衡。正是這個時期,一些新興國家經濟高速發展,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合作加強,使得全球權利的核心正逐漸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美國的霸權遭到削弱,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經濟低迷,整體實力衰落。而亞太地區卻是全球經濟最具有活力的地區,擁有27億消費者,經濟總量占世界的54%,貿易額占全球的44%,這為美國經濟復蘇提供了巨大的商機。美國為分享亞太經濟發展的紅利以促進本國經濟的復蘇,逐步把全球戰略的重點轉向亞太地區,提出“重返亞太”、“亞太地區再平衡”等發展戰略。當然,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是美國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原因。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保持著較快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從2000年1.2萬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3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10.7%,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4.16萬億美元,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低迷、歐洲債務危機頻發,而中國則憑借著經濟實力成功渡過危機,在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使得“中國威脅論”抬頭,美國對亞洲的“霸權焦慮”感倍增。因此,為平衡中國崛起實力,牽制中國的發展空間,美國試圖在亞太地區重新塑造由美國領導下的新秩序,進而將亞太地區納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以維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二)亞太戰略調整的布局及內涵。
在重振美國經濟、牽制中國經濟的發展乃至維持美國世界霸權地位的時代背景下,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后,開始全面推進亞太戰略調整政策,他宣稱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亞太地區是美國未來的戰略重點地區,在出訪亞洲四國時高調宣布“重返亞太”,其后又相繼提出“轉向亞太”、“亞太戰略再平衡”等發展戰略,這些構成了奧巴馬政府亞太戰略調整的內容。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秉持奧巴馬“亞洲第一”的外交理念,發表了系列講話闡述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構想。2010年10月,希拉里在夏威夷發表美國亞太政策的講話指出,美國參與亞太事務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持和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改善地區安全形勢,推動地區繁榮,推廣美國價值觀。”*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U.S.Department of States).2010.10.2011年11月,她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發表了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文章,宣稱:“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關鍵的驅動力”,“世界政治的未來由亞洲決定”,美國未來十年“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持續增加在亞太的外交、經濟、軍事和其他方面的投入”,以“保障和延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2011.11.
具體而言,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包括三大方面,即政治外交、經濟和軍事三方面:
政治上,推行“前沿部署性外交”、“多邊外交”、“價值觀外交”等主要措施。動用全方位的資源,如政府高級官員、學者專家、跨國組織工作人員派往亞太地區,從而實現美國對于亞太地區溝通交流的全覆蓋;美國政要頻繁訪問亞太,參與并主導東亞的多邊合作機制,介入東亞事務,高調宣示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力;宣揚美國的民主與人權,提倡東亞地區加強保護人權的力度,增加政治透明度。
經濟上,美國強力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簡稱TPP)的建立,試圖突破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模式,主導亞太經貿格局,構建以美國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合作機制。美國認為亞洲經濟的增長和活力為其經濟復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投資、貿易以及獲取前沿科技的機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內的財政壓力。
軍事上,推出把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的新軍事戰略,強調進一步鞏固與傳統盟國的關系,同時尋求新的盟友,即“鞏固老朋友,尋找新伙伴”,以強化多邊軍事同盟;增加軍事部署,建造更廣泛的軍事基地,與亞太國家頻頻進行軍事演習,進一步加強軍事合作,并介入南海爭端等亞太地區的安全事務。
綜上所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調整是一個集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多層次綜合戰略,可被理解為一個“全方位的綜合性回歸”。
二、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下的美日關系的戰略博弈
(一)政治層面——同盟關系強化。
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飛速發展,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由于歷史問題,在國際社會上的政治地位不高。日本一直把謀求成為世界政治大國作為最根本、最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而“入常”則是實現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變的重要標志,這需要倚仗美日同盟的力量來提升它的國際地位,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公開表示支持日本“入常”。這充分表明在美國亞太戰略調整背景下,美日同盟關系進一步強化。2012年4月,日本首相野田訪美時與奧巴馬發表了題為《面向未來的共同藍圖》的共同聲明。該聲明稱,“幾十年來,我們的同盟關系向著全面的伙伴關系穩步發展,這不僅有助于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同時也對區域外的和平和安定做出了貢獻”。日本為配合美國亞太同盟伙伴體系,其戰略框架正在向多層次的“網狀模式”調整,正如前日本外相玄葉光一所言,日本要與各國建立新的“開放且多層次的網絡”,“日美+1”的安全合作模式正越來越多的為美日同盟所用,而美日在協調與印度、緬甸、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的爭端與外交事務時均使用了該安全合作模式。
(二)經濟層面——“對抗與討好”兼備。
奧巴馬政府將TPP作為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重點。TPP即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是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國中的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四國發起,于2005年在APEC框架內簽署的小型多邊貿易協定。2008年,美國宣布加入該協議,主導談判并提出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計劃,截至2012年年末,已有11個成員國,這其中并沒有日本。美國一直呼吁日本能早日加入到TPP的談判桌上,一方面鞏固“美日同盟”關系,另一方面企圖借助TPP扭轉本國貿易逆差,實現出口翻番,增加就業機會,復蘇本國經濟。美國公司90%的消費者集中在海外,而亞太地區聚集了全球60%的消費者,所以,TPP成為美國打開亞洲市場的法寶。美國著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亞太自貿區可能使美國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損失250億美元,或約20萬個高薪崗位。可見,TPP是美國依托貿易重返亞洲的平臺。
日本外相岡田克早在2009年參加新加坡APEC會議期間就表現出對這個框架的濃厚興趣,但因日本內部有較大爭議而擱置。2011年11月,日本首相野田表示日本將朝著加入該協議的目標,開始與美國等相關國家進行協商。對于日本政府而言,TPP有著充分的吸引力,在TPP多邊框架下,日美同盟關系將進一步鞏固與加強,這不僅會給日美兩國帶來豐厚的經濟利潤,有助于兩國經濟的復蘇重建,同時也會在政治、安全上獲得更加穩固的信任感。但TPP也是一把“雙刃劍”,會給日本的經濟與政治造成一定的負面效果,尤其是農業。日本是一個農業資源十分有限的國家,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其農產品長久以來高度依賴進口,從1984年起,日本便成為世界最大的食品進口國。在特殊的國情下,日本政府加強了對本國農業的保護力度,直接管制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采取制訂差別農業品關稅、國家財政補貼、提高進口產品加價等手段來最大限度地保護農業。而TPP模式是打造一個更加“自由”與“公平”的經濟貿易框架,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關稅減免,即成員國90%的貨物關稅立刻免除,所有產品關稅將在12年內免除。這對日本農業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據日本農林水產局估算,加入TPP將使日本農業產值減少7.9萬億日元(約合1013億美元),農業部門就業崗位減少350萬個,糧食自給率將從40%降至14%。2012年4月在日本東京數千名日本農民集合抗議“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2013年3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顧國內的反對聲音,正式宣布加入TPP談判,開始與美國攜手打造亞太地區的新型貿易平臺。但是經過多輪談判協商,美國努力說服日本廢除五大農產品(包括小麥、大米、白糖、牛肉、豬肉、乳制品)的高關稅,日本則敦促美國取消針對進口汽車和輕型卡車的關稅。雙方始終未達成協議。
2014年4月底,奧巴馬訪日期間希望利用安保聲明公開力挺日本對釣魚島的管理權,以此換取日本在TPP會談中的讓步,進而獲得經濟紅利;日本則希望借奧巴馬到訪之機消除日美之間隔閡,修復日美關系,盡力尋求美國對日本的支持,結果以失敗告終。
由此可見,日本決定參與TPP談判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層面的考慮,希望通過TPP在政治層面上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系,是對美國繼續向其提供戰略保護和政治支持的回饋,借此重新確立和美國聯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但是,日本也不可能完全拋開自身的經濟利益得失。
(三)軍事層面——從“分工”走向“一體”。
美國的軍費開支在過去十年里大幅增加,保持著世界絕對第一的位置。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為6820億美元,占其GDP的4.4%,約占全球軍費支出的39%;這個數字約是中國軍費(位列第二)的4倍,超過了排名緊隨其后的10個國家的軍費總和。盡管近年由于財政困境,美國政府削減軍費,但2014年國防部預算申請約5270億美元,比2011年預算控制法案規定2014財年國防預算最高限額4750億美元超過近520億美元。過度的軍費開支使美國政府不堪重負,為了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借力”。而在亞太地區,日本擁有強大的海空軍力量及軍事強國的野心,這是美國在該地區提升對華軍事遏制力、維持亞太平衡的重要條件,不少美國戰略界人士認為,美國對日本的承諾應從“保護日本”變為“幫助日本保護自己”,應促使日本認真思考其在亞洲的新角色。2014年4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日期間就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表態,稱釣魚島適用于《日美安保條約》。美國希望借此安撫日本和其他地區盟國,兌現對日本的安全承諾,鞏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同盟網絡。
日本是一個島國,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對海洋的依賴,謀求海洋大國地位,擴展海權一直是日本追尋的戰略目標,也是其“強兵富國”的重要一環。冷戰結束后,日本逐漸興起海洋擴張論,在先進的科技實力和雄厚的經濟實力的支撐下,大力發展海上自衛隊,現已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海上力量,其反潛作戰能力已經達到世界第二水平,實力僅次于美國海軍,借助于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日美同盟關系進一步強化,日本意圖由東亞地區的軍事同盟逐步轉變為全球性的海權同盟,并希望擴大日美在海洋上的合作范圍,以便在未來構建日美主導的國際海洋秩序。
另外,近年來在強化日美同盟關系的旗號下,日本政府通過了《支援美軍法案》、《國民保護法案》等一系列“有事立法”不斷放寬對海外派兵的限制,日本自衛隊活動范圍不斷延伸。當前,為使海外派兵常態化和便捷化,日本嘗試以普通立法取代之前“一事一法”的方式,并在美國的促動下著手“武器出口三原則”,從而大幅提升其在全球軍火產業的競爭力。美日同盟關系正從側重分工轉向軍事一體化,大力深化兩國“聯合力量”和“互操作性”,通過共享情報、共謀規劃、聯合訓練、共建導彈防御系統等多種方式,推動美日軍事一體化。
在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戰略支點,但其中也潛藏著很多的危險。美國企圖大力強化日美的軍事同盟關系,想讓日本更多分擔美國的防務負擔,在亞太制衡中國。但日本則有恃無恐,借機戰略擴張,希望強化防衛能力、在戰略上增加獨立性和自主性,力圖在修憲、行使集體自衛權、歷史認識等問題上突破底線,沿著右傾化道路疾走。日本首相安倍上臺后,在釣魚島問題上顯示強硬立場,爭端逐步升級,中日戰機對峙,局勢有“走火”失控的危險;安倍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無疑是對本已緊張的日韓關系“火上澆油”,這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美國“再平衡戰略”,使得美國近期幫助日本彌合與韓國關系的努力付之東流,建立美日韓三國同盟關系更是遙遙無期,美國罕見地多次以“失望”一詞來表達自己的態度。這些都逾越了美國的戰略底線,成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麻煩制造者。安倍政府積極推動修改憲法,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美國政府雖然支持,但也擔心過度武裝的日本會重演歷史引發鄰國及美國其他盟國的不安。
因此,我們可看到在美國亞太地區的調整戰略下,美日兩國間的合作關系正逐步緊密,美日同盟在政治、安全、經濟等領域所進行的新一輪調整是全面的、深入的、對亞太地區乃至國際形勢都會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我們關注到美日間的同盟關系同樣也受到系列因素的困擾。首先,美日之間仍存在某種程度的互信不足問題。美國對日本低效率的政治體制和僵化的外交機制信心不足,也擔心過度武裝的日本會重演歷史引發鄰國及美國其他盟國的不安,同樣,日本也擔心美國出于對美中關系的考慮而不履行對它的安全義務。其次,美日兩國都面臨著經濟增長乏力、財政預算緊張的挑戰。美日兩國的經濟困境和財政窘境、兩國國內政治派別之間的復雜角力,以及來自亞太地區國家的反制力等因素都會影響到美日兩國之間同盟關系的發展前景。
三、美日關系的調整對中國的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從“重返亞太”到“重心轉移”再到“戰略再平衡”,美國的亞洲戰略一脈相承,都是根據復雜變化的國際形勢而做出的適當調整,其戰略實質都是維護和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毫無疑問,中國的和平崛起是美國亞太戰略中最大的挑戰,也是最為薄弱復雜的一環,而日本因其經濟、軍事實力以及美日同盟關系也一直以來被美國作為其亞太戰略的最重要支點之一。
伴隨著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美日同盟被大力強化和調整,這給發展中的中國及其周邊的利益,尤其中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和解決地區熱點與歷史遺留方面所作的努力帶來各種消極影響。日本為凸顯其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重要性,對中國更多采取了利用美國遏制中國及利用中國與周邊鄰國的矛盾以擴大自身影響力的政策。在美國大力強化美日同盟的形勢下,日本則借機戰略擴張,尤其在釣魚島問題上顯示強硬立場,致使中國退無可退,強硬對付,最終使釣魚島爭端逐步升級,再加上安倍政府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對歷史問題毫無誠意,嚴重影響了中日兩國人民經過長期努力所建立的友好和平相處的民間關系。
經過21世紀前10年間亞太經濟一體化趨勢正逐步加強,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經貿網絡已基本形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也已提上了日程,近期東盟又倡導建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而美國在此時實施的亞太戰略的調整,“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等使亞太地緣經濟失調甚至走向分裂。在美日同盟的強勢下,美國在亞洲推行TPP,日本政府隨后加入TPP談判,從TPP的框架和具體條款可看出其內容是直接針對中國,并把中國排除在TPP的創始成員國之外,一旦TPP達成實質性協議,作為一種關稅同盟大部分東亞國家會選擇盡早加入TPP,這無疑是孤立了中國,使得東亞地區國家關系的離心化,同時也將對中國形成巨大的貿易歧視與貿易轉移效應。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出口總額達到2.05萬億美元,而對美國和東亞地區的出口分別為3517.8億美元、6084億美元,占中國出口總額的一半左右,TPP生效以后將會擠占中國的出口市場,導致中國出口下降,并影響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美日同盟的強化反映了兩國在遏制中國崛起戰略上的共同利益,但美日之間也存在著利益沖突,這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尤其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國際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日兩國在諸多領域不得不加強同中國的合作,以擺脫國內的經濟低迷、財政困境。隨著東亞國際和地區體系的變動,美國重返亞太、中國和平崛起、日本向正常國家邁進的傾向日益明顯,中美日三邊關系更加復雜,形成三角博弈。而三角關系是最不穩定的: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之間的利益共同在迅速增加,相互依存度加深,日本又擔心美國加強同中國的合作,這會使美日同盟的不信任感倍增。因此,中國應堅持現有的外交戰略,一方面增強自身的綜合實力,尋找并建立中國與美日同盟的利益契合點,另一方面通過強大的經濟、政治、文化等交流,鞏固并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消除“中國威脅論”的惡劣影響,加快軍事現代化的發展步伐,抵御美日同盟對中國的圍堵。
四、結論
我們應看到中美日三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經濟體,三國互為重要的經貿伙伴,相互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交往。中美日關系是亞太地區乃至世界最為重要的三邊關系之一,尤其對于亞太地區的經濟、安全及多邊合作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三國之間的關系互動也決定中東亞形式的演變和地區格局的基本走向。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中美日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各自的發展進程中遇到了各自不同的問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能否維持其霸主的地位,歷經地震海嘯災難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日本是否還有復蘇的希望,而轉型中的新興大國中國是否是世界前進的引擎,面對不同的問題三國折射出了不同的政治表情。在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背景下,中美日三國間的相互依存正進一步加強,三國間應經過幾番磨合,達成戰略妥協,將對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納入亞太區域乃至全球戰略層面來考量,盡可能達成共識,爭取建立新的平衡點是三國未來努力的方向。
[1]陳寶森、王榮軍、羅振興:《當代美國經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2][日]瀬口清之:《第2期オバマ政権のアジア太平洋外交と新體制下の日米中関係》,載于《キャノングローバル戦略研究所》2013年第3期,第1~10期。
[3][日]高木綾:《米國世論に見るアジア観》,載于《総合調査「日米関係をめぐる動向と展望」》2013年第8期,第69~82頁。
[4]倪世雄:《競爭、互信與管控分歧——中美互動視角下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載于《學術前沿》2012年第12期,第34~63頁。
[5]俞正樑:《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失衡》,載于《國際關系研究》2013年第2期,第3~12頁。
[6]陳彩云:《合力作用下的戰略調整——奧巴馬亞太東移戰略淺析》,載于《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3年第1期,第97~108頁。
[7]胡傳明:《美中日在南太平洋島國的戰略博弈》,載于《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第51~57頁。
[8]趙可金、殷夕婷:《美國戰略調整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載于《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第71~84頁。
[9]曾蕊蕊:《美日同盟關系的調整變化對中國對外戰略的影響》,載于《吉首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第124~128頁。
*本文為博士后基金課題“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研究與借鑒”的階段性成果(編號:2013M530566)。
F114.49
:A
:2095-3151(2014)67-0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