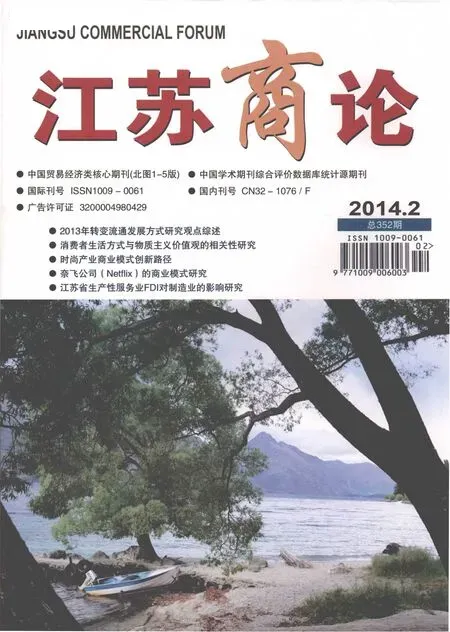溫州文化產業發展的反思——兼論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李 婕
(溫州大學城市學院,浙江溫州 325035)
早在2006年1月在浙江省提出“文化興省”這一方針下,溫州就出臺了《溫州市加快建設文化大市的決定》,提出文化大市建設“六大工程”。然而歷經近7年的發展,溫州文化產業在政府政策的推進下仍只是體征出數量上的空間聚集,而文化的聚集、疊加和溢出則仍為顯現,即集約化程度不高;于文化產業本身而言則凸顯著一種結構性缺陷:以文化產品的制造和消費這些相關層為主,而文化創意等核心層和外圍層不足。本文擬回顧文化產業在溫州發展的制度變遷,以揭示導致溫州文化產業結構性缺陷的制度因。
一、溫州文化產業發展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由先發國家文化產業的演進來看,文化產業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人們的物質財富高度累積后,對文化和精神產品的追求下所自發演化的,而由于其文化、產業、創意的有機結合所產生的疊加和溢出效應,對社會經濟的推動作用而得到政府層面的高度重視而迅速發展起來。也就是說文化產業如同文化一樣,其演化首先是自下而上的,然后才是自上而下的,[1]文化產業雖主要應由市場調節和選擇,但政府的政策對其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因為政府的政策雖然不是所有問題的出處,也不是所有問題的原因,但政府的政策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方向和性質的確定,確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作為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溫州,其文化產業本應主要通過市場進行選擇和調節,但其發展卻是政府制度推進的結果,這可從其文化產業發展的制度變遷中窺其管豹。
為響應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文化強國”這一國家戰略,浙江省提出了“文化強省”戰略,而具有“敢為天下先”精神的溫州,在這些宏觀戰略的引領下,早在2006年就拿出了自己的措施即《溫州市加快建設文化大市的決定》。為了凸顯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以及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功效,溫州政府在“優二強三”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社會經濟更好更快的發展的目標下,相繼出臺了多項有關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條文。溫州市政府還啟動了“1030”文化產業工程,即創辦10個文化產業園區,扶持30家文化骨干企業,并力促一兩家文化企業上市。2010年,《溫州市人民政府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要求盡早編制溫州市文化產業“招商引資項目”;2011年出臺了《溫州市文化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和《溫州市委、市政府關于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優惠措施。并在《溫州市文化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實施步驟。
正是在這些正式的制度安排下,溫州文化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據相關資料顯示,溫州現有文化產業單位15000家,其中法人單位近500家,擁有資產210億元,從業人員超過15萬人。1歐江軒.溫州圍繞創意做大產業文章[N].浙江日報,2012-09-03(11).目前已初具規模的產業園有浙江創意園、智慧谷、東甌智庫,正逐步成長的有溫州工藝美術創意園、龍灣紅連文化創意園、紅太陽設計創意園、鹿城學子創意園、龍灣源大創業園、溫大學生創意園等,以溫州大都市主中心為全市文化發展核心區的空間構想正逐步形成。然而,從這些正式的制度安排中,亦不難發現政府政策推動溫州文化產業發展是采取一種“實用主義至上”的態度,即以文化產業為工具、手段達到消解宏觀經濟問題的目的性,比如提升日漸下滑的城市競爭力、追求文化產業的經濟性(即對GDP的拉動作用)以此達到政府政績的最大化等等。正是在這種“實用主義至上”態度下所采取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使具有良好經濟和文化基礎的溫州文化產業問題迭出。
二、強制性制度變遷下溫州文化產業發展所存在的問題
溫州文化產業在政府政策的強制推進下、在群眾自我訴求的拉動下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帶動下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但也存在著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存在著一個錯位、一個缺陷和一個不夠。
1、“實用主義至上”下的認識錯位
文化創意產業是區別于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外的全新產業,其發展不僅能提升城市的品質和文化內涵,增強城市競爭力,產業的疊加效應也將助推經濟增長。據相關資料和研究表明,全世界文化創意產業創造的產值目前已高達220億美元,并以5%左右的速度遞增。但從國外發達國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演變,和我國的798、田子坊等成功典范的文化創意產業嬗變來看,文化創意產業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因。而不幸的是,政府往往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因。這種政府部門通過相應的政策法規,借助文化產業這一平臺,利用其經濟性將其工具化、手段化進而目的化,可從溫州政府所出臺的各項政策法規其目的指向中窺見一斑。
如為達到“退二進三”和“優二強三”這一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目的,溫州市政府啟動了“1030”文化產業工程,即創辦10個文化產業園區,扶持30家文化骨干企業,并力促一兩家文化企業上市,同時出臺了《溫州市文化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等文件以確保發展文化產業達到產業結構調整的目的。這種定位和認識顯然是基于政策目的性和文化產業經濟性的因果倒置和錯配,將本應是通過產業轉型和發展來帶動和助推文化產業園區和項目建設而倒置。其結果有可能是園區扎堆,同質化現象凸顯,帶來所謂空間集聚的同時產業和文化的集聚仍飄泊于云端的現象,更談不上創意及其價值疊加和溢出。對入園企業而言,則可能囿于同質競爭的殘酷性而出現空巢、轉租和轉向而游離于文化產業之外。不幸的是,這些擔憂目前正在溫州乃至全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上演著,而這明顯有悖于政府當初希望百花齊放、碩果累累的愿景。
再如為提升城市競爭力,在《溫州市文化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提升城市競爭力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這本為當地城市政府的職責和目的,本無可厚非,但這種基于“經濟達爾文主義”的趕超思維,形成了生硬轉型,所有這些均彰顯政府以此為工具消解宏觀經濟問題之目的。[2]
當然,政府的政策也不是所有問題的原因,而且這些政策和措施對于釋放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荷爾蒙、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方向和性質的確定,確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這種認識思想的錯位和因果關系的錯配,勢必如我國對城市化認識的錯位一樣——將之視為解決經濟增長乏力的工具、手段和原因,而不是視之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勢必將如阻礙和異化城市化樣阻礙和異化文化產業的發展,這是我們在發展文化產業時所必須警惕和糾偏的。在這種錯位的認識下,溫州全市各區、市、縣不顧自身實際盲目將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模式生硬植入的做法,其結果就是各種小的、不成規模的文化產業的遍地開花、無序競爭。
2、文化產業層次分布結構性缺陷顯著
政府強力推進下的溫州文化產業,其文化產業外延結構具有結構性的缺陷:以相關層為主而核心和外圍層不足,未能形成文化產業品牌效應和疊加效應,致使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功效未能充分發揮。正如一些研究者的研究結果所表明: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范周(2012)認為,溫州文化產業園區入園企業及其業務同質化現象突出,企業規模小、層次低,缺乏核心層次文化創意產業企業和業務,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對文化產業園區并沒有準確的定位,政策上也沒有準確的標準;[3]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2012)的調查顯示,全國各地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跟風現象凸顯,各種打著文化旗號進行圈地、轉租和空巢現象比較突出,存在大量資源浪費現象。[4]溫州兩會期間部分代表委員表示,溫州的文化創意產業處于低、小、散狀態,而且多個園區餐飲娛樂業扎堆,缺乏真正的創意元素,跟上海、深圳等地的創意園區相比,實在有點“囧”;同樣諸多的溫州民間觀察人士也對溫州這種大批量上馬文化創意園區的現象也表示同樣的擔憂,認為溫州的結果有可能是“政府希望百花齊放,但到最后卻是只開花,不結果。”即政府有可能好心未必能辦好事,愿景為現實無情的打壓。
溫州文化產業的發展仍是處于產業鏈條的末端,仍只是在原有產業的基礎上以文化的名義進行簡單的初次開發和生產,即圍繞傳統的文化產品制造和銷售而展開,以相關層業務作為其主體業務,而文化娛樂、文化科技等作為文化產業主體的核心層和外圍層業務顯著性的不足,文化產業結構性缺陷顯著。如2009年,溫州市核心層、外圍層和相關層分別實現增加值10.48億元、15.15億元和52.12億元,三者之比為 13.5∶19.5∶67.0。 經過 3年政策性推進后到2012年,這種結構性構成仍未有明顯改觀,在138億元的文化產業增加值中,三者的比例關系為14.3:21.2:65.5。2依據《浙江省統計年鑒》和《浙江省經濟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歷年相關數據整理。并且溫州的文化創意產業大都集中于溫州市中心城區,而附近的所謂副中心區其所發展的只是文化產業,而且要么是如龍港印刷城類的文化制造產業,要么只是基于本地自然資源的旅游產業,如楠溪江金珠瀑文化休閑中心、雁蕩山文化旅游休閑區等,并未能將文化、科技和產業有機的融合,只是簡單的借助文化之名進行的餐飲和娛樂消遣等生活方式的噱頭。即便位于市區黎明工業區的東甌智庫創意園區,“唱主角”的也是西餐、咖啡、茶餐廳等,舊廠房改造而成的一棵樹文化藝術中心、小茶悅會茶文化體驗館人氣都很旺,雖目前已有卡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名堂品牌策劃設計機構、菜菜頭動漫等主打創意的企業入園,但核心層的文化創意氛圍仍較缺乏。即園區內企業之間的聚合度仍是低層次的地理集聚和初級階段的相關層業務聚集,沒有形成完備的技術開發體系、區域創新網絡、市場服務體系和政府支持體系,致使園區之間和園區之內產業同構突出,而核心和外圍層的創意產業發展不夠。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政府政策導向的不明、管理和把關的失職,也有溫州在開發文化產業方面的人才吸引和培育的不足、地理區位的短板,更有企業逐利性下的對傳統文化和社會責任認識不夠的使然。而這顯然不利于溫州文化產業的深度發展和增加值的提升,不利于文化產業向文化創意產業的轉向。
3、溫州文化產業發展政策投放的精準度和力度不夠
溫州為利用文化產業的發展助推經濟增長、優化產業、提振城市競爭力,市政府和各級區、縣市當地政府均出臺了諸多的政策條文和規劃,特別是進入“十二五”以來,溫州政府出臺了多項扶持政策,但這些政策投放的精準度和力度仍顯不夠,后續的細化工作和管理工作力度也不夠。
一是雖然有著諸多的扶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法規,但這些政策條文大都只是一個整體的規劃、愿景,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的細化,也缺少必要的對文化產業的管理和把關,致使操作性和執行效果不夠理想,立項、籌建、新建和改造了諸多文化產業園區,但并未帶來文化產業的疊加、聚集。在文化產業的規劃上不能結合溫州傳統產業優勢進行定位,而盲目追求高、新產業。如在《溫州文化產業“十二五”規劃》中擬重點發展10個文化產業園,在其項目內容中“動漫”這個名詞是出現頻率最高的,溫州不少產業園如鹿城文化創意設計園等基地都將其納入項目具體內容。而事實上,溫州由于地處東南一隅,雖在泛長三角、海西版塊和海洋經濟圈之列,但并不具有區位優勢,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已不如開放之初由于其高度發達的民營所帶來的聚集。而且目前政府對待人才的引進和安家落戶,在給予的住房補貼、安家費、科研啟動經費和稅收減免等方面已遠不如十年前那么有力度和具有競爭力;同時溫州企業大都仍是以家族企業和中小企業為主體,大型企業集團和上市公司(10家)并不占主流,加上語言的自成一體、晦澀難懂,流入的人才很難融入企業核心和文化等等,使得在溫州發展動漫產業并無任何優勢。事實上,不僅是動漫,除了像溫州電子商務園區、永嘉雕塑工藝品產業園等單獨立項的產業園,其項目內容都存在交叉重疊的問題,反映出政策投放精準性的不足。而這與文化產業統計工作的非正規性和不透明性有著莫大的關系。目前溫州統計部門所出具的年鑒和公報中,均沒有具體列示文化產業項目,也沒有以文化產業為主體的相關統計指標體系,所有這些均不利于文化產業政策層面的制定和學術層面的研究,不能精準地指導文化產業的發展。
二是政府政策的扶植力度不夠。如在財政支持上,自2011年起,溫州市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作為扶持資金。而在2011年前是沒有相應的財政扶持的。即便是2000萬元對于溫州而言,也只是一套別墅的價格,更何況這2000萬元是為目前從事文化產業的15000家企業共享,平均到每個企業頭上每年只有1333.33元,還不夠其一個月的園區場地費。相比其他省市,其力度遠遠不夠。如江蘇省在“十一五”期間就設立了省級文化產業專項資金1億元,2009年已增至2億元;市級財政方面,南京市每年專項基金1500萬元;常州市和高新區財政5000萬元;蘇州市工業園區投入8000萬元資金。再比如北京2009年是5個億的專項資金,杭州是2.57個億的專項資金,就一個余杭縣2012年政府也有3000萬元的投入。從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項目來看,溫州市在教育、科學技術和文化體育與傳媒上的財政預算占當年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的比重小,而且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
扶持力度的不夠還體現在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機制和政府的管理、后續引導方面。《溫州文化產業“十二五”規劃》雖在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機制改革創新上做出了具體的布局,但文化產業目前在溫州無論從其產值規模還是從從業人數來講,仍屬于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范疇。中小企業融資難為一個歷史性難題,而“十二五”規劃在消解溫州文化產業所作出的指導性綱要上,并設有實質性的制度創新和方式創新。不論是發行債券、發行股票上市融資,還是通過向銀行質押貸款獲取資金,均面臨著諸多制度性障礙和可行性障礙。這些文化產業企業目前根本就不具有《公司法》和《證券法》所規定的發行債券、股票融資的資產和財務要求,而且溫州在知識產權和專利權的保護方面,歷來就沒有保障,依靠這些無形資產來向銀行質押,除非有政府強制性的要求,銀行是不大可能去踐行的。
在引導和管理方面,《溫州市文化產業 “十二五”規劃》,對溫州文化產業有很多優惠政策,以此來鼓勵和吸引企業轉型發展文化產業,這也確實吸引了許多有志于文化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人士、企業入駐園區,但對于入園后企業在文化產業的開發、管理等方面既缺乏引導和把關,也缺乏必要的后續政策支持。只負責將你引進來,至于入園后你做什么、如何做則只是企業自身的事情,故而文化產業只開花不結果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促進溫州文化產業包容性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溫州文化產業是政府制度推進的結果,政府的政策也是溫州文化產業結構性缺陷凸顯的制度原因,政府政策制訂的“實用主義至上”原則,使政策投放的精準性欠缺,制約著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發展,因此,應進行相應的制度創新和改革。
1、要廓清認識
要認清文化產業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正如城市化一樣,文化產業和城市化雖對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而且是當前投資、內需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乏力的很好的替代工具,但城市化、文化產業的發展應該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5]這已為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社會經濟高度發達后才出現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所明證。因此,廓清這一認識,政府制訂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劃、政策就應立足如何通過發展經濟、社會,然后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而不應是相反。
2、要加大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培育和引進,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文化產業以文化為靈魂,以科技和人才為核心,以實現產業和文化的聚合、疊加為目標。溫州高度發達的民營經濟所帶來和累積的物質財富,溫州淵源的甌越傳統文化和優越的自然資源、產業集聚,具有發展、培育人才和吸引人才的優越條件。但不幸的是,近幾年溫州在發展文化、教育和科技上的投入呈現下降趨勢。因此,應探究、清晰導致這種下降趨勢的緣由,同時,應發揚敢為人先的傳統進行相應人才引進的制度創新,制訂更具有競爭力的人才引進和培育政策。其實早在2000年左右,溫州為發展教育事業,所制訂的吸引全國優秀人才的引進政策就是一個很好的示范和創新。
3、優化產業結構
要加大產業、科技和文化的整合度,在傳統優勢產業、文化的基礎上開發、創新新的業務和服務,提升產業和文化的附加值,使之溢出和疊加效應盡可能最大化,進而實現文化產業向文化創意產業的轉向和邁進,扭轉和優化當前溫州文化產業的結構性缺陷,使之形成一種以核心層、外圍層為主,相關層為輔,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平衡、協調文化產業結構。
4、要進行文化產業投融資的制度和方式創新,為其包容性發展提供資力支持
文化產業是一種軟產業,不像制造業和工業那樣有著較多的固定資產和產品,可以較容易的從銀行獲得貸款。但文化產業有基礎產業的物質基礎、有文化這一軟實力,可以借鑒金融工具的創新和資產證劵化等方式,以文化產業為標的構建相應的證劵化資產,向社會進行出售以募集其發展所需的資金。當然,在文化產業證劵化的過程中應引入風險控制機制、風險分散機制,同時必須有相應的政府制度的保障。
另外,政府財政扶持力度的加大、整個社會以一種更包容的心態對待文化產業以及加大文化產業的統計工作和建設,同時加大溫州文化產業走出去的制度創新等等,所有這些均是溫州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要認真反思和創新的方面。
[1]林拓,李惠斌,薛曉源.世界文化產業發展前沿報告:賈斯廷·奧康納,歐洲的文化產業和文化政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77.
[2]李婕,胡濱.中國當代人口城市化、空間城市化與社會風險[J].人文地理,2012,(5):6-12.
[3]范周.溫州文化創意產業園遭遇動漫產業瓶頸[OL].http://www.cccnews.com.cn/2012/0426/6724.shtml2012-04-26.
[4]陳少峰.文化產業新征程[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717981.html2011-12-26.
[5]許焯權.創意產業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EB/OL].http://finance.qq.com/a/20060512/000583.htm2005-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