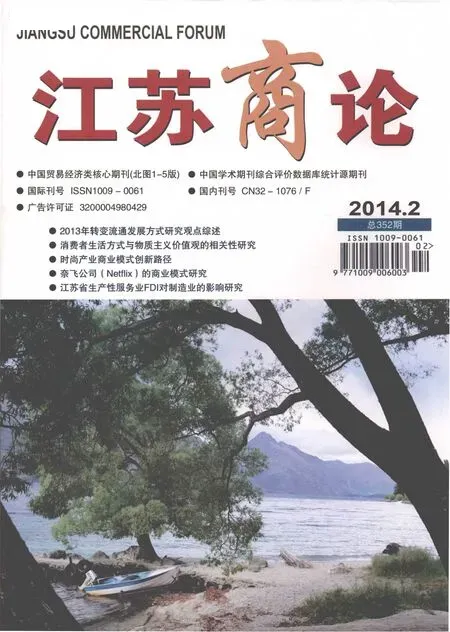經濟供求關系與低端鎖定
沈曉陳,王 領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
一、“低端鎖定”的定義
當前文獻較少對“低端鎖定”一詞進行定義。就語義而言,“低端鎖定”可以分解成兩部分進行理解。所謂“低端”,就現有文獻而言,主要包括兩種指代:一是以技術為著眼點,認為“低端”是指生產采用較為落后的生產技術,如康志勇(2009)、時磊和田艷芳(2011);二是以價值鏈為著眼點,認為“低端”是指生產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如周勤、周紹東(2009)、李美娟(2010)、劉維林(2012)等。 低技術、低增值的生產過程導致低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的產出。所謂“鎖定”,其實質是一種“路徑依賴”(胡國恒,2013),與“低端”結合在一起理解,則是指生產無法完成技術升級、始終處于價值鏈低端的狀態,產出始終以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為主。在現有文獻中,“低端鎖定”有時用來形容微觀的企業(盧福財、胡平波,2008),有時用來形容中宏觀的產業(趙夫增、穆榮平,2007),并主要集中在對后發型工業國“低端鎖定”現象的研究上。
二、我國產業升級現狀
大多數文獻認為“低端鎖定”現象在我國確實存在,但并未給出實證性的研究,多是將其作為一個既定事實。目前,國內外由于對“低端鎖定”概念界定不很明晰,并未形成系統的方法對其進行度量。筆者根據上文對“低端鎖定”涵義的解析,從兩個角度對我國“低端鎖定”現狀進行綜述:一是從生產技術角度,二是從產出增值角度。
1、生產技術角度——全要素生產率
作為衡量一國生產技術水平的重要指標,全要素生產率指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揭示一國的產業是否低端鎖定狀態。當前,國內外對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究竟如何,以及其變化趨勢,觀點并不統一。就絕對水平而言,大多數實證文獻的測算結果顯示,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較低,如吳先華等(2011)采取索洛余值法對美、日、中、俄等19個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比較,發現1999-2006年間中國TFP的平均值排倒數第一,低于墨西哥、巴西、俄羅斯等國,比之排名第一的挪威相差甚遠。就增長率水平而言,則分成針鋒相對的兩類觀點:一類認為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如郭慶旺等(2005)、江春等(2010)、劉建國等(2012);另一類測算得出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較快,如張軍(2002)、孫琳琳等(2005)、涂正革等(2007)、楊向陽等(2013)。 總體來說,認為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的是大多數,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貢獻而非技術貢獻的。
2、產出增值角度——貿易技術結構
一國的出口往往反映著一國的生產結構水平。出口產品的技術結構或附加值結構往往能夠幫助解構一國生產增值水平,揭示一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出口的貿易結構水平或技術含量看法并不一致。一種樂觀的看法是中國出口品的技術復雜度顯著高于其他同收入水平國家,如 Rodrik(2006)和 Schott(2006)。 另一些學者則持謹慎觀點,認為中國的出口技術結構雖有優化,但水平仍低于世界均值。邢玉升等(2012)通過構造相對技術含量指數和整體技術水平指數對中國2001~2008年出口貿易技術結構進行測算,指出傳統方法高估了中國出口貿易技術結構,中國制造業出口品的技術含量仍是低層次的。這也是當前大多數文獻的觀點,即從貿易技術結構來看,中國仍處于“低端鎖定”狀態。
三、我國“低端鎖定”現象產生的原因
當前文獻對“低端鎖定”現象產生原因的解釋相當零碎。大部分文獻在對現狀的描述上多從宏觀角度出發,但對原因進行分析時卻多從企業行為進行展開。目前主要有兩類觀點:一類認為跨國公司的技術封鎖與市場壟斷是后發型工業國 “低端鎖定”現象產生的主因,即“低端鎖定”現象是外源的,以盧福財、胡平波(2008)為代表;另一類認為本土公司對競爭策略的路徑依賴才是“低端鎖定”現象產生的根源,即“低端鎖定”現象是內源的,胡國恒(2013)持此類觀點。事實上,宏觀的供需環境也會對產業升級產生影響。一國產業的“低端鎖定”可以表現為供給結構的低指數化,而供給結構又是在與需求結構的互動中進行變化的。所以,對一國供求結構的分析有助于解釋“低端鎖定”現象產生的原因,而這是當前文獻較少涉及的。下面,筆者通過借構建模型,分析供求結構與產業升級的關系,解析“低端鎖定”現象產生的內在機理。
四、模型的構建與分析
1、幾點假設
假設1:社會總收入只用于消費和儲蓄;儲蓄全部用作投資。即有Y=C+S=C+I。
假設2:國民經濟由兩個部門組成——生產部門和研發部門。生產部門包括生產高檔品的部門和生產低檔品的部門,社會從消費這兩種商品中獲得效用;投資分別進入這些部門并形成產業資本。即有C=C1+C2,其中C1為即期全社會對高檔品的總消費,C2為即期全社會對低檔品的總消費;I=IS+IM,其中IS為即期對研發部門的投資,IM為即期對生產部門的投資;IM=IM1+IM2,其中IM1為對生產高檔品部門的投資,IM2為對生產低檔品部門的投資。
假設3:資本無折舊,投資為資本增量。即有I=K',IS=K'S,IM=K'M=K'M1+K'M2。
假設4:社會總收入相當于社會產出總值,即有Y=Y1+Y2,其中Y1為高檔品部門的產出總值,Y2為低檔品部門的產出總值;產出總值與產業資本成線性關系,高檔品生產受技術加成,低檔品則不受技術加成,即有 Y1=dAKM1,Y2=dKM2,A=wKS,其中 A 為技術水平,d、w為常數系數。
假設5:社會具有穩定的平均消費傾向,即有C/Y=p,p為常數;市場完全競爭,生產部門依據即期消費變化調整產業資本,即有K'M1/KM=C'1/C1,K'M2/KM2=C'2/C2。
定義:需求結構 α=C1/C,生產結構 β=Y1/Y,資本結構 γ=KM1/KM。
從非技術層面判定α、β、γ變動趨勢及動因
對 α、β、γ 進行一階求導, 得到:α'=α (1-α)再進行二階求導,可得到:

(1)α'>0,β'>0,γ'>0
(2)當 α≤0.5,β≤0.5,γ≤0.5 時,α''≥0,β''≥0,γ''≥0;當 α>0.5,β>0.5,γ>0.5 時,α''<0,β''<0,γ''<0。
根據以上性質,得到下圖1:

圖1 情形一:生產結構沿產業升級路徑調整
由圖1可知,產業升級意味著需求結構、生產結構和資本結構的同路徑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保持此演進路徑需要滿足條件,通過數學演算可以得出該條件等同于.這說明在產業升級路徑下,經濟總量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率,此速率至少應當快過低檔品需求的增長速率,否則國民經濟有可能脫離產業升級路徑而陷入“低端鎖定”,如下圖2所示

圖1 情形二:生產結構沿低端鎖定路徑調整
2、從技術層面考察α、β、γ之間的關系及其影響因素
由于 Y1=dAKM1,Y2=dKM2,A 還可以理解為高檔品生產中生產技術貢獻與低檔品生產中生產技術貢獻之比。當高檔品生產中生產技術的使用相對于低檔品生產更有效率時,生產結構相對于需求結構會更高,反之則更低。所以,如果一國高檔品生產相對于低檔品生產在技術上是無效率的,那么該國的生產結構相對于需求結構就會低端化,國民經濟陷入相對的“低端鎖定”狀態。
五、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認為,生產結構的調整路徑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非技術層面上,主要取決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與高低端產品的需求增速的關系;技術層面上,取決于生產技術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相對效率。當經濟增速高于低檔品需求增速而低于高檔品需求增速時,生產結構沿產業升級路徑調整;當經濟增速低于低檔品需求增速而高于高檔品需求增速時,生產結構沿低端鎖定路徑調整。從技術使用的角度看,當高檔品生產中生產技術的使用相對于低檔品生產更有效率時,生產結構相對于需求結構會更高,反之則更低。 可見,要實現一國的產業結構升級,要么高端品生產部門的技術使用實現突破,要么一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需在一定區間范圍內,否則很可能會陷入低端鎖定的狀態。那么,這樣一個區間又是如何確定的?
林德模型認為,一國對產品技術復雜度的需求水平與其人均收入水平正相關。具體而言,當人均收入處于較低水平時,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經濟對低技術產品的需求也會增加,直至超過某一人均收入臨界點,隨后,經濟對低技術產品的需求開始下降,對高檔品的需求上升,當低檔品的需求下降到一定水平時,經濟開始偏向生產高技術復雜度產品,此時經濟因需求的變動完成產業升級。但是林德并沒有具體闡述生產結構與需求結構之間的動態關系,也沒有考慮資本投入的問題,技術在不同部門之間相對使用效率也并沒有考慮到。從這個角度看,本文給林德模型提供了很有力的補充,而林德模型也給本文的結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結合林德模型和本文的結論看,如果一國經濟高速增長,而人均收入處于較低水平時,經濟的增長所帶來的收入增長效應主要帶動了低檔品需求的增加,此時經濟的高速增長可能伴隨著對低檔品需求的高速增長,經濟增速可能因此低于低檔品需求增速而進入低端鎖定路徑。這與我國近幾十年的產業升級狀況相符,即經濟雖然處于高速增長路徑,產業卻沒有順利完成升級,全要素生產率仍處于較低水平。
本文還認為,一國生產的技術應用的相對效率與產業升級密切相關。如果一國的技術應用在高端產品生產部門相對于低端產品生產部門是低效率的,則生產結構相對于需求結構就會低端化,經濟陷入相對的“低端鎖定”狀態。我國研發資本一直處于高速增長的狀態,但對產業升級卻沒有明顯促進作用,原因或許在此。一方面,跨國公司對其核心技術嚴加管理,嚴格控制其外溢效應,其生產技術在國內扎根不深;另一方面,本土公司雖然有技術創新與技術改進,但其在生產中的應用仍多是粗放式的,技術應用的效率不見得比傳統產品的生產部門高。因此,產品生產結構難以跟上產品需求結構的步伐,經濟相對地陷入“低端鎖定”狀態。
針對這兩種狀況,首先,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以促進人們對高檔品需求的增長;其次,倡導企業在注重生產技術研發的同時,更應該注重生產技術效率的提高,即著眼于企業整體生產效率的改善。只有這樣雙管齊下,經濟才有可能擺脫“低端鎖定”,順利進入產業升級路徑。
[1]康志勇.稟賦結構、適宜技術與中國制造業技術的“低端鎖定”[J].世界經濟研究.2009,(1).
[2]時磊,田艷芳.FDI與企業技術“低端鎖定”[J].世界經濟研究 2011,(4).
[3]周勤,周紹東.產品內分工與產品建構陷阱——中國本土企業的困境與對策[J].中國工業經濟,2009,(8).
[4]李美娟.中國企業突破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的路徑選擇[J].現代經濟探討,2010,(1).
[5]劉維林.產品架構與功能架構的雙重嵌入——本土制造業突破 GVC 低端鎖定的攀升途徑[J].中國工業經濟,2012,(1).
[6]胡國恒.制度紅利、能力構建與產業升級中“低端鎖定”的破解[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3,(1).
[7]盧福財,胡平波.全球價值網絡下中國企業低端鎖定的博弈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10).
[8]趙夫增,穆榮平.全球價值鏈中落后國家的產業集群生命周期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07,(12).
[9]吳先華等.基于面板數據的世界主要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計算[J].數學的實踐與認識,2011,(7).
[10]郭慶旺,賈俊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1979-2004[J].經濟研究,2005,(6).
[11]江春等.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2000-2008[J].財經科學,2010,(7).
[12]劉建國等.中國經濟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分異及其影響[J].地理學報,2012,(8).
[13]張軍.資本形成、工業化與經濟增長:中國的轉軌特征[J].經濟研究,2002,(6).
[14]孫琳琳,任若恩.中國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J].世界經濟,2005,(12).
[15]涂正革,肖耿.中國大中型工業的成本效率分析:1995—2002[J].世界經濟,2007,(2).
[16]楊向陽,童馨樂.FDI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影響研究的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3,(3).
[17]Rodrik,D.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R].NBERWorking Paper( 11947),2006.
[18]邢玉升,曹利戰.中國制造業出口貿易的技術水平——測度與行業特征檢驗[J].東北師大學報,2012,(5).
[19]Schott.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6,(4).
[20]S.B.Linder.An Essay 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Wiley.1961.
[21]Wert,Frank S.Demand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A Modified Linder Model.Nebraska Journal of Economics&Business Spring78,Vol.17 Issue 2.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