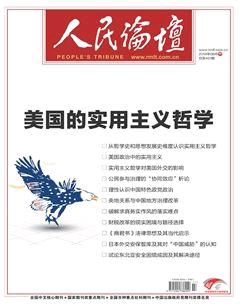人情社會與現代法治秩序重構
王 成
人情社會與現代法治秩序重構
王 成
一個良好的法治國家依賴于人民對法律的信仰,進一步深化法治改革,必須使法律觀念、法律意識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在中國“人情”社會里,我們需要的是人性化的法治。【
法治建設 人情社會 人性化法治
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明確將“法治”作為主題,表明黨和國家推動依法治國的信念和決心。理想“法治”社會里,承載著社會對人的價值的肯定,人民自由平等地生活在有序的社會生活之中。那么,進一步思考,現實生活中,我們需要的法治是什么?
人情社會法治建設需自上而下的改革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人情”社會。這里的人情,有兩方面含義:第一種含義,等同于“民情”,即治下之民的物質精神生活的好壞。另一種含義,指人與人之間交際所隱含的內在的感情,它構成人們互相交往的重要因素。這一感性化的特質在中國人的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周公旦“以人情視天命”、“天惟德是選”到儒家“以德治國”的政治理想,傳統儒家文化之下的“人情”因素在政治活動中影響甚是普遍。時至今日,這種“人情”依然“生機勃勃”,它已經被社會成員普遍接受,存在于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形成了中國人固有的民族特質。重人情、重人際、輕理性的處事原則和人際交往方式已在中國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并漸漸形成中國社會中固有的政治文化因素。而現代法治社會需要的是理性人在一定規則規范內從事的理性活動,這仿佛與我國傳統的文化基礎,與重人情的中國社會格格不入。反觀西方,法治信仰是西方法治社會的根基,即法治是人們可以以任何代價去追尋的理想,人們服從法律和法庭的裁判,是為了維護法治的權威,弘揚法治精神。蘇格拉底為維護法律的權威,曾甘愿接受不公平的裁判,這源于對法律的信仰。但同時,在西方社會,人民的理想力量要求世俗的法律和法庭也應以人們的法治理想為依據,從而實現自由平等的人生理想。通過比較發現,中西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國并不存在類似于西方的法治文化基礎。因此,處于現代化發展的中國,其法治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
四中全會開創法治改革 “新起點”
十八屆四中全會對于推動中國法治建設具有深遠意義。其一,會議明確了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將憲法作為立法的最高依據,突出憲法最高法律效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現實中,立法質量尚需提高,相關部門依據其私利濫用立法權力的現象屢見不鮮。提高憲法的權威,為規范法律體系,提高法治質量提供了基本依據。另一方面,目前存在許多行政權力來源不明,行政職權濫用的現象。憲法作為立法最高依據,對杜絕濫用行政權力,審查行政權力實施具有重要作用。其二,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有重要的引領作用。為此,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近年來,日益嚴重的司法行政化傾向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和司法不公的現象。因此,司法改革應盡可能地排除外界對司法實施的干擾。全會提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制度、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等,從制度因素和人為因素方面排除了對公平公正司法權的干擾。其三,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的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全會第一次提出將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法治應立于民之中,這對缺乏法治文化傳統的中國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深化法治改革,我們需要的是人性化的法治
縱觀中西方國家,一個良好的法治國家依賴于人民對法律的信仰。相對于中國,西方的法治較為成熟,而法治信仰是其重要的法治根基。但在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傳統中國,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影響之下,“人情”觀念極其濃厚。當然,在傳統的文化背景下,出于統治者根本利益的需要,法治觀念也會應運而生并獲得長足發展。在中國傳統治國思想發展中,大思想家荀子首次提出隆禮重法、禮法并舉,對中國法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說明中國傳統社會的“法治”已經認識到法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多是因事而作,它依賴于人的傳統與習慣。由此,法治的實施必定需要法的社會文化基礎。四中全會提出實現依法治國的目標離不開我國人情社會的文化基礎。但不能否認,目前我國社會文化基礎仍深受宗法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個人情社會。面對國情,我們應明確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人情”、“道德”在現代法治建設中具有其積極的意義。首先,“人情”是形成良法的淵源。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有賴于統治者重視體察民情,以民為本。良法的制定要體現人民的利益,而這需要從民情中發掘。其次,人情有利于形成法的親和力。法施之于民,人民的支持對于法的有效實施至關重要。但法不是萬能的,作為明確的文本規范,總有其不能涉及的領域。其所具有的強制特點極易造成人民日常生活與國家政治生活的距離,從而使得法律與大眾心理、社會習俗脫節。而人情因素可調節法的僵化與死板,人性化地宣傳實施法律,使得親和力的法更易于被人民所接受。此外,人情化處理糾紛的方式與人們的情感心理需求能保持一致,因此通過符合人情的方式所形成的秩序更為長久。以德治國作為依法治國的補充,在調節社會關系、形成良好社會風尚方面更是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其二,“人情”社會下,我們需要人性化的法治。“人情”體現人性,“人性化”的法治更易于與人情社會相溝通。人性本善,善的因素自古以來便成為中華兒女共同的心理信仰。孟子曾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的法治就是法治建設的目標。一方面,“善”的因素更易形成人民對法的信仰。另一方面,善體現對人性的關懷,對人的價值的肯定。人性化法治依賴于傳統政治文化基礎,深深植根于中國人民的文化觀念之中,這便需要我們積極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善端”,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服務。如前所述,四中全會所提出構建的法治國家屬于自上而下的權力主導的法治,是黨領導下各部門分工負責的協商的法治。這便說明了我們缺乏自下而上的人民法治意識和法治信仰。如此說來,充分發掘傳統文化的“善因”,培育人民的內心法治意識和法治信仰,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四中全會構建法治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縱觀我國法治建設發展歷程,切合中國人情社會,植根于人民意識中的法治建設可謂“任重而道遠”。當我們更深入思考中國需要的法治是什么之時,不得不面對我國人情社會中自下而上的法治意識缺失這一現實。但同時我們也擁有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其精華成分亟待我們去挖掘,相信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將會越走越好。
(作者為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張景林對此文亦有貢獻)
①陳剛:《法治社會與人情社會》,《社會科學》,2002年第11期。
②姚靜:《試論人情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作用》,《法學之窗》,2011年第2期。
責編/徐艷紅 美編/于珊
D920.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