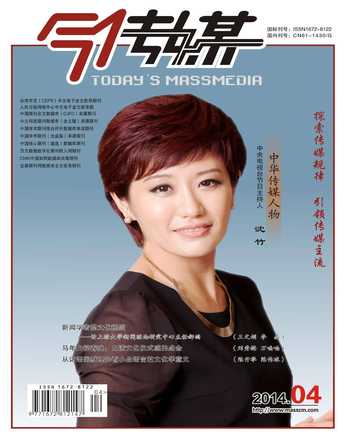解讀本雅明《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
高琳
摘 要:“技術(shù)之于藝術(shù)”是本雅明藝術(shù)思想的核心問題所在。本文對本雅明機械復(fù)制理論的重要著作——《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進行解讀,力圖建立對于其機械復(fù)制理論的客觀全面的認(rèn)識。解讀遵照了以下思路:機械復(fù)制藝術(shù)帶來了靈韻(Aura)的消失,但本雅明對復(fù)制技術(shù)表示了寬容和關(guān)照,肯定了復(fù)制技術(shù)對于藝術(shù)品新的意義。在技術(shù)變革的背景下,相關(guān)受眾關(guān)系呈現(xiàn)出了五個新的變化。
關(guān)鍵詞:本雅明;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靈韻
中圖分類號:J02 文獻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4-0149-03
本雅明在法蘭克福學(xué)派中可謂獨樹一幟,他針對現(xiàn)代藝術(shù)提出的機械復(fù)制理論,不再是單純的否定和批判而是富有技術(shù)樂觀的色彩,這是與阿多諾等代表的精英文化的立場所不同的。
目前,學(xué)界并不乏對本雅明現(xiàn)代藝術(shù)理論研究的新的路徑的探索,主要有1.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解讀,將馬克思主義思想與本雅明的現(xiàn)代藝術(shù)理論進行對照,如王雄[1]、羅良清[2];2.探討本雅明藝術(shù)理論與政治的關(guān)系,將政治作為本雅明藝術(shù)理論的出發(fā)點和歸宿,認(rèn)為本雅明對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的贊揚是寄希望于技術(shù)打破藝術(shù)壟斷,解放藝術(shù)生產(chǎn)、傳受過程中的受眾,促進受眾群體意識的形成并激發(fā)群眾的革命熱情,如溫恕[3]、王洪志[4];3.運用社會歷史分析方法,將本雅明的現(xiàn)代藝術(shù)理論放置于現(xiàn)代性社會理論中加以對照和解讀,如楊玉成、王春燕[5]。事實上,對于本雅明現(xiàn)代藝術(shù)理論來說,對“技術(shù)之于藝術(shù)”的探究是繞不開的。程惠哲[6]把這一問題的考察落腳在“技術(shù)與文藝的發(fā)展”、“技術(shù)與政治傾向”及機械復(fù)制理論上,王才勇[7]則將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為藝術(shù)帶來的三個變化總結(jié)為獨有的靈韻變?yōu)闄C械復(fù)制、膜拜價值變?yōu)檎故緝r值、美的藝術(shù)變?yōu)楹髮徝浪囆g(shù)。
在筆者看來,我們固然可以從本雅明的機械復(fù)制理論進行延展繼而得出更深刻的結(jié)論,但是,本雅明相關(guān)理論的基礎(chǔ)即在于對靈韻的解釋和靈韻消逝帶來的藝術(shù)品傳受方式的改變。因此,本文力圖回到原點,重新解讀本雅明《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以求對本雅明的機械復(fù)制理論有新的客觀全面的認(rèn)識。
一、靈韻的提出
對于機械復(fù)制理論理論出發(fā)點的解說,離不開古典藝術(shù)終結(jié)與現(xiàn)代藝術(shù)崛起這一時代背景。縱觀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軌跡,技術(shù)因素對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產(chǎn)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本雅明《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中提出的機械復(fù)制理論正是以此為起點,點出了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帶來的是藝術(shù)品的即時即地性(原真性)的喪失。他指出,在機械復(fù)制時代,藝術(shù)作品凋謝的東西就是藝術(shù)品的靈韻 [7],“靈韻”即“在一定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近之物的獨一無二的顯現(xiàn)”[7],筆者認(rèn)為,本雅明的“靈韻”(Aura)即是藝術(shù)品的這樣一個氣質(zhì)——時間和空間雙重維度上的不可復(fù)制性。
事實上,并不是本雅明創(chuàng)造了“靈韻”——Aura。早在19世紀(jì)末期Aura就已經(jīng)在被使用。德國文化團體“格奧爾格圈”(George-Kreis)即常用Aura一詞,如該派代表沃爾夫·斯凱爾稱之為“生命的呼吸”,并解釋說“每一種物質(zhì)形態(tài)都散發(fā)著Aura,它沖破了自己,又包圍了自己”[8]。
Aura在本雅明的公開發(fā)表的著作中至少出現(xiàn)過三次。一是在1931年的作品《攝影小史》中,本雅明用Aura來描述舊人像照片的獨有韻味,“一種特殊的時空交織物,無論多么接近都會有的距離外觀”[9]。而后本雅明在他論波德萊爾的專著《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書中,又用Aura來指稱與波德萊爾藝術(shù)相異的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特征:“無意識記憶中自然地圍繞感知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反應(yīng)的轉(zhuǎn)換上”[10]。但在《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中,雖然本雅明對Aura的定義仍是描述性的,但他無疑已經(jīng)賦予了Aura更加明確的內(nèi)涵。前人提到的Aura在含義上顯然與本雅明的觀點有所差別,但正是本雅明賦予了Aura新的含義,同時在理論體系中為其設(shè)置了新的位置。可以說,Aura是本雅明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
但是,本雅明自己并沒有給予“靈韻”以清楚的定義,他解釋的“靈韻”更像是一種佛教禪宗“頓悟”式的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感,這種感覺可以打動人心,使人陷入沉思,但受眾難以準(zhǔn)確地描繪這種感覺。綜合本雅明的表述,“靈韻”產(chǎn)生的條件是距離感和歷史文化背景,距離感是空間上的,歷史文化背景則指向時間,這共同構(gòu)成了“靈韻”時間和空間雙重維度上的不可復(fù)制性。本雅明強調(diào)藝術(shù)品問世的“即時即地性”,所以它在時間空間雙重維度上是獨一無二的,且唯有這種獨一無二才能構(gòu)成藝術(shù)品的歷史,組成藝術(shù)品的原真性。本雅明同時還強調(diào)了原作“靈韻”的不可接近性。受眾面對近在咫尺的原作也要從理智上保持距離,才能體會到藝術(shù)品的原真性和獨一無二,才能為其吸引和打動,當(dāng)藝術(shù)的獨一無二性開啟的距離越遠時,越會贏得人們的親近。
二、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帶給藝術(shù)品的兩個革命性變化
雖然本雅明點明了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帶來的藝術(shù)品“靈韻”的喪失,但并沒有為此而哀悼;他肯定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帶給藝術(shù)作品的革命性變化,復(fù)制品通過復(fù)制技術(shù)從傳統(tǒng)領(lǐng)域中解脫出來。但許許多多的復(fù)制品就取代了原本獨一無二的存在[7]。
本雅明率先在理論上肯定了現(xiàn)代藝術(shù)以機械復(fù)制為特點的生產(chǎn)和存在方式。首先,他肯定了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產(chǎn)物同樣具有藝術(shù)性:“它不僅能復(fù)制一切傳世的藝術(shù)品,從而以其影響開始經(jīng)受最深刻的變化,而且它還在藝術(shù)處理方式中為自己獲得了一席之地。[7]”本雅明認(rèn)可機械復(fù)制產(chǎn)物藝術(shù)性的基礎(chǔ)在于藝術(shù)品先天即具有復(fù)制性:在原則上,藝術(shù)作品總是可復(fù)制的,人所制作的總是可被仿造的。例如,學(xué)生在藝術(shù)實踐中進行仿制,大師為傳播他們的作品而從事復(fù)制,最終甚至還有追求贏利的第三種人造出復(fù)制品來”[7]。本雅明認(rèn)為,藝術(shù)品原作的權(quán)威地位是在與手工復(fù)制的贗品一同出現(xiàn)時才能獲得的,如果與原作進行對照的是技術(shù)復(fù)制品,原作和復(fù)制品之間并不存在價值上的區(qū)別,兩者是平等的。本雅明承認(rèn)藝術(shù)本身含有的技術(shù)的成分,但在本雅明心目中,并不認(rèn)為這些成分與那些非技術(shù)因素在價值上有何區(qū)別。更進一步,本雅明眼中的復(fù)制技術(shù)造成“靈韻”喪失的同時,也帶給了藝術(shù)作品新的內(nèi)涵:1.藝術(shù)品因技術(shù)獲得了新的內(nèi)容;2.技術(shù)為藝術(shù)品創(chuàng)造了新的時空。
(一)藝術(shù)品因技術(shù)獲得了新的內(nèi)容
本雅明在論證這一論斷時提出,技術(shù)復(fù)制比手工復(fù)制更獨立于原作。他舉例說,原作中存在著肉眼無法識別的部分,只有鏡頭可以捕捉,照相攝影使這些部分也得到展示和突出。而且鏡頭的存在帶來了拍攝角度的變化,這帶來了新的藝術(shù)內(nèi)容。此外,新技術(shù)還可以通過放大、慢攝等方法使人們獲取到肉眼不能獲得的形象。本雅明所舉事例成立的基礎(chǔ)在于,承認(rèn)攝影技術(shù)賦予了人全新的觀察世界和表現(xiàn)世界的能力,這一能力本身是不應(yīng)當(dāng)從價值上被貶低的。
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guān)系是藝術(shù)學(xué)乃至哲學(xué)的一個重要命題,“現(xiàn)實的那些非機械的方面就成了其最富有藝術(shù)意味的方面,而對直接現(xiàn)實的觀照就成了技術(shù)之鄉(xiāng)的一朵藍色之花”[7],本雅明的這一論斷最早是針對攝影技術(shù)而得出的,可以說,在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剛剛興起的時代,本雅明能夠?qū)夹g(shù)保持一種麥克盧漢“媒介是人的延伸”式的樂觀態(tài)度,尤為不易。而對于我們后人而言,往往卻是在《阿凡達》為代表的3D技術(shù)成熟之后才開始討論這一問題——足夠創(chuàng)新的形式本身是否就能夠為觀眾帶來全新的內(nèi)容體驗?
(二)技術(shù)為藝術(shù)品創(chuàng)造了新的時空
本雅明的靈韻關(guān)照了藝術(shù)品時空雙重維度上的不可復(fù)制性這一特殊氣質(zhì),也因此,他并沒有忽視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為藝術(shù)品消解時空唯一性的同時,創(chuàng)造了新的時空這一進步。
本雅明認(rèn)為,技術(shù)復(fù)制能把原作的摹本拓展上升到原作本身無法達到的境界。復(fù)制品依靠不計其數(shù)的量,將藝術(shù)品帶到了它本身無法到達的地方,從而賦予了藝術(shù)品原作完全不同的傳播力。本雅明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圣母像可以經(jīng)過流水線生產(chǎn),最大程度地突破空間,出現(xiàn)在每個人的書桌上;我們可以在臥室欣賞管風(fēng)琴演奏,而這原本是只有在教堂才能感受到的。在這里,本雅明肯定了技術(shù)帶來的進步——極大地增強了藝術(shù)品的傳播能力,藝術(shù)不再是特殊群體的禁臠,而可以完全屬于大眾。
三、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帶給藝術(shù)品和受眾新的意義
林賽·沃特斯表示,本雅明的研究路徑類似于古典藝術(shù)理論的先驅(qū)者亞理士多德,因為他從技術(shù)化的角度“像一個機械工那樣從最基本處出發(fā)來解釋藝術(shù)”[11],但不同于亞理士多德古典模仿說的提出路徑,本雅明在樂觀論述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引起藝術(shù)品“靈韻”消逝的基礎(chǔ)上解釋了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引起的現(xiàn)代大眾藝術(shù)接受方式的變革。
追溯歷史上的受眾對藝術(shù)原作的膜拜心理,本雅明認(rèn)為其根源在于藝術(shù)品與儀式的結(jié)合。“‘原真的藝術(shù)作品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價值植根于神學(xué),藝術(shù)作品在禮儀中獲得了其原始的、 最初的使用價值”[7]。他認(rèn)為,“現(xiàn)代大眾強烈要求物在空間上和人性上更易‘接近,接收一件實物的復(fù)制品就使其不再獨一無二”[7]。
首先,大眾對于藝術(shù)品存在著強烈的心理需求:通過占有一個藝術(shù)品的摹本或復(fù)制品來占有這個對象。在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之前的歷史中,人們面對的藝術(shù)作品繪畫、雕塑、文藝作品等由于技術(shù)的限制,“原真性”幾乎成了價值標(biāo)準(zhǔn)的首要標(biāo)準(zhǔn),對于經(jīng)典的藝術(shù)品,人們不得不賦予其崇高的地位,膜拜源于無法占有。可以說,大眾的心理需求正是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使用在藝術(shù)品身上的原因所在,復(fù)制技術(shù)滿足了大眾的接近愿望和占有欲。即便是保存在盧浮宮中的原作,現(xiàn)代人也可以通過復(fù)制技術(shù)方便地獲得復(fù)制品進行欣賞,于是藝術(shù)品的神圣地位被消解了,這固然使藝術(shù)品從被崇拜物淪為玩物,但也意味著藝術(shù)作品從禮儀的寄生中獲得了解放。“被復(fù)制品”從閉合的領(lǐng)域中被解放出來,“復(fù)制品”以其獨特的方式代替了“被復(fù)制品”,于是“被復(fù)制品”的唯一性被減弱了。
另一方面,在人類藝術(shù)史上,藝術(shù)的形式與內(nèi)容一般是不可分離的。比如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中創(chuàng)作的天頂壁畫《創(chuàng)世紀(jì)》,莊嚴(yán)恢弘的西斯廷教堂作為《創(chuàng)世紀(jì)》的存在形式,本身也成為藝術(shù)內(nèi)容的一部分。但是在機械復(fù)制時代,技術(shù)進步使藝術(shù)的形式和內(nèi)容可以獲得很大程度上的分離:壁畫可以變成一張薄薄的照片,呈現(xiàn)在每個人的書桌上,教堂的因素被最大程度上消解了。
總之,充滿了儀式感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活動被局限在了藝術(shù)作品的內(nèi)容生產(chǎn)過程中,而復(fù)制技術(shù)通過海量的復(fù)制品數(shù)量使大眾也可以獲得對藝術(shù)品的“占有”,同時又能通過變更藝術(shù)作品的存在形式剝離其原本的不可親近性。藝術(shù)品創(chuàng)作之后傳播和大眾的欣賞過程中,原有的儀式和高不可攀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本雅明把藝術(shù)從高高的祭壇上拉回到了每個人的身邊。
對技術(shù)帶來的這種改變造就的深層意義,本雅明并未進行完整的表述,但筆者認(rèn)為,我們?nèi)匀荒軓谋狙琶鞯淖掷镄虚g把握他的思想指向。本雅明涉及到的技術(shù)賦予藝術(shù)品和受眾的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五點。
一是增強了藝術(shù)作品的公共性。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成為了大群體的欣賞娛樂對象,它取代了只能被某一個人或一些人觀賞膜拜的古希臘雕塑原作(當(dāng)然雕塑原作仍然可以通過機械復(fù)制,被更多的人以個人化的方式欣賞和解讀),這本身就是藝術(shù)品與受眾關(guān)系的進步。本雅明盛贊技術(shù)帶來的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以較小的成本領(lǐng)略到藝術(shù)作品的內(nèi)在價值。原本唯一的藝術(shù)品成為了大眾可以共享的存在,更多的大眾能夠有條件、有能力接觸到原本只呈現(xiàn)給極少數(shù)人的藝術(shù)作品,這同時造成了受眾群體規(guī)模的急劇增加。
二是豐富了受眾觀看的內(nèi)容。受眾觀看對象的豐富來源于是新技術(shù)背景下藝術(shù)品內(nèi)容的極大豐富。本雅明以攝影和電影藝術(shù)舉例來說明這一點:“攝影機憑借一些輔助手段,例如通過下降和提升,通過分割和孤立處理,通過對過程的延長和壓縮,通過放大和縮小進行介入。我們只有通過攝影機才能了解到視覺無意識,就像通過精神分析了解到本能無意識一樣。[7]”例如攝影技術(shù)的出現(xiàn),突破了肉眼對于繪畫的限制,即便是在在同一觀察視角下,攝影技術(shù)也可以提供肉眼無法看到的內(nèi)容細(xì)節(jié)。而通過特殊技術(shù)的運用,還能給予受眾肉眼無法到達的位置的觀看內(nèi)容,例如我們不能否認(rèn),從高空甚至太空對我們存在的世界進行觀看,其內(nèi)容不能通過藝術(shù)加工成為藝術(shù)。而且,新技術(shù)的應(yīng)用還能帶來現(xiàn)實世界時間流速之外的藝術(shù)欣賞,如高速攝影。
三是增強了受眾的主體性。本雅明肯定了受眾在藝術(shù)品傳播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受眾不只是被動的接收器,而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解讀能力。“大眾是促使所有現(xiàn)今面對藝術(shù)作品的貫常態(tài)度獲得新生的母體。[7]”人們通過個體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可以把在此排除的東西納入到靈韻這個概念中[7]”。本雅明不同于其他論者貶低大眾的欣賞能力的精英主義視角,也與早期傳播研究學(xué)者對受眾被動接受的觀點相區(qū)別,而是強調(diào)了受眾在獲取信息中的主體地位,認(rèn)為受眾可以通過自己對作品的加工解讀,賦予作品新的靈韻。一個圣母像,大眾既可以在教堂做禮拜時進行膜拜,可以擺放在書桌上借以獲取心理的寧靜,甚至可以作為布置居室裝修風(fēng)格的物件。
四是滿足了大眾新的欣賞習(xí)慣。本雅明認(rèn)為在復(fù)制技術(shù)手段的支持下,現(xiàn)代大眾對于輕松的愉悅觀賞有更迫切的需求,以便使自己在日常生活的壓力下可以通過對藝術(shù)品的把玩娛樂獲得放松,大眾對藝術(shù)品教育教化功能的需求下降了,娛樂消遣功能的需要上升了,“消遣性接受隨著日益在所有藝術(shù)領(lǐng)域中得到推崇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覺發(fā)生深刻變化的跡象”[7]。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并未對大眾消遣娛樂的需求進行批評,而是以一種泰然處之的態(tài)度加以冷靜描述,這與法蘭克福學(xué)派其他論者的態(tài)度是有鮮明區(qū)別的。
五是賦予了受眾參與藝術(shù)作品制作的能力。本雅明肯定受眾對于藝術(shù)作品同樣具有制作能力,“極其廣泛的大眾的參與就引起了母體的變化”[7],技術(shù)的發(fā)展與普及不但帶來了藝術(shù)品的生產(chǎn)方式的改變,藝術(shù)作品傳播范圍的擴展,引發(fā)了藝術(shù)作品欣賞消費模式的變革,也使讀者或受眾在藝術(shù)生產(chǎn)過程中可以與作者進行身份互換,文化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者和消費者也處于角色隨時互換的狀態(tài)。本雅明首先以電影制作為例說明這一觀點,在當(dāng)代電影的創(chuàng)作中,演員扮演的就是生活和勞動過程中的觀眾,而每個觀眾都有故事主角代入感的正當(dāng)心理訴求,會下意識地將自己的身份帶入主角的心理、行為和人生際遇之中。而且,本雅明著重指出了新聞出版中的作者與受眾的身份互換更加普遍,“隨著新聞出版業(yè)的日益發(fā)展,新聞出版業(yè)不斷地給讀者提供了新的政治、宗教、科學(xué)、職業(yè)和地方的喉舌,越來越多的讀者——首先是個別的——變成了作者。[7]”
《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作為本雅明機械復(fù)制理論的核心之作,本雅明最重要的論述就體現(xiàn)在解釋“靈韻”和“靈韻”消逝帶來的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但從其字里行間中,我們?nèi)阅馨盐账D對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進行更深刻的剖析:技術(shù)不僅改變了藝術(shù)的生產(chǎn)方式和接受模式,更重要的是技術(shù)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shù)的概念,進而顛覆了傳統(tǒng)的藝術(shù)觀。本雅明為我們構(gòu)建了一個由新技術(shù)崛起帶來的新的觀念,這種對傳統(tǒng)藝術(shù)的變遷和以此帶來的藝術(shù)本身性質(zhì)和功能的變化的研究是富有啟發(fā)性的。我們身處以媒介技術(shù)變革為先導(dǎo)的文化生產(chǎn)方式極具變化的時代,有鑒于藝術(shù)產(chǎn)品與媒介產(chǎn)品等其他文化產(chǎn)品的相通之處,本雅明對于藝術(shù)產(chǎn)品的性質(zhì)、生產(chǎn)模式、傳受關(guān)系的觀點對于其他文化產(chǎn)品的理論建構(gòu)無疑有著特殊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本雅明解讀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帶來藝術(shù)品靈韻消逝時,是從傳統(tǒng)時代藝術(shù)生產(chǎn)的儀式性入手的,如果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傳播的儀式觀[12]”進行考量,事實上機械復(fù)制技術(shù)對于藝術(shù)生產(chǎn)的儀式性并非只是簡單的消解,傳播技術(shù)的發(fā)展反而也同樣可以為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儀式構(gòu)建提供支持。2002年,國內(nèi)電視媒體對宋祖英維也納金色大廳獨唱演唱會的播出,就鮮明地呈現(xiàn)了戴揚和卡茨《媒介事件》中慶典(Coronation)、征服(Conquest)、競技(Contest)三種媒介事件范式中前兩種的意味。所以,如能對傳統(tǒng)藝術(shù)生產(chǎn)的儀式與現(xiàn)代藝術(shù)傳播中的儀式構(gòu)建進行對照,在筆者看來應(yīng)當(dāng)也是頗有研究意義的。
參考文獻:
[1] 王雄.論瓦爾特·本杰明的“藝術(shù)生產(chǎn)”理論[J].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人文·社會科學(xué)),1995(4).
[2] 羅良清.“異化理論”的文學(xué)化表達[J].哈爾濱學(xué)院學(xué)報,2002(3).
[3] 溫恕.從《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看本雅明的藝術(shù)生產(chǎn)思想[J].重慶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版),2004(3).
[4] 王洪志.“技術(shù)主義”政治詩學(xué)論綱[J].滄州師范專科學(xué)校學(xué)報,2005(3).
[5] 楊玉成,王春燕.本雅明論藝術(shù)現(xiàn)代性及其現(xiàn)代性社會理論之建構(gòu)[J].山西大學(xué)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00(2).
[6] 程惠哲.技術(shù)與文藝[J].文藝?yán)碚撆c批評,2003(1).
[7] (德)瓦爾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譯.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
[8] 趙勇.整合與顛覆:大眾文化的辯證法—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大眾文化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
[9] (英)伯格著.吳莉君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shù)[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
[10] (德)瓦爾特·本雅明.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11] (美)林賽·沃特斯.美學(xué)權(quán)威主義批判——保爾·德曼、瓦爾特·本雅明、薩義德新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
[12] (美)詹姆斯·W·凱瑞著.丁未譯.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