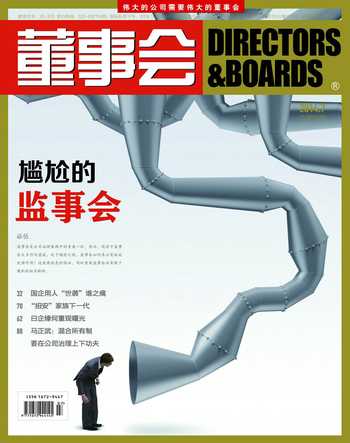虛擬運營商生存“陷阱”
李華國

去年年底,工信部正式發放首批移動通信轉售業務,包括話機世界、迪信通、樂語等在內的11家企業獲得首批牌照。截至今年5月,已有19家企業正式獲得牌照。在虛擬運營商牌照發放后,人們更為期待的是,虛擬運營商究竟何時落地,會對當前電信市場格局產生何種影響?
隨著阿里、京東等企業所謂的170號段套餐價格真正的公布,人們此前的很多期待瞬間消失了。即便是有蝸牛移動這樣宣稱采用互聯網思維顛覆傳統行業格局的企業,整個虛擬運營商市場帶給人們的卻更多還是失望。當前,雖然虛擬運營商們竭力在制造著一些差異化的“賣點”,但僅僅圍繞在資費的小幅調整上,沒有從根本上沖擊當前的通訊市場格局。這似乎與虛擬運營商誕生的初衷并不相符。
“虛熱”背后
逐利是所有資本共同的屬性。如果按照這一觀點衡量當前的虛擬運營商熱就會發現,不少人儼然將通信轉租當成了資本金礦。據工信部數據,到2015年年底預計我國移動轉售業務用戶將達到5000萬戶,占全國移動通信市場用戶總數的3%左右。雖然總體上占比并不高,但由于總量數額巨大,虛擬運營商市場依然非常可觀,這正是能夠吸引眾多企業紛紛進入這一領域的重要原因。
目前進軍電信市場的共有19家虛擬運營商,其中既有像國美、蘇寧這樣擁有“品牌、零售渠道、電商平臺”資源的企業,也有京東這樣的電商平臺,還有擁有硬件產品的企業。但無論是何種企業,其推出的虛擬運營商套餐卻沒有本質上的顛覆與創新,大都還是處在電信運營商分銷商的角色定位下。
仔細盤點已公布的虛擬運營商資費計劃可以發現,幾乎每個虛擬運營商都提出類似流量結轉、流量不清零、資費個性化定制等做法,并借此宣傳其資費計劃和流向服務差異化。而在進行新賣點宣傳的同時,虛擬運營商大都開始探索業務捆綁和交叉補貼的變化,在基礎業務上與原來業務進行捆綁,再用交叉補貼的方式把規模做大。
虛擬運營商們或許用一種全新的思維去做經營,這種經營體現在模式以及產品設計兩個層面。在商業模式上,免費模式的運用成為此輪虛擬運營商熱潮中的最大看點。如蝸牛移動推出的170“免”卡產品,對語音和短信等基礎電信業務全部免費,售卡價的全部收入(399元)體現在游戲增值服務上。在產品設計層面,用戶開始“自主”設計套餐,最大程度地體現了互聯網時代的用戶思維。阿里通信在放號前就通過微博造勢,發動人們參與其產品和套餐設計。
然而,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稱,目前虛擬運營商從三大電信運營商獲得的“批發價格”并不低,其中短信業務批發價為7分/條,流量業務價格在120元/GB,高于基礎運營商給予普通代理商的價格。從現階段來看,虛擬運營商的競爭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母公司的競爭,價格戰或將成為這個市場發展的主旋律。
因此從整體而言,虛擬運營商并未帶來預想中的徹底顛覆,一些“差異化”的做法還很容易被模仿。它們只是轉變成一個同質化的渠道分銷者角色,而這一角色顯然是缺乏競爭力的。
“退燒”之路
無論什么產業,只要是被一窩蜂式的產業資本或產業玩家集中發力,那么最終的結局很可能就是打碎重組,鋼鐵、光伏、水泥行業都是如此。如今,虛擬運營商存在著被產業玩家再次“毀掉”的風險,如果不能創新出差異化的發展路徑,虛擬運營商們自身的存在感將被電信運營商以及用戶所拋棄。
正如工信部電信研究院一位專家所言,轉售市場是規模化經濟,需要龐大用戶群才能實現盈利。但從國內現狀來看,受限于運營商高額的終端補貼和渠道傭金,各大轉售商在第一年內基本上無法實現盈利,起碼需要發展到80萬左右的用戶,才能在3—5年內實現正向現金流,5—7年內實現累計盈利。
由此看來,虛擬運營商們首先要做的就是積累用戶資源,但這種用戶積累不能是以簡單的資費價格戰進行,因為這一方式帶來的用戶資源是最不穩固的,一旦這種價格優惠消失用戶隨時存在著流失的風險。對虛擬運營商來講,比較可行的方式就是讓用戶參與到套餐設計中,就像阿里那樣,我們且不論其最終的真實性,僅僅是這種討論以及參與過程就會讓企業收獲很多用戶資源,這才是企業所樂見的。
在掌握用戶需求的同時,企業更應該做的是探索一種成熟的商業模式,而這個商業模式必定不能是基于燒錢基礎之上。從目前蝸牛移動的免費模式看,其未來依賴的盈利方式就是為用戶提供應用、內容等增值服務,通過這些增值服務收費而獲利,這或許是對未來發展模式探索的一個嘗試。當然,這其中還有企業既有線下的實體店優勢,也有網絡零售平臺的用戶資源整合,這些企業要做的不僅僅是整合用戶資源與探索商業模式,更重要的是充分結合自身的優勢,優化用戶體驗,通過全方位的體驗經濟去推動商業模式的探索與成熟。
對虛擬運營商而言,當前要做的不是一窩蜂地涌入,從而掉入同質化的發展窠臼,只能通過價格比拼去拓展市場。舍小利而謀遠,虛擬運營商們必須讓這場過熱的產業游戲“降溫”,在回歸理性后以成熟的模式驅動穩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