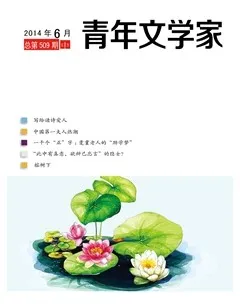試析舒婷詩歌的正能量及現實意義
摘 要:舒婷是朦朧詩派代表詩人,她的詩歌充滿了對真善美的摯誠追求,表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愛國愛民的情懷,及對愛情友情的熱情謳歌,即便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痛苦中仍懷揣勝利的信念,與同時代詩人對比中表現出充沛的正能量,在當今時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舒婷;正能量;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王彥,女(1964-),廣西灌陽人,廣西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大學語文、職業口才與文化禮儀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4)-17-0-03
舒婷是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從民間走上詩壇的朦朧詩派代表詩人,經歷過文革十年帶來的傷痛,可是她的詩作卻與同時期或其后的詩人有著很大區別。她的詩歌表現哀而不傷,字里行間透出的是包容,是寬恕,是母性,是優雅。這些詩句仿佛和煦的春風吹拂著每一顆受傷的心靈,安撫著人們心中的傷痛。舒婷詩歌的主旋律始終貫穿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愛,對光明和真善美的摯誠追求,透露著光明意識,散發著正能量。
“正能量”是一個心理學概念,英國著名心理學大師理查德.懷斯曼(Richard Wiseman)認為,“正能量”就是一切能夠給予人、激發人向上和希望并促使人不斷追求,從而使得人的生活獲得圓滿幸福的動力與感情。而詩歌的正能量無疑是詩人通過詩歌作品傳遞積極情感和情緒,從而激發閱讀者積極向上的情緒體驗,以實現人們精神生活的健康、愉悅、順暢、和諧的一種心理能量。對詩歌正能量的關注與研究,是很有意義的學術探尋與詩學追求,而對從十年動亂年代成長起來的詩人舒婷詩歌正能量的研究,尤其值得嘗試。
一、詩歌主題蘊含正能量
在中華經典文學寶庫里愛國恤民的篇章歷來為人們所稱頌,如“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些都為主流價值觀所肯定,是積極向上,充滿正能量的。而“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道德情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責任意識,“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氣節,都鼓舞、激發著人們的正面情感。如果把愛國愛民思想、道德操守、理想信念、責任擔當、民族氣節綜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中華民族詩歌的優秀傳統,而舒婷詩歌無疑是繼承了這種傳統的。
(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愛國愛民的情懷
舒婷的詩歌表達了對世界的認知和感受,抒寫了自己的生活體驗,雖然時代的累累傷痕,投射到她的詩歌中,有表現對生活無奈、憂愁與矛盾的詩篇,但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國觀念早已深入舒婷等人的血液,對社會的關注、對他人的同情憐惜,使得苦難中成長的這一代人擁有更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愛國愛民的情懷。
在《獻給我的同代人》中,舒婷勇敢地追求著“新理想”,因為這種追求人的價值,渴求真善美的理想,與祖國、民族、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為了民族、祖國振興,為了人民的幸福,包含著舒婷在內的一代人甚至不惜犧牲一切,表現了為“大我”的幸福而犧牲“小我”的決心。因而我們看到舒婷詩作并不沉湎于個人的傷痛,而關注的是他人的坎坷,國家民族的命運,從而更加大氣優雅,也更打動人心。
舒婷自己也說:“我的詩是積極的。”她用詩抒寫了對祖國的真誠苦戀,詩情柔曼憂傷,詩魂透明執著。在《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中,詩人娓娓訴說:“我是你十億分之一,……/我親愛的祖國!”而在《會唱歌的鶯尾花》中,她唱道:“如果子彈飛來/就先把我打中” 表現出為了祖國繁榮昌盛,為了光輝的理想,犧牲自我的決心,甚至當她這一代不能實現她憧憬的理想時,還希望下一代接班頂上:“我在防洪堤上/留下一個空出來的崗位讓所有沖擊過我的波濤/也沖擊你的身體吧/我不后悔/你不要回避。”(《遺產》) 別林斯基認為:“……不管祖國的情況怎樣,我們都不能不愛祖國:不過,這種愛情必須不是因陋就簡的自滿,卻是迫切要求改進的愿望, 總之,對祖國的愛必須同時也是對人類的愛。”(《別林斯基選集》二卷454頁)舒婷正是愛之深責之切,才有這“迫切要求改進的愿望”, “對于一個完備而又健康的人說來,祖國的命運總是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別林斯基選集》二卷454頁),她期待民族中興的愛國之心如金子一樣閃閃發光。她呼喚人的價值是對人類的愛,她企盼改革中興是對祖國的愛。在“憂國憂民”的詩情中,“美麗的憂傷”顯示出溫柔的魅力、明亮的色調。
(二)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痛苦中懷揣勝利的信念
十年浩劫是國家命運的逆轉,也使舒婷這一代年輕人經受了心靈的洗禮與考驗,原先狂熱追求的信仰被撕碎,理想無所依托,迷茫、痛苦、不滿和憤怒無處發泄,在新、舊時代交替,理想與現實矛盾沖突的大背景下,他們強烈渴望訴說他們的心聲,于是訴諸筆端,用詩歌來傾訴對理想與現實之間距離的思考與失落,來排解身處政治陰影還沒有完全消逝的年代中的壓抑與憂傷。而在這一代年輕人中,悲觀絕望者不乏其人,舒婷的可貴之處在于,即便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也從沒放棄希望。
舒婷的詩歌既不低順眼,自我放棄,也不大喊大叫,怨天尤人,而是柔中有剛,痛中存望,她在《致一一》中道出了心聲:“我是火,/我舉起火的旗子/引來春風/叫醒熱烈響應的每一株草/”。
她不是豪氣干云的英雄,但更不是逆來順受的弱者,舒婷優雅地展現著自己的悲傷,忍受著失望又懷著勝利的信念,在《海濱晨曲》中,抒情主人公雖然感到大海的怒吼來勢兇猛, “以雷鳴震驚了沉悶的宇宙”但始終堅信“我將在你的濤峰謳歌”,并且展示了“讓你的狂濤把我塑成你的性格”的堅韌不屈。而在《當你從我的窗下走過》這首詩中,詩人明寫燈還亮著,實際上表達的是希望、信念永遠不滅的堅強信念。
舒婷在《這也是一切》中吟道: “一切的現在都孕育著未來/未來的一切都生長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為它斗爭/請把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詩言志,我們從舒婷的詩歌中,不僅看到小女人細膩優雅的綿綿情思,其中不乏懷疑、痛苦、徘徊,更體悟到一個堅強女性的堅韌不拔,灑脫大氣,正如她自己所說“這世界上有沉迷的痛苦/還有覺醒的歡欣。”(《這也是一切》),她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沉緬于十年浩劫帶來的精神上的沉重負擔,心靈傷痛,而要向前看,努力地克服、戰勝自己的軟弱和疲倦,懷揣勝利的信念。
(三)對愛情友情的熱情謳歌
舒婷詩歌最柔婉、溫馨、動人的篇章,首先表現在對愛情的歌頌上,顯得既溫柔,又熱烈。如在《我愛你》中,詩人將“我愛你”三個字“用貝殼嵌成一行七彩的題詞”,讓所有看到它的人都被感動,從而“染上無名的相思”。而《無題》,詩人又將抒情主人公熱戀中的矜持、矛盾、敏感等心理刻畫得細膩入微,惟妙惟肖,使人獲得審美享受的同時,也感受到了愛情的美好迷人,在《雨別》中,“我真想拉起你的手,逃向初晴的天空和田野”的想象,表現的是與雨中痛苦別離截然相反的理想境界,體現出詩人對美好理想與愛情的追求。她還大聲疾呼:“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神女峰》),為婦女解放、為愛情自由振臂吶喊。在《致橡樹》中,她宣示了孜孜以求的是心靈相通,人格相映,生命旅程中分擔痛苦,共享歡樂的理想愛情,從而獲得女性的廣泛共鳴。
總之,她抒寫愛情中各種場景,有戀人間重逢的纏綿,離別的思念,等待的煎熬, 約會的甜密等等,表現了人類最真實美好的情感。
與之同時,友情也是她歌頌的主題。“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的生死與共,肝膽相照的美好情誼。“只要夜里有風/…… /兄弟,我在這兒”(舒婷:《兄弟,我在這兒》),表達了舒婷對互相支持、相互信賴、高度理解的友情的贊美。人是社會的動物,需要友情的溫暖,就像萬物生長需要陽光空氣一樣,而舒婷正是細膩地感受到人的這種內心情愫:“人在月光里容易夢游/渴望得到也懂得溫柔。”,舒婷用她溫馨的友愛之歌撫慰了人們的心靈,仿佛讓你沉醉于甜柔的月色。而舒婷之所以能寫出如此之多充滿愛情友情的感人詩篇,從她的真心告白我們可以感受到:“今天,人民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溫暖,我愿意盡可能地用詩來表現我對人的一種關切”,“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夠相互理解的,因為通往心靈的道路可以找到。”
二、與同時代詩人對比中顯現正能量
李白和杜甫同為唐代偉大詩人,毛澤東在評價李杜時,曾說,李白詩“奇異脫俗”,而杜詩“哭哭啼啼”不喜歡。憑毛澤東的文學造詣,對李杜詩歌藝術的成就是了然于心的,而之所以褒李白貶杜甫,從兩人的詩中可見一斑。杜甫膾炙人口的詩歌《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其風格的沉郁頓挫,確讓人心緒郁結;而李白詩《贈汪倫》,即使寫離別,也爽朗明快,讓人心情愉悅。詩風格調不同給讀者的感受迥異。因而李白詩正面表現多,杜甫詩負面揭露多,或者說,李詩更讓人愉悅、順暢、和諧,陽光、熱情,積極的正能量比較足,杜詩負能量偏多。也許,正是因為他們正能量的比例不同,毛澤東才會揚李而抑杜。
同樣,舒婷與同為朦朧派領軍人物的北島相比,如果說舒婷詩是旭日暖陽的話,北島詩則是當頭棒喝,舒婷詩更多表現的是愛,是對真善美的歌頌,北島更多表現的是恨,是以冷峻深刻的思想,以懷疑否定的態度,對假、丑、惡進行無情揭露。
恨是北島詩歌的主要基調,他恨的內容之深廣,恨的情感之強烈,對文革十年的現實社會秩序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之鮮明,從他的詩《回答》中就可看到,“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經歷了那個是非顛倒、真假難辨的社會,詩人對一切充滿了不滿和敵意,在他筆下“到處都是殘垣斷壁”,他的詩歌形象陰冷地令人顫栗,如他的詩歌《惡夢》,“惡夢依舊在陽光下泛濫/……沒有人醒來”, 在那冰冷得“又結起薄霜”的環境里,竟“沒有人醒來”。甚至在表達愛情的篇章里,都沒有花前月下、郎情妾意的美好和甜蜜,詩人描繪的是“即使在約會的小路上/也會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時/降落的冰霜”,(北島: 《愛情故事》)。詩人充滿了絕望和無奈,他在詩歌《一切》中深深嘆息: “一切都是命運/一切都是煙云。”
對當時社會的不公正、不合理和不人道充滿仇恨,使得北島詩歌充滿冷峻,缺乏暖色,讓人壓抑、窒息。可生活在同一時代,經歷過同樣命運的舒婷,卻給人帶來更多的溫暖和希望。
在《春夜》中,舒婷描寫的主人公有理想、有擔當,對時代遭際善于思索,對民族命運勇于承擔,對“友人”則滿懷情誼,真摯友善, 《雙桅船》一詩讓我們看到了詩人對忠貞愛情的歌頌,或者更可看作是對美好理想的執著追求,《陽光巖下的三角梅》通過對三角梅無私品德的贊美,實際上謳歌了雖經時代磨難,但對國家、民族忠貞不渝的年青一代,特別是《祖國阿,我親愛的祖國》中, 詩人直抒胸臆,既以拳拳的女兒心,掃描著祖國的貧窮與落后,表達著哀怨的深情,但更在沉迷的痛苦之后,表達出希望的歡欣,為實現這美好的希望,詩人表達了一種獻身的愿望,抒發了強烈的愛國之情和歷史責任感。
舒婷柔婉詩情中流露的對光明和希望的渴望,在娓娓傾訴中流淌的對真、善、美的執著追求,使欣賞者在真善美的詩意境界中愜意地徜徉、瀏覽,內心自然而然地經受了一次美、善的洗禮,經歷了一次審美的崇高享受。這種“善”的主題相對匕首,似乎更能改造世道人心。舒婷詩中充沛的正能量,比起如“匕首”的北島詩歌,對今天的社會更有意義。
三、當今時代需弘揚正能量
當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進入到關鍵階段,需要13億人民團結一致,攻堅克難,奮發向上。然而,我國目前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經歷著大變局,國內社會深刻變化,隨著對外開放不斷深入,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集中呈現,人們思想活動的多樣性、復雜性不斷增強,消極看待一切的社會思維有所抬頭,整個社會逐漸表現出失望的心態和一盤散沙的狀態。
社會急需要宣揚正能量,澄清模糊認識,從而引導社會情緒、社會心理朝著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正能量的文學藝術對世道人心的教化作用,就更為珍貴。舒婷及其充滿真善美的詩篇,在祖國民族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理應發出更璀璨的光芒,讓人們獲取更多精神營養,增強團結向上的力量。因而,研究探討舒婷詩歌的正能量,不僅是學術研究的需要,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舒婷.青春詩會[J].詩刊, 1980, (10)
[2]舒婷.青春詩會[J].詩刊, 1980, (10)
[3]丁宗皓.人格的界碑:北島的位置[J].當代作家評論, 1988 (4)
[4]劉德崗. 撼人的壯美與動人的優美[J]. 前沿, 200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