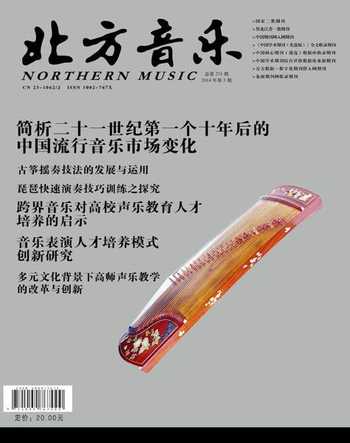淺議陜北秧歌的祭祀形態
崔珊
[摘要]陜北秧歌起源于儺祭,在社火和祈雨祭祀中傳承和發展,結合當地宗教信仰和地理環境逐漸形成了以謁廟秧歌、排門秧歌、轉九曲和二十八宿秧歌為主要代表的秧歌活動。文章初步分析陜北秧歌在表演過程中的祭祀形態,展現了其獨特的祭祀文化內涵。
[關鍵詞]陜北秧歌;祭祀;儺祭
一、前言
陜北位于黃土高原,土地貧瘠、氣候干燥、經濟落后、交通閉塞,形成了一個較為封閉的地域,正是在這種落后和封閉的環境中,陜北秧歌以及當地其他民間藝術,都保存著較為原始而古樸的風格,帶有明顯的祭祀色彩。陜北秧歌作為一種溝通人和神的民間藝術形式,吸引了大量的群眾參與其中,成為一種民俗性活動,它和當地百姓的風俗習慣、思想信仰等方面有著密切的關系。陜北秧歌是民族藝術的瑰寶,對陜北秧歌祭祀形態的探討,將對我們了解陜北秧歌的民俗文化有著極大的啟發作用。
二、祭祀與陜北秧歌的起源
有關陜北秧歌的起源,目前存在不同的說法,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儺儀祭祀在陜北秧歌的起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代生產力極度落后,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有限,往往會以敬神驅鬼的儀式以期消除天災人禍,稱之為儺儀祭祀,簡稱儺祭。因其儀式多為模仿動物跳舞,故稱為儺舞,并衍生出儺歌、儺戲等類目。儺祭的表層目的是驅鬼逐疫、除災呈祥,而其內涵則是通過各種儀式活動達到陰陽調和、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國富民強、人壽年豐和天下太平的目的。其人物扮相所佩戴的臉譜、面具殘存著儺祭的痕跡,使用的腰鼓、傘、虎撐等也來源于儺祭中的法器。
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生產由原始漁獵文明轉入農耕文明,土地成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基礎,為了達到風調雨順、農作豐收或驅鬼逐疫的目的,以“社火”祭地,“祈雨”祭天的祈禳性祭祀活動便產生了。據史料記載,“春‘鬧社火俗名‘鬧秧歌。村眾合伙于神廟立會,集資購置鬧時應用之衣服樂器,成班后,由會長率領排門逐戶跳舞唱歌,悉中節奏有古鄉人儺儀風。謂如是則本社本年不生瘟疫,并于元宵購放花炮可無雹災,頗著效。”這說明在古代已有排門秧歌習俗并頗具儺儀色彩,人們通過秧歌的表演儀式驅鬼逐疫,祈求福樂安康。到了宋朝百姓就已在立春之際組成社火舞隊,其祭社舞蹈與陜北秧歌舞蹈比較,也有相似之處。《村田樂》中社火人物形象,如貨郎、拉花、大頭和尚及蠻婆、蠻漢等在陜北秧歌中仍可見到。
此外,古代農業生產極度依賴氣候,而降雨更是重中之重。陜北干旱少雨,氣候干燥,每遇旱情百姓為求風調雨順,都會進行祈雨祭祀。據《神木縣志?藝文志》中記載:“秧歌唱共趁霄晴,客歲中秋夜月明。我道祈年還祝雨,入春陰雨最宜耕。”這就道出了陜北秧歌“祈年”、“祝雨”的目的。祈雨時祈雨者掛著鑼鼓邊擊邊跳,與陜北米脂縣的一種掛鑼鼓表演的秧歌非常相似,扭秧歌時兩手拿兩根筷子,以象征擊鼓。在舊秧歌詞中也有“掛鼓子的哥哥你別逞能……”這樣的句子,說明秧歌與祈雨之間的密切聯系。在祈雨祭祀中,降雨不受等級制度和社會貧富的制約,若祈雨成功百姓內心得到了“公平”的滿足,加強了對“神靈”的信仰,從而獲得直面自然災難的勇氣。
所以筆者認為,來源于儺祭的社火和祈雨祭祀是陜北秧歌的雛形,其主要目的是“娛神”,體現了早期表現形式。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歷史的進步,社火和祈雨祭祀中“娛神”的目的逐漸淡化,“娛人”目的逐漸增強,進而結合當地的多種藝術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民間藝術形式。而由于陜北秧歌是從儺祭中衍變、傳承和發展而來,所以其表演形式仍帶有濃厚的祭祀性內容和程式。
三、不同形式陜北秧歌的祭祀形態
(一)謁廟秧歌的祭祀形態
謁廟秧歌屬于神會秧歌,有著鮮明的祭祀目的。一直以來在榆林市榆陽縣保寧堡鄉和米脂縣郭辛莊,流傳著典型的謁廟秧歌。廟中常敬的神靈多以老君為主,也有土地爺、送子娘娘、龍王等。秧歌開始之前,先由族長率領大家去敬神燒香,族長向神磕頭、敬香、燒黃表完成祭祀禮儀后,傘頭再燒香磕頭。祭祀活動結束后,傘頭便即興創作唱詞,演唱符合神靈身份的秧歌,而隊員則在原地扭起“十字步”。待秧歌隊謁神完畢后,便開始在廣場上表演秧歌。村里的各家各戶也都要虔誠拜神,以求神靈對家人的庇護。這成為當地百姓的一種精神寄托,也是一種信仰表現。謁廟秧歌的唱詞也有很強的祭祀性,如拜如來佛唱詞是:“進得廟門一卜槐,槐枝槐稍掛金牌,金字牌,銀字牌,佛祖老穩坐蓮花臺。”這些唱詞由傘頭即興編唱,言簡意賅,朗朗上口,反映了舊社會陜北群眾祈求神靈庇佑,盼望五谷豐登的祈愿。
可見,謁廟秧歌是宗教儀式在民間的遺存,在肅穆的廟宇中表演秧歌,形成了一種固定而虔誠的拜謁儀式。另外,統治階級為了凝聚民心,在面對社會矛盾和自然災害威脅時,將宗教儀式融入謁廟祭祀,寄托于神靈佑護,起到抵御外侮、促進團結的重要作用。隨著社會進步,謁廟秧歌已從原始的以“娛神”為目的的祭祀活動,演變為一種“娛人”的儀式性舞蹈,帶有濃厚的政治文化意義和多種社會功能。
(二)排門秧歌的祭祀形態
謁廟秧歌結束后,秧歌隊會逐門逐戶給鄉親們拜年,這種形式稱為“排門”,也叫“沿門子”。百姓認為秧歌隊進院入戶吹吹打打、唱唱跳跳可以消災免難、驅邪避疫。秧歌隊進入后先鳴放鞭炮,主人、族長、傘頭等人互敬酒之后,傘頭便帶領秧歌隊扭大場。秧歌結束后傘頭便根據主家情況即興編排吉利之歌。如:“進得門來仔細看,這里住戶莊稼漢,掏溝洼,溜崖畔,黃谷打下幾十石……”秧歌隊在得到主人獎賞后,便進入下一戶繼續表演。受封建意識的影響“排門”順序也有講究,要按照先官后民、先富后貧、先南后北、先東后西的順序進行。在結束本村的排門拜年之后,秧歌隊還可以拜訪鄰村,稱為彩門秧歌。彩門秧歌是村際之間進行的禮儀性的拜訪活動,在村落之間的展示表演、一問一答中可以取長補短、相互學習,了解鄰村風土人情,以增進村落之間的友誼。
排門秧歌保留著上古百姓的驅鬼遺風,將祝福帶到各家各戶滿足百姓的需要。但是在封建社會下,為進一步強化封建等級制度和統治階級的權威性,排門秧歌因此而受到制約,講究根據當地住戶的地理位置、社會地位和門第高低進行。隨著社會的進步,現在的排門順序,由秧歌隊根據情況安排,挨門逐戶的向大家拜年問好。
(三)“轉九曲”的祭祀形態
米脂縣志中記載:“四、五、六三日,闔邑僧眾于十字街頭作齋醮;關城外以高粱桿圈作燈市娓曲迥環,游者如云,俗名‘轉九曲”。“轉九曲”民間又稱“轉燈”、“轉九曲黃河陣”,源于軍事布陣,后用于祀神。于正月十五鬧元宵期間舉行,群眾認為參加轉九曲可吉祥如意、消災免難。上燈時分,人們將九曲燈點著,共有九個小曲均設星君牌位,秧歌隊走在前面邊敲邊跳,從入門開始每至一門,傘頭都要即興演唱吉利秧歌:“秧歌進了東方門,東方星君來觀燈,今夜晚上觀了燈,十分的災星去了一分……”如踩斷繩索、破壞燈盞等,都是不吉利的象征。
陜北歷來是邊關重地,受古代排兵布陣的影響,轉九曲與其他形式陜北秧歌的隊形如“秦王亂點兵”、“霸王鼎”、“長城圖”、“盤腸大戰”等表現出軍事布陣的特點,類似于古代部隊的軍儺,作為尚武精神的贊頌。此外,九曲隊形含有道教陰陽五行八卦陣的特征,與佳縣白云寺流傳的道教祭祀活動“打醮”頗為相似。
(四)“二十八宿”秧歌的祭祀形態
榆林市佳縣沙坪村等地流傳著“二十八宿秧歌”。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有二十八宿的說法,傘頭為神權象征組成的二十八宿秧歌隊,具有古老的祭祀性質。傘頭扮成劉秀,執黃羅傘,后跟二十八員大將,執兵器、著戰袍、神情嚴肅、氣宇軒昂,似天神下凡。他們邊跳邊祈禱,以期五谷豐登、風調雨順。群眾認為劉秀是紫微星下凡,二十八宿都是天上的神靈,下凡輔佐劉秀推翻王莽政權。唱詞寫到:“五月里來五端陽,劉秀十二走南陽,姚期、馬武來救駕,二十八宿扎昆陽。”
據考證,二十八宿形成于戰國中期,既是天神的象征,也代表著人間的帝王將相。二十八宿秧歌是古代祭天儀式流傳下來的民間祭祀活動。它以漢光武帝劉秀為膜拜對象,是因為劉秀推廣儒家思想,以德治國,體恤民情獲得百姓擁戴,表達出廣大群眾希望得到統治階級體恤和神靈佑護的心愿。
秧歌的道具也有祭祀含義。關于所使用的傘有幾種說法,其一、古代先民認為太陽是至高無上萬物賴以生存的神靈,對太陽既崇敬又恐懼,于是模仿太陽形狀將傘做成象征物叫“日照”,意為太陽光芒四射,結構為直徑50厘米的流蘇傘。宗教祭祀活動中常把它作為神權象征由執事者舉著,象征陽光四射普照萬民。其二,古代帝王將相出行常打的黃羅寶蓋傘,形狀比“日照”大,“在傳統的二十八宿秧歌中,傘頭扮成劉秀的形象,是權利、擁戴、保護的象征”。虎撐和蠅甩也都是娛神驅鬼的法器,與古代儺祭聯系密切。表演秧歌時傘頭右手執傘,左手拿虎撐或蠅甩,跟隨伴奏節拍用力轉動、揮舞,指揮秧歌和鼓樂隊。這些道具象征涵義豐富,在秧歌表演中必不可少。
四、結語
在陜北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的影響下,陜北秧歌受祭祀活動的影響衍化出多種表現形式。其中,謁廟秧歌在拜神謁廟時的表演,彰顯了百姓與神靈之間的崇奉與佑護關系,以及人與神之間的某種秩序化聯系。排門秧歌則類似于儺祭的驅邪儀式,保存著古代祭祀文化的殘跡遺俗。轉九曲則有軍儺的特點,體現出神靈與村民的一種互惠性的供奉關系。二十八宿秧歌則體現了百姓對神祗的崇拜和對皇權的擁戴,表現出獲得精神歸宿和得到生活救助的渴望。這些不僅反映了廣大群眾美好善良的意愿,也表現了民間世俗傳統的審美觀點。
如今陜北秧歌經過文藝工作者和廣大群眾的錘煉和再創造,其內容更加豐富、完整,已成為陜北當地傳統民間歌舞形式。隨著我國對傳統藝術重視程度的不斷增加,陜北秧歌也得到了推廣與宣傳,對這一中華民族文化遺產起到搶救和保護作用,也為豐富群眾文化生活,促進精神文明建設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2006年5月20日陜北秧歌經國務院批準納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廣大藝術工作者應當承擔起繼承和發展的重任,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