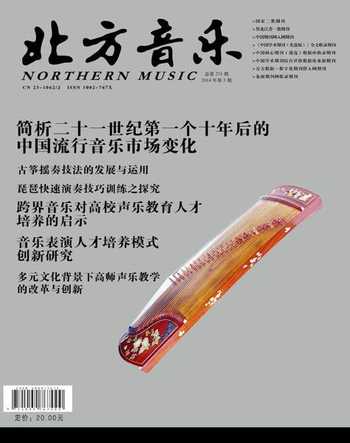戰火紛飛中的“天籟”之音
[摘要]2007年,廣州軍區戰士文工團話劇隊創作演出的話劇《天籟》,一經公演就引起強烈反響,一時之間,紅色話劇奏響“天籟”之音。獲得觀眾的肯定和好口碑之余,這部作品的榮譽也紛至沓來,榮獲國家文化部“紀念中國話劇誕辰100周年暨第五屆全國話劇優秀劇目展演”一等獎。紅色精神無疑是這部作品最動人之處,而這部話劇表現藝術上的獨特魅力也十分值得思考。
[關鍵詞]天籟;話劇;文藝;音樂視角
話劇是一種以對話為主的戲劇形式。雖然可以使用少量音樂、歌唱等,但主要敘述手段為演員在臺上無伴奏的對白或獨白。《天籟》和傳統意義上的話劇有很大不同,其中充斥著大量音樂元素和音樂類表現手段,如炮火中伴著快板的合唱、歌舞《打騎兵舞》、組曲《長征小調》,還有不時加入的配以背景音樂的人物旁白,旋轉立體的舞臺,這樣多姿多彩的表現形式非但沒有干擾或減損語言在該話劇中的表現力,反而和作品親密無間地融合在一起,讓這部話劇變得靈動起來,如行云流水般的天籟之音或激越或婉曲地流淌過觀者的心田,這是對傳統話劇一種大膽的突破。我們將從以下方面對這部話劇進行音樂視角下的解讀:
一、文藝戰斗方式的表現
劇中的戰士劇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最早的文藝團體之一、1933年成立于井岡山。劇社的性質是一個文藝團體,那就決定了文藝表演是劇社成員們最主要也最常態的工作、戰斗方式。《天籟》很多場景展現了戰士們文藝演出的情景,作品也借此表達了“戰地演出,是有著特殊意義的戰場”這一主題。劇作一開場就展演出一幅湘江戰役的戰斗畫面,這時出現了一段合唱和竹板書:
(合唱)哎呀來炮火聲來戰號聲打個山歌給你聽快跟敵人決死戰打到撫州南昌城哎呀來山歌來自興國城句句唱來感動人前方戰士更興奮更加有勁殺敵人更加有勁殺敵人
(竹板歌)說湘江道湘江英勇的紅軍來渡江不怕它水深波濤急不怕敵人逞兇狂鐵的紅軍勇難擋打得敵人叫爹娘為了戰略大轉移克敵制勝過湘江
這是對隊員們在硝煙彌漫的戰火中冒著槍林彈雨堅守在鼓動棚戰斗精神的一次生動刻畫。這樣的演出場景還有很多,如劇社轉移休整中進行的擴紅宣傳,進入藏區為藏民進行文藝表演,借助紅色宣傳為主力部隊籌集糧食,這當中出現了活報劇《救救童養媳》《打騎兵舞》等表演。其中的《打騎兵舞》,針對對敵軍騎兵作戰中戰士們打擊騎兵不得要領,朱卉琪聽從田福貴的意見,用載歌載舞的方式把打騎兵的技術要領編排到舞蹈動作里:
敵人的騎兵不可怕沉著應戰來打它目標又大又好打排子槍快放齊射殺我們瞄準它我們打垮它
我們消滅它無敵的紅軍是我們打垮了敵人百萬兵努力在學打騎兵我們百戰要百勝
這樣的演出形式既起到了鼓舞戰斗信心的作用,具有教育示范效果,觀賞起來又很有美感。
臘子口的國民黨守軍都是甘肅、寧夏等地的士兵,所以李槐樹、馬冀特地學習了當地的河州花兒在戰斗間歇演唱,以喚起守城士兵的思親情緒,起到瓦解敵方戰斗信心的作用:
叫一聲拔了命的尕娃娃,你在為誰賣命哩,屋里頭白了發的老母親(娘親),正在把你想著來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完成了二萬五千里的戰略大轉移。戰士劇社的隊員們也歷經千難萬險,終于跟隨大部隊到達陜北,在慶祝紅軍勝利會師的軍民聯歡會上,他們演出了自己編排的《長征小調》:
“十月里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于都河,古陂新田打勝仗。十一月來走湖南,宜臨藍道一齊占,沖破兩道封鎖線,嚇得何鍵狗膽寒。十二月里過湘江,廣西軍閥大恐慌,四道封鎖線都突破,勢如破竹誰敢當。一月里來梅花香,打進貴州過烏江,連占黔北十數縣,紅軍威名天下揚……”
每一段“長征小調”就如同一張富有詩味韻律的長征大事月表,生動記錄下紅軍當月的重要戰斗、重大事件和取得的重要成就。而演員們在呈現這些的時候使用的全是當年紅軍的原作,曲子用的也都是當年使用過的江西民歌、湖南花鼓、廣西民歌等民間小調,并用各地方言合唱、對唱、獨唱,結合舞蹈和快板書加以表現。
音樂和歌舞的出現,既是劇社隊員們戰斗豐姿的展現,又是對話劇對話表現力的有力補充,因為這些內容僅靠語言敘事表現不出來,這讓《天籟》這部宏場主旋律的話劇,比之于以往同題材的話劇作品少了些呆板的說教氣,而多了靈動性和活潑之氣。
二、背景音樂的穿插和鋪墊
雖然話劇是以對話為主的戲劇形式,但是它并不排斥音樂、歌唱,可是由于要給人物語言留出表現的空間,往往會在音樂、歌舞的擇取上很慎重。如《北京人》中烘托古宅的由小提琴營造出的幽幽之聲,再如《窩頭會館》當中不時響起的憂傷而低沉的口琴聲,音樂的采用都非常隱曲而謹慎,從來沒有一部話劇作品是像《天籟》這樣大量使用背景音樂而又不顯得贅余的。
隱密的綠色樹林,是戰士憩息的地方,比之于前一場湘江戰役的緊張激烈,這一刻的營地里顯得是那么的寧謐安詳。這時管樂響起,隱隱約約的還有早起戰士開嗓練唱之聲和著鳥兒的鳴叫。紅軍進入草地前,戰士們又圍坐在留聲機前預想著草地以及未來的戰略轉移生活:
藍天白云底下,一望無際的綠苗,綻放著黃色的、紅色的、藍色的野花,無數的蝴蝶在飛舞……
這里充滿著戰士們詩意的猜想,表現了他們的革命浪漫情懷;而舞臺即時轉入到雄壯的《國際歌》大合唱:
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這又抒寫了他們無比的戰斗豪情。可是草地的殘酷是朱卉琪他們遠沒有想到的:小魏打著竹板倒在了行軍路上,小陳為采演出化妝用的紅花陷進了沼澤,他們沒有看到想象中的綠草和花叢中飛舞的蝴蝶。但他們死去的生命卻化作了蝴蝶,在那片草地上快樂地飛翔。這一刻配合著戰士們在茫茫草地艱難跋涉的身影,肅穆而又沉重的背景音樂響起。
在作品中,背景音樂還很好地展現出人物的內心活動。當在劇社獲得人生尊嚴的周月兒被突然出現的那個她作童養媳時打罵她的丈夫整個攪亂的時候,憂傷的月兒看著那盲了眼還努力地磨著唱針的槐樹,欲言又止,她仰首望月,這時響起的琵琶聲,深深契合于月兒憂郁的心緒;月兒犧牲之時,緩緩撥動的琵琶之聲再度響起,伴著她最喜歡聽的《田園》交響曲,槐樹抱起月兒走向遠方。而在劇尾,當田福貴粗糙的手掌一筆一劃地觸摸著朱卉琪刻在泥土上那個“籟”字時,豪邁而又昂揚的信天游響起,和著粗獷而嘹亮的嗩吶聲撞進我們的耳鼓。旋轉立體的舞臺上,出現的是行走在長征路上的戰士們各種文藝戰斗身姿雕塑般的造像,柏崇新雄渾厚重的旁白音響起,作品的紅色主題在這一刻被演染到了極致。
三、推動情節、塑造人物性格
在《天籟》中,音樂不僅是戰士們戰斗方式的表現,而且在構建和推進情節方面亦起著重要作用。大多數戲劇作品的矛盾雙方是兩極對立面:破壞的和建設的,壓迫的和被壓迫的。而《天籟》雖然是紅色革命戲劇,但是戰爭的緊迫被處理成話劇的大背景:看作品,我們能真切感受到戰士們戰火紛飛中每一步艱難的跋涉,但是具體的戰斗場面并沒有出現在正面舞臺。話劇的戲劇矛盾是在出身不同、教養不同、性格不同但同為革命奮斗的革命戰友間展開的。最初他們有誤會,有沖突,最終則走向了理解、認同甚至愛慕。那么這一漸變過程中,化身在戰士劇社細節活動中的音樂元素起著推動作用。
如在對受傷戰士李槐樹的安置問題上,田福貴認為槐樹應該安置到當地百姓家中好好養傷而不是隨軍延置整個劇社的轉移速度,這種安排在周月兒和朱卉琪看來是極不通情理的,雙方發生爭執互不退讓,朱卉琪提出槐樹可以演唱山歌作為文藝戰士而繼續跟隨劇社,這時槐樹那嘹亮而又清厲的家鄉民歌響起:
當兵就要咯吱里咯當紅軍紅軍戰士咯吱里咯最光榮勇敢沖鋒把敵殺解放天下咯吱里咯窮苦人
槐樹的去留問題得到解決,但田福貴卻因為自己決策的受阻去找上級領導要求調離,他的“有情緒”也使得故事繼續向下發展。這樣的設計在周月兒的身上體現得更多。這個可憐的姑娘,過往的生活留下了太多痛苦的印跡,只有在部隊上她才感覺自己是像個“人”一樣地活著的。留聲機里緩緩流動的聲音給她帶來了無盡的安慰,她也把護衛留聲機當作自己的使命,并最終為保護留聲機英勇犧牲了。因為留聲機月兒還獲得了她從不敢想過的“愛情”,她保護留聲機時槐樹為她擋下了敵人射來的子彈,而她的愛情之花在照顧槐樹傷勢的過程中得以綻放,是留聲機架起了兩人情感的橋梁。
劇中,“音樂”消彌著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吸引著不同出身、不同個性的人們往一起靠近,最終凝聚成一股無比強大的力量。這在男女主人公的故事上體現得最充分。田福貴和朱卉琪的性格可以說是南轅北轍,但最終兩人從分歧走向相互認同并欣賞,還締造出一段愛隋佳話。田福貴是貧苦出身的戰斗英雄,田家20余口人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忍殺害,背負血海深仇的他疾惡如仇,性如烈火。他所認可的戰斗方式是在前沿陣地,在刀尖槍口。而留學蘇聯的朱卉琪是那個時代中國文藝精英的代表,她熱愛劇社,深諳劇社宣傳、鼓動戰斗的精神力量。當粗獷的田福貴以粗暴的態度來處理劇社事務時,二人之間生出很多的摩擦和誤會。不僅對文藝戰斗心存輕視,田福貴對上級要他帶領這樣一支隊伍很抵觸,處處感到別扭不痛快,而那個男人婆似的連打槍姿式都不對的朱卉琪讓他很不舒服。尤其是朱卉琪在謎語游戲中拿他的名字設謎引來大家伙發笑,芥蒂也似乎越來越深。田福貴甚至還想過把那個他看著完全沒什么用處的洋玩意兒——留聲機給扔掉,這當然遭到了以朱卉琪為首的戰士劇社全社成員的反對。可是隨著劇情的發展,這部留聲機潛移默化地成為他和朱卉琪還有其他戰士團結戰斗、情感凝聚的催化劑。他漸漸地明白了,留聲機就像他手中的鋼槍一樣,是劇社社員們戰斗的武器。他不由自主地被這支隊伍融化。留聲機的唱針壞了,他也加入到磨制新唱針的行列里;朱卉琪病倒后,他自覺地帶著文藝宣傳隊去演出,成長為一手拿著筷板打好文藝宣傳戰斗,一手拿著鋼槍打好軍事戰斗的全能型戰斗英雄,而朱卉琪也漸漸地被這個五大三粗的漢子吸引并為其身上的英雄之氣所傾倒。
像留聲機這樣的道具還有朱卉琪那副特殊的快板,快板本身是進行鼓動宣傳時再普通不過的一種節奏性樂器,但是朱卉琪的快板卻代表著她摯愛的兩位紅色伴侶。快板的一片,是湘江水畔犧牲的劉社長留給朱卉琪的唯一遺物。劉社長犧牲后,朱卉琪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帶領著戰士們繼續演出戰斗。后來田福貴補齊了這副竹板。可在臘子口之戰,田福貴掩護劇社突圍,朱卉琪再度面臨和戀人的生離死別。紅軍勝利會師,熱烈的歡慶演出之后,這個在演出中沉浸在為戰士們演出快樂而忘記所有的女性,在人群背后寂寂地輕撫著那副顏色不統一的快板流下淚來,只有這一刻我們才看到這個女戰士的真性情:堅韌倔強又柔情百結。人物性格借助于特殊音樂道具的前后穿插得到了飽滿的展現。
四、主題的烘托和升華
關于這部話劇的創作初衷,編劇唐棟曾這樣介紹,他想要借這部作品“濃縮戰士劇社在長征途中的生活,節選這段最能體現紅色文化的戰斗生活,從另外角度對長征作出新的詮釋:
‘長征不僅僅是軍事、政治意義上的長征,也是文化層面和民族精神的長征,是個人心靈史的長征。”對于《天籟》這個劇名,唐棟解釋說:“紅軍在長征中留下的聲音,它是最自然、最純凈美好的聲音。戰士劇社的歌聲、琴聲和竹板聲,還有他們的舞姿身影,都應當和長征本身一樣,永遠留在我們心中。”而在主題的烘托上音樂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朱卉琪和田福貴這一對紅色戀人間有一個非常浪漫的約定——教認一千個字:等沒有文化的田福貴認到第一千個字的時候,就是朱卉琪正式成為他女友的時刻。這一約定的所求在今天的婚姻觀看來是那么的簡單甚至有些草率,但這恰恰是紅色年代里人類解放事業追求者純美人性的折射。劇終,當傷愈歸來的田福貴要朱卉琪教他第一千個字時,朱卉琪指著留聲機要他仔細去聆聽,田神貴說留聲機沒有放唱片怎么會有聲音?朱卉琪告訴他:“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你用心去聽,它就會在你的耳邊響起:從江西、到陜北,一年來,一路上,我們唱出多少歌曲,我們宣傳了多少革命道理,這些聲音,留在了湘江赤水,留在了雪山草地,留在了紅軍戰士的心里,也留在了劇社每一個宣傳隊員的生命里。”朱卉琪用戰刀在地上深深地刻下了一個字:天籟的“籟”。天籟,原始義指自然界的聲音,物自然而然發出的聲音。如風聲、鳥聲、流水聲等,而人類的音樂之聲即是起源于對自然界聲音的模仿。話劇名為“天籟”,其意旨顯而易懂,劇中這聲音更指的是人類最普遍和最具代表性的心愿和情感:戰爭是人類沖突的最高形式,人們總是盡可能地消彌它,戰士劇社的隊員們不畏犧牲奔赴革命戰場最終的目的,還是消滅破壞和平生活的反動政府,消彌戰爭,解放全人類。為此即便流血犧牲,他們也一往直前。
劇中始終有一首流淌在戰士心底的旋律——《田園》交響曲,貧苦的農家姑娘周月兒、戰士馬冀、李槐樹……每一位隊員都被這首曲子深深吸引。對一首外國交響曲衷愛若此,這對于沒有機會接觸西方文藝甚至連文化都可能不多的周月兒和戰士們來說顯得有點不可思議,其實是《田園》交響曲表達的人類的共同情感讓戰士們在聽到它時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完成于1808年的《田園》交響曲,是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寫成這部作品的時候,恰逢貝多芬雙耳失聰,這部作品表現的就是他在這種情況下對大自然的依戀之情,“初到鄉村時的愉快感受”,“溪邊小景”,還有那“暴風雨過后歡樂和感激的心情”等等,整部作品細膩動人,樸實無華,寧靜而安逸。聽這樣的曲子很自然地會使人們感受到投身到大自然后的喜悅心情。戰士們衷愛《田園》交響曲,并被它深深地吸引,其實是對田園幸福生活的向往,正如田福貴所說,“革命勝利了,他不會變,他的理想是回到老家種地然后和自己的愛人生兒育女,回歸平靜的田園生活”。那么話劇《天籟》除了對紅色精神進行華美的抒寫和歌頌之外,更高層次的希冀是表達對人類和平生活的向往,紅軍官兵不管是識字的文化精英還是不識字的普通戰士,心中都有這樣一個對美好生活的理想,這也就是他們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歲月里不畏犧牲前赴后繼的原因和目的所在。
通過分析,可以說“音樂”既是話劇《天籟》的呈現內容和表演方式,同時亦是這部話劇的精神主題之一、從音樂元素采擷尺度的拿捏到巧妙融合進故事情節的安排,最終做到為對話錦上添花而非喧賓奪主,這部作品的成功之處很值得我們今天的話劇創作者細心研習。
作者簡介:李小虎(1977-),男,甘肅定西人,天水師范學院音樂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中國音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