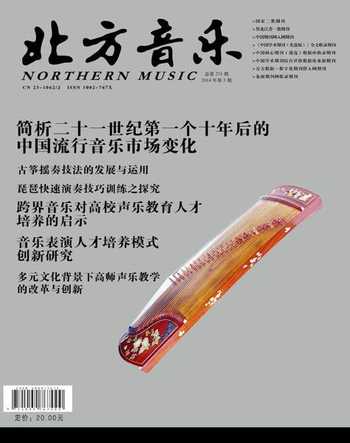從京劇現代戲《智取威虎山》的音樂改革看樣板戲現象
[摘要]京劇現代戲《智取威虎山》是我國京劇音樂改革史上的著名劇目,它在唱腔設計、板式創新、音樂編寫和樂隊改革等方面,均取得了明顯進步和巨大成功。文革期間,江青一伙對包括該劇在內的諸多音樂戲劇作品的“閹割”和“強奸”,既給它帶來了許多甚堪思量的嚴重戕害,又使它得到了最廣范圍的流傳和最大影響的發揮,從而造成了我國當代音樂史上頗令人費解的所謂“樣板戲現象”。
[關鍵詞]京劇現代戲;智取威虎山;音樂改革;樣板戲現象
“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以下簡稱《智》劇)是我國廣大群眾極為熟悉的一部戲曲音樂劇作,它和其他所謂的“革命樣板戲”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曾經十分活躍,客觀地說,它們也的確贏得了廣大聽眾的喜愛。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初的20世紀80年代,這些劇目曾一度消失,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它們在90年代中后期,又陸續恢復了上演。這一看似簡單的現象,其實隱含了一些令人頗費思量、甚至難以理清的棘手問題。所以,在新世紀業已來臨的今天,我們很有必要對這些劇目及其相關問題做一客觀、深入、嚴肅、認真的學術審視和理論總結。而選擇《智》劇作為切入點,是因為它各方面的遭遇及其在戲曲音樂改革上的成就,大可作為“樣板戲”的代表。
一、《智》劇的兩個版本
《智》劇是上海京劇團根據曲波的小說《林海雪原》及同名話劇集體改編創作的,初演于1958年,1964年6月曾參加在京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獲得了較大成功。這時參與唱腔設計與音樂編寫的主要有李慕良和劉如曾等,而這個出現于“文革”之前的所謂“京劇現代戲”,即為江青等人染指之前的原版《智》劇。
“文革”初期的1966年底至1967年初,江青一伙把包括《智》劇在內的《紅燈記》《沙家浜》等“革命現代京劇”,連同《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革命現代舞劇”,以及所謂的“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等8部不同種類的戲曲、音樂作品,一起竊為己有,并炮制了所謂“革命樣板戲”的稱謂。在組織專人對上述作品進行了大肆篡改后定稿,并將它們拍攝成了電影舞臺藝術片。而這個當時無處不有、無時不在的影片或錄音中的“革命樣板戲”,即為江青一伙“閹割”或“強奸”了的篡版《智》劇。
二、《智》劇在戲曲音樂改革上的經驗和教訓
(一)深入學習《智》劇在戲曲音樂改革上的經驗
通過以上回顧可以看出,《智》劇,尤其是原版《智》劇,首先是廣大戲曲和音樂工作者嘔心瀝血的藝術結晶。所以,我們必須深入學習包括《智》劇在內的所有樣板戲劇目在音樂方面,尤其是京劇音樂改革與創新方面的可貴探索和巨大成功。因為它們首先是廣大戲曲和音樂工作者在艱辛的藝術生產實踐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
1.認真學習、深入鉆研京劇藝術的傳統,掌握其神韻與精髓
古老的京劇藝術,程式嚴謹、博大精深,想要在保持京劇傳統神韻的基礎上,對京劇音樂進行成功的現代化改革與創新,就必須通過學習和鉆研,真正把握其音樂風格的奧妙、領會其精神內容的實質,才能確保“京劇姓京”,才能創作出既有傳統神韻,又有時代風采的京劇音樂。當時先后參與《智》劇唱腔設計與音樂編寫的李慕良、劉如曾和于會泳等戲曲、音樂工作者,不是長期從事京劇工作的行家里手,就是對京劇有著深入研究的音樂專家,他們的藝術生產活動,也從實踐層面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明證。
2.立足傳統的目的是為了突破創新,決不能反被傳統所累
《智》劇唱腔設計與音樂編寫的原則和方法,的確是以京劇音樂的傳統為基礎的,但又不受那些舊有程式和傳統套路的苑囿與束縛,堅持以表現現代生活和現代人物的時代風采為原則,選擇適當的腔式、板式、行腔和潤腔手法;唱腔設計與音樂編寫和劇本的創作同步進行,堅持從劇情、人物和表現內容出發,對全劇唱腔和音樂做總體布局,在保持京劇音樂傳統神韻的基礎上,借用、改造舊有程式,并對它們進行必要的發展和創造,打破傳統的板式組合與行當間的嚴格分工;借用我國其他劇種和民間音樂的傳統曲牌與慣用手法等等。如:《智》劇全部唱段的吐字、咬字和道白的腔調等,均采用了白話文與普通話的發音;第7場“發動群眾”中,李勇奇領唱、群眾齊唱的“春雷一聲天地動”一段,則明顯來自川劇“幫腔”的常見形式。凡此種種,均極大地豐富了京劇音樂的藝術表現力,尤其是使《智》劇唱腔與音樂的性格化和表現現代生活、現代人物的可塑性與適應性得到了甚為有效的加強。
3.選取著名革命歷史歌曲音調作為塑造音樂形象的基礎;采用主題貫穿發展等西方作曲技術來強化主要角色音樂形象的統一性
《智》劇中屢屢出現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主題,是楊子榮這個主要角色的音樂形象;劇中多次出現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主題,是參謀長這一角色的音樂形象;劇中還兩次出現了《東方紅》主題,它無疑代表了“黨中央、毛主席”的光輝形象。這些膾炙人口的著名革命歷史歌曲,流傳十分廣泛,為上述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令人易于接受的良好素材。而《智》劇獲得的巨大成功也證明了,對該劇人物形象的刻畫而言,主創人員選擇的上述歌曲是極為恰當的。
《智》劇的主要音樂形象,作為類似于主導動機的“特性音調”,幾乎從頭至尾地貫穿在該劇的始終,為全劇音樂的統一提供了最好的技術保障。上述楊子榮和參謀長的音樂形象自不必說,座山雕等土匪角色的音樂形象也是前后統一、且多次出現的。不僅如此,在音樂編創的具體寫法上,也有主題貫穿式的典型運用:“打虎上山”一場“迎來春色換人間”一段唱的“迎來春色換人間”句,其編曲與配器手法簡練、效果尤好;在“計送情報”一場“胸有朝陽”一段唱的尾句,這一寫法的再次出現,起到了前后呼應的作用,效果甚佳。
4.按照科學系統的西方樂隊學的編制和寫法,創建新型的京劇樂隊
《智》劇所用的京劇樂隊,除了傳統京劇伴奏樂隊的“三大件”和打擊樂外,還引進了以單管制為主的各種規模與編制的中小型中西混合樂隊。前者“托腔保調”的傳統功能,在以為劇中人物演唱伴奏為主的段落中,得到了有效地發揮;后者則在以序曲、幕間曲、閉幕曲、場景音樂以及人物唱段的前奏、間奏和尾奏等為主的部分,得到了更大的運用。如“打虎上山”一場,大段的樂隊引子,極為形象地描繪出了冰天雪地的北國林海景象:急促的弦樂音型既是遒勁凍風的生動刻畫、又明顯來自戲曲音樂“緊拉慢唱”的常用手法;其間特別引人注目的圓號主題,英姿颯爽、雄勁穩健,更是將偵察排長楊子榮匆匆穿行于莽莽雪原中的英雄形象描畫得惟妙惟肖。前述“迎來春色換人間”句,對長笛、雙簧管、鋁板鐘琴和曲笛等樂器的選用極為恰當,其編寫也以極其簡練的筆觸,在轉瞬之間就傳神地勾勒出了一幅春回大地、冰雪消融的動人畫卷,從而引發出人們對最后勝利的美好憧憬和無限向往。在“夾皮溝遭劫”、“急速出兵”等場次的幕間曲,“發動群眾”一場的“急救音樂”和“沉思音樂”,“急速出兵”一場的“滑雪音樂”等場景中,也不乏這樣優秀的器樂段落。
《智》劇在京劇樂隊的創建和京劇音樂的編寫上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與廣大戲曲、音樂工作者(尤其是于會泳)在藝術上能動的創造性勞動是分不開的。如上所述,《智》劇使用了不同于單純傳統京劇伴奏樂隊的、按照西方樂隊學編制和寫法而創建的新型京劇樂隊。這種在傳統京劇樂隊基礎上引進了以單管制為主的各種規模與編制的中小型中西混合樂隊所演奏的京劇音樂,是按照科學系統的和聲、復調、織體和配器等交響化的西方樂隊寫法來創作的,定腔定譜并寫定總譜,在司鼓外專設樂隊指揮來統攝全局的音樂工作。凡此種種,都極大地加強和豐富了京劇樂隊的表現力,為推進戲劇沖突、烘托戲劇氣氛、刻畫音樂形象、描繪自然環境和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等,提供了多種音樂手段,為《智》劇音樂的成功,奠定了扎實的基礎。這種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也成為了樣板戲音樂的一大特色,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普遍歡迎和業內人士的一致好評,尤其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學習并大力繼承、發展。
(二)深刻汲取《智》劇在戲曲音樂改革上的教訓
我們還應看到,在當時的大背景下,《智》劇的編創在取得了戲曲音樂改革上的巨大成功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有以下弊端。
1.指導思想上的極“左”傾向,最終造成了“題材決定論”
在20世紀50、60年代“以現代戲為綱”、“大放現代戲衛星”,尤其是1963年12月毛澤東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舞臺做出批評,傳統劇、新編歷史劇等被當作牛鬼蛇神趕下舞臺的歷史背景下,《智》劇也無法幸免地顯示出極“左”政策的嚴重影響。如在題材內容上無視生活本身的無限豐富性,排除了現代題材、革命歷史題材以外的所有內容,從而具有了狹窄、雷同的片面局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非此即彼,根本不容許所謂“中間人物”的存在,從而表現出了單一化、極端臉譜化和正面人物形象“高大全”的不良傾向;在藝術表現上存在著公式化、概念化與標語口號式等嚴重問題;在劇詩和歌詞的創作上,也顯示出假、大、空、套的明顯不足等等。
2.在對待傳統戲曲音樂遺產問題上,暴露出簡單粗暴的過激態度
建國初期就已開始的戲曲音樂改革,一直受到來自政治領域的極“左”思潮影響,而不能客觀、公正、辨證、批判地繼承戲曲音樂的傳統遺產。對此,廣大戲曲音樂工作者早就發出了“京劇姓京”的必要告誡。《智》劇誕生于20世紀50、60年代之交的特殊時期,在前述的特定歷史氛圍中,其編創也主動而決絕地丟棄了某些京劇音樂的良好傳統。對傳統戲曲音樂的選擇、改造、發展和創新自然無可厚非,但若對其不加甄別地大量擯置,甚至全盤否定,則是我們極力反對的,因為這樣無疑會導致戲曲音樂傳統精髓和獨特個性的湮滅與喪失。
3.音樂風格上的“高硬快響”與具體寫法上的“貼標簽”
當時歌曲創作中大量存在的“高硬快響”等不良風氣,對音樂創作的其他領域發生了較壞影響,《智》劇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此種現象俯拾即是。器樂創作中大量存在的“貼標簽”手法,也在該劇中有所體現,如前述為表現“黨中央、毛主席”光輝形象,而兩次出現的《東方紅》主題,即是“貼標簽”手法的典型例子。二者皆為《智》劇在以音樂編創為主的京劇音樂改革上的明顯缺陷。
上述三個弊端,在原版《智》劇中就已不同程度地存在,而經江青一伙粗暴篡改后的所謂篡版《智》劇,在整體上“幫味”越發濃厚、“幫氣”更顯十足,故上述問題也就發展到了愈演愈烈的程度。若非《智》劇本身的唱腔和音樂還有許多成功之處的話,它就毫無價值可言了。
三、“革命樣板戲”與樣板戲現象
1964年6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出現了一批優秀的京劇現代戲劇目,其中的《紅燈記》《蘆蕩火種》(后改名為《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和《海港》5部作品,與同一時期出現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及所謂“革命交響音樂”《沙家浜》一起,在“文革”初期被江青看中,遂被冠以了“革命樣板戲”的稱謂,從此,這一稱謂便登上了中國當代音樂史的舞臺。1972年以后,陸續上演的《龍江頌》《杜鵑山》和《沂蒙頌》等劇目,使樣板戲的數目進一步擴大,到“文革”后期已有20余部之多。
這些音樂戲劇作品在“文革”期間的音樂文化生活中,確實取得了極為廣泛的社會影響,但因為它們與這場政治浩劫之間呈現出一種“扯不斷、理還亂”的特殊關系,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幾乎可以與“文革”劃上了等號,所以這些所謂“革命樣板戲”的音樂戲劇作品的理論和實踐,便在中國當代音樂史上寫下了甚為奇特的一筆,引起了許多音樂界人士廣泛而持久的爭論。今天,我們把這些音樂戲劇作品和由此引發的各種音樂文化現象,統稱為“樣板戲現象”。
四、我所主張的對樣板戲的態度
(一)正確認識樣板戲與江青的關系
由于樣板戲具有“欽定”的特殊身份,“四人幫”又采用了行政手段強令群眾反復聽、看,所以導致了人們的強烈反感,當時民間就曾流傳著“八億人民八臺戲”的俏皮話,以諷刺“四人幫”統治時期的法西斯文藝政策。尤其是在樣板戲音樂永無休止的聒噪聲中遭到無數批判和迫害的許多善良的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把樣板戲與“文革”聯系在一起,把樣板戲當成了“文革”的一種特殊標志和音響符號,甚至干脆把樣板戲與“文革”劃上了等號,所以對之深惡痛絕并徹底否定。對此,我們深表理解,但一旦上升到學術層面來討論,我們就不能對樣板戲作出簡單的全面否定的評價。
樣板戲出現于“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間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江青為了達到其個人目的,炮制出所謂“革命樣板戲”的稱謂,
“四人幫”及其爪牙對第一批8部樣板戲的大肆篡改與公開掠奪、對后續樣板戲創演的全力支持與鼓噪吹捧,雖假借了所謂“戲劇革命、音樂革命”的名義,但其真實目的則在于為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野心撈取政治資本,實際上是對文藝作品,尤其是對上述第一批8部樣板戲的一種利用和“強奸”。不可否認,江青一伙對樣板戲編、改、演、傳的支持,始終是不遺余力的,但必須認清的是,他們對樣板戲的“用心”如此“良苦”,絕不是對我國當時音樂文化事業的真正關心;而林彪、康生及“四人幫”御用文人吹噓,8部樣板戲是江青從事“文藝革命”的結晶、是她“親手抓出來的”,則更是一個彌天大謊,是對廣大文藝工作者辛勤勞動的一種公開掠奪。所以,在討論樣板戲現象時,我們必須界定清楚的是,樣板戲首先是廣大文藝工作者藝術生產勞動的結晶。
既然樣板戲首先是廣大文藝工作者藝術生產的結晶,那么我們就應該對其中優秀的、有價值的東西進行必要的學術意義上的梳理、總結、研究和繼承,絕不能因為樣板戲(尤其是上述8部)曾經受到過江青的利用而把它一棍子打死。新時期以來,樣板戲的一度消失和近年來的再度上演,除滿足了廣大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變化以外,還反映出我國整體音樂環境的發展已開始走向了健康、有序的良性軌道——寬松的社會、政治空氣,廣大人民的需要,及音樂界有識之士的研究和呼吁等,已使今天的人們能夠較為冷靜而客觀地認識、看待樣板戲這一奇特的音樂文化現象了。
(二)京劇現代戲和現代芭蕾舞劇的出現是歷史的選擇
古老的東方戲曲京劇和西方芭蕾舞劇,都是擁有著悠久文化積淀的高雅藝術品種,在其數百年的發展歷史中,曾涌現出難以計數的大師和杰作。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人們審美心理的更迭,二者漸趨固定的藝術程式和較為明顯的舊時代印記,已逐漸遠離了人們的現代生活,尤其是不能滿足新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建國后,黨和政府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制定的文藝路線,努力貫徹“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和“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原則,積極鼓勵廣大文藝工作者進行包括戲曲改革在內的各種文藝形式的藝術創新活動。而上述8部樣板戲,也的確是在江青染指之前就已登上了當時的音樂舞臺,并在運用嚴謹、古老的京劇和芭蕾藝術表現現代生活,尤其是表現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斗爭歷史方面,做出了大膽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特別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紅燈記》《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等劇目,均成為我國在這兩方面的優秀代表作品,它們在當時和隨后的音樂文化生活中,都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所以,我們應該看到,任何一個藝術品種的產生、發展、演變等進程,除了整個社會、政治的影響之外,廣大觀眾的需要及其自身藝術規律的內在要求,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京劇和芭蕾藝術在我國發生的、具有當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變革,絕不單單是行政指令措施的結果,歷史的大潮波濤洶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而京劇現代戲和現代芭蕾舞劇的出現,一定有著其歷史必然性的一面,這絕不是憑任何個人的主觀好惡就能夠改變的歷史趨勢。
(三)認真總結并深入學習樣板戲的音樂經驗
誠然,由于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尤其是江青的粗暴篡改,導致樣板戲在整體上“幫味”濃厚、“幫氣”十足,顯示出了種種明顯的不足,甚至致命的缺陷。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無視樣板戲在音樂方面,尤其是京劇音樂改革與創新方面的可貴探索和巨大成功,因為它們是廣大戲曲和音樂工作者在艱辛的藝術生產實踐中取得的寶貴經驗。
(四)一分為二地看待于會泳的問題
原上海音樂學院教師于會泳,作為當時一名既對我國戲曲音樂有著深入研究,又具備現代作曲技術理論素養的音樂工作者,曾參與了樣板戲的唱腔設計和配器工作。從“文革”前《海港》的創作,到“文革”期間主持《智取威虎山》的修改,以及主持《龍江頌》和《杜鵑山》的創作等,于會泳曾在上述劇目中創作了《細讀了全會公報》(《海港》)《打虎上山》(《智取威虎山》)《家住安源》和間奏曲《亂云飛》(均出自《杜鵑山》)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經典唱段和器樂曲。其創作善于打破行當間的唱腔界限,在女腔中較多揉進生行的唱腔,使女腔既秀麗柔美,又剛健堅毅;能夠突破傳統唱腔程式的窠臼,如:改“眼起”為“板起”,突破七字、十字格式,故顯得層次更為豐富;主動運用各種轉調手法,除了較為傳統的四五度關系的調變換以外,還運用了同主音大小調和遠關系調的轉換,使京劇音樂表現劇情的自然環境和人物內心變化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在板式創新方面,也有“西皮寬板”、“反二黃流水”和“反二黃快板”等創造性開拓。這些都表現出于會泳所具有的傳統京劇音樂的扎實功底和他對京劇音樂改革與創新的獨到見解。所以,我們應該看到,于會泳首先是一個音樂工作者,他在京劇音樂改革與創新的工作中,的確做出了較大貢獻。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由于于會泳卷入到了“四人幫”的政治陰謀活動中,在被江青一伙提拔為文化部部長后,積極主動地配合、貫徹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政治罪行。但我們在研究、回顧“文革”期間的音樂問題時,不能因為于會泳在政治方面犯下了巨大罪孽,就忽略,甚至否定他在音樂上的作為;相反,我們更應該以人為鏡、以史為鑒,再不能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同樣錯誤,而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于會泳的問題,嚴格區分他在京劇音樂改革與創新上的藝術貢獻與他在“文革”中的政治罪行,適度地把握藝術與政治的辨證關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對待于會泳在京劇音樂改革與創新方面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甚至巨大財富,為我們今天的音樂建設事業服務。
(五)堅決擯棄毫無價值的所謂“樣板戲理論”
至于極其“神化”與“僵化”的所謂“樣板戲理論”,不是江青一伙自我吹捧的欺世盜名之辭,就是妄圖扼殺一切文藝創造的精神毒劑,非但沒有任何價值可言,而且在當時及隨后的各種文藝創作中,曾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消極影響。對此,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徹底否定并堅決擯棄。
五、小結
通過以上回顧、梳理,我們可以看出:《智》劇等第一批“革命樣板戲”之所以在運用嚴謹、古老的京劇藝術表現現代生活,尤其是表現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斗爭歷史方面,取得了巨大藝術成功、產生了廣泛社會影響,原因就在于它在唱腔設計、板式創新、音樂編寫和樂隊改革等方面,的確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創新和不同凡響的大膽探索。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并深入學習。但在學習的同時,我們還應堅持批判繼承與主動揚棄的思想原則,因為上述劇目,尤其是遭到江青一伙“閹割”的各篡版,也委實存在著若干弊端,對此,我們必須引以為鑒并盡力避免。
作者簡介:張學旗(1976-),男,河南開封人,臺州學院藝術學院音樂系教師,研究方向:音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