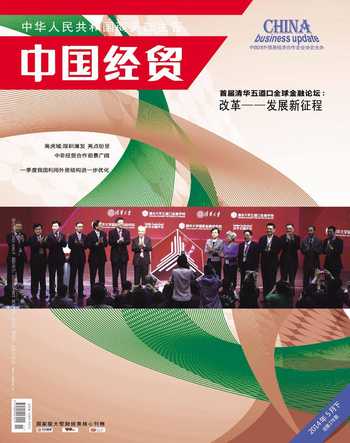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發展中農民工市民化的戶籍問題研究
黃雨艷
【摘 要】黨的十八大提出要走新型城鎮化道路,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解決城鎮化高速發展中的問題。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著重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人”是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和核心,“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實行不同規模城市差別化落戶政策。同時對未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建立居住證制度。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農民工;市民化;戶籍
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人”是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和核心,與以往城鎮化重在追求土地的城鎮化有著本質區別。2013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為136072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為73111萬人,城鎮化率為53.73%,比上年末提高1.16個百分點。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戶籍城鎮化率非常低,僅為27.6%。農民人戶分離現象嚴重。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著重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核心和本質就是著重解決人口的城鎮化問題。其中,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首先需要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可以根據不同規模的城鎮進行差別落戶。其次為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攤問題,構建多層、多樣的政府、企業、個人多元分擔模式。最后為暫不落戶或無法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建立居住證制度。
一、我國戶籍制度的變遷
1958年1月,我國第一個戶籍管理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頒布,該條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了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達到相應條件或得到遷入憑證。二十年后,《關于解決部分專業技術干部的農村家屬遷往城鎮由國家供應糧食問題規定》由公安部、糧食部、國家人事局聯合頒布,對于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的“農轉非”在指標約束上進行了放寬。改革開放35年,我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各項改革不斷深入。當跨入21世紀,我國政府將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權限下放到了最了解當地農民情況的地方政府,城鎮戶籍制度的改革參考當地的經濟、人口、人員流動等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進行。同時,城鎮戶籍制度從指標約束控制改變為準入條件制,根據不同地方的情況,準入條件也在不斷的改變和降低。
2014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了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在2014年重點工作中李克強總理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明確了我國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本質和工作目標。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成為政府需要著重解決的“三個1億人”問題。而“人”的城鎮化的提出也將農業轉移人口落戶的問題提上日程。
二、現有戶籍制度下農民工市民化制約因素分析
1.農民人戶分離現象普遍,農民工難求社會福利
2013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3.73%,而戶籍城鎮化率則徘徊在30%左右。我國的二元社會結構使得城鄉隔離情況突出,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二元社會制度導致持“農業”和“非農”戶口的公民享有不同的制度體系。越來越多的農民為了發展、生計等各種原因進城工作,這些農民所在的地域變了,職業變了,但是無法進行身份轉移,不能徹底市民化的農民就成了城市里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相比城市居民,一方面,他們無法享受城市戶口上附著的眾多社會福利,包括低保、住房、教育、醫療、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等保障。另一方面,由于這類人群普遍學歷不高,在城市中的謀生以打零工為主,就業制度、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歧視性的就業環境和匱乏的就業信息對于這些“農民工”都是不公平的。一紙戶口將這些為城市建設做出貢獻的農民變成了城市邊緣人,難以得到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
2.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高,政府動力小
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較高,政府財政能力有限制約了地方政府對于戶籍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城鎮化建設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放大了的公共福利事業,一方面現有的公共服務和城市基礎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生活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政府財政也不堪重負。
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指使現有農民工將身份、地位、價值觀、權利、生活等全面向城市市民轉化并順利融入城市社會所必須投入的最低資金量。通過構建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模型,采用市轄區的城市生活、教育、社會保障、城市住房、基礎設施的人均成本5個指標,在分地區、分類型的基礎上測算出了全國43個城市的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東部沿海地區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分別約為10萬元和9萬元,內陸地區的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分別約為 6萬元和 5萬元。
3.2/3農業戶籍人口不愿轉為非農戶口
2014年4月1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主持的中國城鎮化大規模入戶抽樣調查數據。調查顯示,和過去人們期望變成非農戶口、“吃商品糧”的情況不同,目前持農業戶籍的人,近2/3的人表示不愿意轉為非農戶籍。因為擁有農村戶口就可以保留農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盡管政策上中小城鎮的戶籍早已放開,但由于就業機會少,流動人口沒有去落戶的動力。調查還顯示,大學畢業生也出現不愿轉戶籍的現象。其中,80后的大學畢業生有30%的人不轉戶籍,而90后大學畢業生中不轉戶籍的達到51.9%。高房價、高生活成本、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問題使得在二元社會保障制度下的農業戶籍人口把戶籍上附著的土地作為自己的保障,在城市生活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情況下,守住土地成為農業人口的第一選擇。
三、解決農民工市民化戶籍問題的途徑
1.健全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制度,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堅持自愿、分類、有序原則。要采取“因城而異,因群而異”的分類指導原則,按城市類型、經濟規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的戶籍遷移管理辦法。對于人口達到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如北上廣,主要在于落戶規模和節奏的調整,積分制的階梯式落戶通道是相對合理的選擇。對于人口在300-500萬的大城市,既不能關死城門,堵住農民進城之路,也不能一步完全放開戶籍,要依據城市綜合承載力,對不同類型農民工群體逐步放寬落戶條件。要優先把有穩定勞動關系,長期舉家工作、生活在城市,有穩定住所、工作和收入,并基本融入城市的“沉淀型”農民工逐步轉為城鎮居民。人口在100-300萬的大城市,要重點解決新生代農民工落戶問題。在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是市民化意愿最強的群體,同時也是比較容易融入城市的群體。對于中小城市,要向進城農民工打開城門,鼓勵其進城落戶。對于小城市、縣城和建制鎮,則要敞開城門,讓農民自由進城,當然也要以合法穩定就業和住所為前提條件。讓農民能進得了城,能在城市發展,才能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
2.政府、企業、個人多渠道分擔市民化成本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僅是為其辦理戶口遷入的行政手續那么簡單。政府將面臨的是農民工市民化帶來教育、住房、養老、醫療等一系列的市民化成本支出壓力,同時城鎮公共資源是有限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如果無法合理分攤,政府財力有限,對于戶籍改革的力度自然無法加大,那么新型城鎮化的道路是無法可持續的發展下去的。我國需要構建多層、多樣的政府、企業、個人多元市民化成本分攤模式。一方面,由政府主要負責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支出,政府要在“人”的城鎮化的新形勢下改變“錢跟戶籍走”的老做法,讓“錢跟人走”,以“誰受益,誰承擔”來明確主體責任。如:孩子跟著父母從蘇北到蘇南讀書,該學生的教育財政支出就要撥給蘇南,而不是戶籍所在地蘇北。另一方面,在社保支出方面,則需要主要由企業和個人共同分擔。將看似較高的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通過構建政府、企業、個人多主體共同參與的成本分擔機制進行分攤,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使政府在進行戶籍改革時沒有后顧之憂,進而加快地方政府對于戶籍改革的力度和速度。
3.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建立居住證制度
解決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過程的。對于未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要深化配套制度改革,政府和公安部門要建立相應的居住證制度。居住證制度中要明確在該地有合法穩定工作和住所卻沒有戶口的流動人口在就業、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各方面能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務。截至2013年,深圳發放居住證已超過2000萬張。2013年7月,《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開始實施,改變之前的A、B、C證的條件管理方式,采用新的積分管理辦法。而一直實行工作居住證制度的北京也將在2014年全面推行居住證制度,擬為長期在北京工作又沒有戶口的人提供與北京市民同樣的公共服務。居住證制度是戶籍制度改革的基礎配套制度,它必須與以往政府推出的暫住證制度有明確區分。政府要將管理職能轉變為服務職能,明確居住證制度不再是政府進行人口管理和統計的手段,而是讓更多公民能享受公平的社會資源、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方式,也是農民戶口遷入、改變戶籍、落戶城鎮,真正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過渡。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2014-02-04).國家統計局網
[2]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大流動的中國城鎮化進程[J].環境與生活,2013(11):38
[3]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回顧2013年工作.[EB/OL],(2014-03-05).中國新聞網
[4]姚秀蘭.論中國戶籍制度的演變與改革[J].法學,2004(5),46
[5]宋嘉革.中國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村人口城市化轉移[D].東北財經大學,2006:61
[6]張國勝.基于社會成本考慮的農民工市民化:一個轉軌中發展大國的視角與政策選擇[J].中國軟科學,2009(4):56-69
[7]梁平.社會學家李強:2/3農業戶籍人口不愿轉為非農戶口[N].中國青年報,(2014-04-14):07版
[8]海燕.戶籍改革需從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入手[N].中國商報(2014-02-21):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