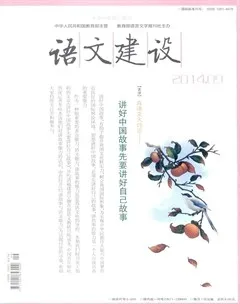對語文本體的思考與闡釋
關于“語文本體”,是多年來人們一直追問、探討和爭論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能否正確把握語文教育的本體根基和語文課程的目標與方向。我們認為,切實廓清語文本體的構成基質和元素,對語文本體從根本上做出明確的闡釋,有助于打破“泛語文”“非語文”“超文本”“教學形式化”的弊端,昭示真語文教學的本色與特質,以大力倡導實實在在教語文、認認真真學語文、扎扎實實用語文的教學新秩序。
一、何為語文本體
簡單地說,語文本體即語文本身構成的基質和元素。語文本體論是關于語文自身的學問,它要闡釋和描述語文的生成構成與存在形態。“本體”是一個較復雜的概念,曾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和認識。在這里,我們無意于形而上的概念性思辨,只是著眼于具體探討語文的本體問題,但有一點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許多本體論專家早就明確地指出,本體問題或存在問題是和語言緊密交織同構于一體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這個眾所熟知的名言,說的就是“本體即語言”的道理。“語言是存在世界的現身情態,存在世界是在語言中現身和留住的”,“世界是人類語言的命名”,“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沒有語言,存在世界的現身形態就難以得到呈現和說明。對此,筆者在《語文教學本體論》一書中做過具體的分析和探討,在這里不需要再贅述。如果離開語言,何談本體?因此,“本體即語言”“語言即本體”,是本體論語言學早就有明確定論的問題。
其實,本體和語言緊密交織同構的問題,是本體論語言學長期爭論和探討而得出的一個結論。“自柏拉圖起,關于在語言中指陳非存在物的問題就一直困擾著西方哲學;從中世紀起,關于唯名論與唯實論的爭論就十分激烈,一直到當代也沒有解決。安瑟倫關于上帝的本體論證明是從語言中使用某種謂詞而推出實在的典型,直到康德才證明這種推論是荒謬的,而康德的關于‘存在’不是謂詞的主張在當代語言哲學家那里有熱烈爭論。當代語言哲學家認為,利用現代語言分析手段,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本體問題,對古已有之的問題給出嶄新的、確切的答案。”語言學界的這種認識分歧與爭論,可引發我們對語言與本體的多方面的思考和深層的醒悟,使我們深刻認識到語言和本體原本就緊密交織而同構于一體,談“本體”就不能不談“語言”。本體和語言的這種交織同構關系,啟示我們對語文本體的闡釋,更應該從本體論語言學的視點出發,來透視語文本體構成的真義,這就是談語文本體不可能不談語言和文字。只有立足于語言和語言得以符號化的文字,才能真正觸摸到語文本體,切實把握語文本體。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語言及其文字作為本體和存在世界現身情態的符號,具有其他事物所沒有的特質,即它是情感的符號、思維的符號、生命的符號。比如,它作為一種文化的構成物,不同于房子構成的磚頭和土木;它作為一種工具,也不同于斧頭鐮刀之類的純工具。這就是說,語言及其文字作為特定的符號代碼,特別是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其本身就具有形象性、情感性、意義性和審美性等特質,但是房子構成的磚頭和土木,并不具有這種符號性,它們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物,之所以稱為“磚頭”和“土木”,也只不過是人類語言對它們的命名。“磚頭土木”可視之為各種“房子”的材料,而“語言文字”卻不可視之為各類“作品”的材料。因此,“語言文字”和“磚頭土木”并非是一個邏輯起點上的概念,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不能走過去語言學關于本體爭論的老路,否則,就難以弄清楚語文本體。在這里,我們即從這種本體論認識出發,來重點探討語文本體構成的兩個基本問題。
二、語言文字構成語文本體
長期以來,語文教育界對語文是什么,即語文本體的構成問題,存有多種不同的闡釋和認識。概括來說,主要有四種代表性觀點。第一,語文是“語言文章”,認為“口頭為語,書面為文,合而言之,稱為語文”。這種闡釋強調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主張語文課既要對學生進行口頭語言的訓練,即聽和說能力的培養;也要對學生進行書面語言的訓練,即讀和寫能力的培養。也就是說,這種對語文本體的闡釋,寓含著語文教學要對學生進行全面的語文能力訓練,提高語言文章素養的思想。第二,語文是“語言文字”,認為語文課即語言文字課,語文教學應當扎扎實實地進行語言文字訓練。這種闡釋強調語文教學如果不抓語言文字這個根本,忽視字詞語句的教學,尤其講文學作品,總喜歡大講人物,大講形象,大講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那么,這樣的課就不是語文課,而是文學課了。因此,他們曾提出一個口號,叫作“不要把語文課講成文學課”,要求語文課把著眼點放在字詞語句的教學上。第三,語文是“語言文學”,認為文學是語文固有的因素,語文課應當重視文學性的教學,加強文學教育。這種闡釋強調,如果文學作品的教學把文本拆解為單純的語言文字,忽視文學性教學,那么就會抹殺文學作品的生命和藝術魅力,其語言文字也失去光彩,造成語文教學的失誤。第四,語文是“語言文化”,認為語文是文化的構成,語文是文化的符碼,語言和文化血肉同構,融注于一體。這種闡釋強調,如果否定語文是語言文化,也就否定了語文課,忽略或脫離語言文化的語文課,就不可能是有“語文味”的真語文課。
關于語文是什么和對語文本體的闡釋,之所以存有這樣的認識分歧,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語文是多因素構成的復合體,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闡釋。特別是漢語文內涵的多義性,漢語文內容的豐富性,漢語文功能的多重性,容易造成人們不同的認識。第二,對語文本體的闡釋也受時代和社會發展的制約,不同的歷史時期對語文有不同的闡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50年代注重“語言文字”,因為當時強調識字讀書學文化,后來又注重“語言文學”,語文課也分為“語言”和“文學”兩科;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新文化思潮的涌入,語文又被視為“語言文化”。第三,從對語文本體的闡釋及其認識分歧的形成來看,與人們研究問題的思路和視角不同有關。如搞語言文學的,往往強調語文是“語言文學”;搞語言文化的,往往強調語文是“語言文化”。這也是造成對語文本體的不同闡釋和認識分歧的原因之一。
我們通過以上所述可見,對語文本體的這些不同闡釋和認識分歧,主要表現為兩個不同的闡釋角度。
第一,從語文的形式上來闡釋語文本體,認為語文是“語言文章”或“語言文學”,然而,這二者實際上都是以語言文字為基質和構成要素的。因為文章是語言文字構成的語言形式,語言文字是文章構成的基質要素;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語言文字的藝術構成品,語言文字也是文學文本構成的基質元素。這就是說,文章也好,文學也罷,其實都是語言文字構成的語言形式。如果沒有語言文字,就沒有文章的構成,也沒有文學文本的存在。為此,有的專家認為語文本體即語言文字及其作品。把作品看作語文本體,或許也是一種新說法,但加以分析可見,這會給語文本體帶來誤解。語文教材中有各類不同的作品,如果把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各類作品都視為語文本體,顯然就會造成本體的泛化、模糊化。因此,把作品視為語文本體是不妥的。
第二,從語文的內質上來闡釋語文本體,認為語文是“語言文化”。眾所熟知,人類的生存文化,分為飲食文化、服飾文化、居室文化等,語文也就是一種與之并稱的語言文化。我們說,語文就是文化,并不是泛指各類文化,而是指語言文化。語言文化是以語言文字為載體而存在的,語言文字是語言文化的符號和代碼,沒有語言文字,也就沒有語言文化,這就是說,語言文化構成和存在的本體也是語言文字。由此說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肯定性的結論:無論是“語言文章”“語言文學”,還是“語言文化”,顯然都離不開語言文字,都是語言文字的本體構成品,是語言文字構成的不同形式、表現形態和存在方式。文章構成的基質元素是語言文字,文學構成的基質元素是語言文字,文化構成的基質元素也是語言文字。據此,語言文字構成語文本體,這是不可置疑的。我們還要強調指出的是,為了切實廓清語言文字構成語文本體的基本認識,確立“語言文字”構成的語文本體觀,并非排斥“語言文章”“語言文學”“語言文化”等語文構成要素,而是指三者構成的基質元素都是語言文字,即語言文字構成的語文本體融合同構著文章、文學、文化的基質和元素,語言文字是語言文章、語言文學、語言文化構成的基質元素和存在的基本方式。
毋庸置疑,語言文字構成的語文本體,是一個復合性概念,它包容著文章的、文學的、文化的、語體的、文言的等多重性內涵,并非一個單一性的載體,但需要明確指出的是,語言文字是構成語文本體的基質和主要元素,語文的本體世界是語言文字構成的世界。或許語文也是一個動態性概念,其內涵是不斷發展、不斷生成的,不同的時代和歷史時期,對它會有不同的闡釋和解讀,但語文本體的世界里無論在什么特定的歷史和時代中,都是語言文字的生成物,都是以語言文字為基質和元素構成的。我們在以發展的、變化的眼光來闡釋語文的時候,都應該尊重語言文字構成的語文本體這個客觀事實,不可以離開語言文字構成的語文本體,對語文進行某種特定角度的“當代性闡釋”。
三、漢語言文字構成的特性
在確立語言文字構成語文本體的基礎上,我們要建構切實體現漢語文特點的語文教育觀,還必須把握漢語言文字構成的特性。
漢語言文字的構成具有豐富的內在意蘊和鮮明的文化特質,它具有形象性、情感性、表意性、審美性、象征性等特征。對此,我們可從漢語言文字本體的構成切入來進行分析和認識。漢語言文字有其特殊的構造方式和結構特征,它獨特的形體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文化意蘊。漢語言文字形體結構具有直觀性、象征性等特點,其形體構成與人的思想、情感、生活和行為往往有機地聯結在一起,充溢著豐盈的文化意蘊。如“字”的形體結構本身就蘊含著一個有關人的生命延續的故事,即在一家房子里,一個女子生養了一個孩子。實際上漢語言文字形體結構的每一個筆畫、每一個線條,往往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內涵。漢字的構成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完形,它有外形和骨架、有思想和神韻、有情感和精神。漢語言文字的這種特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漢語言文字是表意性文字,一個漢字往往就是一個特定的意義世界;漢語言文字是表情性文字,一個漢字往往就是一個特定的情感世界;漢語言文字是象形性文字,一個漢字往往就是一個特定的形象世界;漢語言文字是審美性文字,一個漢字往往就是一個審美世界。
漢語言文字作為世界語言中唯一的表意文字,它與西方拼音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特性。拼音文字是抽象的字母線性排列形態,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將語言摹寫記錄下來,文字和概念有著較大的距離性,與其所指的實物和意義是一種非直接性關系,而無任何形象結構上的內在關聯。拼音文字的這種特點,就是先記錄語音,后由語音而知意義。文字與意義沒有直接的聯系,語音是文字和意義的中介,文字對語音有很強的依附性。但是漢語言文字與其全然不同,它所特有的象形性和平面結構方式使它具有鮮明的直接表意性,即可以直接表達概念和意義,其形體結構本身近似實物,或形似或神似。正如有人所說:“漢語言文字用它自己的形體來表達人的思維活動、認知活動和情感活動。當人們寫一個漢字的時候,目的在寫它自己的思想而不僅僅為的是寫語言;當人們看到漢字的時候,也只是看到它所包含的內容,不一定把它當作語言;只有把它讀出來的時候,才由漢字轉化為語言。”漢語言文字的認知方式不是由音到義,而是由形直接到義,不依附于語音。這種字形結構的表意特征使漢語言文字成為獨立于語音之外的第二符號系統,使漢語言文字符號系統可以超越語音的羈絆,借助視覺系統進行直接性的文化信息傳播,使人們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直接從字形結構中解讀出字義來。這就是說,漢語言文字的形體結構保存了遠古造字時代的文化背景,人們可以通過其形體來窺視遠古社會的生活狀況;同時,漢語言文字在發展的過程中又不斷地把社會文化凝聚其中,所謂“字里乾坤”說明的就是漢語言文字的這一文化特性。因此,漢語言文字成為漢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切實地保存了漢民族文化的原生態。
語文教育的內容是以漢語言文字為中介傳遞給學生的,如果在教學中不能理解和把握漢語言文字的文化特征和意蘊,只將其作為簡單的信息來處理,那么漢語言文字豐富的內涵和靈動的精神就會在教學中枯萎、流失,對字義了解不深,對文意的理解也只能限于浮光掠影,甚至走向誤讀。相反,如果在教學中能夠挖掘漢語言文字的文化意蘊,呈現給學生,并能積極地調動學生的興趣,激發學生的想象、聯想,就會有事半功倍之效。瑞典語言學者林西莉在《漢字王國》一書中談及她的漢語言文字教學體會:將漢語言文字所反映的文化現象、文化精神給學生解釋得越清楚,學生就越容易理解和掌握,并且理解得清楚,掌握得牢固。反觀我們現實的語文教育,對這一點的關注和實踐非常欠缺,漢語言文字教學不得法導致的教學質量差更是困擾廣大師生的難題。針對這些問題,主要的對策就是重視漢語言文字的文化特性,從漢語言文字的本體特征出發進行教學,以切實提高語文教育的效率和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