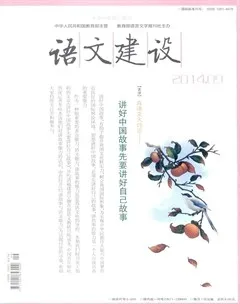如何定位教學內容深淺
兒歌《小小的船》因其內容淺顯而又富有想象力,常被選人小學一、二年級的教材,關于此文本的閱讀教學設計,教師很少對其中的內容及藝術手法存有疑問。當然,如果單從識字本身人手,把這首兒歌僅視為識字的材料,也許可以不管兒歌本身的內容,教學設計的深淺問題也就沒必要提出來。只是近年來教育界倡導有意義的學習,隨文識字日益得到教師的重視,識字教學不僅僅是要求學生學習:≠詞的詞典義,而且還要理解其文本中的語境義,乃至進一步思考所學的字詞對語境本身來說意味著什么,這就需要我們深入思考詞語與文本的復雜關系。如何定位《小小的船》這一文本教學內容的深淺度,也就成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為討論方便,先把這首兒歌引述下來:
彎彎的月亮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兒兩頭尖
我坐在船上抬頭看,
只看見閃閃的星星藍藍的天
開頭一句,雖然確實是把月亮比作了一條船,但沒有直接寫“彎彎的月亮像條船”,而是采取月亮與船并置的方式,所留下的思維邏輯上的空缺,讓讀者自己通過想象來連接。第一句的描寫不僅看似省略了聯系詞的一個比喻(為何說是“看似”,下文另有討論),而且因為兩者并置,使得前后關系有了互文的效果,即月亮和船都是既彎且小的。不過,盡管是互文,先提“彎彎”而后提“小小”,是因為以“彎”的特征說明,月亮用“船”來比喻要比“小”更具關鍵性,是直接排除圓月的可能性。此外,疊詞“彎彎”和“小小”在含義上有強調作用,就不能再用“很”來修飾,閱讀起來也要比用“很”更容易產生親切感。再從整句的句子看,成分是五字短語向四字短語的轉換,節奏上則形成3/2/3/1的節拍,最后以一字節拍來收尾,自然就有一種頓挫感。
下面來看這首兒歌思維的推進方式。因為在想象上似乎已經把月亮比作了小船,所以接下來的第二句,思維就站到了船的位置來展開:“小小的船兒兩頭尖。”這句看似對船的描寫比前一句深入了,似乎全是站到船的立場上說話,但實質上也是緊扣前一句而來的,那就是把前一句的兩部分內容在這一句做了前后顛倒,近似于修辭的回環。除了“小小的船兒”重復前句外(當然船后加“兒”,既是為了音節的需要,也是為了強化親切感),“兩頭尖”不就是和前一句開頭“彎彎的”呼應嗎?但第二句畢竟不是第一句的回環,是因為“兩頭尖”的意思雖由“彎彎的”所引出,但“彎彎的”著眼的是月亮也是船的整體,而“兩頭尖”是在“彎彎”中取了兩頭的局部狀態,從而把船的中間這部分空缺了。進一步看,兩頭尖雖然是對局部狀況的描寫,但局部中有整體,就是這樣的描寫,其實已經是一種普遍性的概括,它并沒有顧及這一頭和那一頭、前頭和后頭可能的差異性。因此,當作者用“兩頭”這樣的詞語時,它已經把兩頭內部可能有的差異給略去了。因為在這首兒歌里,這一差異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對兩頭與中間的不同的描寫,讓人看起來覺得月亮更像一只小船,也能夠把中間留出的不言而喻的不尖的位置,讓人坐上去。這其實是思維流動中做出的先期暗示,即當你從外部來看對象時,你容易關注的是整體,而當你進入內部時,就不太容易再來關注整體,而且容易把你所在的位置忽略掉,以你所在的位置作為思維的出發點,來關注你的周邊,比如處在中間而關注兩頭。當然,這只是思維的潛流,作者的真正用意,是要讓人進入小船后抬頭看。也就是兒歌的第三句。
第三句是“我坐在船上抬頭看”。與上兩句相比,這句里既沒有疊詞,節奏也不僅僅是在結尾用一個字的節拍如“船”“尖”來造成頓挫感,而且,除開結尾的一字節拍“看”外,開頭以“我”起頭,接以“坐在船上抬頭看”,形成一種比較呆板的而不是流暢的1/4/3或者可細分為1/2/2/2/1的節拍,開頭和結尾都是頓挫的一字停頓,中間沒有節奏變換,這樣不得不讓整個句子從頭到尾的閱讀速度都放慢下來,從而形成的正是作者所要追求的一種慢慢看的閱讀效果。同時,也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這里出現的“我”是誰?與前兩句描寫所隱含的那個“我”是不是同一個人?一般都會認為這就是作者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與前兩旬描寫的隱含抒情者相同,這可能不會有異議,但由此引出了這篇兒歌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常常被教學者所忽視。這個問題見于兒歌的最后一句:“只看見閃閃的星星藍藍的天。”在這最后一句,第三句暫時丟失的疊詞又回來了,讀者似乎又回到了對天空仰望的遐想中,兩次疊詞運用的強調意味似乎在呼應開頭句兩次出現的疊詞,但仔細回味,卻發現畫面已經變味了。從第一句開始并且貫穿了前三句、作為兒歌主線的月亮以及喻體小船突然在畫面中消失了。這樣,疊詞對出現在畫面中的物象之強調,也隱含了對突然沒有的物象月亮之強調,甚至是一種慢慢尋找而不得的強調了,因為在整首詩的四句,最后一句是句子最長、節奏也最舒緩的。據此,第四句開頭的“只”揭示了這種“看見”中的看不見。這樣的結果是怎么發生的呢?因為當抒情主人公“我”把自己放在月亮上,讓自己內在于月亮時,作為天上景觀之一的月亮,就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了,也形成了兒歌常有的那種捉迷藏般的思維跳躍和趣味。從文學作品結構本身來說,則是一次戲劇性的大逆轉。這樣也就解釋了何以開頭一句沒有采用“像”這樣的聯系詞的部分原因,也許我們一上來認定首句為比喻只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成見。作者固然把月亮和船并置在一句中,但并沒有明示讀者這里就用了一個比喻,首句的含義為何不可能是天空、水面的一種并置呢?或者,如果河水清澈的話,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里,月亮和小船在空間上不就是挨在一起了嗎?這樣的聯想其實完全是合理的,也是詩句引發人產生不同聯想的奧秘所在。正是有歧義理解的可能,或者作者故意引人走向理解的歧途,最后一句寫坐在船上的人突然不見了月亮,才修正了讀者此前可能的另一種解讀,就像揭開謎底一樣,讓人對這首詩產生了重新理解。
概括起來說,這首篇幅短小的兒歌,有著兩種基本的解讀思路。第一種是認定了首句的比喻性,從而概括出想象性的三次思維跳躍:第一次是把月亮比成小船,拉近了空中的月亮和自己的距離,增加了景觀的親切性;第二次還是通過想象,從旁觀者變成身臨其境者,讓觀察者到了月亮上,增加了兒童游戲的參與性(盡管這一參與本身也是想象的)和趣味性;第三次通過自己在月亮中的再次想象性觀察,展現了全新景觀的狀態,也把對其自身立場同時也是對閱讀的反思性內容置于這種新的景觀中。第二種是原生態的閱讀思路,更注重閱讀過程中形成經驗的自我修正。第一句先不把月亮和小船視為一種比喻,而僅僅是月亮下的小船,或者是倒影中的月亮和小船的聯系。然后二、三句都是坐實了關于在水面小船的描寫和自己坐上了小船,只是當讀到第四句“抬頭看”時,突然發現月亮的消失,從而把此前所有的誤讀修正過來,完成理解的戲劇性逆轉。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么來確定這篇教材作為小學低年級的教學內容呢?
首先當然是生詞學習。對低年級學生而言,形容詞“彎彎的”“閃閃的”和“藍藍的”,還有“尖”以及名詞“船”等,都有可能是他們在課堂上第一次接觸的,都可設定為教學的內容。這既包括對詞的音形義的學習掌握,也涉及如何引導學生把詞語放在文本語境中來理解。這里尤為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個詞在語境中的意義差別,如文本內部“兩頭尖”與“抬頭看”中的“頭”的含義差別(還可以比較其他課文句子“河邊有頭小水牛”中的“頭”),第一句中的“船”與第二句中兒化的“船兒”,還有文本中的作為比喻性的“船”與生活中真實的船的含義差別,疊詞的含義以及在文本中所起到的特殊效果,也不應被忽視。
其次是對兒歌的誦讀。既要注意節拍的停頓,也要注意同韻詞的使用給誦讀詩歌所增加的流暢性。這里不僅押腳韻,而且開頭的“彎彎”以及最后一句中間部分的“閃閃”“藍藍”也是使用同一韻母。根據學生具體的學情,在熟讀中把這些簡單的規則總結一下,也是有可能的。
最后就是對兒歌內容的理解,究竟應該定位在什么程度?生詞的隨文閱讀,不可能也不應該把對內容的理解完全撇開,關鍵是要確定哪些內容點適合于低年級學生學習。這里有兩點不應該省略。第一點是比喻問題(這當然是忽略了理解的歧義性問題)。這自然可以跟詞語“船”的學習聯系起來。也可以把“船”作為喻體,讓學生展開想象,對取其一點展開想象的比喻特征,有更多理解。所以在教學前,可以有意收集一些以船為喻體的兒童詩歌,如斯蒂文森的名作《我的床是條小船》。…第二點,這首兒歌的最后一句,展現了一個謎底式的懸念解答,即人在月亮而看不到月亮。這問題比較復雜,往深處走,可以談到思維規律問題,但對小學生來說,如果能結合小學生自身的體會,還是有可能領悟的。不過,這也需要跟最后一句的“只”字聯系起來學,強調“只看見”的含義是對看見了的和看不見的一次區分。從而使得整體的教學設計牢牢建立在詞語學習的基礎上,不會脫離小學生的學情。
那么,這樣的一首兒歌也可以作為中學生教材嗎?
其實,從以上對文本的解讀來看,已經為中學階段學這首兒歌預留了很大的空間。雖然這里似乎已經沒有中學生不認識的生詞和難字了,但也可以在文本理解上加以深化。這樣的學習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對小學生學習的知識從認同角度加以進一步拓展,比如除開學習比喻這一修辭手法外,還可以學習首句中蘊含的互文修辭手法。或者將所學的比喻手法加以深化,如對比喻思維特點及功能的透徹理解,對比喻取其一點到多方取比的博喻,還有比喻與比擬與借代的比較性分析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嘗試從反思角度,對自己所學內容以及自己的學習立場加以反思。
就這首兒歌來說,有三點可以值得我們加以反思性探究。其一,首句理解的歧義問題,阻止文學欣賞中的先入為主,可以真正領會到欣賞過程中的戲劇性逆轉。其二,一種概括性的描寫比如“兩頭尖”,其“兩頭”的歸并描寫對內在差異性忽略以突出描寫的側重點。這里涉及“一頭”“一頭”分開的具體描寫和“兩頭”合并起來概括性描寫的功能比較。其三,當“我”作為一個理所當然的抒情主人公時,讀者的立場是不是也會自然而然認同這樣的“我”,并替代了這樣的“我”?但當兒歌中的“我”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中說只看到星星和藍天時,外在于兒歌的“我”,是能夠看到自己和月亮的一體性的。這樣,作為讀者的“我”,究竟取怎樣的欣賞態度才是合適的呢?是與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我”徹底擁抱、互相滲透,還是保持一段旁觀的客觀距離?從現在網上流行的一些教學設計來看,教師大多會出示小孩在月亮中的圖畫,作為理解這首兒歌的輔助手段,但這一圖畫掩蓋了這首兒歌所表現的那種在月中而看不到月的真相。同樣令人遺憾的是,不論是名師斯霞老師的示例課,還是北大附小郭瓊老師的教學實錄,他們都忽視了兒歌在最后一句中所用“只”的真正意義。盡管斯霞老師在課上引導學生分析了“只”的含義是“光光、單單的意思。就是只看見這個東西,沒有看見別的東西”,但是她只強調了所看見的星星和藍天,卻未提及沒有看見的是什么。
由這樣頗具普遍性的教學現狀來看,揭示這種掩蓋和忽視,并反思掩蓋和忽視產生的根源以及自身依托的立場,也許是在更高學習階段,比如大學教學中所確定的主要內容吧?不妨說,立場從認同向反思的漸變,是構成教學內容由淺入深的重要設計思路,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作品本身的豐富性,也為這種教學設計在內容深淺度的漸進性提供了可能,哪怕這是一首貌似非常簡單的兒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