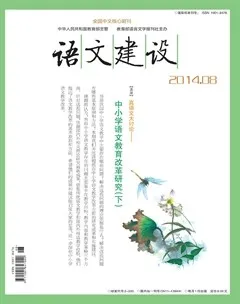我這樣確定《伶官傳序》的教學點
我曾上過一節《伶官傳序》的市級公開課,后來有機會聽別的教師上《伶官傳序》的公開課,雖然“同唱一首歌”,但風味全然不同。靜而思之:我教了什么,是怎么教的?別人教了什么,又是怎么教的?這篇或者說這類文章還能怎么教?教與不教這篇文章對學生有什么不同呢?這樣一想還真是頗有意趣,這大概就是遲到的教學反思吧。
今人讀古文,就是一場超越時空的對話,從中讀到了什么,領悟了什么,這是對話最大的意義。教讀《伶官傳序》要讓學生讀到什么,悟到什么呢?高二學生依據注解,自讀本文,領略情感,理解大意,不會有什么困難,但要深入品味其中蘊含的復雜情感與深刻思想,不僅要仔細揣摩文體,還要聯系時代、聯系作者的身世遭遇,才能探微知著。一般教師會做如下安排:借助注解疏通文句并順暢朗讀,借助教輔材料進一步夯實文言文基礎知識。這兩項學習任務對高中生來說完全能自主完成,教師只要適當安排合理監控即可。課堂教學注重“一課一得”,這“一課”不僅指“一課時”,也指“一課文”;“一得”就是通過教師的教讓學生習得的學習重點,這“一得”要從教材、文本、教師、學生四個維度綜合思考來確定。那么,《伶官傳序》有哪些合適的“教學點”呢?以下可以作為參考:一是對比舉證的文章結構,二是氣貫中脈的論述風格,三是宏遠博大的君子情懷。且細釋之。
一、模擬對比舉證的文章結構,學習議論類文章的經典范式
《伶官傳序》選入人教版高中選修《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第五單元中,單元說明指出要學習古代散文“散而不亂,氣貫中脈”的風格。《伶官傳序》有很好的范式性。
從文章結構上看,《伶官傳序》開篇提出觀點,中間兩段正反對比論證,結尾歸納總結,這是議論性文章常見的三段論結構。
從論證方法上看,《伶官傳序》通過“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兩個角度,用事實論證“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的中心論點,這是議論性文章常見對比舉證的論證方法。
從中間兩個議論段上看,莊宗“得天下”與“失天下”有敘有議,觀點與事例、情感與態度水乳交融天衣無縫,給學生學習觀點與論據如何黏合提供了很好范例。
以《伶官傳序》篇章結構、論證方法、議論段的寫作等作為教師教學的切入點,適當延伸拓展,模擬對比舉證的文章結構,學習寫作議論類文章,形成“以讀促寫,以寫帶讀”的良性循環,不失為一種很好的“落教點”。我在教讀本文時就將對比舉證的文章結構作為教學的延伸點。
二、深入文本逐句品讀,領悟氣貫中脈的論述風格
《伶官傳序》是一篇史論,雖然議論的成分占了主要篇幅,但讀著有強烈的感染力,其奧妙何在?對文章密詠恬吟一番,你會發現始終有一種情感的力量和一股氣勢在影響著讀者;再仔細分析咀嚼,你會豁然開朗,文中議論、敘事的語句,都帶有鮮明而強烈的情感色彩,駢散結合,鏗鏘有力。且以第三段為例,逐句咀嚼,共尋經典的魅力。

從內容上看,得天下與失天下,盛與衰,一一對舉,但歐陽修對莊宗得天下與失天下并不是純客觀的分析,而是對莊宗得天下時的“憂勞”肯定贊賞,對失天下時的“逸豫”否定嘆惋,形成一種情感充沛、氣勢如虹的文勢,有力論證盛衰之理在于人事的觀點,說明“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給歷代統治者敲響警鐘。
從語言風格上看,一系列動詞連用,四言、五言、六言等短促的句式連用,一氣呵成,表現出得失天下變化之速,形成一種排山倒海的氣勢,給讀者以強大的情感沖擊力,情感的濃烈與古漢語的精練發揮到了極致。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評論歐陽修的散文:“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見于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可謂知之者。
因此,深入文本逐句品讀,領悟氣貫中脈的論述風格,適當延伸拓展,仿寫融記敘、議論、抒情于一體的議論段,也是一個很好的“落教點”。我聽過的公開課中就有這樣的寫作遷移訓練:
寫作要求一:得天下與失天下的例子很多,你還可以舉幾個?請根據下列句式簡要描述,至少寫出兩句,形成排比。
開元君王唐玄宗,開創盛世,卻因專寵貴妃,導致盛唐衰落;______,______,卻因______,導致______;______,______,卻因______,導致______。
(教師示例:得失天下的君王有齊桓公、夫差、勾踐、李煜、宋徽宗等。
春秋霸主齊桓公,稱霸諸侯,卻因親近小人,導致禍起蕭墻;吳國國君夫差,雄霸南方,卻因貪戀美色,導致國破家亡。)
寫作要求二:根據你在“寫作一”中的觀點及采用的事例,改寫中間兩個論證段及結尾。可用文言,可用現代漢語,也可文白相間。
三、細品盛衰之道,追慕宏遠博大的君子情懷
將《伶官傳序》編入教材,作為“散而不亂,氣貫中脈”的教學范例,但作為史論,其見解之高低正誤也不可輕忽。《伶官傳序》氣貫中脈論述“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篇末通過與“人事”密切相關的“禍患”與“智勇”進一步推論出“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論斷,這并非僅是出乎個體直覺的感悟,而是建立在翔實的歷史研究和深入思考上,足以令昏者醒而智者悟,這也是本文能夠獨步千古、世代誦讀的原因之一吧。
歐陽修不僅是文學家,更是政治家。作為政治家,他的眼光不會只停留在歷史研究上,他的更深刻處在于現實的針對性。本文是歐陽修為《新五代史·伶官傳》所寫的序言,在已有薛居正主編的《五代史記》以后,歐陽修重修一部體例寫法都不一樣的《新五代史》,目的何在?《宋史·歐陽修傳》對此說明:“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意在抨擊他認為的沒有廉恥的現象,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由此可見,文章本意不僅于一篇序言的功能,更是以史為鑒,直指當下政治的缺失:北宋王朝日益腐化,北方少數民族不斷進犯,北宋王朝納幣輸絹以求茍安,這樣的局面能維持多久呢?作者借唐莊宗興亡事來諷諫當代,指出王朝興亡不在天命,在于人事,“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用心可謂良苦!
行文至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論證已經完整了,但歐陽修的不凡之處還在于能順勢點上一筆再上一層:“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雖是簡單的一句話,卻是境界大開:從君臣之道到處世之道,從家國大事到日常修為,頓在其觀照之下!以史為鏡,不但可以“知興衰”,還可以“明得失”。在如此短小的篇章中要通過鮮明的對比闡述深刻的盛衰之道,已屬不易,又能在如此封閉的結構中別開洞天,表達出如此深邃而豐富的思想,真乃大家手筆!
當然,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去撰寫史書,使得《新五代史》比薛居正主編的《五代史記》有進步性和可讀性,但也有其不足:由于歐陽修著意學《春秋》“微言大義”,所以文字過分簡約,“一字褒貶”有時顯得拘泥。如他最喜歡以“嗚呼”開頭,評論五代歷史,慨嘆五代是個黑暗時期,諷諫當代,突兀而起,情勢充沛,但卷卷評論都以“嗚呼”開頭,也使行文變得板滯,過于模式化。因此,清代文史大家章學誠譏稱它:“只是一部吊祭哀挽之集,如何可稱史才?”可見,史論中把握個人情感表述的分寸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