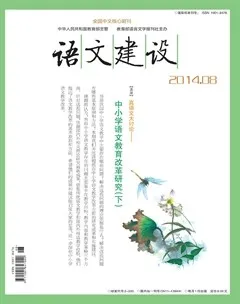“人艱不拆”等網絡詞語用動機初探
網絡語言從誕生之日起就被當作一種研究對象受到關注,時下一批貌似成語的四字格語言單位更是受到某一類言語交際主體的追捧。請看下列各例中畫橫線的四字格:
(1)一直主打科技健康住宅的朗詩,這次為了自己的推廣策略,真的沒有做到人艱不拆的美德。(騰訊網2013年10月28日)
(2)在當下這個“累覺不愛”的現(xiàn)實里,來一口這樣的雞湯還是頗令人欣慰的。(《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年2月21日)
(3)所以,我們現(xiàn)在很需要一些“不明覺厲”的娛樂節(jié)目,也很需要一些“不明覺厲”的專家評委。(《京華時報》2014年1月22日)
(4)隨著馬年春節(jié)的漸近,優(yōu)惠還將陸續(xù)有來,請密切關注本刊的相關報道,即使不買,也要多多轉發(fā)我們的優(yōu)惠信息——趕緊“火鉗劉明”。(《羊城晚報》2014年1月17日)
(5)一幕幕的劇情,可謂包羅萬象,讓人“細思恐極”。(《溫州晚報》2013年12月22日)
(6)面對泛娛樂化,我們究竟是應該“喜大普奔”還是“不明覺厲”?(《人民日報》2014年2月21日)
(7)求愛有風險表白需謹慎,默淚,人艱不拆,讓我們來看看那些年讓人黯然神傷的十動然拒事件。(人民網2013年10月12日)
上面例子中的“人艱不拆”“累覺不愛”“不明覺厲”“火鉗劉明”“細思恐極”“喜大普奔”“十動然拒”等不僅被應用在主流網絡上,即使一些主流報紙也對之不拒,這說明這些四字格有一定的使用空間。
從音節(jié)結構上看,毫無疑問,這些四字格和現(xiàn)代漢語詞匯的發(fā)展趨勢具有一致性。據《現(xiàn)代漢語頻率詞典》對9000個常用詞統(tǒng)計,有6400個多音節(jié)詞,其中6258個是雙音節(jié)詞。這些四字格毫無例外地都是通過雙音節(jié)和雙音節(jié)構成的復合語言單位,“人艱不拆”只能讀斷為雙音節(jié)加上雙音節(jié),即“人艱”和“不拆”,而不能讀斷為“人艱不”“拆”或者“人”“艱不拆”;同理,“喜大普奔”也不能讀斷為“喜”“大普奔”或“喜大普”“奔”,“不明覺厲”不能讀斷為“不”“明覺厲”或“不明覺”“厲”。可見,這些四字格貌似成語,與成語在音節(jié)組成的數(shù)量上較為相似。大多數(shù)語言學家都認為四字格為漢語成語的一般組成特點,雖然也有少數(shù)二字格和多字格的成語。
此外,這些四字格有特定的理據,與漢語成語神似。有人認為它們形成的事件性可以為其賦予“成語”身份。如“十動然拒”便是基于以下事件: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男生王文瑾,向他心儀的女生送出了一封他用212天時間寫的16萬字情書。這封情書的內容包括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體,內容主要是回憶兩人在一起做的事或借景抒懷。他將其裝訂成冊并取名《我不愿讓你一個人》。女孩十分感動,然后拒絕了他。于是“十動然拒”就產生了。“人艱不拆”則出自歌手林宥嘉《說謊》的歌詞“人生已經如此的艱難,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累覺不愛”源自豆瓣網上一個帖子,一名“95后”男孩感嘆“很累,感覺自己不會再愛了”。
然而,如果辯證地看待四字格的成語身份問題,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四字格的這種理據符合成語的一般特質,即典故性,但由于其時間沉淀很短,在語義上還沒有形成比喻義或引申義。因此可以這樣說,當下的“四字格”嚴格意義上說只有“典”而無“故”,這既可以看作網絡四字格發(fā)展的新特點,也可以視為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成語理據的不同。由此,學界提出一個嶄新課題,網絡出典能否被看作典故?網絡的理據能否被認為是一種新的“書證”?
除此之外,我們發(fā)現(xiàn)作為網絡用語的四字格尚未進入書面語。通過檢索語料庫發(fā)現(xiàn),這些四字格還未進入作家的作品中,在北京大學“CCL語料庫”和中國傳媒大學文本語料庫中,都未見這類四字格。當然,我們不能回避其網絡語言之“新”,于是又自行設計了100萬字的最新網絡小說語料庫,結果同樣未發(fā)現(xiàn)這類四字格。網絡檢索這類四字格時,檢索工具會自動提醒檢索其他某個四字格的意思、出處和用法。這說明,使用者的范圍相當受限,即使是網絡一族對其使用也非常有限。筆者曾對某大學一年級中文系學生做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5%的同學不知道這些四字格的具體語義,更不要說使用了。因此,其短命還是延年,尚難定論。正如姚小平先生所言:“語變是逐漸的過程,個人變異則往往突然發(fā)生,比如心血來潮,自造了一個新詞。這個新詞即便能進入語匯,得以流通開來,也需要一段時間。”
時下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這些四字格進入語言流通領域的語用動機。
首先,這反映了人們追求語言變異、求新的心態(tài)。使用者往往是年輕一代的網民,而當受眾對此不解時,通常會對這種語言形式詬病,所以其創(chuàng)新性可以說是在異議中產生的。再加上其“貌似成語”的身份特征本身也會吸引眼球。
其次,這種四字格的使用還會彰顯使用者的個性特征,使說話人貼上較強的自我標簽。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語言形式必須要借助網絡才能傳播,否則受眾不知所云,所以網絡在充當“病毒式傳播”的催化劑。即使是和言語交際主體無年齡或受教育程度差異的受眾,有時也會對這種語言形式感到陌生。這樣,言語交際主體就會產生一種“人無我有”的自得心態(tài)。
最后,使用這種極簡的語言形式,反映了言語交際主體由用語言到玩語言的娛樂心態(tài)。使用者通過簡單的語言單位疊加實現(xiàn)復雜的命題表達,在體現(xiàn)語言經濟性的同時,也表現(xiàn)出說話人游戲語言的輕松戲謔的非嚴肅心態(tài)。這些四字格難登大雅之堂,也佐證其非正式言語交際形式的特點。
網絡語言的發(fā)展日新月異,其語言形式也復雜多變,可以說虛擬世界的語言生活和現(xiàn)實中的語言生活一樣,詞匯形式是語言本體中最為敏感的,最為迅捷反映社會變遷的語言單位,網絡語言的詞匯層級,其社會屬性都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有意義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