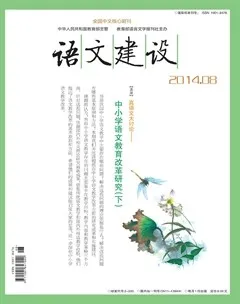從敘事學角度讀《項鏈》
莫泊桑的《項鏈》是19世紀世界短篇小說領域里的經典之作,其著眼于巴黎普通下層職員的生活現實,揭露了彌漫社會的虛榮風氣,具有強烈的批判和諷刺特色以及認知和教育價值。本文試從敘事學的原理出發,對《項鏈》加以梳理和詮釋,以期獲得新的認識和啟發。
一、上帝眼中的瑪蒂爾德
莫泊桑寫作《項鏈》時,全程采用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非零度聚焦),站在上帝的位置上來全面觀察、講述整個故事,進行細致的描繪。
“世上有一些美麗可愛的姑娘,就像命運安排錯了似的,偏偏出生在小職員的家庭里,這一個姑娘就是如此。”[1]小說以一種自然而然的敘述口吻開篇,這是莫泊桑小說的一大特色,具有較強的代入感,不僅方便進一步交代故事情節,而且能夠抓住讀者的好奇心,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同時似乎還隱隱約約地預言著人物的某種命運。
接下來,小說用六個段落的篇幅從內到外介紹了女主人公瑪蒂爾德的情況。瑪蒂爾德很漂亮,但沒有陪嫁資產,“沒有任何辦法讓一個有錢有地位的男人認識她、了解她、喜愛她、娶她”,不得不嫁給一個教育部的小科員。她覺得自己就是為一切豪華精美的事物而生的,她實際上卻過著沒有身份、沒有地位、住房簡陋、墻壁寒酸、家具破損、衣服難看的生活,她因此感到痛苦和傷心。接著小說又進一步深入,用六個“夢想”,如夢想“精美的晚餐,閃閃發光的銀餐具,墻壁上掛滿的繡有古代人物和仙境般森林中的珍奇鳥兒的掛毯”,“想到了用精致考究的餐具盛著的一道道珍饈美味”等,展現了她對物質生活的極度渴求。小說開篇這一部分主要通過認知性的心理描寫揭示瑪蒂爾德理想生活和現實生活的巨大落差。這樣的描寫是以零度聚焦(上帝的眼睛)進入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避免了內聚焦視角只能“猜測”的局限,把一個貪圖物質享受、向往貴婦生活,卻又貧窮困苦、憂愁怨恨的瑪蒂爾德活靈活現、一覽無余地展示給讀者。
西摩·查特曼在《故事與話語》中提出人物的“特性”說,并且將特性看作“相對穩定持久的個人屬性”。[2]這種屬性可以通過情節事件表現出來,它是人物整體的特性。從這個角度出發,《項鏈》開篇六段的全景觀照告訴了讀者一點事實,那就是:瑪蒂爾德是個愛慕虛榮的人。“愛慕虛榮”就是瑪蒂爾德的屬性。天生麗質的瑪蒂爾德認為美可以“使得一些平民人家的姑娘和最高貴的夫人平起平坐”,但她的美麗沒能讓她過上貴婦人的生活,卻成了一個小科員的妻子,過著普通得讓人無法忍受的生活。這種強烈的反差,讓她陷入極度的痛苦和失望中,越發對虛榮的奢華生活產生渴望。“她沒有好衣裳,沒有首飾,什么也沒有。可她偏偏只喜歡這些東西……她心里總是那么強烈地希望自己能夠招人喜愛,能夠被人羨慕……”因此,愛慕虛榮就是她人格特點的集中體現,貫穿小說始終,這成為整篇小說的基石和鋪墊,也是瑪蒂爾德宿命的淵源。
《項鏈》首先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窺探了瑪蒂爾德的生活世界和內心世界。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在這種整體俯瞰下,上帝的觀察點也根據需要在瑪蒂爾德和她的丈夫、朋友三人之間不斷游移。總體看來:
故事開始時的觀察點集中在瑪蒂爾德身上,對其個人進行全方位展現;
接著故事聚焦在一個晚上,盧澤瓦爾先生拿著教育部長的請柬回家,故事的觀察點開始以對話的形式在二者之間來回轉換,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項鏈丟失和借錢還項鏈;
之后觀察點再次回到了瑪蒂爾德一人身上,描述了她辛苦還項鏈、滄桑變老的狀況;
最后瑪蒂爾德與福雷斯蒂埃太太相遇,視角觀察點再次通過對白在二人之間轉換,直至福雷斯蒂埃太太道出項鏈是假的真相。
觀察點在不同人物之間的游移是上帝視角的一大優點,能使小說富于變化,飽滿生動,產生畫面感,具有可讀性。然而,這種觀察點的游移,總體上還是落在主人公瑪蒂爾德身上,每次轉換都點到為止,不做過多鋪展,通過人物之間簡單的對話和心理描寫,迅速推進情節發展,既增強了故事的彈性,避免了拖沓駁亂,又協調了人物間的關系,突出了女主人公的命運走向。
上帝在觀察和講述瑪蒂爾德故事的同時,還對她的命運進行了評價。文中在瑪蒂爾德辛苦十年還完欠款后有這么一處描寫:
如果她沒有遺失那串項鏈,會是怎樣的情況呢?誰知道呢?人生多么離奇古怪,多么變化無常!只需一點點小事情就可能把您毀掉或者使您得救!
這一段話顯然是上帝對可憐的瑪蒂爾德的發問和評判,是上帝突破敘述者固定的格局,由旁觀敘述轉向了干預敘述。這一手法增強了小說的批判性、真實感和教育意義,道出了瑪蒂爾德的可憐可悲之處。
二、故事情節中的秘密
俄國民間文藝理論家普羅普在《故事形態學》中提出了關于角色與情節的著名概念——“功能”。功能是“從其對于行動過程意義的角度定義的角色行為”[3],“構成了故事的基本組成部分”[4]。據此,可將《項鏈》的故事情節分解為以下八個功能單位:
A1獲邀;A2借項鏈;A3參會;A4失項鏈;A5尋項鏈;A6借錢還項鏈;A7還錢;A8知道是假。
顯然,這八個功能單位是故事中最基本的事件,并按時間先后依次排列,但它們并不適用于普羅普提取的“外出”“禁令”“打破禁令”等功能的任意連接。因為普羅普的理論是采集一百個俄羅斯民間童話故事加以分析的,且著眼于行為本身,與人物無關,與特定故事的特定角色之間缺乏黏性。因此,他提出的功能組合連接只適用于童話故事,煩瑣生硬、有局限性,無法推廣到更廣泛的敘事作品中。
克洛德·布雷蒙在《敘述可能之邏輯》中對普羅普的功能連接進行了修正與優化。他提出了功能的“序列”,“三個功能一經組合便產生基本序列”[5],基本序列則由三個功能構成:新情況的形成、針對情況采取行動、行動的結果。這里,“這些功能在序列中并不要求前一個功能發生以后,后一個功能一定要跟隨發生”[6],而是考慮了各種情形:新情況的形成具有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情況形成后要么采取行動,要么沒采取行動;行動的結果可能成功,可能失敗。這種改變“采取的是演繹法,是從可能性、變動性出發,來‘修改方法’”[7],為每個功能的產生和發展添加了必要的前因和后果,梳理出了各功能之間的內在邏輯,使其適應了更廣泛的敘事作品。
以《項鏈》八個功能做分析:瑪蒂爾德的丈夫供職于教育部,所以才有可能獲得舞會邀請,此時A1形成;瑪蒂爾德在丈夫的勸說下采取行動,為舞會購置衣物,向朋友借項鏈,此時A2形成;結果她成功了,在舞會上成為最閃亮的女主角,行動達到了目的,此時A3也成立。布雷蒙的基本序列完全符合《項鏈》的故事情節。但《項鏈》的故事情節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基本序列,而是一個由基本序列相互銜接的復合序列,功能與功能之間有密切邏輯聯系,一環扣一環,呈鏈接式,即前一個序列的結尾同時又是下一個序列的開始,如此接續直至故事結束。顯然,小說的核心故事情節就是這樣一個鏈接式的復合序列,步步深入,層層推進。
在《項鏈》的鏈接式復合序列中,對情節發展至關重要的兩個功能單位是:A4失項鏈和A8瑪蒂爾德得知項鏈是假。
故事一開始是在平穩推進,但到了項鏈遺失這一環節,陡然轉折,短暫的舞會榮光隨著項鏈的丟失瞬間煙消云散,主人公的命運徹底改變。舞會上的一切虛榮和陶醉,都變成了一場痛苦的夢幻。瑪蒂爾德不得不為自己一時的虛榮埋單,因而賠上自己十年的生活。十年之后,“盧澤瓦爾太太現在看上去像個老婦人了。她已經變成窮苦人家的那種身強力壯,既冷酷又粗暴的女人。她頭發梳得亂七八糟,裙子穿得歪歪扭扭,兩只手通紅,說起話來嗓音很響,洗起地板來用大盆大盆的水沖。”原先還能雇得起小保姆的瑪蒂爾德已經連從前的日子也過不上了,她的命運就像小說中評價的那樣“只需一點點小事情就可能把您毀掉”。
故事情節本可以到瑪蒂爾德用十年青春還項鏈,從此“過起了窮人過的可怕生活”處旋即收尾。至此,瑪蒂爾德受到了教訓,小說對法國彌漫的奢靡成風、物欲橫流的社會弊病的揭露和批判已達圓滿。然而,莫泊桑卻設計了序列中的最后一個功能A8,讓瑪蒂爾德的人生落入了更加殘酷、更加諷刺的境地。瑪蒂爾德巧遇福雷斯蒂埃太太,福雷斯蒂埃激動地說:“啊!我可憐的瑪蒂爾德!可是我那串是假的。它頂多值五百法郎……”小說至此戛然而止,原來為瑪蒂爾德帶來榮耀的項鏈竟然是假的,而她卻為這個假項鏈賠上了十年的青春,多么諷刺,多么可悲,瑪蒂爾德所向往的上流社會竟是如此一個讓人分不清真假的虛幻名利場。故事的情節至末尾再次劇烈轉折,懸念在最后一刻開釋,如晴天霹靂,如酒后醒鐘,巧妙收尾,讓人驚嘆不已。作者運用“留白”手法,不再描寫瑪蒂爾德知道真相后的反應,更不會對其之后的人生展開敘述,讓整部作品的高潮到了頂點卻陡然消失,一切全憑讀者與文本的交流,留給讀者自己去猜想。小說的曲折性、懸疑性、諷刺性升華到了頂點,讓人回味悠長。再多一句,都是廢話!
三、故事時間的魔力
時間問題是研究敘事文學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問題。對虛構故事發生的總時間進行分配可以控制故事速度,實現特定的敘事效果。
小說中的時間可以分為“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故事時間即是虛構故事發生和演變的自然時間或物理時間,而敘事時間則是這些虛構故事在文本中呈現的分配狀態(表現為篇幅長短),它可以將故事時間加速、減速、暫停或打斷,這種狀況“會有意無意間透露出作者的寫作意圖、社會立場和價值觀念,并且也會直接影響到接受者對文本意義的理解與闡釋”[8],因而可以達到獨特的美學效果。敘事時間和故事時間在多數情況下是不相等的,這種不相等反映為“時距”關系差異,即“這些事件或故事段變化不定的時距和在敘述中敘述這些事件的偽時距(其實就是作品的長度)的關系”[9],并引發敘事速度變化。結構主義學者熱奈特將這種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的時距差異分為四類:敘事時間無限大于故事時間為“停頓”;二者相等為“場景”;敘事時間小于故事時間為“概要”;故事時間無限大于敘事時間為“省略”。
在具體文本中,故事時間的時距由虛構事件在文中出現的秒、分、時、日、月、年計量,敘事時間的時距以行、頁等文本長度確定。時距差異所產生的獨特效果,在《項鏈》中有著巧妙的反映。
小說開篇六段內容是對瑪蒂爾德的全面刻畫,屬于故事鋪墊,沒有形成情節,因而它的故事時間幾乎為零,但其大量的篇幅占據著重要的敘事時間,故其屬于“停頓”現象,是對故事背景的交代,這種背景決定了主人公的命運。
對于小說余下的部分,仍以八個基本功能作為分析對象:
A1:“沒想到一天晚上……想法買一件漂漂亮亮的連衣裙”。夫婦接到舞會邀請并討論買衣服參會。約34行,故事時間只有晚上二人談話的幾分鐘時間。
A2:“晚會日子近了……這三天來你怎么變得這么古怪……第二天她到她的朋友家里去……帶著她的寶物急急忙忙走了”。瑪蒂爾德買衣服后借項鏈。約34行,故事時間約4天。
A3:“晚會的日子到了……她如瘋似狂地跳著舞,別的什么也不去想了”。瑪蒂爾德在舞會上大出風頭。約8行,故事時間1個晚上。
A4:“她將近凌晨四點才離開……怎么會不見了……這不可能!”乘車回家后猛然發現項鏈丟失。約22行,故事時間只有舞會結束后的幾個小時。
A5:“他們在連衣裙的褶層里(尋找)……她丈夫七點鐘左右回來了……她呢,等待了一整天……一個星期后他們完全絕望了”。夫婦倆到處尋找項鏈卻無果。約27行,故事時間約8天。
A6:“第二天,他們帶著首飾盒子……要求珠寶商人在三天之內不要賣出去……她不會把她看成一個小偷吧?”二人借錢還項鏈。約22行,故事時間約4天。
A7:“盧澤瓦爾太太過起了窮人過的可怕生活……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十年……”瑪蒂爾德夫婦十年還錢的苦難生活。約21行,時長達10年。
A8:“沒想到有一個星期日……”至末尾,瑪蒂爾德與朋友巧遇并得知項鏈是假。約29行,故事時間只有二人見面的幾分鐘。
由以上分析可知,A1-A3故事段所用篇幅(敘事時間)逐步遞減,在與故事時間對比后發現,這一區間逐步由“停頓”轉向“概要”。A1-A3是瑪蒂爾德追逐榮耀的過程,敘事時間呈現出加速度的狀態,在A3處故事急劇加快,寥寥數行的舞會榮光不過是一閃而過的夢幻。A4失項鏈環節再次回到停頓狀態,之后再加速。A5、A6敘述舒緩,基本算作“場景”,處于故事的逐步轉折過程。A7是瑪蒂爾德十年還項鏈的苦難生活,故事時間極長,敘事時間卻極短,但除去還錢前后狀態的描寫,幾乎是用“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十年”一筆帶過,可以看作“省略”。十年痛苦生活與舞會榮光的瞬間即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二者敘事時間在文中最少,卻一個是榮光,一個是苦難,諷刺性和批判性被調動起來。末尾的A8處故事時間較短,敘事時間卻很長,說明小說幾乎是以一種極為緩慢的“停頓”姿態收尾的,可以看作對前文加速的一種調劑和緩沖,在情節上將懸念最后釋放,留給讀者無限回味和遐想。
通過技術上的煩瑣證明,不難發現莫泊桑在《項鏈》小說的敘事時間分配上可謂用心良苦,故事呈現出“加快—平緩—加快—放慢”的整體節奏,極具不平衡感,讓讀者閱讀時的心理體驗更加曲折,特別是對舞會榮光和十年苦難的加速度描寫,凸顯了瑪蒂爾德追求虛榮之“虛”。而結尾的舒緩節奏則強化了作品的戲劇意味,是作者對瑪蒂爾德十年之苦的嘲諷,加深了虛榮“虛假”這一核心命題。
參考文獻
[1]本文所引原文內容及對文本的分析均采用郝運、王振孫譯.莫泊桑中短篇小說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428-436.
[2]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41.
[3][4][俄]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M].上海:中華書局,2006:18.
[5][6][法]克洛德·布雷蒙著,張寅德編選.敘述可能之邏輯[A].敘述學研究[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154.
[7]王鍾陵.法國敘述學的敘事結構研究及建立敘述學的新思路[J].學術月刊,2010(3).
[8]徐曉軍.論敘事節奏與敘事效果的達成——以莫泊桑的《項鏈》為例[J].甘肅理論學刊,2011(3).
[9][法]熱拉爾·熱奈特著,王文融譯.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