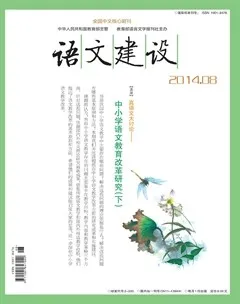詩人之“目”——多維立體析《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首流傳歷代的五言絕句,其中“目”字是全詩的核心。詩的題目點出了在哪里看——目之視點,前兩句描寫的是看到了什么——目之映象,最后兩句點出如何才能看得遠——目之超越。只有深入理解“目”,才能感受詩中咫尺萬里、雄渾壯闊的氣象,理解詩的內涵哲理。
一、目之視點
視點(這里指時空視點)是人們觀察或呈現對象世界時采用的時空角度和位置,包括時空的起點和移動的順序。《登鸛雀樓》作者的視點既是固定的,又是流轉直至消逝的。通過了解視點,能夠感悟作者的思想,更好地理解文本。
固定的視點。從詩的題目就知道詩人視點在鸛雀樓。詩人在登樓的過程中,視點由低到高,視線由高至低,西望至“白日依山盡”,東望至“黃河入海流”。隨著詩人視野愈來愈寬,詩的視域愈加寬廣,氣勢愈加非凡宏偉。
流轉的視點。據《蒲州府志》記載:“鸛雀樓舊在郡城西南黃河中高阜處。”假如我們親臨古鸛雀樓,踏著詩人的腳印來到最高層,上下左右瞭望四方,感受古人之眼界、古詩之氣度時,定會詫異。因為我們向西極目遠眺,是一望無際的八百里渭河平原,看不到“白日依山盡”;樓下的黃河水正由北向南奔流不息,向東遠望更不見黃河蹤跡。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中條山位于鸛雀樓的東面偏南,它恰恰擋住了我們遙望黃河奔流向東的視線,我們看到的是“河流入斷山”(暢當《登鸛雀樓》)。那么,作者的視點在哪兒呢?
宋代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訓》提出了著名的“三遠說”:“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后,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古代詩人同畫家一樣,并不受一時一地的局限,被眼之目睹所障礙,他們可以仰山巔、窺山后、望遠山,視線如沈括所說“折高折遠,自有妙理”,他們的視點不是固定在一處,而是分布在多層的散點。他們可以“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遙游》),可以“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登鸛雀樓》正是如此。詩人在登臨鸛雀樓后,視點沒有固定在鸛雀樓,視線不受渭河平原、自北向南而流的黃河所局限,也不受中條山所障礙。他心靈的眼睛不停地“更上一層樓”,早已超越當下:既高遠近前中條山,又平遠天下之山;既仰視當空白日,又遠望紅日落山;既俯瞰眼下流水,又深遠入海黃河。詩人的視點,既在立身處又在思緒遼遠處,既在鸛雀樓又在浩然長空。他的視點是流動的、折轉的,由高轉平,由仰轉遠,由俯轉深,整個宇宙都在他的俯仰之間。
消逝的視點。“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詩人不斷地攀登高樓、超越高樓。他用俯仰往返的視線撫摩、眷戀著萬物,而萬物皆備于詩人,來親近、扶持詩人。詩人飲吸大山名川于胸懷,山川吸納著詩人之情之心。山川與詩人相互融化、彼此難分,“白日”“黃河”融化了詩人之心,詩人之意浸入“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之境。此時詩人的視點由外物轉向內心,凝聚了相融在一起的“物我”。隨著物我的徹底相融,詩人達到了“與萬化冥合”(柳宗元)的兩忘境界,隨之詩人的視點奇異般地消失了……
二、目之映象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是詩人心靈與宇宙相融而出的影像,它是詩人目之“映象”。該映象是一個多層立體畫面,具有表層、中層、深層結構。為了便于說明,本文把這幾個層次的景象稱為淺景、中景、深景。
1.淺景
董其昌說“詩以山川為境”,可見描摹山水者繁多。與其他山水詩相比,“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之淺景有以下特點。
一是日暮黃昏。淺景畫面描摹的時間是“白日依山盡”之“盡”、“黃河入海流”之“入”時。此黃昏時分,斜陽余暉染紅天角,返照山光水色,與大海渾然一體。落日沉沒,大地漸暗,暮色已起,銀灰色籠罩無垠大地。二是意象宏大。白日、高山、黃河、大海,在中華文化中都是宏大意象,內涵豐富(有專家專項研究“白日”,稱在唐詩中共出現650處,僅在李白詩中就達50處,其意蘊豐富多樣)。“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所描摹的宏大意象,白日運轉落山,大河奔流入海,為天地注入無限生機。三是意象關聯。“白日”為依山“盡”,“黃河”為入海“流”。大河滾滾北流,經華陰,抵潼關,挾渭水轉向東去,越過三門峽,奔赴無邊大海,與之交匯融合。宏大意象的交會,動人心魄、高深莫測。四是空間浩大。白日在西方高山目之所“盡”處,黃河遠在東方海陸相連處。天上之景,日月星辰、云霞虹霓,而作者只繪白日一輪放置遼遠。地上之景,山川草樹、樓閣亭臺,而作者只畫黃河一線,終極大海無邊。這是詩人精心經營的位置,畫面空曠簡潔至極,構圖恣意粗放,浩氣逼人。五是時空一體。在中國人傳統意識里時間空間不可分,如成語“日薄西山”“流年似水”就是例證。“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就是時空一體的畫面,它既是時間的流逝又是物體的運動,它是時間率領下的空間畫面。
可見,詩人描摹的淺景是一幅客觀山水圖,它不同于“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表達詩人內心的情感,而是把情感隱藏在景物中,用幾乎純客觀筆墨描述景象。這幅廣袤的“千里”景象,就是黃昏時分率領下的“白日”、高“山”、“黃河”、大“海”構成的氣勢恢宏的時空一體圖畫。
2.中景
淺景恢宏雄偉,特點耐人尋味。我們應該緊緊地抓住詩的關鍵字“盡”和“流”,細細咀嚼“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感受詩中描寫的時空動態變化,由淺景進入中景,體會其味。
時間的流淌。從詩句之間的關系看,“依山盡”的“盡”為仄聲置于句末,突出了時間較短;“入海流”的“流”為平聲位居句末,突出了黃河入海交匯的持續時間較長。“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就是短暫的時間流淌到長久的時間。從詩句內部關系看。在古人意識中,日出日落、大河奔流不息就是指時間永恒流動;與時間永恒流動相比,“依山盡”和“入海流”突出了日落和黃河入海之水交合消失時間相對較短。“白日依山盡”和“黃河入海流”就是短暫的時間流淌入永恒的時間流中。
意象的運動。“白日依山盡”是白日西落的過程,“黃河入海流”是黃河向東歸入大海的流動。它們的運動軌跡分別是:太陽的運轉—與高山相交—日的隱去,黃河水的流動—與大海相匯—黃河水的消失。意象的運動驚心動魄,極富意蘊。一是日的運轉、河的流動。“盡”“流”是日的東升后西落、大河由西到東奔騰不息入海的節點,由此可以想見浩瀚長空、無垠大地上,太陽的運轉和黃河流動的完美運動軌跡。二是意象與高山、大海相交。“依山盡”“入海流”都是意象之間的相交,特別是“黃河入海流”,“河”“流”都是平聲,“河”“海”“流”都有三點水,這從字音和字形上突出了大河與大海交匯的氣勢。三是意象的消失。“依山盡”之“盡”、“入海流”之“入”,就是白日隱于山后、黃河水融于大海,最終的消失。
空間的變幻。“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描述的浩大空間,是從燦爛到蒼茫虛無的變幻過程。燦爛,“白日”在字義(白指日光)和字形上(白和日都由“日”構成)突出了絢爛的太陽及燦爛的大地;蒼茫,白日依山“盡”,凸顯了日落時天穹的轉暗、大地的昏黃、宇宙的蒼茫;虛無,遙遠的白日、入海的河水,意味著對于近在咫尺的忽略,對于當下事物的省略,使得浩大的空間盡顯神秘虛無。
由上可見,中景是一張具有動感的視頻截圖,一幅充滿張力的畫面。它是一幅意象運動相交到消失、時間短暫到長久、空間燦爛到蒼茫虛無的宏大場景。《易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無往不復”是中華傳統的宇宙觀。“盡”“流”突出的是“無往不復”的關鍵節點,“往”之終點和“復”之起點,隱含了消失必會再運轉,短暫一定長久,蒼茫虛無必然再浩大燦爛的觀點。中景實際上就是無往不復的宇宙。
3.深景
由中景到深景的暗道仍是“盡”和“流”。我們只有在仔細體會中景滋味之時穿越其通道,才能隱約感受到深景的存在。
歌德在《浮士德》中說,“一切消失者,只是象征”。“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詩人所描繪的“盡”與“流”就是消失之景,是時間的流逝、燦爛的隱退、白日的落山、黃河的遠去。它們象征著“道”。宗白華說:“‘道’‘真的生命’是寓在一切變滅的形相里”,“‘道’就是實中之虛,既實既虛的境界”。“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所描寫的就是從有到無、從有限到無限、從實到虛,也就是既有既無、既實既虛的境界。可見,深景就是既實既虛的大道境界。
目之“映象”的淺景、中景、深景是為了便于說明問題而區分的,實際上目之“映象”是個多維立體的半透明結構,它是一個完形,一個渾然一體的有機整體。這個整體有外在之形、內在之真和核心之道,它既描摹了宇宙大地的浩瀚恢宏和無往不復,又表現了詩人對道的思考,與天齊的胸懷和境界。這個整體既具有客觀性又具有主觀性,是主客不分的一元體。
三、目之超越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千古哲理名句,它告訴人們只有登高才能望遠的道理。“窮”字在這里是窮盡、窮究的意思,“千里”指廣袤的世界、宇宙,“更”指再、繼續,“上”指攀登、提高,“層”指層次、境界。登高望遠的深層含義,就是如果要想看到、看清、看透世界宇宙,既能看其表層,又能觀其中層和深層,就需要不斷攀登,提高層次,提高人生境界。
“欲窮千里目”,就必須“更上一層樓”,提高人生境界,超越眼睛之看。根據目之視點和目之映象,目之超越有三個關鍵。一是超越目之固定視點。目不能受所在位置的限制,要努力達到“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使心靈得到解放。二是超越目之所見。“五色令人目盲”,不能被眼見所障蔽,要看透世事,不斷提升人生境界。三是超越自我。要達到物我一體相融的“天地與我同生,萬物與我同根”的境界,從而對宇宙、人生獲得一種哲理性的領悟。
“更上一層樓”就是超越眼睛、超越自我,最終使精神得到自由,攀登至人生的最高層。此時人的靈魂得到釋放,視點得以流轉,既能望遠世界表象,又能深探宇宙奧妙,人與物相融合,靈魂得以逍遙自在。
閱讀古詩《登鸛雀樓》,通過詩人目之映象,可以感受宇宙的廣袤和奧秘,體驗詩人的廣闊眼界和深邃目光;通過古詩哲理名句,能夠直接感受詩人目之超越,理解古人深刻的思想;通過詩人流轉的視點,更能感受古人靈魂的自由和與天齊的人生境界。總之,通過詩人之“目”,既可以感受古詩雄壯氣象,體會其中道理;又可以深入理解古詩內涵,感受詩人的胸懷和氣度;更能修煉自我,使自己也努力做到窮盡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