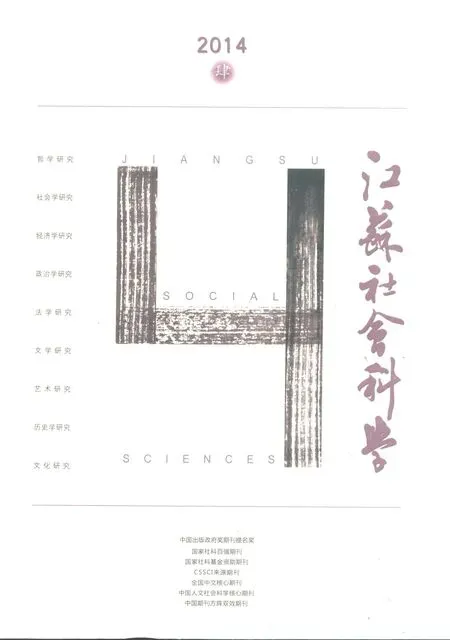全息:傳統糾紛解決機制的現代啟示
郭星華 李飛
全息:傳統糾紛解決機制的現代啟示
郭星華 李飛
熟人社會有大量的初級關系,也就會有初級糾紛產生。如果初級糾紛無法得到及時解決,就有可能演變成次級糾紛,繼而形成新的緊張和激烈程度更高的次級糾紛。在現代社會的語境下,法治基本只關注“此時此地”的次級糾紛,但有時并未使這些糾紛得到徹底的解決,也隨之埋下了將來發生更大糾紛的隱患。然而,反觀傳統社會在處理糾紛時所遵循的還原糾紛“全息”的過程,在修補初級關系的同時,盡可能防止發生新的次級糾紛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因此我們認為,傳統社會的糾紛解決方式無疑對現代社會有一個很好的啟示作用。
全息 初級糾紛次級糾紛 調解
自清末立憲修律以來,中國開始了漫長而曲折的現代法治建設之路。在取得法治建設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必須看到中國的法治建設一直深陷西方法治模式和法律文化的影響,而且建設進程對于我們而言更多是被動卷入:法治體系移植于西方,與傳統文化有著較為明顯的歷史裂痕[1]這種裂痕也是必然的,中國在被卷入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的同時,已經沒有時間依靠傳統文化自生出一套現代社會制度來適應這一體系,而中西文化內核的重大差異使得中國的某些社會制度包括法治體系與傳統文化表現出一定的不契合性。。于是,當“先進”、“文明”、“普適”的西方法治隨著現代化的大潮大舉推進時,被打上“落后”、“愚昧”、“地方性”標簽的傳統文化只能步步退讓,它所維持的地方秩序也在逐步瓦解。法治在現代社會固然有其總體上的合理性,但傳統文化的遺產在當今語境下絕不應該被一味地摒棄和批判,它同樣有其積極的歷史和社會價值[2]蘇力:《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和法治》,〔北京〕《法學研究》1998年第1期。。本文將從糾紛解決入手,結合相關社會環境來探討傳統糾紛解決機制的價值理念和運作邏輯,以期對現代法治建設有一些借鑒和啟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11JJD840005);北京鄭杭生社會發展基金會·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子項目《農村流動人口與同城化研究——以社會動員為視角》(13ZHFD07)的階段性成果。
一、初級糾紛與次級糾紛
糾紛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可以說,有人的地方就有糾紛。然而,社會中的大量糾紛往往源于人與人之間的生活瑣事,它處于糾紛金字塔(dispute pyramid)[1]參見William L.F.Felstiner,Richard L.Abel and Austin Sarat: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Blaming,Claiming…,Law&Society Review,Vol.15,1980-1981,pp.631-654.的底層,通過忍著、雙方協商私了就能得以解決,并不需要中立第三方的介入,我們將這類糾紛稱之為“初級糾紛”(primary dispute)。一旦雙方無法自行解決,相關的主張和利益訴求無法得到滿足,初級糾紛就會流向糾紛金字塔的高層從而得以升級,也就會對社會秩序形成了一定的沖擊,此時需要中立第三方的介入。這個第三方在現代社會可能是政府、司法部門或其他仲裁機構。我們將此類糾紛稱之為“次級糾紛”(secondary dispute)。很顯然,無論在緊張程度還是激烈程度上次級糾紛都要高于初級糾紛。如果將糾紛作為一個譜系,在這個譜系中,次級糾紛緣起于之前尚未得到解決的初級糾紛。如果次級糾紛依然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就會形成新的緊張-激烈程度更高的次級糾紛,很有可能造成流血沖突甚至人命案件,日常生活中的民事糾紛轉化為刑事案件就說明了這一點[2]我們在東北某市監獄調查得到的一個案例就是在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矛盾越積越深,最后因為一點小摩擦,造成故意傷害罪被判的。參見郭星華、曲麒翰:《糾紛金字塔的漏斗化——暴力犯罪問題的一個法社會學分析框架》,〔南寧〕《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儲卉娟:《從暴力犯罪看鄉村秩序及其“豪強化”危險:國家法/民間法視角反思》,〔上海〕《社會》2012年第3期。。

對于民間糾紛的處理,現代法治尤其是現代審判方式[3]本文的“法治”都特指“現代法治”,因為只有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解釋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法律問題才是有意義的,參見劉星:《現代性觀念與現代法治——一個診斷分析》,〔長春〕《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年第3期。即本文的“法治”更多從狹義來理解,尤其是指以程序、證據等為標志建立起來的現代審判制度。基本只關注進入其視野的“此時此地”發生的次級糾紛[4]需要指出的,這里糾紛的劃分有相對性和時間上的動態性,如在初級糾紛——次級糾紛這個時段上,初級糾紛是“彼時彼地”的事件,次級糾紛是“此時此地”的事件;而在次級糾紛——新的次級糾紛的時段上,次級糾紛則成為了“彼時彼地”,新的次級糾紛成為了“此時此地”。但現代法治只為“此時此地”設置了相應的制度空間。,并只對這一部分的糾紛做出“非白即黑”的裁判,以實現其程序上的正義。可是,法治面對的次級糾紛僅僅只是涉及到了當事人全部關系中出現糾紛的一小部分[5]王建勛:《調解制度的法律社會學思考》,〔北京〕《中外法學》1997年第1期;郭星華:《序》,載劉正強著《新鄉土社會的事件與文本——魯縣民間糾紛的社會學透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這樣一種“外科手術式”的“斷面式”[6]有學者將這種“斷面式”的處理過程稱其為“甩干”,即法律在面對具體案件時有一套固有的邏輯:通過舍棄道德、習慣、經驗等諸多非法律的元素,最終對案件做出權威性的“純粹”處理,從而完成“潔凈化”的目標。參見劉正強:《新鄉土社會的事件與文本——魯縣民間糾紛的社會學透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前言)、第106-115頁。處理方法雖然使糾紛得以暫時解決,但時常不能令雙方滿意,并且人們受損的社會關系未得到及時修補,也隨之埋下了將來新的次級糾紛乃至更大沖突發生的隱患。電影《秋菊打官司》對此有過生動的描述:秋菊最終討到了法律上的“說法”,但這個說法卻不是她希望得到的結果。在現實社會中,糾紛是呈譜系狀的,一起糾紛的產生往往會牽涉到過去的許多人和事[1]這種說法是相對的,一起偶然糾紛的發生,如一人將另外一人誤傷可能就只存在糾紛譜系中的一個時段。(即“彼時彼地”)。此時糾紛中受害的一方,在過去的事件中有可能是傷害他人的一方,法治如此“斷面式”的處理方式當然很難讓當事人服氣。
糾紛的譜系化存在決定了其實踐邏輯是“全息”的。所謂“全息”,是指部分能夠反映整體的全部信息,強調的是一種最大限度和最徹底的整體性,即“在一個整體中,不僅整體具有整體性,而且每個部分也具有整體性”[2]嚴春友、嚴春寶:《全息論對系統論與還原論的超越》,〔石家莊〕《河北學刊》2008年第2期。。將全息所揭示的這種“全整體性”以及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引入糾紛研究,很容易看到現代法治在糾紛解決中的局限:由于它將視野僅集中在一個部分(次級糾紛),致使糾紛的整體性沒有得到全部呈現。如北京房山區的一起案件:2005年,韓某6歲的兒子被張家13歲的兒子掐死,法院判決張家賠償韓某15萬多元,但兩年過去后韓某一分錢也沒拿到,怨恨在心的她把硫酸潑向了張家的女兒致其毀容。房山區法院依法判決韓某有期徒刑13年,并賠償受害者48.8萬元。宣判后,憤怒的韓某和張家父親在法庭上爭執起來,休庭后脫下法袍的主審女法官目睹這一幕后,怒斥張家在當初的賠償問題上違背良心。因為據法院調查,張家有兩輛車。糾紛是全息的,但法院卻只能以“此時此地”潑硫酸的事實依法判決韓某有罪,而不能溯及之前的糾紛(雖然在量刑上會有所考慮)。女法官也深知法治的局限,因而只能脫下法袍,以一種道德性話語表達自己情緒也實屬無奈[3]詳見《喪子母親硫酸潑仇家女被判13年,領刑后與原告再起爭執,法官庭后斥責原告沒良心》,〔北京〕《京華時報》2007年8月28日A08版北京·社會。。
糾紛的全息性要求第三方在解決糾紛特別是熟人之間的糾紛時應觀照到雙方當事人既往社會關系的糾葛,現今糾紛產生的歷史緣由和將來關系的修補。不僅依據“此時此地”的事實,還要追溯“彼時彼地”的事實,同時也需考量當事人雙方未來的關系走向,努力還原糾紛“全息”的過程。全息的傳統糾紛解決機制體現為一種“瞻前顧后”式的糾紛解決方式,“瞻前”,即在處理當前次級糾紛的同時也要追溯到雙方以前發生的初級糾紛;“顧后”,即處理當前次級糾紛的時候,要考慮當事人雙方關系的修補,并防止雙方有可能產生的新的次級糾紛。這一點無論是糾紛金字塔理論還是其他相關理論都有一定程度的忽視。而傳統社會的糾紛解決方式無疑較好地適應了糾紛這種“全息”式的特點,這也是我們提倡從傳統文化遺產中找尋可資借鑒的出發點。
二、全息與傳統社會糾紛解決方式的交融
“全息”式糾紛在傳統鄉土社會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文化根源。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明確指出,中國基層社會有兩大基本特性,即鄉土性和地方性。鄉下人離不開泥土,以種地謀生,世代定居成為常態;同樣,人們以村落為單位聚集而居,安土重遷,也就形成了地域上的限制和孤立的社會圈子。由此,鄉土社會就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一個熟悉的、沒有陌生人的社會[4]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頁。。在這樣一個以道德、禮俗、情感和經驗支撐維系的鄉土秩序中,鄰里鄉親的家長里短、磕磕碰碰固然不可避免,但很少溢出其共同體之外,大多消解于彼此間的血緣、親緣和地緣的關系當中。除了社會結構外,文化環境及其相關價值觀念的影響或許更具穿透力。李約瑟在談及中國文化時指出,“古代中國人在整個自然界尋求秩序與和諧,并將此視為一切人類關系的理想”。“和諧”不僅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訴求,也影響了人們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5]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93頁。。儒家倫理所體現的入世理性主義因素也要求人們能克己復禮,通過學與知來實現自身人格完滿的終極價值,以順應社會秩序的和諧[1]〔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03-206,219-222頁。。因此,一起糾紛(確切地說是“次級糾紛”)能浮出水面出現在公共視野,尤其是熟人的視野之中,很多情況下是由于之前初級糾紛等矛盾逐步積累的結果。人們能舍棄面子將次級糾紛拋入公共領域,足見此類糾紛往往紛繁復雜,較多的社會關系和人情世故粘附其上,在解決過程中如果不溯及以往,還原糾紛“全息”的過程,則很可能導致事實的不公和民眾內心的不滿,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
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是道德氣氛濃重,“融國家于社會人倫之中,納政治于禮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統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氣氛特重,確為中國的事實”[2]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20頁,第21頁。。在這樣一個注重人倫、禮俗的文化環境中,“秩序”的穩定和諧成為第一要務。糾紛的產生已經對當地社區、社群的道德倫理和聯結紐帶構成了挑戰,此時不以“情理”[3]滋賀秀三指出,清代的“民事審判,無論是官府是還是民間的,并不依成文法或習慣法來進行,而是根據每一具體事件的特殊性,以合乎‘情理’為最終的解決”。梁治平也指出,整個中華帝國的法律都是建立在情理的基礎上面。均參見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頁。黃宗智關于民間調解的“情理”也有相關論述,具體參見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頁。等對全盤關系進行調解而執意訴諸官府審判,這無疑宣告了當事人之間原有關系的解體。此外,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也沒有法律生長的土壤[4]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或者說法律發展的結果只能是與道德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帶有濃重的道德、倫理傾向[5]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頁;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02、278-322頁。,最終法律的地位也只能是“立于輔助道德禮教倫常之地位”,且“其法常簡,常歷久不變”[6]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20頁,第21頁。。如此之法在傳統社會中解決“全息”式糾紛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更多的是對糾紛當事人的一種威懾。因此,調解這樣一種游走在“情、理、法”之間,較好兼顧三者之間的關系,且帶有較強人格化傾向的糾紛解決方式被廣泛運用于“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社會,恰恰適應了中國傳統追求以和諧為整體目標的道德化社會秩序。不僅能夠達到息爭止訟的效果,也觀照了當事人之間的初級糾紛和潛在的新的次級糾紛,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生活訴求,體現了其真實的生活邏輯,有效維持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可以說,利于當事人未來利益的最大化和良好的社會效果是調解的正當性所在[7]范愉:《從訴訟調解到“消失中的審判”》,〔長春〕《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5期。。
三、法治與現代社會及其糾紛解決方式的契合
當人類由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其組成單元和組織原則則會發生本質的變化。傳統社會是一個基于血緣、情感、倫理等建立起來,有某種共同價值觀念的有機體;而現代社會則是由個人組成,以工具理性、個人權利等為基礎的契約聯結而成的群體[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6頁;金觀濤:《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頁。。簡而言之,傳統社會是一個關系親密的熟人社會,現代社會則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即費孝通先生筆下的“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的社會。由于傳統鄉土社會中熟人之間的信任在現代社會中漸趨消失,在無法形成穩定預期的前提下,作為一種建立在分離個體基礎上的契約,法律自然走向前臺,以此來規范社會秩序。此外,傳統社會權威體系的瓦解,傳統權威的衰落,對正式法律的需要便應運而生[9]勞倫斯·M·弗里德曼:《法治、現代化和司法》,傅郁林譯,《北大法律評論》1998年第1卷第1輯,第280-309頁。。可以說,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遷過程中,社會日趨多元化,個人權利和工具理性得到極大的張揚,契約也隨之具有了“高于傳統血緣、道德和有機的人際關系的正當性并成為一切社會制度的框架”[1]金觀濤:《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頁。。因此,從社會變遷伊始,法治(法律)[2]“法治”、“法律”、“法”等概念在具體涵義上有一定區別,限于主題和篇幅,這里不做過多探討,本文在廣義上對以上概念通用。便與現代社會表現出與生俱來的親和性和極高的契合度。
現代社會的高度復雜不僅基于人們之間關系的陌生化、匿名化,更是由于社會組織原則和價值系統的轉換,當然這一過程也必定伴隨著社會風險的增加,這就對人的行為合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這種合理性的實現必然表現為“非人格化”的法律統治,在一些學者看來只有從這個角度來認識法與現代社會的關系才可能是深刻的[3]梁治平:《法辯——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7頁。。而法律統治的非人格化則要求法律的“形式化”[4]在韋伯看來,法律的形式化是指“在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只有具有確鑿的一般性質的事實才被加以考慮。這種形式主義又可分為兩種:具有像感覺資料那樣能被感知到的有形性,才可能是法律與之有關事物的特征……另一種類型的形式主義法律表現為通過從邏輯上分析意義來揭示與法律相關事實的特征,以及被明確界定的法律概念是以高度抽象的法規形式構成的和應用的”。轉引自公丕祥:《韋伯的法律現代性思想探微》,〔哈爾濱〕《學習與探索》1995年第5期。,注重程序、證據和邏輯,追求一種普適性價值。在韋伯看來,法律的形式化是法律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和集中體現,也是現代法治區別于傳統法治的基本尺度[5]公丕祥:《韋伯的法律現代性思想探微》,〔哈爾濱〕《學習與探索》1995年第5期。。因此,現代社會中人們之間的關系處理、糾紛解決就被置于這臺工具或技術合理的“形式化法律”的機器之下。在審判車間的流水線上,受證據、程序和邏輯的操控指示,一個個案件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在案件的生產過程中,法律的形式化決定了它僅需要關注當下“次級糾紛”本身,其他的道德、人情、禮俗、關系這些傳統社會色彩的元素在這里均需讓位,或者進一步說是被法治所壓制。法治在現代社會中取得正當、合理的地位凸顯了人們之間關系的契約性,社會組織原則和機制的變化也使得現代社會并不需要像傳統社會一樣重視對受損關系的修補以防止新的次級糾紛的產生,“全息式”糾紛及其解決方式在現代社會似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四、全息式糾紛解決方式對現代社會的啟示
毋庸置疑,法治與現代社會之間存在很高的契合性,法治也在維持現代社會秩序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過有一點需要強調,“現代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組成的契約社會”作為一個學術命題總體而言沒有異議,但就現實而言并不完全符合實際。即使現代社會已經發展到很高程度,在其整體框架下依然還有“熟人社會”的存在,正處于社會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更是如此。城鄉二元結構框架下的農村自不待言,即便是城市社會還是存在血緣、地緣和業緣關系,甚至在一些行業還出現了次級關系的初級化現象[6]王思斌:《中國人際關系初級化與社會變遷》,〔北京〕《管理世界》1996年第3期。。因此,在現代法治的語境下,面對現實生活的高度復雜性,如何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構筑和規范良好的社會秩序是一個值得進一步反思的問題。
由上述命題反觀具體現實,可以發現“熟人社會”其實就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彼此間仍保持著某種“身份”的對應,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在今天依然有很強的解釋力。理性籠罩下的現代社會既然還有熟人社會存在的土壤,對“全息”式糾紛及其解決方式的討論也就有了現實意義[7]不少學者也指出了中國社會在變遷過程中一些傳統村落共同體出現了虛無化的現象,人際關系也呈現理性化和原子化的態勢。應該說此類判斷沒有問題,但只要存在初級關系就有初級糾紛發生的可能性,若初級糾紛不能及時解決,次級糾紛乃至更為激烈新的次級糾紛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看來,與其說“全息”式糾紛與現代社會是天然抵牾,毋寧說相對西方,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更為復雜。脫胎于傳統,至今仍帶著鄉土秩序鮮明胎記的中國社會,道德、禮俗、倫常、情感和經驗在秩序建構中依然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我們承認法治保證西方現代社會合理運轉,造就資本主義燦爛文明的同時,也要看到在中國古代“法治”從來都不是正常社會必需的一部分,僅僅是服從文化的根本追求,實現社會“絕對和諧”的一種手段[1]〔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四版),張理京譯,馬清槐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88頁;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08頁。,因而探討現代法治與中國社會的磨合也就是研究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的題中之義。況且目前法律大多由西方社會移植而來,而非自發內生,如果將法律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它也就必然存在與本土資源的適應與沖突。這一點在規范和構建熟人社會秩序,特別是解決“全息”式糾紛時顯得更為突出,秋菊們的困惑也就由此而來[2]如上文所述,影片《秋菊打官司》展示了現代法治在解決熟人之間全息式糾紛時的弊端,不僅造成了秋菊的困惑和不解,甚至秋菊有可能會遭到村落的“驅逐”和“流放”這樣極為嚴厲的處罰。讓我們做一個大膽的想象:一個可能的畫面是秋菊在村中受盡蔑視,無人與之相處,在無法忍受現況后,只好收拾行囊,抱著孩子,和丈夫一起帶著愧疚與不舍,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這個村莊。。
熟人社會中“全息”式糾紛之所以難以通過法治徹底解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證據和邏輯推理為基礎的現代法治發生作用的前提是分離的、原子化的個體社會,而熟人社會中的人們卻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有一定生活聯系的群體,因而現代法治在這樣的環境中常常不能有效運作[3]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頁。。此外,糾紛當事人之間的初級關系,以及初級關系上附著的道德、情感、人格等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這種類型的糾紛某種意義不是“事實”,而是“關系”,或者說作為“標的”,它本來就無法化約為事實[4]劉正強:《新鄉土社會的事件與文本——魯縣民間糾紛的社會學透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頁。。因而,形式主義的法治在面對此類“整體性”糾紛時往往無法下手,其結果是只能就糾紛本身進行強制斷面切割。對于當事人而言得到是程序正義,失去的可能是永遠無法彌合的親密關系,甚至引發新的緊張和激烈程度更高的次級糾紛;對于社會而言是法治的又一次精彩出場,失去的則是社會秩序的破損。
那么,在現代法治社會的語境下,應該如何處理熟人社會中的“全息”式糾紛?前文所述的“調解”這一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是否還有用武之地?毫無疑問,答案是肯定的。調解在當今社會多元糾紛解決體系中依然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通過分類管理,對于“全息”式這類熟人間的糾紛盡可能采用調解的方式,在解決次級糾紛的同時,修補當事人之間的初級關系,而不是將其全部置于法治審判的規制之下。這里所說的調解[5]本文并不打算對調解類型對進一步的嚴格細分,更多只是從調解的一般性意義上對其進行討論。,從解決主體看,不僅包括訴訟外通過中立的第三方促成雙方當事人在自愿的基礎上達成一致,也指在審判的框架下通過法院的工作來促成雙方形成的和解,并且要特別重視雙方當事人的主體作用以及交涉性的合意作為其正當性基礎;從解決方式看,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創新。現代法治社會的調解理應包含一定的契約精神,從而與傳統的“和稀泥”式的妥協、權威主義或威壓性的調解區別開來[6]季衛東:《當事人在法院內外的地位和作用》(代譯序),載棚瀨孝雄著《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第7頁。。通過調解這樣一種兼顧“情理法”的糾紛解決方式,還原糾紛全息的過程,以達到雙方利益的平衡,同時盡可能杜絕新的次級糾紛的發生,以維持一種長遠、穩定的關系。
法治與現代社會的契合,法治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這里無需再贅述。我們只是強調法治應當回應社會的真實需求,法治的源泉和真正基礎是社會生活本身[7]蘇力:《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和法治》,〔北京〕《法學研究》1998年第1期。。此外,在現代法治建設過程中還需從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立足當下,借鑒傳統是現代法治建設的必由之路。如果不顧社會的需求,一味強行地用法治審判來切割真實的生活,將人們的全部關系都置于法治的監管下,那很可能“造就一個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1]〔美〕羅伯特·C·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鄰人如何解決糾紛》,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頁。。從另一個角度看,調解也是廣義法治的一部分,雖然調解與審判在法社會學理論中往往被構建為兩種相互對應的糾紛解決方式,但實際上二者是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的。即使是通過調解方式完成的糾紛解決也并不是在與審判無關的地方獨立地發揮作用,而是在法律制度的蔭影下,與審判、判決制度的現實機能密切相關[2]〔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頁;Marc Galanter,“A Settlement Judge,not a Trail Judge:”Judicial Med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Law&Society,1985, Vol.12,No.1,pp.1-18.。可見,將現實生活中的糾紛解決過程截然加以區分是不可能的。因為相關影響因素總是混在一起,不斷流動的,且隨著糾紛當事者、利害關系者的利益所在、力量對比等狀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3]〔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14頁。。
五、結語與討論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西方社會的法律以純粹形式和高度合理著稱,因而也就保證了西方社會秩序的協調運轉。而東方法律的本質是價值合理性的,追求的是實質原則[4]〔德〕馬克斯·韋伯:《法律社會學》,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頁;公丕祥:《韋伯的法律現代性思想探微》,〔哈爾濱〕《學習與探索》1995年第5期。。或許韋伯在這里已經做出了自己對東西法律文明價值上的判斷,但也正是他所肯定的西方形式理性在后來為他構筑了一個“理性的牢籠”。這個牢籠不僅使韋伯個人在思想脈絡上陷入掙扎,也是西方社會秩序發展危機的最好注腳。這使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東方法律文明的“價值合理性”(實質原則),可能對我們解決實際糾紛,構建和規范社會秩序更具啟發性和建設性。我們在本文中提出“全息式”糾紛及其相應的解決方式正是繼承和借鑒東方法律文明的體現,同時也是對浸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國家法治觀保持一種警醒態度。這種反思源于我們對歷史的感知以及當下生活經歷和切身體驗的理解[5]強世功:《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體現為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它使我們走出西方法治萬能的迷陣,真正關注中國社會發展的真問題,關照普通民眾真實的社會訴求。而本文所做的努力只能算是這方面一點小小的嘗試。
應該說,在當今社會“全息”式糾紛依然有其普遍的意義。不僅在熟人社區,在非熟人社區類似糾紛也時有發生,屢屢出現的惡意報復事件就是明證。法治在處理此類糾紛時很少能還原糾紛全息的過程,雖然在量刑等方面有所考慮,但基本還局限于次級糾紛本身。基于其形式化的屬性以及由此導致的斷面式視野,對初級糾紛的關注較少。即使有,也只是法治的運作者——法官個人的“造法”。此時法治展示給我們的更多的是“邏輯面相”,而其“經驗面相”則被懸置或隱藏,由此糾紛當事人實現了程序上的正義和公平,而實質正義的需求可能并未得到滿足。“法的生命不是邏輯的,而是經驗的”(霍姆斯語),包括法治在內的一切制度只有關注民眾的生活向度,致力于解決民眾的實際問題才能維持其生命的活力。
其實,各個社會都有共同點,也都有自身的特色。現代法治之所以在西方社會能取得成功與其社會結構、法治傳統不無關聯。西方社會的人們有了糾紛是不是都會不管不顧地走進法庭將其付諸于訴訟?很顯然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說西方社會也存在一個個小的“熟人社會”,即使是商人交易這樣的陌生人圈子,很多時候人們也并不簽訂法律合同,而是依靠信用維持交易的進行。這不僅沒有產生大量的商業糾紛,反而有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6]Stewart Macaulay,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A Preliminary Stud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3,Vol.28,No.1,pp.55-67.。另外,西方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ADR)的勃興也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可見,即使在法治高度發達的西方,現代法治也并未一統天下。而民間習慣制度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法律精神的重構后也并沒有消失殆盡,因為人類社會對某些規則的需求終究不是以精英理性建構為基礎的[1]淡樂蓉:《論藏族“賠命價”習慣法與國家法的互動及其發展趨勢》,〔濟南〕《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
對西方中心主義法治觀的反思還需要強化我們對自身文化自覺和自信的意識。以調解為例,近年來調解作為一種糾紛解決的重要方式在西方社會得到了廣泛應用,其本質原因在于調解等非訴訟解決方式在幫助人們實現正義的同時,也適應了其經濟、快捷、符合情理地處理糾紛的需求。而我國調解發展的狀況卻不盡人意,在經歷了建國后和改革開放初期極端化的發展后(如“調解為主,審判為輔”、“著重調解”等方針)[2]王建勛:《調解制度的法律社會學思考》,《中外法學》1997年第1期;強世功:《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頁。,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調解的衰落也就成為必然。當現在重新對調解等非訴訟解紛方式加以重視時,我們推崇的卻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ADR,對有悠久歷史的傳統調解則不以為然[3]范愉:《以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保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北京〕《法律適用》2005年第2期。。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固然需要學習,但“出口轉內銷”的教訓也著實不少。立足自身的基礎上學習西方,同時貼近普遍大眾的生活,滿足民眾的生活需求才是調解制度將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方向。
當然調解與審判一樣,并不是一劑“萬能藥”或“宇宙藥”,也有其無法克服的弊端。就“全息”式糾紛而言,這種類型的糾紛多發生于關系親密的當事人之間。雙方如果撕破臉皮,把糾紛鬧到法庭,意味著彼此間的關系可能面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這給調解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因此,防患于未然,將糾紛特別是次級糾紛化解于發生的早期,或許是此類糾紛解決的出路之一。此外,對調解方式的過分強調是否會像一些學者所擔心的那樣對國家法律體系產生不良影響,如司法開始脫離法治預期的軌道,糾紛解決逐漸脫離法律的規制;對審判制度形成沖擊[4]范愉:《從訴訟調解到“消失中的審判”》,〔長春〕《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5期。;造就腐敗空間形成新的不公正等問題都需要我們長期加以關注。很明顯,如果單從價值判斷和邏輯推論來理解法治顯得過于理想主義,但隨著現代法治理念越來越向現實主義回歸,更多反映普通民眾生活向度,符合民眾生活邏輯的法治的推行,或許會讓秋菊們少一些不解和困惑,得到他們想要的那一個“說法”。
〔責任編輯:方心清〕
Holography: Modern Implications of Traditional Mechanism of Dispute Resolution
Guo XinghuaLi Fei
There are much preliminary relationships in the society of acquaintances,where preliminary disputes occur.If a preliminary dispute has not been solved,it can develop into a secondary dispute, which will become more intense and fierce.In modern society,rule-of-law just focuses on the secondary dispute under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but it cannot be solved completely sometimes.As a result,more serious disputes are likely to be caused.However,in traditional society,the dispute could be solved by means of returning to dispute holography,which would fix up preliminary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avoiding subsequent secondary disputes.Therefore,the mechanism of dispute resolution in traditional society has implications for today.
holography;preliminary dispute;secondary dispute;mediation
郭星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100872
李飛,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日本愛知大學中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