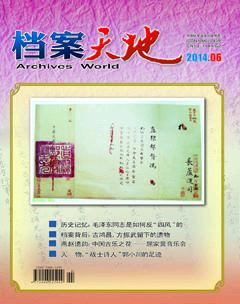“戰士詩人”郭小川的足跡
烸鉑
抗日風潮中的小詩人
1919年9月2日,郭小川出生于河北省豐寧縣風山鎮(原屬熱河省)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庭。父母親都知書達禮,父親郭覺生,前后教了四十多年書;母親李有芳,當過幾年縣立女子小學校長。他3歲起識字,5歲讀《詩經》。在小學念書時,郭小川已經明顯表現出對文學的興趣。幼年從父母那里受到的良好文學熏陶,為郭小川以后成長為一名革命詩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3年,由于日本侵略軍侵占了東北三省,郭小川一家避難到了北平。在1936年北平學生舉行的“六一三”大示威運動中,郭小川自愿擔任糾察隊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的民族解放先鋒隊。不久他考入設在北平的東北大學工學院補習班,學名郭健風。在抗日救亡的革命大潮中,郭小川迅速成長起來,開始展露寫詩的才華。他開始用“郭蘇”、“健風”、“湘云”、“登云”等筆名寫詩,不少作品發表在當時北平的救亡刊物上。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引起了全民抗戰,郭小川由東北大學“民先”組織聯系,從北平幾經曲折到了太原,在那里報名參加了八路軍。9月22日,郭小川和康世恩等二十多個青年學生,在王震、關向應、肖克等人帶領下,來到八路軍120師師部,受到了師長賀龍和師參謀長周士第的親切接見,并分配到第359旅,成為這個隊伍中光榮的一名抗日戰士。入伍以后,郭小川先在旅政治部的“奮斗劇社”工作。后隨部隊從河北的平山,到山西的孟縣、榆次等地。參軍后不到兩個月,郭小川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郭小川擔任了旅司令部的機要秘書,在王震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在戰斗工作之余,他寫了不少詩歌和劇本,有些詩如《黨的生日》刊載在當時359旅的《戰聲報》上。有代表性的還有《熱河曲》、《我們歌唱黃河》等。
1941年1月,部隊首長送他到延安學習。從這時起到1945年7月,他在延安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和中央黨校三部學習。在延安,郭小川積極參加了毛主席領導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是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他拿起筆來歌頌我們偉大的黨,贊譽黨的革命事業。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毛澤東之歌》,他以樸素而誠摯的階級感情把第一支頌歌獻給毛主席。另外,他還寫了《一個聲音》、《草鞋》以及《老雇工》等詩作。1942年5月23日,郭小川參加了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后,他積極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深入基層,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并把在群眾中學到的民間秧歌,改造發展成為新型的秧歌劇。此外,郭小川和中央黨校的其他同志對古老的京劇藝術進行了一次大膽的革新,嘗試編演了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該劇公演時,毛澤東兩次觀看該劇,親筆寫信,稱贊這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在國家民族的韻律中寫作
黨的“七大”在延安勝利召開后,延安干部遵循“七大”路線奔赴各個戰場,投入更加波瀾壯闊的斗爭。1945年10月,郭小川背著背包,回到自己家鄉任熱河省豐寧縣縣長,熱西專署民政科長,還領導了縣支隊清匪反霸工作。1948年夏天,郭小川被調到黨的宣傳部門工作。從1948年6月至年底以前,他擔任中共中央晉察熱遼分局的機關報《群眾日報》的副總編,兼任《大眾報》的負責人。同年12月,平津戰役打響,郭小川隨軍入關。天津解放后,郭小川擔任《天津日報》第一任編委兼編輯部主任,為黨報寫了大量的社論、短評。
1949年5月,郭小川隨軍南下,6月,被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宣傳科副科長,不久任宣傳處處長。1951年7月,他又被調到中南文藝戰線任領導工作。這期間,郭小川一直在中南地區從事黨的理論宣傳工作,經常為黨報起草包括社論在內的各種評論。他把自己學習黨的方針政策的心得體會一一記錄下來,寫了大量的政論,深入淺出地宣傳毛主席倡導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由于郭小川在宣傳工作上的突出表現,1953年3月7日,黨中央調郭小川到中央宣傳部任理論宣傳處副處長,一年后又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1955年,他又被調到中國作家協會任秘書長、黨組成員,以后又擔任黨組副書記。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歷經戰亂,百廢待興。作為一個革命戰士和人民詩人,郭小川義不容辭地再次握住詩筆,熱情洋溢地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斗爭和許多普通的斗士”唱出了最雄壯的頌歌和戰歌。其間,他先后創作出《投入火熱的斗爭》、《向困難進軍》、《在社會主義高潮中》、《把家鄉建設成天堂》、《人民萬歲》等膾炙人口的詩篇。這些詩,隨手一掬,都閃耀著哲思的珍珠,都是振奮人心的戰斗號角。
1955年至1956年,郭小川寫了一組詩,題名叫《致青年公民》。組詩一經發表,立即引起廣大讀者的喜愛和熱議。它的巨大魅力,不僅在于內容上充滿革命朝氣,在于詩歌語言的鏗鏘有力、抑揚頓挫,還在于它那新穎和富于音律美的排列形式。他認為,音樂性是詩形式的主要特征。詩歌的音樂性還是一個群眾化民族化的問題。為了把握詩歌的音樂性,作者只有多向我國民歌和古典詩詞吸取營養。他自己寫一首詩,雖然大多數時候是因為深入生活第一線,激情噴涌,一氣呵成,但也不乏仔細推敲,千錘百煉之作。他說:“詩,應當是由一個個最準確表現內容的、新鮮的、富麗的句子所組成。”一首詩,不但要有別具一格的語言,尤其是從人民群眾那里學習和積累來的語言,還要有意味深長、引人思索的警句。而他的詩,正是這樣實現著,體現著。
這期間,他曾一度出訪,參加國際性的作家會議,遵循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為建立國際文學界的反帝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這期間,他寫了不少好詩,歌頌祖國的躍進,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如《縣委書記的浪漫主義》、《正當山青水綠花開時》、《雪兆豐年》等。除此,他還精心創作了優秀的長篇敘事詩《將軍三部曲》。郭小川是一位政治性很強的詩人,其政治熱情之高、之強烈,遠遠超出一般作家詩人。他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極力謳歌革命,謳歌時代。
1960年春,郭小川到內蒙古自治區的草原鋼城包頭深入生活,進行參觀訪問。看到祖國第一個民族自治區內蒙古結束了“手無寸鐵”的歷史,看到蒙古族第一代鋼鐵工人變山石為寶的壯舉,那草原上流淌的鋼花,如春風一般催動了詩人心上的歡樂之花。他學習并運用民歌形式,寫下了《平爐王出鋼記》,為草原上噴射出來的“跟天安門的焰火成了對對”的鋼花歡呼。全詩共分三個部分:“五一節的焰火飛上天安門”、“看鋼人等看那打頭的鋼”、“平爐王的鋼水出來了”,這首詩既融有陜北民歌的風格,也明顯有群眾口語化的色彩。早在1958年,郭小川就在一篇題為《詩歌向何處去?》一文中提出,社會主義詩人要向“人民群眾的詩——新民歌”學習,吸取其中精華部分的養分,再為廣大的勞動人民寫出革命新詩。對于植根于中國的土地、植根于人民群眾中的充滿活力和生機的新民歌,郭小川至為推崇。
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嚴重困難時期。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國民經濟的基本比例完全失調,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處于嚴重的不平衡狀態,加上自然災害和一些國際原因,全國物質生活處在嚴重匱乏之中。但人民以頑強的毅力和革命干勁,克服了無數困難,經受了種種考驗,沖出了低谷,取得了巨大的勝利。1962年初,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郭小川認真學習領會毛主席的講話,并獲得了一年的創作假期。1961年2月,他被安排到遼寧鋼鐵和煤炭生產基地的鞍山、撫順參觀訪問,搜集素材進行創作。東北發生的巨大變化使他十分激動。他熱情飽滿,勁頭十足,決心把中國工人階級克服困難的沖天干勁寫出來,既是歌頌他們,也鼓舞全國人民。為了創作,他不顧勞累和身體不好,甚至放棄了春節回家休假,和鋼鐵工人生活在一起,和他們同戰斗,共歡樂。經過長期積累,他創作出《鞍鋼一瞥》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出鋼的時候》和《追蹤老孟泰的腳步》等反映鋼鐵工人生活的詩篇……接著他連續寫出了幾十首好詩,結集出版了《甘蔗林——青紗帳》和《昆侖行》兩本詩集。這兩本詩集中的詩,和詩人過去創作的詩歌相比,既保持了原有豪邁雄偉的氣派,又有了新的發展。其作品以其深刻新奇的主題思想、對現實斗爭的獨特的思考與見解和優美完整的藝術形式、生動而具有民族氣派的藝術風格,強烈地傳達了我們的時代精神。可以說,這些詩表明了郭小川的詩歌創作躍上了新的高峰,標志著郭小川的詩歌創作進入了思想和藝術上全面成熟的時期。這些作品富有時代的戰斗精神,且特別注重美的開掘及詩歌形式的創新。這些激越慷慨的作品在歌頌人的精神的同時,還張揚了一種人生的選擇,或一種在生活困境中應該保持的姿態與情懷。
人生低谷中寫就的深刻
正當郭小川的詩歌創作如日中天之際,全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70年1月,郭小川和作協機關的干部一道,下放到湖北咸寧向陽湖畔的“五七”干校,從此,他和大家一樣參加圍湖造田的重體力勞動。郭小川以他詩人特有的生活態度和精神面貌來到了湖北咸寧。在這里,他仍堅持創作,堅守自己革命詩人的戰斗崗位。他先后寫了《柿情歌》、《歡樂歌》、《花紋歌》等作品。這些詩在當時自然大部分得不到發表機會,有的只能在干校墻報上刊登,有的或在集會上朗誦。在當時的環境里,詩人憑著自己對黨對毛主席的信念,保持他胸懷的磊落光明,保持著他當年年輕戰士的天真,繼續放聲歌唱。讀著郭小川當年的詩句,我們很難想象作者是一個正在“五七”干校被“改造”的文化人。1972年夏天,周總理打破江青等人的阻撓,對中央文化部的運動進行了干預。總理指示,在干校的十二級以上的干部,統統先回北京,能工作的工作,不能工作的先養病。但“四人幫”嫉恨郭小川,把他說成文藝黑線上的“代表人物”,抗拒總理的指示,獨獨扣下了郭小川。
1974年12月,咸寧干校撤銷,郭小川隨原屬中國作協的一批干部并入天津附近靜海縣的團泊洼“五七”干校,繼續勞動和接受“審查”。在團泊洼,盡管環境更加惡劣,郭小川仍不顧病體,努力研讀革命理論著作。從1975年春天起,他學習了四卷本《列寧選集》,接著又鉆研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資本論》。1975年9月,郭小川在團泊洼被隔離審查,突然聽到了毛澤東關于電影《創業》的批示,他懷著無比激動和振奮的心情,揮筆寫下《團泊洼的秋天》,表達了一個共產主義革命戰士堅定不移的革命斗志。他的詩充滿浩然正氣,擲地有聲。與其說它是一篇革命戰士的宣言,不如說它是向“四人幫”投擲的一顆重磅炸彈!對革命文藝創作,郭小川始終積極倡導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方法。他在《我們需要最強音》一文中說:“浪漫主義,這里當然指的是革命的浪漫主義,作為藝術創作方法,它的意思大致是:不拘泥于細節的真實,表現人民的英雄氣概和對于未來的夢想。”“缺少這種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缺少革命的浪漫主義,我認為,實質上就是缺乏思想,缺乏共產主義的深刻的思想。”在幾十年的創作實踐中,他根據自己的創作經驗總結道:“我們都已熟知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但是,什么是革命浪漫主義?最根本的,恐怕是使作品表現出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什么是革命現實主義呢?最根本的,恐怕是從革命的實際出發。而這兩者都是要從革命斗爭中來,從革命生活中來,決不是只說幾句‘豪言壯語……”
同年10月間,中共中央領導人召見了郭小川,對他給予了慰勉,并且決定采取實際措施,把郭小川的組織關系由文化部轉到中央組織部,幫助他擺脫“四人幫”的禁錮,從而更好地生活和創作。一個月后,他實現了到河南農村深入生活調查研究的愿望,先后到當時“農業學大寨”的先進縣——林縣和輝縣考察,還準備到大寨、遵化參觀學習訪問,后因身體原因未能成行。但郭小川還是寫出了《拍石頭》、《登九山》、《輝縣好地方》等反映農村題材的好詩。由于“四人幫”一伙的長期迫害,郭小川的身體越來越差,周恩來、毛澤東幾位中央領導人去世時,正是郭小川的身體極度虛弱時期,但詩人含悲忍淚寫出了《痛悼敬愛的周總理》、《痛悼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未完成)等詩篇。
1976年10月,一向關注時局變化的郭小川,此時遠在河南林縣,雖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現的新情況,但憑著詩人慣有的政治敏銳感,仍能從收音機、廣播的用語和語氣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變化。他決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他計劃先到安陽探親訪友,再去鄭州與省委書記劉建勛話別。10月13日,他剛到安陽招待所,就耳聞“四人幫”被捕的喜訊。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終于發生了,內心深處充滿了激動。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習慣地點著香煙,他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睡。無奈,只好按慣例服用安眠藥。不一會兒,他迷迷糊糊進入了夢鄉,然而他手上夾的煙蒂卻未掐滅,從而引發了火災。郭小川不幸逝世,終年僅57歲。
永遠的“戰士詩人”
郭小川有“戰士詩人”之稱,這個稱號與其大多的詩作有關。他經歷過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參加過八路軍,曾在編輯部工作,擔任過地方領導,“過早的同我們的祖國在一起,負擔著巨大的憂患”,這些,都為他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5年郭小川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工作,開始以強烈的責任感和火一般的激情為新中國放聲歌唱。22年里,他用詩歌謳歌生活、贊美人民,為新事物吶喊,他用詩歌寫出一個詩人對新中國的無限深情。他用戰士的歌喉,戰士的情感,為新中國歌功頌德。
從他的第一首政治抒情詩《投人火熱的斗爭》到最后的詩作《秋歌》這種特點一以貫之。他鼓勵人們開拓、奮進(《向困難進軍》),謳歌祖國的風姿、英雄的人民(《廈門風姿》),抒發人定勝天的豪情(《望星空》),表達對“四人幫”的憎恨(《團泊洼的秋天》)……詩人不僅是英雄業績的歌唱者,也是參加者。他不是社會生活的旁觀者, 而是愛其所愛,憎其所憎,以強烈的責任感推動時代前進的戰斗者。郭小川以其豐富的想象,深邃的思想,精湛的哲理揭示了時代風貌的內涵。
《向困難進軍》闡明了“在我們的祖國中,困難減一分,幸福就要再長幾寸”的道理,《廈門風姿》中作者由此而想到了它是整個中國的風姿,《團泊洼的秋天》更是想得奇、想得巧、想得深,從靜靜的團泊洼想到“全世界都在喧騰”,從“同志式溫存的夜話”想到了“戰士的深情”、“戰士的性格”、“戰士的愛情”、“戰士的歌聲”。雖然“四人幫”在肆行非度,但人們相信“這矛盾重重的詩篇”到“明春準會生根發芽”。郭小川的詩對斗爭生活有獨到見解,獨特感受,又洋溢著強烈而鮮明的時代精神,給人以藝術享受,育人以理想、追求和信念。
郭小川的一生是為黨的事業勤勉勞動,頑強戰斗,始終充滿著活力的一生。他在中國革命文藝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戰士的閃光的腳印和一個詩人的獨特豐碑。不管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年代,他始終滿懷革命激情,站在時代斗爭的潮頭,站在工農兵中間。他的一生,幾乎踏遍了祖國的每一寸土地。戰士與詩人,這兩個人類神圣職業的名稱,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馮牧在《郭小川詩選·代序》中這樣高度評介郭小川的創作:“他的詩篇,他的歌,使我們看到了時代前進的腳步,使我們聽到了時代前進的聲音。郭小川的詩并不盡是杰作,……任何一個革命的作家和詩人,只要他堅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只要他堅持深入火熱的斗爭生活和正確的創作方法,他的作品就一定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時代的精神,就象每一滴露珠都會反射出太陽的光彩一樣。”
不管身處什么樣的逆境,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身心飽受“四人幫”一伙的殘酷摧殘,他始終懷著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的無比深情,謳歌不停,戰斗不止。
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學創作實踐生涯中,郭小川始終堅持走富有獨創風格的藝術道路。他認為:文學的價值在于它的時代性和特殊性,社會主義文學當然也不例外。一個無產階級詩人或作家,其作品在緊緊把握時代脈搏的前提下,必須要有“個人特色”。而這特色“是作者的全部氣質和全部修養在創作上的綜合表現……”他還曾具體地指出詩要“四化”:即革命化、典型化、群眾化、格律化。他無愧于我們時代杰出歌手的稱號!更無愧于“革命戰士詩人”的崇高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