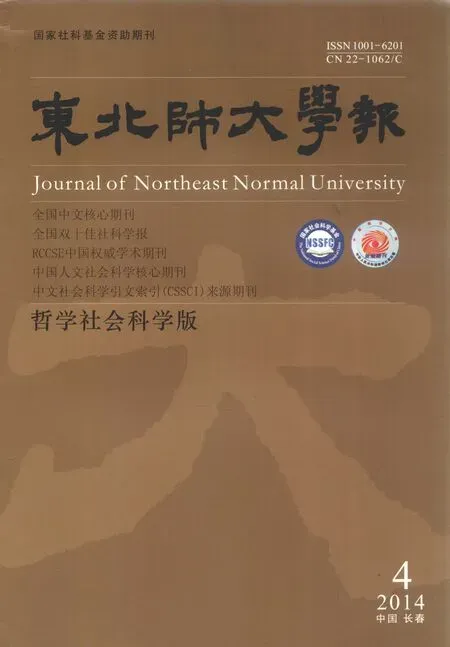近代日本外交危機的肇始
李小白
(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東北師范大學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長春130024;2.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長春130024)
近代日本外交危機的肇始
李小白1,2
(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東北師范大學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吉林長春130024;2.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吉林長春130024)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利用日英同盟和日俄密約,將幾乎等同于本土面積的殖民地攫取入懷,并向袁世凱提出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一些大國成為日本的同謀,一些大國只在旁觀。但美國卻開始以鐵路中立化計劃向“滿洲”滲透勢力,發起“金元攻勢”。威爾遜總統提出新外交理念和準則,完全改變了東亞國際政治的環境。近代日本的外交危機由此而肇始。
二十一條;密約同盟;金元外交;威爾遜主義
1890年,第三任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提出了“主權線”和“利益線”,是人所共知的。但人們普遍忽視的是,如果主權線“乃國家之疆域”,而利益線“乃與主權線切實相關之區域”[1]203,那利益線所涉范圍將大大超過“主權線”,故而這種政策實際包含著:(1)“利益線”自被日本認定為“利益線”后日本則必用強力去奪取;(2)用“利益線”來包裹主權線乃最積極的安全保障戰略,“利益線”面積越大,主權線便越有保障。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約簽訂后,日本“領有”了內蒙古東部,迄止當時,近代日本已經擁有了兩個殖民地(朝鮮和中國臺灣),一個規模巨大且幅員仍在擴展中的殖民地會社(滿鐵及其附屬地附屬事業),一個勢力范圍(內蒙古東部),一個遼東租借權以及大量在中國內地從事間諜活動的據點,還有難以估測的隱在勢力范圍。當時日本全國領土面積約38萬平方公里,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面積已達30萬平方公里[2]。1918年,以戰勝國的姿態從德國手中接收山東權益,并領有南洋諸島,自詡已躋身“一等國”行列的日本,躊躇滿志地在凡爾賽和會登堂入室。若再考慮到1917年之后日本利用一戰“天佑”一舉而由債務國躍升債權國,成為國際社會中的“成金者”(暴發戶),1890年的“國是”可謂名實俱符地得到了兌現。怎不令日本舉國上下在神龕前撫額相慶!
一
1914年底,大隈內閣通過對華“二十一條”議案,翌年1月,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要求案本,威逼袁世凱保密并必須全盤接受。事后各國各方公認此乃日本企圖獨霸中國用心的自我暴露,又是日本企圖利用一戰之機乘隙而成為各國在華利權之首的精心策劃。在日本發出最后通牒的逼壓下,袁世凱不得已在5月9日接受日本要求。這一天被中國舉國上下一致排斥的民眾定為“國恥日”之事實表明,“日中之間決定性的敵對局面之契機形成了”[3]。
“二十一條”第二號的主訴是關于日本在東部內蒙和“滿洲”的特殊利權。“滿洲”地接朝鮮,事實上早已被日本帝國主義視為“帝國疆域”的自然擴展空間。1905年日本冒亡國危險打贏日俄戰爭,明治天皇親自譜寫“黃海大捷”軍歌,鼓勵將士們“忠勇義烈之戰,挫敗敵氣勢”,以使“我太陽旗高照黃海波濤,凱歌響四方”[4],向世人宣告“滿蒙”之地得之不易豈可輕易喪失之決心。巨大資產國策會社“滿鐵”自創建之始,便一直在擴容增資,運營里程逐年上升,首任總裁后藤新平認為:“如能不出10年將50萬國民移入滿洲,俄國雖倔強亦不得輕慢我而開戰,和戰緩急之利依然在我手中”[5]。基于“大連中心主義”建設的大連港,至1912年已超過營口成為東北地區的第一大港。滿鐵在附屬地內所獲的經營權,正在向殖民地制度過渡。將“滿蒙”作為自身行政區域來經營的意圖,已是昭然若揭。
在日本一步一步將“滿蒙”攫取入懷的過程中,對“三國干涉還遼”還是保持著深刻的記憶的。國際政治中的角色有強弱之分,當兩個強弱分明的國家簽訂條約,弱勢一方將本屬自己的主體利益讓與強勢一方后,會因此導致該地區國際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必有其他國家在此力量變化中受到隱性傷害。如此,這樣的國際勢力便會尋找一個由頭,挑起事端,表明對條約所造成的利益轉讓和所導致的戰略態勢失衡不予承認的態度。這種狀態還會將該地區的國際糾紛向另一層級推動。所以,要將“滿蒙”特權牢靠地據為己有,日本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但沙俄仍是東北亞地區日本最大的競爭者。俄國在戰爭中敗北,向東亞南下的發展勢頭被日本有力地阻止,其外交政策和鋒芒有轉回西亞和巴爾干的趨勢。鑒此,戰前力主英日結盟的山縣有朋反過來與伊藤博文一道推動日俄交涉,于1907年、1912年和1916年與俄國達成密約,這些密約在根本不考慮中國、蒙古等國主權的前提下,將日俄兩國的勢力范圍劃分得清清楚楚。憑這些密約,日俄兩國關系一時進入相安無事狀態。
于1902年簽署的日英同盟條約,不僅將日本在韓國和中國的利權與英國在中國的利權作了交換,而且明確暗示指向俄國的第三方針對,此后該同盟條約曾于1905年和1911年兩次改訂。第一次改訂確認將攻守同盟約定延長到今后10年;第二次改訂則明確將美國排除在同盟實施對象之外。通過這般的外交斡旋,日本利用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成立以來,承認弱肉強食和物競天擇故而不顧正義與否的“天然優點”,采取用一系列秘密條約和同盟條約的“舊外交”手段,運作了一整個如桑蠶織繭一般的工程。將密約和同盟織成抵抗外壓的繭殼,而將“滿蒙特權”緊緊包裹,保護起來。圖示如下:

1908年1月,山縣有朋在向政府提出的《對清政策所見》意見書中談到:“最近一兩年,清國的外交政策是所謂對外的一味耍硬,不用說有理時則竭力爭之,即便無理也固執己見,有絕不屈服的架勢。(中略)我邦犧牲數萬人,耗資十幾億而贏得的在滿洲的利權,根本不能因清國持有異議就可以退縮,更何況拋棄之。依今日形勢推測,在今后十幾年租借地期滿,清國恐怕要求我歸還關東州租借地。即使如此,只要世界形勢和東洋局面不發生極大變化,我國決不能答應這種要求。這是理所當然的。我一天也不能疏忽大意,要精心經營滿洲,伸張利權,而鞏固地位的計劃決不可懈怠”[1]101-102。這表明,在參與國家重大決策人物們心中,正因為“滿蒙”屬于核心利益,欲奪取之守衛之,風險意識斷不可少。
與此同時,另一種運動也在同時進行。內田良平在1913年發表“滿蒙獨立論”,提出:“謀求在滿蒙人的自由之下,在南滿洲和東部內蒙建立獨立運動”[6]。頭山滿和內田等可稱為是具有從事間諜活動的天才,一直在期待“滿蒙”脫離中國本土,制造一種“自愿”假像,為政府肆意利用制造借口。其計劃是:派川島浪速策動宗社黨和前清余孽肅親王善耆,蒙古王公巴布扎布,在“滿蒙”起事,發動“滿蒙獨立”運動。1916年第二次“獨立”運動小成氣候,但旋被張作霖擊滅,日本在猶豫之中最終決定扶植和利用張作霖,以達到“在滿洲為所欲為”之目的[7]。間諜浪人所期待的結果是:“滿蒙人”自愿獨立——日本人基于“俠義心”出手相助——軍事勝利——宣布獨立——同日本簽約。
所以可以說,迄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心中期待獲取的“滿蒙特權”,依其自我評價,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引人注目的是:近代日本為達到目的,根據對象和自我設計的目標不同,充分地利用了外交條約內和條約外的兩種策略手段。
二
不斷地擴張利權,有許多人沉浸其內而沾沾自喜,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卻認為“勝利”與風險其實是同步存在的。元老松方正義批評大隈內閣的對華政策,認為“二十一條”是“將可稱作帝國外圍的中國驅趕到敵人一方”,因此“會喪失帝國在國際上的信用”[8]。松方眼中的“敵人”主要言指美國。5月11日,威爾遜政府發表聲明:“凡關于損害美國之條約權利及旅華美國人民權利,美國政府絕不承認”[9]。該聲明所顯示的態度斷然而明確。事實上,“二十一條”的提出也構成為美國對日本遏制政策肇始的契機。
現代國際政治的原則和慣例是幾經變遷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維也納體系以及俾斯麥的大陸聯盟體系,從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20年代覆蓋世界約270年。最初誕生的萬國公法就是在這些雖講求秩序但更講求力量的外交理念支配下形成的。固然避免了某些地區性和局部沖突,但世界由多極向兩極過渡,至20世紀初形成同盟與協約的對立,最后釀成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禍。在漫長的近300年時間內,有一些強國憑恃武力獲取了領地和資源,趾高氣揚,但仍意猶未盡;但大多數國家的中世紀平靜被擊破,失去土地和尊嚴,唯悲嘆力虧氣蹇,命運不濟。一些精于利用既有矛盾和對立的外交活動家,絞盡腦汁總在謀劃利用這些體系的空隙而圖一時之快,獲一時之利。在新的外交原則為人們公認之前,這個稱作“舊外交”的時代,許多不公正非正義卻被所謂“條約”和“同盟”甚或“秘密同盟”所包庇。日本從1871年起同中國清朝簽約,開始品嘗“舊外交”的甜頭。“舊外交”仿佛一個大泥淖,只要陷入便永遠只有在混水中沉浮,冷酷的計算和動輒翻臉訴諸武力的慣例使古代政治文化中因襲而來的正直正義仁愛遭到滅頂之災。
面對日本在“滿蒙”肆意妄為,新崛起的美國是有想法的。利用因調停日俄戰爭而獲得的話語權,由時任美國駐奉天總領事司戴德策劃一份“滿洲開發計劃”,運動美國著名的鐵路大王哈里曼出資,向滿洲輸出資本,以日美共同經營南“滿”鐵道的方式,試圖插足“滿洲”,還與日本首相簽訂了諒解協定,躋身東亞政治格局。美國可為日后的發言權鋪設立足點。美國判斷:“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為工具,進行無孔不入的殖民主義的滿洲經營”[11],但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識破了這一點,一舉予以廢除。1909年美國國務卿諾克斯提出“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試圖在“國際共管”的名義下推動“金元外交”,以此削弱和遏制日本在滿蒙的獨往獨來勢頭。該計劃設計由美英日俄貸款中國政府,由中國政府利用這筆貸款贖回“東三省”的所有鐵路,將其置于主要由英美參與的管理系統之下。這項計劃分明是主要針對日本的,其動機是:新任美國總統塔夫脫對前總統羅斯福的遠東政策是不滿的,要取得在遠東利益僅靠民間資本是不夠的,遠東應當進入政府外交政策框架內。“這個政策的特征是,以金元代替槍彈。”[10]272
“金元攻勢”一波連接一波。首先,1908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了退還庚子賠款的議案,此舉不僅表現出對“辛丑條約”的反省和批評,也極大地博取了中國民眾的好感。唐紹儀去往美國致謝并勸說美國資本輸出東北;同年,因移民問題引發的日美矛盾,雖然由羅脫—高平協約妥結,但相互妥協中清楚地含有彼此已經互為敵手的含義(美國強調了維護中國獨立及領土完整);1909年10月,作為“中立化計劃”的一部分,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同奉天巡撫程德全簽訂《錦璦鐵路借款草合同》,計劃要修筑的路線同日俄控制下的中東路在很大距離上處于平行狀態,而錦州港與大連港分別處于渤海灣的兩端,競爭意圖明顯;是年美國強行介入湖廣鐵路借款計劃;從1908年起,美國致力于挑撥日俄關系,希望由俄國提出出售中東路,而由美國出面“贖買”。這迫使后藤新平作出了“新舊大陸對峙”的判斷[12]。
1913年3月,威爾遜出任美國第28屆總統,此前,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此后,日本提出了對華“二十一條”。威爾遜意識到:金元攻勢并沒有取得成功,“二十一條”的姿態表明日本試圖實行對中國的強硬政策。這使美國反省:行動緩慢的“金元攻勢”“犧牲了一個最好的機會”[13]。1916年7月,第四次《俄日密約》簽訂,其中的針對敵人也包括美國。在這個刺激下,美國政府照會日本,希望日俄之間的協定,不能有損于中國領土主權及“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美國原則。同時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海軍撥款法案,龐大的海軍造艦計劃是為了“抑制日本的亞洲野心”[10]327。1917年5月12日,美國國務卿蘭辛主動向日本要求美日應就中國形勢交換意見。是年9月至11月,經過13輪磋商后,最后達成了著名的蘭辛—石井協定,美國雖承認日本在滿蒙擁有“特殊利益”但強調了“門戶開放”和“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要求,在雙方異乎尋常爭辯中,美國還試圖用“卓越權益”去取代“特殊權益”。蘭辛——石井協定的意義還在于:美國已經基本放棄還將“金元”作為手段去壓制日本,因為過往的交涉證明:日本一直在敷衍,實在無法周旋便蠻橫地表示不答應,且拉俄國入伙對抗美國。這表明:在舊外交秩序內仍然奉行慣例手段去對抗敵方,是不會取得多大效率的。
三
1917年10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俄羅斯被后來的蘇聯取代,沙皇政權垮臺,蘇俄政權逐漸穩住腳跟并成為新的統治者,對日本來說長年以來一直通過日俄密約與之勾搭瓜分利權的主體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
1919年朝鮮爆發“三一運動”,中國爆發“五四運動”。長年受日本壓迫的朝鮮和中國以民族主義的覺醒和明確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大大增加了日本試圖繼續維持既得利益的困難。殖民地或勢力范圍人民群眾的反抗對壓迫者而言,這種危險是任何密約或同盟所無法解消的。
1911年7月,日英之間簽訂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條約。日英同盟又獲得了10年的效力延長期。但是,根據英國的意愿,一旦日美之間發生戰爭,英國沒有參加戰爭的義務。日英同盟的第三國針對性已經消失。“日英同盟是帝國外交的真髓”[10]285,一旦針對性不再則“真髓”亦無實際意義。其原因是前一年,美國曾提議同英國締約,英國政府表現出積極態度。從1902年起一直支撐日本軍事擴張的日英同盟將在1921年屆滿期終。1906年日本制定第一次國防方針時,俄國是為第一假想敵國,當時陸軍認為美國尚無列入假想敵國之列的必要;1918年日本改訂國防方針,美國排位蘇聯之后,是第二假想敵國;第三次改訂時,美國已是頭號假想敵國。即:當美國的威脅越來越強烈也為日本所深刻意識的同時,曾答應日本幫助其作戰的英國卻悄然抽身而退了。1921年后,日英同盟條約被華盛頓會議通過的《四國條約》所取代。
對日本外交來說,最大的危機源自于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發布的“十四點計劃”。從其具體內容看,似乎主要是針對歐洲事務,與日本無關。但從其原則上看,其公開外交和廢止秘密外交,歸還戰爭中被占土地,公道處置殖民地,裁軍和限制軍備,尊重領土主權完整,強調不干涉主義等等,日本只要一想到自己在朝鮮和中國的所作所為,皆可一一對號入座。充滿著理想主義的威爾遜主義,充分展示了一種新的學說在其誕生初期的純然性。此后的歷史進程證明,威爾遜主義是舊外交的終止符,新外交的里程碑。對舊外交秩序無視正當正義原則的挑戰,使當時的中國民眾對美國懷有無限的想象空間。三年以后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完全地兌現了美國主持下的新外交在亞太地區所追逐的目標。
這就是說,至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日起,自甲午戰爭以來有利于日本向外侵略擴張的國際環境完全改變了。日英同盟一去不復,日本喪失最可憑恃的盟友;日俄密約因蘇維埃政權宣告一切舊條約失效亦已無狼狽為奸的密約可以依靠;中國朝鮮的民族主義浪潮明確提出收回利權,這最令日本不寒而慄;而新環境主要創造者美國憑籍其新理念新秩序,在崛起的同時毫不含糊地暗示:日本若試圖對抗將無條件地成為新外交秩序的試驗品。
日本學者服部龍二在其獲獎專著中,提出舊外交軸心被以美國為首的新外交軸心所替代,可稱為以美國為代表的外交新秩序的形成;蘇聯的出現和中國的改變導致國際政治中新角色的加入,特別是中國身為參戰戰勝國反而受到和戰敗國一樣的處理,其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被同時喚醒,對東亞國際政治沖擊巨大;由于國際環境的改變,日本外交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理性的外交家對外奉行“協調外交”,政黨政治對內奉行民主主義,與激進的外交家標榜對外強硬,專制者對內強調總體戰計劃,形成了根本無法協調妥協的局面,將日本推向不斷發動新的侵略戰爭的境地,越陷越深,全面陷入孤立并在戰爭軌跡上一直走到1945年戰敗,等等,所有一切的變化,皆因1918年威爾遜主義所開創的國際政治新環境所導致[14]。上一世紀20年代美國的亞洲政策表現出對中國政治和中國民眾極大的同情,同時也是當時諸列強中第一個給予中國的積極變化以支持的國家,這種同情因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深終于發展成對日作戰對日懲罰的主體政策。當然會有學者認為美國的世界戰略中包藏有對國際政治主導權的覬覦,但是積貧積弱的中國當時的確需要這種支援。仔細吟味,上世紀初美國向東亞國際政治的介入使日本的中國政策倍感壓力,有許多細節可以慢慢咀嚼琢磨。美國的國際戰略政策在其提出之初,其理想主義的特征,至今令人追憶。日本外交危機的初顯現,于中可以一覽無遺。由此危機肇始日本近代外交的歷史進程,有許多教訓值得汲取。
[1]大山梓.山縣有朋意見書[M].東京:原書房,1966.
[2]百瀨孝.昭和戦前期の日本[M].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2.
[3]川島真,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國際政治史[M].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7:98.
[4]鴻明,木易.明治天皇傳[M].沈陽:沈陽出版社,1997:243.
[5][日]依田憙家.日本帝國主義研究[M].卞立強,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9.
[6][日]歷史研究會編.日本史料.4.近代[M].巖波書店,1997:299-300.
[7]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7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69.
[8]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196.
[9]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組.中國近代史對外關系史料選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73-374.
[10]崔丕.近代東北亞國際關系史[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
[11]崔丕.近代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緒論[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5):6-65.
[12]北岡伸一.外交指導者としての後藤新平[J].近代日本研究會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山川出版社,1980:73.
[13]李抱宏,盛震溯,譯.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55.
[14]服部龍二.東アジア國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1918——1931[M].東京:有斐閣,2005:1-18.
The Germination of Modern Japan's Diplomatic Crisis
LI Xiao-bai1,2
(1.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ey Research Bas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Center for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Wit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and 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Japan seized the colonies which is nearly as large as Native Japan before the end of World War I,and proposed to Yuan Shikai the Twenty-One Demands in order to occupy China by itself.Some big countries became the accomplice with Japan,while others did nothing in response.However,the United States infiltrated its power into Manchuria through the Knox Plan and initiated the Dollar Diplomacy.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proposed new diplomatic ideas and principles,and entirely change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East Asia,which triggered the diplomatic crisis of modern Japan.
the Twenty-One Demands;Secret Treaty Alliance;the Dollar Diplomacy;Wilsonianism
K313.41
A
1001-6201(2014)04-0007-05
[責任編輯:趙 紅]
2014-05-1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2BSS008)。
李小白(1957-),女,黑龍江鶴崗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東北師范大學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