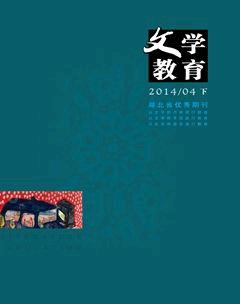文學倫理學視閾下的《咱們死人醒來的時候》
內容摘要:《咱們死人醒來的時候》是易卜生的戲劇收場白,描寫了藝術與人生的基本關系。在這部戲劇中,透過愛情的故事,婚姻的抉擇,逐漸顯現出來的是人的主題。藝術固然是重要的,個人事業也是必須的,但絕不能凌駕于個人的生命價值和情感、靈魂之上。本文擬從文學倫理學的角度,結合戲劇中的三重倫理關系,探析“易卜生式的人道主義”以及倫理視閾下作家對理想兩性關系的思考。
關鍵詞:《咱們死人醒來的時候》 文學倫理學 藝術與人生
三幕劇《咱們死人醒來的時候》完成于1899年,是71歲高齡的易卜生在漫長的創作道路和藝術生涯中完成的最后一個劇本,在這部戲劇中,易卜生將聚光燈直接對準了藝術家,描寫藝術與人生的基本關系。在易卜生的世界里,總是藝術朝一個方向運動,而生活朝另外一個方向運動,藝術家總是要同生活保持相當的距離才能夠心無旁騖地進行創造性勞動。易卜生借魯貝克之口向愛呂尼辯白:“第一是藝術作品——其次才是人類”(易卜生291)。而愛呂尼也糾正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藝術。藝術家也許確實擁有一些天生的特質讓他更敏銳、更豐富、更深刻,能夠進行思考和創造。但藝術家也是人,擁有人的自然本性,擁有人性的優點和弱點,有對愛情的渴望,對婚姻的憧憬,對家庭生活和美好幸福的期待。也生活在一定的社會倫理環境當中,與周遭的人事發生著緊張的關系。易卜生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并以他的方式為我們呈現了藝術與人生的沖突是怎樣形成、開始和結束的。這也是他長達半個世紀對此問題思考的結晶。
一.三重倫理關系下的藝術和人生
(一)魯貝克和梅遏——聊勝于無的婚姻
他們是實質上的婚姻關系,卻是一段聊勝于無的婚姻。藝術家魯貝克在聲名漸起而靈感卻離他遠去之時遇到梅遏,他看重的也許是梅遏的年輕貌美和充沛的生命活力,他確實需要一個年輕的身體和靈魂來慰藉自己日漸衰朽的身軀和疲乏困頓的精神。而梅遏的貧窮和無知也促成了這樁婚事。
梅遏是和魯貝克完全不同的人,她沒有什么精神上的追求,不受倫理道德的約束,也不認同藝術和藝術家。但她離開藝術家魯貝克,不能單單理解為選擇了獵人烏爾費姆。烏爾費姆只是外因,內因則是梅遏的獨立和自己的想法。首先,她并不喜歡藝術和藝術家的生活方式,這也是她不可能對魯貝克產生愛情的根源。其次,在這段婚姻關系中,丈夫并不關心自己的妻子,不理解她心理的變化,甚至可以說是漠不關心的。在這里,魯貝克犯了同對待愛呂尼同樣的錯誤,沒有將梅遏看做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人格平等有感情需要的妻子。他仍然沉浸在自己藝術家的世界中,以自我為中心,他從未嘗試過理解自己的妻子,她的快樂和痛楚,她內心的想法和苦悶的心情,他一概不知。而共同生活在陶尼慈別墅的幾年,梅遏一直感覺自己像憋屈在一個潮濕昏暗的籠子里透不過氣來。
他們的婚姻關系是不穩定的,沒有穩固的基礎也極易遭到破壞。究其根源就在于他們的人生態度和選擇沒有任何的相似之處。這樣的婚姻生活可以說是名存實亡,雖生猶死的。魯貝克說他絕不易在懶散的享樂中消磨人生,也承認這種婚姻生活讓他疲倦到了極點。幾年的共同生活讓他看清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藝術家的本性讓他體內那種蠢蠢欲動的創造欲念逐漸復蘇,無法再消磨時光、虛度年華,而這與梅遏是不相為謀的。他們婚姻的解散表明真正的婚姻應當建立在愛情基礎之上;而在一段婚姻關系當中,丈夫與妻子應當互相關心和理解,應該受社會倫理道德的約束,否則極易遭到破壞乃至解體。這也表現了易卜生對于愛情、婚姻的思索和倫理道德理想。
(二)梅遏和烏爾費姆——“消遣的好伴侶”
梅遏將烏爾費姆戲稱為“羊人”,而羊人是古羅馬神話中農牧之神,半人半羊,生性淫蕩。而且按照羅馬神話的傳統,農牧之神是和豐饒之神梅遏結為夫妻的。在劇中,梅遏和烏爾費姆確實代表了一種相似的生活追求和價值載體,這是與魯貝克和愛呂尼相對立的。
烏爾費姆身上有獸的印記,是一個獸性因子很強的人。一方面他直接、坦率、不拘小節,似乎帶著野人般“自然之子”的神秘力量。他告訴梅遏他和魯貝克的工作都是同硬材料打交道:“他對付大理石塊,我對付繃緊顫動的熊筋。最后,我們都打了勝仗——征服、控制了我們的材料”(易卜生282)。可見作為一個男人,他同樣有事業心,他是個獵人。在這里,烏爾費姆的職業同樣是帶有象征色彩的,易卜生將一個男人在生活領域的事業描述到接近男人的原始本性——獵取獵物。這與追求精神和藝術的魯貝克恰恰相反,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另一方面,他不僅“獵熊”,也“獵色”。首次出場的時候他便告訴梅遏他是打熊的獵人,“凡是我捉得到手的獵物,我都有法子整治——無論是鷹、狼、女人、麋鹿、馴鹿——只要它們新鮮、水分多、血多”(易卜生282)。他不僅具有獵人強悍、勇敢、無所畏懼的特性,而且他也把女人當做自己的獵物和消遣的玩物。他認為梅遏是“消遣的好伴侶”(易卜生323)。由此,他接近梅遏,引她上山的目的昭然若揭。他看重梅遏的年輕貌美,這是他所需要的,他需要向制服獵物一樣征服女人,滿足自己的欲望。他的行為和思想主要被本能的欲望沖動所操縱著,獸性本質一目了然。當他想要與梅遏將“生活的碎片拼綴在一起”,“拼湊成一種人的生活來”(易卜生326)的時候,他考慮的這段關系也只是一時的神仙伴侶,并不能長久,若是他們彼此玩膩、彼此厭煩的時候,就會把真面目露出來,兩個人依然可以隨心所欲地各奔東西。
這樣的一段關系是更加不穩定的,有著莫大的風險,因為它純粹建立在肉體性愛的基礎之上。“食色,性也。”人有自然的本性,但若僅僅將自然本性等同于人的本性,無疑將人墮入低等動物之列,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烏爾費姆以打獵為生,終日與高山森林為伍,過著原始人般的生活,不具備一個人應有的感情,他的行為由純粹的本能和欲望支配,沒有一個人所應當具備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上的約束。但是,梅遏最后為了“自由”投向了他的懷抱,他們最后避開了暴風雪和死亡,也是一種生存的選擇。可見這種原始的沖動和動物性的欲望是一個人所不可缺少的,是人的精神自由的必要條件,是靈肉一體的兩性關系中的的重要一環,這也是易卜生對于他身上所具有的生命力的肯定。
當梅遏在深谷得意地唱歌“我自由了!我自由了!牢獄生活從此休!像飛鳥一樣自由!”(易卜生333),這里所歌唱的自由并不能讓人信服,反而充滿諷刺的意味。就像梅遏和烏爾費姆由于畏懼山路和暴風雪,匆匆下山回到了山谷,而并沒有到達高山頂上。而魯貝克和愛呂尼卻反其道而行之,向著高處進發,即使他們明知道登上高峰的道路是一條死亡之路,然而他們仍然選擇了這條路,義無反顧地勇往直前,絕不折轉返茍且偷生。
易卜生通過梅遏與烏爾費姆的關系發展暗示了生活不能取代一切,愛情和婚姻不能僅僅建立在肉體性愛的基礎之上,真正的自由不止是肉體的滿足,而需要有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也需要有社會倫理道德的約束,其中一個途徑就是追求藝術化的生活。真正的愛情和婚姻也必將以靈與肉的和諧統一為前提。
(三)魯貝克與愛呂尼——從觸不到的戀人到攜手走向死亡
這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關系,不是普通的情侶關系,也不是平常的藝術家和模特之間的關系。易卜生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愛呂尼象征著“真理與詩”(易卜生《易卜生書信演講集》353)。大概是某種最本質、最純粹和最理想狀態下愛的化身,并且這種愛被賦予了藝術的美感和追求。愛呂尼是一個覺醒的女性形象,她不像一般女模特那樣被動地供雕塑家取材,而是以全部身心投入雕像的創作。為此她一往情深地稱雕像為“咱們的孩子”。她被易卜生賦予了主動追求美的精神。也正是這種人性本質上的相似和心靈相通的默契讓兩個人心心相印,成為天造地設的匹配者。正如海默爾認為愛呂尼是魯貝克的孿生靈魂。“她(愛呂尼)代表著藝術家本人的精粹本質部分,也就是他內心生活和思路開展的另一部分”(海默爾533)。
但魯貝克卻沒有對愛呂尼的愛做出回應,他確實被愛呂尼美麗動人的身體弄得幾乎發瘋,也并非沒有感覺到愛呂尼純真真摯的愛和內心的波瀾。但他將藝術看得高于生活,高于人性,高于愛情,他把愛呂尼當成了“只準供養,不許觸犯”的圣物,而不是一個人,一個年輕熱血的女人。他與愛呂尼保持著相應的距離,拒絕承認和接受這份真正的愛情,就像與世俗的生活保持著距離一樣,“如果我對你發生了感官欲望,我就會褻瀆自己的靈魂,因此就不能完成我的事業”(易卜生290)。
魯貝克在雕像完成后激動地握著愛呂尼的手說這次相遇所激發的靈感和創造是“一首千金難買的插曲”,卻換來了愛呂尼的出走和消失數年杳無音訊的結果。愛呂尼多年后回憶這段往事時仍然耿耿于懷,她指責魯貝克“損害了我內在的本性”(易卜生289)和踐踏了她“年輕的活的靈魂”(易卜生294)。在愛呂尼走后,藝術家的“生命也變成了荒漠”(易卜生309)。由愛呂尼帶來的那種靈感,所有創造性的才華都離他遠去。梅遏看出他生了病,而愛呂尼認為他已經死了。的確,作為藝術家的魯貝克已經死了,他開始為紳士淑女們雕像,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賺大把的錢,滿足外在的一切欲望。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愛呂尼身上,她離開藝術家之后就在沒有靈魂的世界里飄蕩。由此,他們彼此分開之后生命中的靈與肉就截然分離了。愛呂尼利用自己出賣色相生存,魯貝克也出賣了他作為藝術家的節操。
多年之后,當愛呂尼與魯貝克重逢后,經歷了枯燥乏味的婚姻,屈從于現實的壓力,創作力日益衰竭的藝術家幡然悔悟,意識到自己“斷送了生活”。他恰恰是把一個至關重要的關系搞顛倒了——第一是人類,其次才是藝術或其他個人的事業。他們都為過去輕易地放棄了生活的美而惋惜,在迎來愛情復活和靈魂復活后手挽著手登上高處,穿過雪地、迷霧,不畏風暴,一直朝上走,結果,他們葬生于大雪之中。
二.倫理內涵下作家的創作理想
易卜生通過這四個人物形象以及交織其中的三重倫理關系思考了這樣兩個問題。首先,人生的意義是什么?在生活領域中,是事業的成功還是愛情的獲取?在藝術領域中,藝術家又應當如何處理藝術與人生(這里主要是藝術與愛情)的關系?要成為一個藝術家需要付出多少人性的代價,而藝術家的創造性勞動是否與生命價值永遠沖突,如何化解?第二,一段真正的愛情關系需要哪些要素,靈與肉能否和諧共存于現實生活當中?
正如俄國批評家查爾斯基所說:“易卜生在這里指出,把純粹人的感情和關系作為犧牲的那種目標的非人性,是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接受的。”這也反應了易卜生主義的一個向度——易卜生式的人道主義。王忠祥認為“易卜生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易卜生式的人道主義,一種審美的人文主義,充滿審美的烏托邦倫理道德理想”(王忠祥42)。在這部劇中,透過愛情的故事,婚姻的抉擇,逐漸顯現出來的是人的主題。這部收場白也可以說是易卜生人道主義的一次堅守與升華。藝術固然是重要的,個人事業也是必須的,但絕不能凌駕于個人的生命價值和情感、靈魂之上。在該劇中,能否正確對待人(這里指“女人”),珍惜人的情感,珍惜人的熱血的身體和年輕的活的靈魂,實現真正的、健全的、豐富的、美好的人性,構成了易卜生在這部劇中關于人文主義的探索。
審美的人文主義還體現在易卜生在這部劇中的另一個追求,即靈肉一體的兩性關系,這種兩性關系充滿著烏托邦性質的倫理道德理想。易卜生深刻地揭示了現代人兩性關系中靈肉分離現象,這無疑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正如魯貝克和梅遏的婚姻,魯貝克和愛呂尼的愛情一樣。靈肉和諧的兩性關系在藝術創作中都是極為罕有的,在現實生活中就更難實現了。而在兩性關系中達到靈肉和諧的狀態和人類真正的復活——精神的復活,靈魂的重獲,卻需要肉體的死亡,軀殼的蛻卻來實現。就如魯貝克和愛呂尼在重拾愛情之后想要將“生活的滋味嘗個徹底痛快”,登上高山盡享榮華,他們要“走上光明的高處,走進耀目的榮華!走上樂土的尖峰”(易卜生332),卻淹沒在皚皚的白雪當中。但這死亡的價值和意義在于,他們的愛情和靈魂復活了,他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義所在——“生活的幸福,愛情的幸福”(易卜生331),而不是“死的粘土”。但這就是實現靈魂復活的唯一途徑嗎?這也反映了靈肉一體的兩性關系在現實生活中的難能可貴,甚至是帶著理想主義色彩的,難以實現在世俗生活的土壤中。
參考文獻:
1.比約恩·海默爾:《易卜生——藝術家之路》,石琴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2.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七卷,潘家洵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3.易卜生:《易卜生書信演講集》,汪余禮.戴丹妮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
4.王忠祥:“關于易卜生主義的再思考”,《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第5期,42-44。
(鐘秀,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與湖北文理學院聯合培養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