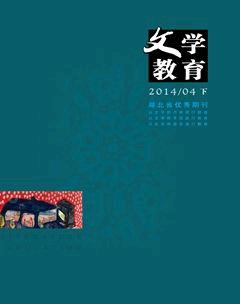《古詩源》中所收晉詩研究
連潔雨
內容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批評。清人沈德潛《古詩源》中收錄晉詩以陶潛、陸機、左思數量居多,對其三人亦抱有很高評價。沈德潛重視詩的教化作用,并將詩人的人品與詩歌的教化功用相結合來進行詩歌批評。這種詩學觀的形成與其生活的時代環境有著一定的關系,是生活在滿清統治下的漢族士人內心民族情感的流露。
關鍵詞:《古詩源》 晉詩 詩教
兩晉的歷史單純從年限上劃分,始自公元二六五年晉武帝司馬炎篡魏,終于公元四二〇年劉宋代晉,歷時156年。在司馬氏短暫的統治下,動蕩的局勢充斥著各種矛盾,士人們普遍形成委時任運、放任自全的心態。從古以來,士人便是文學活動的主體,當這種心態反映到作品中,便形成了兩晉文學的時代性特點——輕綺靡麗。
清人沈德潛在其編選的唐以前詩集《古詩源》的例言中,如此評價兩晉詩作:“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軒輊;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太沖拔出于眾流之中,豐骨峻上,盡掩諸家,鐘記室季孟于潘陸之間,非篤論也;后此越石景純,聯鑣接軫;過江末季,挺生陶公,無意為詩,斯臻至詣,不第于典午中屈一指云。”上述例言,提到的均為兩晉著名的詩人,從中可見,左思、陶潛是兩晉詩人中為沈德潛特殊推重的兩位。這反映了沈德潛的以“教化”論詩、以“人品”論詩的詩學觀念,某種程度上亦代表著清代前期學人對于兩晉詩歌的接受角度。
一.《古詩源》所收晉詩淺論
《古詩源》從司馬懿的《讌飲詩》到無名氏的15篇謠諺,共收錄晉詩32家,103篇(一題數首的以一篇計)。其中重要詩人及其作品收錄如下:
張華:《勵志詩》《答何劭》《情詩》(兩首)、《雜詩》,四篇;
傅玄:《短歌行》《明月篇》《雜詩》《雜言》《吳楚歌》《車遙遙篇》,六篇;
陸機:《短歌行》《隴西行》《猛虎行》《塘上行》《擬明月何皎皎》《擬明月皎夜光》《招隱詩》《贈馮文羆》《為顧彥先贈婦》(兩首),《赴洛道中作》(兩首),十篇12首;
陸云:《谷風》《為顧彥先贈婦》(兩首),兩篇;
潘岳:《悼亡詩》(兩首),一篇2首;
左思:《雜詩》《詠史八首》《招隱二首》,三篇11首;
張載:《七哀詩》一篇;
張協:《雜詩》(四首);
劉琨:《答盧諶》(并序)、《重贈盧諶》《扶風歌》,三篇;
郭璞:《贈溫嶠》《游仙詩》(六首);
陶潛:《停云》《時運》《勸農》《命子》《酬丁柴桑二章》《歸鳥四章》《游斜川》《答龐參軍》《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九日閑居》《和劉柴桑》《酬劉柴桑》《和郭主簿二首》《贈羊長史》《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桃花源詩(并記)》《歸田園居五首》《與殷晉安別》《乞食》《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移居二首》《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飲酒》《有會而作》《擬古》《雜詩》《詠貧士》《詠荊軻》《讀山海經》《擬挽歌詞》,三十四篇。
所選作品均是詩人文質兼美的代表性作品。從數量上看,陶詩居首,陸機、左思次之,正與例言中所評相契。
東晉詩人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超群,他以自己獨特的人格特征與生命體驗創作出一首首“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飽含田園生活氣息的詩歌。例如所收著名的《歸田園居五首》,在詩末有沈德潛的一句評價:“儲、王極力擬之,然終似微隔,厚處樸處,不能到也”,“儲、王”指的便是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詩人儲光羲和王維。不妨將三位詩作做一比較: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陶潛《歸田園居五首》其五)
種桑百余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余,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閑園里,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儲光羲《田家雜興》其八)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陶詩自然天成,不見雕琢。草木叢生的崎嶇小路,清淺可濯足的山澗,以及歸家后對于家庭生活的描寫,漉酒、局雞、暗室、荊薪,勾畫出田園農家質樸生活的自由與愜意,表現詩人高潔的品格與恬淡自適的心境。儲詩風格極似陶詩,對于農家生活亦進行了生動的描寫,但誠如沈德潛所感“終似微隔”。以下王詩的田園生活更多地體現出文人化的審視視角,雖然不乏得到絕佳的合情合理的藝術成就,比如“渡頭馀落日”二句,但目的并非是表現田園生活本身。儲、王是唐代優秀詩人,他們在藝術創作上都有很高的造詣。然陶淵明之所以能在這類詩作中獨領風標,原因主要在于兩方面:獨特的個人生命體驗和時代背景。由于二者的不可復制性,成就了陶淵明在詩歌史上的獨一無二。所謂“時勢造英雄”,細味之,有時所言不虛,自明矣。
陸機與左思同是太康文學史上的佼佼者,左思的一篇《三都賦》引起了“洛陽紙貴”的轟動效應,陸機更是由于在文學上不斷鉆研而取得的成就被譽為“太康之英”。而沈德潛對于兩人的評價卻有其獨特的思索在里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結合身世論詩。
在書中陸機名下,有這樣一段評論道:“士衡以名將之后,破國亡家,稱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詞旨敷淺,但工塗澤,復何貴乎,遂開六朝排偶一派,指摘稍多”。陸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典型文人,他對于文學的鉆研純粹而深入,從他大量的擬作中就可以窺見其用力之一斑。《古詩源》中收入兩篇,且看其一《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物節,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陸機擬作)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
明顯可見,陸詩于字句用功的痕跡,而“涼風”二句更可用于后來的律詩。不可否認陸機對于詩歌藝術美的追求與創造之功。于其人生出處,只能說限于當時的政治環境,時代背景,畢竟任誰也無法跳出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
對于左思,沈德潛無疑十分推重,“太沖胸次高曠,而筆力又復雄邁,陶冶漢魏,自制偉詞,故是一代作手,豈潘陸輩所能比埒!”左思出身寒門,且貌寢口訥,仕宦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在看重士族門第的政治環境下難以騁志。他的《詠史》詩,借古人之是非,抒己之塊壘。如“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再如將“赫赫王侯居”與“寂寂楊子宅”的鮮明對比,都表現出現實的灰暗。故而他從古人的經歷中汲取慰藉,悟得“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顧余”的哲學以自解,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成為他文學成就的代表作品,并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不論是陶潛、陸機還是左思,透過《古詩源》的字里行間,很容易發現編纂人沈德潛對于詩人的人品詩品相結合的評論視角,而這一視角,實是源自他最為核心的詩學觀念——詩教。
二.沈德潛的詩學觀及時代成因
“詩教”顧名思義,著眼于詩的教化功用。《說詩晬語》是集中體現沈德潛詩學觀念的理論著述。開宗明義即寫道:“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將詩的功用提升到了可以經國大業的崇高地位。這種觀念又與他的老師葉燮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沈德潛與其師葉燮的詩學觀不盡相同。葉燮反對前后七子的復古主義文風,這一點上沈德潛的立場不如老師那樣強烈,而在對詩歌風骨上的趣尚確是相同的。
葉燮是浙江嘉興人,父親是明天啟時進士。而葉燮本人于清康熙九年進士及第,十四年任江蘇寶應縣知縣,時值三藩反清,時局動亂,沒多久便因“伉直不附上官意”被罷歸。據《清史稿·列傳九十二》記載,沈德潛在“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試未入選。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這樣一個年紀不由讓人陷入疑惑,且三年后,乾隆皇帝授官時稱之為“江南老名士”,可知沈入仕前已聞名士林。乾隆曾說過“朕于徳潛,以詩始,以詩終”,表面上看兩者關系是君臣風雅,惺惺相惜,實際卻潛藏微妙。沈德潛死后的一件事,暴露出了這一潛在的問題。《清史稿》沈德潛本傳記載:
四十三年,東臺縣民訐舉人徐述夔一柱樓集有悖逆語,上覽集前有德潛所為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為法,上不懌。下大學士九卿譯,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謚,仆其墓碑。
滿清入關后為鞏固統治,一方面尊崇儒教,開博學鴻詞科,另一方面對漢族知識分子實施文化高壓政策,滿漢之別的神經從未松懈過。清朝的統治者及其階層始終信奉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漢族官員往往動輒得咎,即便是身居高位也必須謹言慎行,滿漢之間始終存隔膜。從政治層面上看,清朝統治者之所以提拔重用漢官,其實質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葉、沈二人的經歷正是力證。葉燮與沈德潛二人雖然入仕清朝,但在他們身上有著學人的耿介,內心有著濃郁的民族感情。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接受角度。這是受各自的時代環境所影響的。晉代詩歌史上陶潛田園詩成為不刊經典,左思的《詠史詩》的郁勃不平,陸機擬作的突破創新,離不開時代的造就;沈德潛的詩教觀與人品相結合的評詩角度也是清代民族隔膜下,漢族知識分子內心民族情懷的流露。
參考文獻:
[1]沈德潛選,《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P125-P186.
[2]沈德潛著,霍松林校注,《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P185-P278.
[3]呂思勉著,《呂著中國通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年:P334-336.
[4]《二十五史·清史稿》,http://www.eshunet.com/,E書時空制作。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