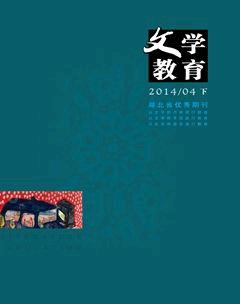高度珍視傳統語文教育的價值
畢玉俊
內容摘要:在傳統教育中,中國語文教育素來都是背誦。讓孩子在心靈純凈的童年時期記誦下足夠的精神財富,成為他生命成長中的精神能源和人格養料。通過反復的背誦,來體會書中的微言精義。通過大量的背誦磨練,形成一種對古代語言的認知接受模式,從而對語言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得到極大的飛躍,達到一種不同尋常的高度。熟讀背誦并非只是為了閱讀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寫作。現在的語文教學理論同傳統語文教育思想相對照,存在著極大的背離元素。因此,現在亟需借鑒傳統語文教育中那些積極的有價值的東西,來解決目前語文教學中存在的一些重要問題。
關鍵詞:傳統教育 熟讀背誦 教材特色 寫作意義
綿延幾千年的傳統語文教育根植于中華民族,是適合我們民族的語言、思維、心理的特點的,是有許多寶貴的東西值得堅守、探討、和借鑒的。可是自“五四”以來,受到對傳統文化虛無主義思想和西方教育理論的影響,對傳統語文教育愈來愈淡化,甚至不加辨別地否定和丟棄,致使我們的語文教育效率不高,效果不好,國民語文素養普遍低下。1978年呂叔湘先生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說:“十年的時間,二千七百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事情究竟“怪”在何處?我們能不能靜心思之?當然,問題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是我們不可回避的事實——對傳統語文教育的背離。
那么,傳統語文教育有哪些思想精華值得我們珍視和借鑒呢?這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但在一些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加以澄清,創新誠可貴,守本價更高。
一.傳統語文教育重視熟讀和背誦
幾千年以來,中國語文教育素來都是背誦。讓孩子在心靈純凈的童年時期記誦下足夠的精神財富,成為他生命成長中的精神能源和人格養料。清代陸世儀《論小學》中說:“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則多記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識既開,則多悟性、少記性。故凡人有所當讀書,皆得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誦讀,且不能誦讀矣。”國學大師南懷瑾晚年傾力于弘揚國學傳播,創辦太湖學堂,致力于兒童經典誦讀實踐,他在諸多次演講中反復申說,我現在講的東西都是十三歲以前背誦的,不管講到什么地方或誰的學說,都是信口說出,不帶差錯的。諸如陳寅恪、王國維、梁啟超、梁漱溟、季羨林等都是受過傳統教育的國學大師,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背出來的大師。再如大家所熟悉的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都是在幼年時期受過這種啟蒙教育,有了中國文化的底子,然后又接受了新時代的科學思想,才影響了這百年的歷史。
二.傳統教育重視反復誦讀和知識內化
古人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孔子說學而時習之,這不是夸張和簡單的重復,而是讀書的真正奧義。清代唐彪的《父母善誘法》中說:“讀至百遍外,雖甚拙者,亦能記背矣。”在實踐中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明確要求:“當設籌以記遍數,每讀十遍,令繳一籌,”務使“書之遍數得實,不得虛冒。”清人崔述在他的《考信附錄》記載道:“述五歲始授《論語》,每一字旁必朱書平上去入字,使不誤于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讀百遍,以百錢置書左而遂傳之右。既足則令少憩,然后再授如前。”而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教條》中對誦讀有著更嚴苛的規定:“必正心肅容記遍數,遍數已足,而未能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在古人看來,這背誦不是迂闊,而是一種讀書的功夫和定力,是一種心神高度專精的求知境界。通過反復的背誦,來體會書中的微言精義。通過大量的背誦磨練,形成一種對古代語言的認知接受模式,從而對語言的理解和運用能力得到極大的飛躍,達到一種不同尋常的高度。只有這樣,經典才能真正融入生活,當學生熟悉了這些經典的文字,隨著學力的提高和閱歷的增長,其中的意蘊自會隨時隨地得到闡發,而所謂的分析解讀,即使是大家名作,也難免是囿于闡釋者自身學術背景的一孔之見,會對學生全面把握全文產生遮蔽和干擾,也無法使初學者領悟到古文的簡潔流暢的自然之美。
三.傳統教育重視教材編寫與誦讀背誦相適應
古人一般三歲、四歲開蒙,進蒙館,以識記和誦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為主要內容。六歲至八歲進學館,主要任務是讀經,讀原典的“四書五經”,朗讀背誦不解釋。十二、十五歲入官學,學習的主要內容是解經。由此可以看出,在15歲以前學習的內容都是背誦。古代一個讀書人從3歲開蒙到15歲,大約要背誦30-50萬字。為了適應背誦,其教材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別是初級蒙學教材,從我們今天來看,首先能根據兒童的心理特點、年齡結構、知識程度,將識字教育、基本知識教育及倫理道德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較好地體現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即“文道合一”。其次,蒙學教材在編寫形式上采用整齊押韻的形式,文字簡練,句式簡短,節奏明快,通俗易懂,便于記誦。如《三字經》全書1248字,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數成句,句式簡短,隔句用韻,結構整齊。《千字文》全文125句,1000字,四字為句,沒有重復字。《急就篇》用三字、四字、七字句,句式整齊而又不呆板。三字句和四字句隔句押韻。七字句每句押韻。《千字文》是每兩句為一組,每組雙句均押韻。第三,在內容上則兼具故事性、濃縮性、知識性、教育性。如《三字經》中的“融四歲,能讓梨。香九齡,能溫席。”十二個字,兩個故事,并且人物、情節、意義清晰完整。
四.傳統教育特別重視熟讀背誦對寫作的意義
元代程端禮在《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談到作文要讀韓愈的文章時說:“日熟讀一篇或二篇,亦需百遍成誦,緣一生靠此為作文骨子也。”“作文如鑄器,銅既銷矣,隨模鑄器,一冶即成,只要識模,全不費力。所謂勞于讀書,逸于作文者,此也。"十分形象地說明了誦讀與寫作的關系。加強誦讀教學并非只是為了閱讀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寫作。這正如清代唐彪在《讀書作文譜》中所說“文章讀之極熟,則與我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吾意所欲言,無不隨吾所欲。應筆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熟讀背誦是為了強化對語言的認知接收模式,是為了在寫作時將這種語言認知模式不斷內化。達到“與我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的程度,所謂“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讀千賦,能為之。”的道理。
如上種種,都是語文教育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恰恰在這些問題上沒有引起高度的重視。現在的語文教學理論同傳統語文教育思想相對照,存在著極大的背離元素。因此,現在亟需借鑒傳統語文教育中那些積極的有價值的東西,來解決目前語文教學中存在的一些重要問題。
(作者單位:山東省萊蕪市第一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