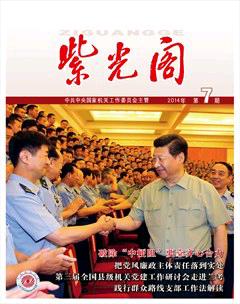“我沒有辜負對組織的誓言!”

入黨:這是必然的人生選擇
我是1949年初入的黨。在思想匯報上我引了列寧說的一段話: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性把血流光;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光,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光!
當時我在上海交通大學讀大四。進入交大后我就加入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叫“山茶社”,這是共產黨員領導的社團,主要進行一些革命教育。1948年夏天我就向組織提交了入黨申請書。當時局勢非常危險,國民黨在上海對我們的地下黨組織的鎮壓是非常殘酷的,有的同學就犧牲了,沒有迎來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實施大逮捕,組織通知我們臨時撤出學校。兩三天后學校又平靜下來,我們就又回去了,準備迎接解放軍渡江了。那天夜里學校里響起了機關槍的槍聲,我非常激動,是解放軍來了!但其實是國民黨的士兵進校搜捕學生黨員。我就躲在廁所里,有個同學冒險悄悄跟我說,樓梯口的士兵換防了,正好沒人,讓我趕快上三樓,那里不是搜查重點,比較安全。我就趁著這個機會一口氣跑到三樓,躲在別的同學房間里,這才逃過一難。我隔壁的黨員同學就是那天犧牲了。
加入共產黨對我來說是必然的。我1926年出生在廣東海豐,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沿海城鄉學校都停課了。那時我近10歲,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參加了當地的抗日宣傳隊。靠近除夕,日本鬼子馬上要進城了,我們上臺演出話劇,叫《不堪回首望平津》,說的是老百姓逃難的事。我男扮女妝,主演流亡的小姑娘。我們演得特別認真,臺下看的人很多,也很動情。演著演著臺上臺下就越來越激動,抓到漢奸了,臺下無數的觀眾含著淚水一起高喊:“殺!殺!”那時我就想,長大了,我一定得為國家做一點事情。
求學:懷揣報國理想上征程
懷著這個信念,我踏上了求學之路。中學進了聿懷中學,抗戰時聿懷遷到了揭陽的五經富,在山溝里。那時我14歲,跟著哥哥去五經富,交通斷了,就靠兩條腿走了整整四天,腳都磨出了好幾個血泡。但是沒有哭,我要讀書啊!那么危險、那么艱苦的環境,大家都挺著。五經富的學校搭的就是草棚,也不安全,日本飛機時不時來轟炸,我們就跑到更偏僻的山溝里。那時我又參加了抗日宣傳隊,到鄉村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我還是男扮女裝,演小姑娘。
后來,我們幾個同學又跑到桂林入了桂林中學。畢業后就到了柳州,從柳州坐火車到貴陽。那時都在大撤退。好不容易擠上車,行李都丟了。那時唐山交通大學遷到了貴陽,我就報考了。但是同學們還是決定到重慶去。在重慶我報考了中央大學的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學的造船系。結果兩所大學都錄取了。上交大的造船系我考了第一名。最終我選擇了上交大。因為我在海邊出生,海邊長大,對大海有感情啊!而且上交大被稱為“中國的MIT(麻省理工學院)”,理工科水平是國內最好的。
使命:對祖國盡忠就是最大的孝
工作以后,經組織選派,我參加了蘇聯援助中國的幾型艦船的轉讓制造和仿制工作,這也是保密性的工作。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中國希望蘇方能援助核潛艇項目,被拒絕了。赫魯曉夫提出成立中蘇聯合艦隊,由蘇聯艦船保護中國國土。當然我們也拒絕了。赫魯曉夫很狂妄,認為中國人搞核潛艇是“異想天開”。毛澤東主席很生氣,下定決心,一定要自己搞成,說“搞一萬年也要搞!”
那一年我就被調到了北京,一開始組織上就講得很清楚了,這是最高密級,必須隱姓埋名,絕對不能透露工作性質和工作單位。對此我是有思想準備的,服從組織決議,保護組織機密,這是一名黨員職責所在。
但是當時誰也不知道,這一搞就是三十年。1956年陽歷年的除夕我到廣東出差,順路回了老家,過了元旦兩三天我就又走了。一直到1988年我才又回了老家。
那次見面母親就跟我說,紹強(黃旭華原名),你從小就離家求學,我一直祈禱你平平安安的,現在都解放了,天下太平了,我們年紀也大了,希望你能常回家看看。實際上,1958年參加核潛艇研究后,工作就異常緊張,我就不可能回去,連信也極少寫。母親一直為我操心。我既不回家,也不聯系家里。她就給我寫信,問我,紹強,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無法回答。
1962年父親去世了,我沒有回去;1985年,二哥去世了,我沒有回去。那時應該寬松點了。夫人對我說,你回去吧,不然你會后悔一輩子的。我還是沒有回去。家里人意見很大,我兄弟姐妹一共九個,母親把他們叫在一起,說,你們要相信三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實母親也想不通,她的三兒到底在做什么呢?她自己不知道在心里流了多少眼淚。
1988年,我到大亞灣出差,終于順路回了老家。我62歲,母親95歲,我不知道說什么。跪在父親的墳前,我說,爸爸,你的不孝兒子回來看你了!你會像母親一樣原諒我吧!
有人說忠孝不能兩全,但是,對國家的忠,不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嗎?對母親的承諾我沒有做到,但是我沒有辜負對組織的誓言。這么多年,我的確虧欠父母、妻子、女兒太多了。我夫人李世英一直默默支持我,家里所有的事情都靠她一個人。
奉獻:我們這一代人都是這樣;
我們屬于核潛艇,無怨無悔
核潛艇的技術綜合性很強,三個方面“艇”指潛艇,“堆”指反應堆,“彈”指導彈缺一不可。剛開始我們只搞過蘇式仿制潛艇,而核潛艇與潛艇有著根本區別。要攻克的技術難題太多了,物質條件也跟不上,但我們靠的就是一種精神,一種責任。
1988年,我們在南海按設計極限作“深潛試驗”,這是最后關鍵環節也是危險性最大的試驗。在深海,一張撲克牌大小的鋼板就要承受一噸水的壓力,一艘艇100多米長,只要一個小環節出了問題,那就是致命的。70年代末,美國的“長尾鯊號”在做深潛試驗時就沒有上來,艇毀人亡。
有的同志給家里寫了遺書,做好了一切準備。同志們唱《血染的風采》,很悲壯。我覺得這樣不行,就召開技術骨干會,我說,我們都是搞科學的,要用技術說話,用技術保證安全性;我們的工作做得很細的,是有一定把握的;作為總設計師,我和大家一起下去!
你問我作為總設計師可不可以不下去呢?我必須得下去!即使我不下去,萬一有事,我怎么對得起大家,怎么對得起組織?我夫人也支持我下去。我說,我們不唱《血染的風采》,我們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試驗成功了。核潛艇安全順利靠岸,大家激動得哭了。后來我寫了一首詩以示紀念:南征應搗龍王廟,此戰驚雷震滿天;騎鯨日游八萬里,馭龍直上九重天。
“兩彈一艇”對新中國很重要,彈是原子彈、氫彈,艇就是指的核潛艇。我們這個團隊,幾十年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我們自己概括核潛艇精神就是四句話: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無私奉獻。我認為這種精神永遠不會過時,也適合現在的年輕人。還有,不要以為引進外國技術就什么都解決了,尖端技術,人家是不可能給你的。
核潛艇研制成功是集體智慧的結果,我只是其中一員而已。我們這個團隊的每一個人都沒有考慮過自己的事情,事業是第一位的。有很多同志,60多塊的工資一拿就是幾十年,退休了也沒趕上工資改革調整。我們在荒島上試驗,條件很艱苦,但是沒有一個人掉隊。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都是這樣的。我們屬于祖國,屬于核潛艇,我們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