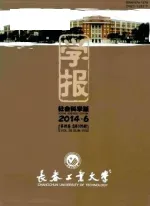先秦儒家“教化”思想的意識形態性及其功能
陳宗章
(南京郵電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南京210023)
先秦儒家教化思想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是在小農經濟、專制政治與宗法血緣制度下孕育和生長的,是歷史和社會實踐的產物。先秦儒家教化思想以“仁”為核心理念,以禮樂教化為主體內容,旨在一方面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一方面引導人們的行為合乎禮義道德規范,從而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筆者以為,其存在和發展的形態既表現為一種道德倫理,一種歷史文化資源,還表現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從而呈現出“多面”、“多維”的特征。探討先秦儒家教化思想的意識形態性,對于深化對其理論本身的理解,正確看待其歷史地位和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一、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教化”思想
一般以為,“意識形態”一詞最早是由法國學者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創造和使用的。在廣義上,“意識形態”一詞包含了政治性的意識形態和非政治性的意識形態。較之后者,前者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與意圖,并多依靠政治力量的支持,與世俗權力存在密切的關系。作為一種文化象征系統,新的意識形態的產生多與社會脫序相聯系,試圖重新確立社會發展的目標和方向,給整個世界提供一種指導性的說明。先秦(春秋戰國)時期恰是中國歷史上意識形態活動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先秦儒家提出了系統的“教化”理論,試圖拯救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在闡發其教化思想的過程中,先秦儒家構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化內容體系。它以“仁”為最高理念,使之作為處理人倫關系的根本道德規范和實現“為政以德”的根本法則,統攝其全部理論;同時,“禮樂教化”是其教化實施的核心內容和主要依賴路徑,具體又涉及義利觀、忠孝觀、誠信觀、榮辱觀、廉正觀、智勇觀和氣節觀等主要道德條目,從而構建起系統的內容體系。具體到個體與他人的關系,主張“仁者愛人”,踐行“推己及人”的實踐路徑;在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上,即表現為“為政以德”,達成社會的等級性和諧;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更是提升到“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境界,要求把人道與天道統一起來。
總體來說,先秦儒家教化思想不僅是一種道德倫理和文化資源,更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從而表達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從孔子、孟子到荀子,雖其教化理念略有差異,目的追求從“德政”、“仁政”到“王政”亦有發展,但在諸多差異的背后,可以明顯體悟到他們在思想內容和思維邏輯上的一脈相承性,其實質都是在踐行“為政以德”的根本理念,重視道德教化對于個人修養和國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理路。對先秦儒家教化實施的目的而言,在個體層面上,追求修身養性,培養一種君子品格,力圖通過教化使得“自然的人”最終轉變為“道德的人”;在社會層面上,其最終目的在于整合社會、治理國家,維護有序的社會等級秩序,[1]從而體現出滿足社會、政治發展需要的工具性意義,最終把道德個體轉變為“政治的人”、“社會的人”,同時使得社會“成為人的社會”。總之,先秦儒家的教化是從人的“治氣養心”開始的,由“修身”而“平治天下”,呈現出其內在的目的結構。它不僅強調個體在道德修養上的主體性發揮,還注重過程的潛移默化、循序漸進,并最終指向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務實的政治實踐目標。由此,它把道德理想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把個體修養與國家治理結合起來,把個體價值與社會價值結合起來,把理想人格與理想社會結合起來。最終,把“形上立道”與“形下行道”相統一起來,努力構建出自身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可見,雖然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自西漢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起才上升為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但是在先秦時期,作為一般意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就已經形成了。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分析到,以政治為業有兩種方式:一是“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而生存。[2]對于先秦儒家的教化實施而言,正是體現了這一點。力圖實現“以德為政”的先秦儒者們,一方面秉持“道”的精神,發揮道德對于政治的提升和轉化功用;另一方面又以“入世”的精神,使自己的道德與政治學說融入現實的政治實踐之中,很好地體現了“為”政治與“靠”政治而生存和發展的雙重意蘊,體現出濃厚的“意識形態性”。
二、政治意識形態話語權力的建構
俞吾金曾指出,教化是通過語言來進行的,個人接受教化的過程也就是學習語言的過程。而語言在實際的傳授和運用過程中,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一定的意識形態為導向,傳授語言的過程本質上就是傳授意識形態的過程。[3]先秦儒家已經意識到了語言或言論對于國家政治發展的重要性作用,充分體現在其“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基本判斷之中。因此,先秦儒家在其教化思想中充分展現了對意識形態的引導和控制功用的重視,以期構建起儒家學說在社會意識形態競爭中的話語權力。
在孔子的教化思想中,就包含了對異己思想的排斥。《論語·為政》有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處“異端”多指與孔子相異的主張和論斷,或為不正確的諸類議論。孔子之所以提出這一思想,與其“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判斷是分不開的。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在與定公的對話中,孔子立足于君王在政治運行中的模范性作用,指出其言論正確與否對國家興衰具有重要意義。由此,君主的一言一行被賦予強烈的道德倫理色彩,以至在對君主個人言行的約束中表達出對具有高尚道德修為之君主的期盼。孔子正是覺察到言論對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從而在其教化思想中提出了“攻乎異端”的思想。
在這一點上,孟子提出了他的“定于一”的思想,積極反映了戰國時期統一戰爭的社會發展趨向。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強調只有天下歸于一統,才能實現安定。他進一步指出,只要君王“不嗜殺人”就能統一天下,使民心歸服。實質上,孟子在闡明實施“仁政”的重要性,勸說梁襄王只有“為政以德”,才能安定國家。而這里的“定于一”不僅僅是政治上的統一,還內涵思想上實現大一統的意蘊。對此,可以通過孟子的其他言論得以明證。孟子生活的年代,是一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年代,對此孟子深表憂慮,明確提出:“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觀點,即要消滅楊朱、墨翟的學說,發揚孔子的仁義之道,以至于達到“正人心,息邪說,距陂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的目的。孟子的這一思想應該是對孔子“攻乎異端”思想的發展,闡明了臣民的隨意言論對于君主絕對權威和政治統治的威脅。他還進一步分析到:“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明確指出片面、過分、不合正道和閃躲的言辭都存有弊端,如不加以控制,它們就會“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害于其事”,從而破壞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較之孔孟,荀子“援法入禮”,把“法”視為實施教化的重要手段,積極主張禮法并用。對于“法”的重視,表現在荀子的教化思想中就是“以言治罪”思想的產生,試圖依靠刑罰來壓制異己言論,體現出嚴厲的治世思想。荀子認為:“圣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后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荀子·非相》)認為社會上錯誤的輿論和小人之辯帶有很大的破壞性,其惡劣影響甚于盜賊,從而主張對異己的政治意識形態實行強力的壓制。由此觀之,先秦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世之顯學,乃至后來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獲取主流的教化地位,與其教化思想中積極構建自身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權力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然,伴隨自西漢以降政治化儒家思想的運作,其對于言論控制的思想亦為專制統治者所利用和改造,從而成為專制者壓制民眾言論、打擊異己力量的重要手段。
三、在道德與政治之間:功能呈現及本質
第一,既服務于現存的社會關系,又勾畫出未來的社會發展圖景。從先秦儒家教化思想的產生可以觀之,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教化思想是與當時的社會條件緊密聯系的。先秦儒家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入世”中談論“人”的問題,在現實中尋求提升人性的最佳解決方案,而不是把它放置于一種脫離現實生活的超越性狀態之中。由此,我們務必把先秦儒家教化思想放置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進行理解。如薩金特(L·T·Sargent)所以為:“意識形態為其信仰者提供了這個世界‘是如何’及‘應如何’的圖像,并借此將這個世界驚人的復雜性,組織成極簡單且可理解的事物。”[4]簡單來說,先秦儒家的教化設計基于先秦時期的社會現實,努力恢復周禮在社會中的積極作用,以期改變“禮崩樂壞”的混亂無序狀態。它的入世精神是積極服務于現實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之重構的。同時,它又展現出自身明確的道德價值取向和政治理想目標,為人們設計出一幅美麗的“王道”圖景。可見,先秦儒家教化思想不僅體現為一種道德行為規范,還體現為一種政治理路,從而把個體的道德行為與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秩序等同起來。[5]
第二,以一般民眾為取向,積極引導人們的社會(政治)行動。有些研究者以為先秦儒家還沒有獲得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它僅僅局限于一種觀念系統,不具有社會實踐意義。其實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并非只有官方意識形態才能以實踐狀態存在。先秦儒家教化思想不僅是一種觀念系統,也是一種實踐系統,只是其實踐價值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不具有普遍性意義。先秦儒家的教化實施首先指向的是為政者階層,隨后擴大到所有受眾。其根本性意義在于通過意識形態的傳播和教育活動,引導人們的社會行為符合禮義道德規范的具體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把人從自然存在物提升為社會存在物,成為合格的“道德的人”與“政治的人”。這個過程的展開更多地是在“仁道”理念的指導下,通過“禮治”實現的。正所謂“為國以禮”,“禮”成了人與人之間的主要交往形式,并在對“禮”的遵守中不斷認同國家的政治等級秩序。這樣,個體作為主體的意識形態性就得到表達,即在先秦儒家的教化體系中,個體只有獲取對“禮”的普遍性認可,才能更好地生活于現實社會之中,才能維護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第三,體現了教化理念與政治發展之間的契合性互動關系。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先秦儒家教化思想很好地體現了自身的教化理念與現實政治發展之間的“合拍性”。在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中,一方面它肯定了人在政治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中庸》)荀子亦有曰:“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荀子·君道》)這種思維的習慣主要源于先秦儒家把政治放置于道德之中,即通過對人的道德本體的反思來把握政治的意義與價值,從而體現政治的人文情懷。這種理念設計,使得道德主動介入政治實踐之中,力圖實施王道政治,從而為抗議暴政、反對政治上的投機行為提供了理論基準,同時也為人治模式的專制政治提供了合法性明證。另一方面,政治的實施過程被理解為道德教化的過程,力圖通過個體的道德修為來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在孔子的教化學說里,即使坐而論道宣講自己的教化理念,不必居官也是一種政治實踐上的努力。這種“儒家式”的政治參與,根本上就是要建立和維護一種和諧的社會價值秩序,實現自身努力追求的道德和政治理想。先秦儒家對于現實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極大關懷,恰恰體現了自身積極的入世精神,是對儒者或士階層社會角色和責任擔當的預設,以便把自己的教化理念在道德理想主義的引領下落實到國家政治實踐之中。同時,先秦儒家教化思想所構建的“軟硬兼施”的教化模式也有效地把封建倫常觀念深入到民本的“仁”與宗法的“禮”的規范要求之中。
針對于此,需要進一步探討的一個問題是: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純粹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嗎?有研究者明確表示,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家教化思想是一種純粹的為世俗權力服務的政治工具。持此類觀點的研究者,多是把教化思想與宗法等級直接聯系起來,以為宗法等級制度是壓抑人性的、是戕害人的生命價值的,所以建基于這一“社會存在”之上的教化思想必然是否定個體的,而僅僅是專制者用來統治民眾、愚弄民眾的權力手段和工具。需要思考或辨析的問題是,對于(先秦)儒家而言,其教化思想與宗法等級并非機械地一一對等的關系。因為,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教化思想一定要反映當時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但是它自身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換言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為我們研究一種思想或意識形態提供了基本的方向,但是這種方向卻不能簡單地決定著由社會存在的性質而直接斷定某種思想或意識形態的性質。比如,同樣是先秦的社會存在,就可以產生儒、墨、道、法等等具有較大差異的社會意識形態。否則,那將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僵化、教條式的解讀和運用。而事實上,出于對“道德”與“政治”密切關系的理性認知,在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識形態之中始終滲透著“道統”的精神,這是一種道德對政治的批判和約束精神,充滿了先秦儒家力圖以自身的教化系統制約、引導和轉化世俗權力系統的努力,而其教化思想中,如“泛愛眾”、“舍生取義”等思想亦包含了諸多超越宗法等級、血緣家族制度的理念,這是我們必須理解和承認的部分。
歸根結底,先秦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質在于“道德的政治”,道德是作為統攝和引導政治的意義出現的,它并不是要把道德作為實現政治的工具性手段,恰恰是把政治作為達成道德理想的現實條件,而“視道德修養為實現政治理想的指導原則”。[6]那么,為什么會出現上述的觀點呢?從先秦儒家教化思想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孔子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以禮樂教化為表征的政治意識形態。但是,由于當時的思想完全受制于天帝的絕對權威和宗法血緣,因此帶有較強的強制性。正是孔子把“仁”引入禮樂教化之中,通過“仁”與“禮”的互動關系,才使得一種外在的強制性規約轉化為道德主體內在的自覺,促使這種新型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再局限于政治力量的強制,而是發源于內心的自覺意識。換言之,傳統儒家教化思想集中在道德領域,旨在升華人性,即便在政治領域,也是為了達成“為政以德”的理想目標,以道德轉化現實政治,而非期許一種權力的控制,從而最終使“人”成為“人”的存在,使社會成為“人”的社會。而這一切都建基于人性的訓練和養成,完成自我在內在精神上的升華和超越。由此,傳統儒家“否定了政治是一種權力的觀點,更否定了國家純是壓迫工具的讕言……于是人與人之間,不重在從外面的相互關系上去加以制限,而重在因人自性之所固有而加以誘導熏陶,使其能自反自覺,以盡人的義務。”[7]
但問題的關鍵是,這種把道德視為權力的尺度的理想性構思,在一定程度上把政治的約束局限于道德規范,從而忽視權力制約機制的整體性建構,不僅起不到真正的約束功能,相反道德往往為世俗權力所利用乃至扭曲,使得教化系統成為政治權力的附庸。同時,由于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建立在宗法等級制度之上,是很難發展出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和法制精神的。因此,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在人格缺失和權力的監督機制缺失的情況下,非常容易導致政治上的腐敗、扭曲。于是,自西漢以降,儒學由一般性的政治意識形態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一方面它的理想性的道德話語依然發揮作用,并作為批判性的話語體系不斷與世俗的專制權力展開斗爭;另一方面,政治化的儒學亦借助政治的權威來維護自身的權威,并為專制政權作合法化的辯護,成為“一家一姓”的意識形態,淪為世俗權力的工具。由此,對于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這一政治意識形態,務必從其發展的整體過程來對待,才能展現其全貌。切不可對之作化約主義的認識,簡單作出“是一種政治統治工具”的結論,否則,容易抹煞先秦儒家教化思想中“道統”的一面,影響后人對它的理性批判與科學繼承。
[1]陳宗章,尉天驕.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轉型的“教化論”審視[J].學術論壇,2011,(2).
[2]〔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M].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3]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修訂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L·T·Sargent,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rev.ed.,Homewood,IL:Dorsey Press,1972.
[5]〔美〕利昂·P·巴拉達特.意識形態:起源和影響[M].張慧芝,張露璐,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
[6]杜維明.杜維明文集[M].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7]徐復觀.徐復觀文集[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