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輕與重——對(du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女性代碼的再解讀
張巧歡
(嘉應(yīng)學(xué)院 文學(xué)院,廣東 梅州514015)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米蘭·昆德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昆德拉是小說(shuō)革新派的佼佼者,他慣有的創(chuàng)作模式是以小說(shuō)的形式進(jìn)行哲學(xué)的思辨,因此在這部作品中充斥著大段的抽象論述,以及跳出故事情節(jié)的哲理思考。但是無(wú)論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敘事性的還是思考性的敘述,小說(shuō)最后的旨?xì)w總是在對(duì)主題的把握。
昆德拉說(shuō)過(guò):“世界過(guò)去表現(xiàn)為男人的形象,現(xiàn)在將改變?yōu)榕说男蜗蟆K匠夹g(shù)性、機(jī)械化方向發(fā)展,越是冷冰冰、硬邦邦,就越需要惟有女人才能給予的溫暖。要拯救世界,我們必須適應(yīng)女人的需要,讓女人帶領(lǐng)我們,讓永恒的女性滲透到我們的心中。”[1](P329-330)因此,《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除了對(duì)人類生存進(jìn)行探尋之外,還特別關(guān)注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特蕾莎和薩比娜這兩個(gè)女性代碼則集中表達(dá)了昆德拉的這種關(guān)注,而且這兩個(gè)女性形象也帶給現(xiàn)代女性以啟示和反思。
一、存在之重的代表——特蕾莎
“最沉重的負(fù)擔(dān)壓迫著我們,讓我們屈服于它,把我們壓到地上。但在歷代的愛(ài)情詩(shī)中,女人總渴望承受一個(gè)男人身體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負(fù)擔(dān)同時(shí)也成為了最強(qiáng)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fù)擔(dān)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實(shí)存在。相反,當(dāng)負(fù)擔(dān)完全缺失,人就會(huì)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huì)飄起來(lái),就會(huì)遠(yuǎn)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個(gè)半真的存在,其運(yùn)動(dòng)也會(huì)變得自由而沒(méi)有意義。”[2](P5)這是小說(shuō)中關(guān)于“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輕”的解釋。其中的“生命”一詞,筆者認(rèn)為它在原文中是更為抽象的“存在”(being)。因此,討論“生命”的“輕”與“重”,其實(shí)就是探詢“存在”的“輕”與“重”。生命之重是人存在的沉重感、壓抑感。在生命中,人有著理想、欲望、責(zé)任和與之而來(lái)的束縛,而這一理想或欲望的滿足又會(huì)產(chǎn)生新一輪的欲望,無(wú)休無(wú)止,便使人體會(huì)痛苦、深重與壓抑。而生命之輕則是在生命中追求自由自在、隨心所欲、身心愉悅和心靈放縱。
小說(shuō)中,特蕾莎以弱者的形象出現(xiàn)。在整個(gè)人生中,她不斷追求自己的理想和試圖滿足自己的欲望,但隨之帶來(lái)的卻不是幸福,而是無(wú)比的沉重感。特蕾莎是存在之重的代表,她承受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一)特蕾莎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
特蕾莎成為“重”的代表的首要因素是其成長(zhǎng)環(huán)境。特蕾莎成長(zhǎng)在一個(gè)極其不幸的家庭。在這個(gè)家庭中,貧苦的物質(zhì)環(huán)境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不算什么,但貧瘠的精神環(huán)境對(duì)她造成的卻是致命的打擊。因?yàn)樘乩偕幸粋€(gè)“自我毀滅”的母親。她的母親曾經(jīng)是一位被稱贊像拉斐爾畫中的圣母一樣的漂亮女人。在她談婚論嫁的時(shí)候,曾經(jīng)有九個(gè)男子向她求婚,分別是英俊、機(jī)智、富有、健康、高貴、才學(xué)、旅行者、音樂(lè)家、男子漢,她最終選擇了第九個(gè)。并不是因?yàn)樗钣心凶託飧牛且驗(yàn)閼焉咸乩偕坏貌患藿o他。最后她覺(jué)得另外八個(gè)人的求婚,每個(gè)都比第九個(gè)強(qiáng)。所以,母親認(rèn)為特蕾莎是其不幸生活的罪魁禍?zhǔn)住榱诵梗谩白晕覛纭钡姆绞饺仐壦拿利惡颓啻海灿谩白晕覛绲呐e止”去體現(xiàn)粗俗的自己。為了報(bào)復(fù),她也讓特蕾莎過(guò)著與自己同樣“自我毀滅”、沒(méi)有羞恥的生活,剝奪了特蕾莎的一些自由與權(quán)力,摧殘著特蕾莎的靈魂。在特蕾莎母親看來(lái),“在這個(gè)世界里,青春和美貌了無(wú)意義,世界只不過(guò)是一個(gè)巨大的肉體集中營(yíng),一具具肉體彼此相像,而靈魂是根本看不見(jiàn)的。”但是特蕾莎從小就有一個(gè)理想,她渴望脫離母親,脫離“肉體的集中營(yíng)”;渴望著真正的自己,一個(gè)具有靈魂的自己;渴望著自己靈與肉和諧統(tǒng)一的理想。但是人生中理想的實(shí)現(xiàn)并不是輕而易舉的,在與母親對(duì)抗的過(guò)程中,特蕾莎感受到了生命的沉重。所以,特蕾莎選擇實(shí)現(xiàn)自己理想的那一刻就是其選擇承受生命之重的開(kāi)始。
(二)特蕾莎的性愛(ài)觀與現(xiàn)實(shí)的沖突
特蕾莎的理想是追求靈與肉的和諧統(tǒng)一。但是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體驗(yàn)每一次都使她體會(huì)到了靈與肉沖突的兩重性和矛盾性。這讓她覺(jué)得非常沉重。“當(dāng)她第一次邁進(jìn)托馬斯寓所門檻的時(shí)候,肚子一陣陣地咕嚕咕嚕叫,這與瘋狂的愛(ài)同時(shí)產(chǎn)生,當(dāng)靈魂要進(jìn)行一場(chǎng)激情歡愛(ài)時(shí),肉體卻肆無(wú)忌憚地產(chǎn)生了饑餓感,與靈魂相抗衡。”她也試著把靈魂懸置,去嘗試肉體的放縱。雖然暫時(shí)出現(xiàn)了肉體的滿足,但是最終并沒(méi)有產(chǎn)生愛(ài)情。西美爾認(rèn)為:“對(duì)男性來(lái)說(shuō),性只是他做的一件事情;對(duì)女性而言,性是其存在的方式。”[3](P150)特蕾莎將性與愛(ài)看作一體。性愛(ài)不僅是愛(ài)情的所在,更是自我存在的方式。然而她的愛(ài)人托馬斯卻將性愛(ài)分離,以及由此帶來(lái)的無(wú)數(shù)謊言給特蕾莎帶來(lái)了難言的傷痛。靈魂與肉體的和諧統(tǒng)一是特蕾莎神圣美好的追求,然而她的愿望始終沒(méi)有實(shí)現(xiàn),這讓她的生活如此沉重,但她卻又始終無(wú)力改變。
(三)特蕾莎的軟弱性格和依附意識(shí)
“軟弱”的性格、對(duì)男性的依附和服從也讓特蕾莎承受著生命之“重”。在“自我毀滅”的母親眼里,特蕾莎始終處于自我缺失的狀態(tài)。特蕾莎的母親肆意踐踏肉體、夸耀丑陋的同時(shí)也在踐踏著特蕾莎的尊嚴(yán)、摧毀著特蕾莎的靈魂。因此,特蕾莎努力逃離母親的世界,試圖尋找真正的自己。特蕾莎在托馬斯的強(qiáng)大力量中去尋求依靠和庇佑。然而托馬斯的男人世界卻讓她變得更軟弱。特蕾莎成為了托馬斯男性世界里的所謂“他者”,沒(méi)有自我存在的基礎(chǔ)。特蕾莎的根本就是托馬斯這個(gè)男人。托馬斯的一句“把衣服脫了”,就能讓特蕾莎激動(dòng)不已,只想聽(tīng)命于他和服從于他。雖然特蕾莎知道托馬斯是一個(gè)不能信任的男人,并且無(wú)法接受托馬斯的背叛和生活方式,但是她的軟弱又使她沒(méi)有能力離開(kāi)托馬斯,沒(méi)有辦法不去依附這個(gè)男人生存。即使是她決定離開(kāi)蘇黎世回到布拉格獨(dú)自生活的原因也還是因?yàn)樗能浫酢L乩偕能浫踝屗粩嗟匾与x生命之“重”,但又始終讓她承受著生命之“重”。小說(shuō)最后寫到特蕾莎為了逃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而回到了田園牧歌式的大自然,這便成了她最后的安息之處。
二、存在之輕的代表——薩比娜
薩比娜是小說(shuō)中“存在之輕”的代表與特蕾莎完全不同的生命體驗(yàn)。這個(gè)女性形象順從自我感覺(jué),完全卸下生命背負(fù)的重?fù)?dān)。在她的人生中,她通過(guò)不斷的背叛和反抗媚俗的方式去追求自由自在、隨心所欲、身心愉悅和心靈放縱的生命體驗(yàn)。她承受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
(一)薩比娜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
薩比娜的整個(gè)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是一個(gè)不斷背叛的過(guò)程。可以說(shuō)背叛對(duì)薩比娜來(lái)說(shuō)有著致命的誘惑。她的背叛是從背叛父親開(kāi)始的。在她十四歲時(shí),她愛(ài)上了一個(gè)男孩,但受到其父親的反對(duì)。薩比娜為了報(bào)復(fù)父親,去學(xué)父親瞧不起的立體派美術(shù)。中學(xué)畢業(yè)后,她就去了布拉格,并為背叛了家庭感到一絲的寬慰。她的背叛之路從此開(kāi)始。后來(lái)她又繼續(xù)背叛了她的另一個(gè)“父親”——共產(chǎn)主義,原因是美術(shù)學(xué)院并不允許她像畢加索那樣地去畫畫,而是必須遵循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派的畫法。她還選擇嫁給一個(gè)離經(jīng)叛道的平庸丈夫,氣死了她的父親。接著她又離開(kāi)了丈夫,因?yàn)樗X(jué)得她的丈夫不再是一個(gè)乖張的浪子,而是變成一個(gè)討人厭的酒鬼。“第一次的背叛不可挽回。它引起了更多的背叛,如同連鎖反應(yīng),一次次使我們離最初的背叛越來(lái)越遠(yuǎn)”。所以,她只能不停地背叛。背叛讓薩比娜擺脫了成長(zhǎng)中的一切沉重與束縛,是她承受生命之輕的開(kāi)始。
(二)薩比娜是反抗媚俗的代表
上面說(shuō)到,薩比娜背叛一切盛行的東西,歸根結(jié)底,她背叛的是媚俗。而薩比娜也因?yàn)榉纯姑乃椎倪^(guò)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個(gè)性和自由讓她成為了“輕”的代表。
媚俗是什么?媚俗一詞源于德語(yǔ)的Kitsch,被米蘭·昆德拉在多次演講中引用。昆拉德認(rèn)為:媚俗是人類的一種通病,是一種以撒謊作態(tài)和泯滅個(gè)性來(lái)取悅大眾,取寵社會(huì)的行為。劉小楓說(shuō):“昆拉德講述的薩比娜反抗媚俗,顯得像是卡吉婭的男友們的女人想象的言語(yǔ)謀略。”[4](P98)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薩比娜反抗的媚俗是整個(gè)帶有男權(quán)特征的政治制度和極權(quán)文化,以及從古希臘蘇格拉底起就被定義了的善與惡、美與丑的“絕對(duì)價(jià)值觀”。
性愛(ài)是薩比娜與男性對(duì)抗的場(chǎng)所。在與弗蘭茨的性愛(ài)過(guò)程中,她顛覆了傳統(tǒng)男權(quán)思想中男性凝視女性,女性被看的模式,取而代之是女性凝視男性,男性被看的嶄新模式。弗蘭茨在薩比娜面前是弱小的,“做愛(ài)時(shí)他總是閉著眼睛。”而薩比娜則睜著眼睛,目光高高在上,仔細(xì)觀察對(duì)方的一切,就像托馬斯喜歡觀察不同女人做愛(ài)一樣。這就是薩比娜的對(duì)傳統(tǒng)男權(quán)思想的背叛,一種反抗媚俗的行為。她用背叛的方式來(lái)宣泄女人在男人面前失去自我的憤恨。她用這種反抗媚俗的態(tài)度、觀念和行為,構(gòu)建了她的女性話語(yǔ)和女性世界。
薩比娜這個(gè)女性形象選擇了背叛作為其人生的準(zhǔn)則,背叛她生命中一切可以背叛的東西,直至最后走向空虛。她的悲劇不是因?yàn)橹兀且驗(yàn)檩p。壓倒她的不是生命之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三、兩個(gè)女性代碼的現(xiàn)代啟示
盡管特蕾莎和薩比娜這兩個(gè)女性已經(jīng)成為代碼,并不特指生活中的具體某一個(gè)人,但是在她們身上,現(xiàn)代女性或多或少能找到一些自我的影子。這兩個(gè)女性代碼給予現(xiàn)實(shí)中的女性極為重要的現(xiàn)代啟示。
(一)特蕾莎人物代碼的啟示
特蕾莎不失為現(xiàn)實(shí)中女性的一種典型形象。這類女性試圖抓住一個(gè)男人,并且緊緊依附著這個(gè)男人生活。本以為可以組建一個(gè)幸福的家庭以逃離原本不幸福的家庭,但最終發(fā)現(xiàn)生活其實(shí)是不完美的,她們失去了最為重要的自我生活,她們只是從一種不幸逃到另一種不幸。
特蕾莎期望一個(gè)男人來(lái)?yè)崞匠砷L(zhǎng)中的委屈與恐懼,把自己當(dāng)作公主來(lái)對(duì)待。而一旦這種不切實(shí)際的期望無(wú)法達(dá)到,就心懷憤怒,把自己的恐懼軟弱和不幸統(tǒng)統(tǒng)歸罪于身邊的男人。考慮到托馬斯的生活方式,特蕾莎的恐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對(duì)于一個(gè)從小就時(shí)刻練習(xí)著要在睡夢(mèng)中緊緊抓住男人的手的女人,我們懷疑并不會(huì)存在有能力讓她感到安全與幸福的那個(gè)人。其實(shí)特蕾莎不是真的愛(ài)托馬斯,托馬斯只是她逃離讓她痛苦的母親的手段,一根救命稻草。依賴與愛(ài)是不相容的,愛(ài)是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自主選擇。這種建立在女人依賴男人,以喪失自我為代價(jià)來(lái)?yè)Q取安全穩(wěn)定的生活的婚姻必然成為愛(ài)情的墳?zāi)埂U嬲膼?ài)情對(duì)女性而言不是依附而是獨(dú)立、自由。正如波伏瓦所說(shuō):“真正的愛(ài)情應(yīng)該建立在兩個(gè)自由人相互承認(rèn)的基礎(chǔ)上;這樣情人們才能感受到自己即是自我又是他者;既不會(huì)放棄超越,也不會(huì)被弄得不健全;他們將在世界共同證明價(jià)值與目標(biāo)。對(duì)于這一方和那一方,愛(ài)情都會(huì)由于贈(zèng)送自我而揭示自我,都會(huì)豐富這個(gè)世界。”[5](754)
雖然特蕾莎有著軟弱、依附的缺點(diǎn),但是她并沒(méi)有失去對(duì)女性主體意識(shí)的探求和思索。特蕾莎不堪忍受生命的沉重,最后逃遁到風(fēng)光美麗的鄉(xiāng)村田園,過(guò)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她夢(mèng)到托馬斯變成了一只野兔,這個(gè)夢(mèng)有兩重含義。一是意味著在特蕾莎的世界里托馬斯不再是強(qiáng)者,從此特雷莎沒(méi)有了男性的強(qiáng)大力量和肉體對(duì)她的壓迫;二是意味著大自然里人與弱小的動(dòng)物都擁有同等的生命和權(quán)利,人也無(wú)非是地球的管理者,并沒(méi)有誰(shuí)比誰(shuí)強(qiáng)的說(shuō)法。特蕾莎這個(gè)時(shí)候才終于覺(jué)得自己獲得了幸福。其實(shí)特蕾莎的這種感悟與生態(tài)女性主義的觀點(diǎn)是一致的。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試圖尋求一種不脫離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文化,反對(duì)人類中心論和男性中心論,主張改變?nèi)私y(tǒng)治自然的思想。在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看來(lái),地球上的生命是一個(gè)互相聯(lián)系的網(wǎng),并無(wú)上下高低的等級(jí)之分,女性更接近于自然,而男性的倫理的基調(diào)是對(duì)自然的仇視。[6](P84-85)特蕾莎生活的田園鄉(xiāng)村就是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所認(rèn)為的世界,而這個(gè)世界可以說(shuō)就是生態(tài)主義構(gòu)建理想的真實(shí)寫照。
(二)薩比娜人物代碼的啟示
特蕾莎的逃避幼稚不徹底,而薩比娜的逃避則是漫無(wú)目的,形式大于內(nèi)容。她為了背叛而背叛,以為一切的背叛都是在反對(duì)“媚俗”。在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中,或許我們都有過(guò)類似薩比娜那種憤世嫉俗、反對(duì)一切的想法。但是當(dāng)我們年齡漸長(zhǎng)才逐漸意識(shí)到,這樣的反叛是毫無(wú)建設(shè)性的,是既無(wú)力量也無(wú)價(jià)值的。總有一天,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我們也和薩比娜一樣,會(huì)有無(wú)從背叛的時(shí)候,也就是自己被背叛本身背叛的一天。一旦自己成為被背叛的對(duì)象,而不再是背叛的主體,背叛就不再是輕飄飄的革命浪漫主義的一首詩(shī),而是沉重的十字架,一片黑暗凄涼的死亡之境。
如果說(shuō)特蕾莎選擇生活的方式與當(dāng)代生態(tài)主義觀點(diǎn)一致的話,那么薩比娜可以說(shuō)是文化女性主義或是激進(jìn)女性主義的代表。文化女性主義或者激進(jìn)女性主義強(qiáng)調(diào)兩性的差別,并且認(rèn)為這種區(qū)別中女性屬于比較高明的一方。例如,從倫理道德方面看,女性高于男性,女性的自我犧牲、母性和關(guān)懷理論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暴力(著重攻擊性)和競(jìng)爭(zhēng)性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那么現(xiàn)代女性是否應(yīng)該效仿薩比娜成為文化女性主義或者激進(jìn)女性主義的倡導(dǎo)者呢?在這里筆者的觀點(diǎn)是:首先我們要承認(rèn)薩比娜這個(gè)女性形象的進(jìn)步性——醒悟到兩性的區(qū)別及女性不應(yīng)該在男性之下,不應(yīng)該在男性面前失去人格和尊嚴(yán)。但是,我們也不能走向另一個(gè)極端,認(rèn)為這個(gè)世界應(yīng)該是女尊男卑的世界。筆者認(rèn)為,現(xiàn)代女性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可以更傾向于后現(xiàn)代女性主義的觀點(diǎn)。后現(xiàn)代女性主義主張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人有各種差別,但不一定是對(duì)立和截然兩分的狀況,而是一個(gè)以黑白為兩級(jí)的充滿各種間色的色譜系統(tǒng)。在他們眼中,兩性差異不是簡(jiǎn)單的兩極分化,而被視為一個(gè)復(fù)雜的、多側(cè)面的、動(dòng)態(tài)的體系。所以,我們?cè)诳创齼尚圆町惖膯?wèn)題上不能夠簡(jiǎn)單地認(rèn)為這個(gè)世界是男尊女卑的世界或者是女尊男卑的世界。
其實(shí)特蕾莎和薩比娜這兩個(gè)女人都是拼命要從自己原有的生活中逃離的弱者,只是選擇的手段不同,導(dǎo)致成為“存在之重”與“存在之輕”的代碼。那么通過(guò)特蕾莎和薩比娜這兩個(gè)女性代碼,現(xiàn)代女性應(yīng)該覺(jué)悟到,雖然女性由于先天生理上的特點(diǎn),成長(zhǎng)中所受的教育,在社會(huì)生活權(quán)利分配中相對(duì)弱勢(shì)的地位,導(dǎo)致在傳統(tǒng)意義上女人的相對(duì)軟弱,但是我們作為一個(gè)個(gè)體仍然能夠選擇努力自強(qiáng)成為自己的主人,我們應(yīng)該爭(zhēng)取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兩性的平等,承認(rèn)和保留兩性的差異,為女性生存的個(gè)性發(fā)展和自我完善創(chuàng)造充分的條件。
[1]〔捷〕米蘭·昆拉德.不朽[M].寧敏,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2]〔捷〕米蘭·昆拉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M].許鈞,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3]李銀河.西方性學(xué)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劉小楓.沉重的肉體[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全譯本)[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guó)書籍出版社,1998.
[6]李銀河.女性主義[M].濟(jì)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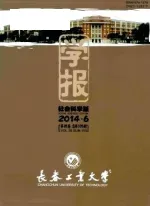 長(zhǎng)春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年2期
長(zhǎng)春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年2期
- 長(zhǎng)春工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在遼寧的鴉片政策研究
- 東漢磚文與《太平經(jīng)》引進(jìn)處所介詞“在”的使用情況
- 能源期現(xiàn)二市場(chǎng)內(nèi)核信息流動(dòng)雙層多主體博弈研究
- 技術(shù)性貿(mào)易壁壘對(duì)中國(guó)農(nóng)產(chǎn)品出口的影響效應(yīng)分析
- 管理概念源頭追問(wèn)
- 從設(shè)計(jì)的細(xì)節(jié)關(guān)注老齡化社會(hu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