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quán)利貧困視角下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困境及出路
楊芳+張昕
摘要: 隨著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農(nóng)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發(fā),嚴(yán)重?fù)p害農(nóng)民的群體利益。然而,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行動(dòng)卻經(jīng)常陷入困境:在權(quán)利制度供給不足和公力救濟(jì)渠道不暢的情況,農(nóng)民往往選擇徘徊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私力救濟(jì)手段,由此產(chǎn)生的非理性維權(quán)又常陷入政府剛性維穩(wěn)困局,最終形成維權(quán)與維穩(wěn)相互掣肘、私權(quán)與公權(quán)相互抗衡的局面。解決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之困的關(guān)鍵要從以下幾個(gè)方面消除權(quán)利貧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環(huán)境公正;完善權(quán)利救濟(jì)機(jī)制,提高公力救濟(jì)效能;變非法維權(quán)為依法維權(quán),避免權(quán)利濫用;變剛性維穩(wěn)為韌性維穩(wěn),防止權(quán)力恣肆。
關(guān)鍵詞:農(nóng)地污染;權(quán)利貧困;維權(quán);維穩(wěn)
中圖分類號(hào):F323.2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9-9107(2014)04-0022-10
一、問(wèn)題的提出與理論構(gòu)建
伴隨著我國(guó)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深入發(fā)展,因工業(yè)污染轉(zhuǎn)移引發(fā)的農(nóng)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發(fā),由污染導(dǎo)致的農(nóng)民維權(quán)事件也頻頻發(fā)生,由于農(nóng)地污染往往牽涉眾多農(nóng)民的群體利益,維權(quán)活動(dòng)一般也以群體形式出現(xiàn),有時(shí)還采取過(guò)激行動(dòng),甚至釀成群體性治安事件,具有一定的違法性、危害性[1],因而研究者大多關(guān)注群體性行動(dòng)對(duì)社會(huì)穩(wěn)定的消極影響,并從公共治理或政府維穩(wěn)角度考察其發(fā)生機(jī)理及治理對(duì)策,而忽視其背后的農(nóng)民權(quán)利貧困現(xiàn)象,相應(yīng)地,從權(quán)利救濟(jì)視角研究其積極的意義則相對(duì)遲滯和薄弱。因此,從權(quán)利視角考察群體性事件對(duì)破解政府維穩(wěn)困局,不失為一個(gè)必要可行的研究思路,也頗具現(xiàn)實(shí)意義。
本文的理論建構(gòu)既是對(duì)我國(guó)政府多年維穩(wěn)經(jīng)驗(yàn)的深刻反思,也是法治社會(huì)政府創(chuàng)新社會(huì)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核心問(wèn)題是理順社會(huì)管理與民主法治、公權(quán)力與私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平衡。就農(nóng)地污染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而言,意味著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在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的過(guò)程中,應(yīng)當(dāng)把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與群體性治安事件區(qū)別開(kāi)來(lái),認(rèn)真地對(duì)待農(nóng)民的維權(quán)訴求,努力讓受損的權(quán)利得到充分、有效、便捷的救濟(jì),使權(quán)利的光輝驅(qū)散困擾社會(huì)穩(wěn)定的陰霾。其理論依據(jù)和法治基礎(chǔ)在于:首先,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具有正當(dāng)性基礎(chǔ)。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動(dòng)力機(jī)制雖然復(fù)雜,但最根本的還是被動(dòng)的“壓迫性反應(yīng)”[2],是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環(huán)境權(quán)、生存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等合法權(quán)益被肆意侵害后的無(wú)奈之舉。其次,群體維權(quán)凸顯農(nóng)民權(quán)利意識(shí)的覺(jué)醒,有助于農(nóng)民法律情感的養(yǎng)成和農(nóng)村環(huán)境法治的實(shí)現(xiàn),正如耶林所言,“為權(quán)利而斗爭(zhēng)有助于培養(yǎng)國(guó)民的法感情”,“這種培養(yǎng)……是把正義原則實(shí)際地貫徹于一切生活關(guān)系”[3]。再次,群體維權(quán)暴露農(nóng)民訴求表達(dá)機(jī)制和權(quán)益保障機(jī)制的脆弱,對(duì)社會(huì)穩(wěn)定起到“報(bào)警器”和“減壓閥”作用,社會(huì)能通過(guò)它進(jìn)行適時(shí)調(diào)整[4]。政府倘能以積極維穩(wěn)觀和權(quán)力觀,因勢(shì)利導(dǎo),理性應(yīng)對(duì),便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shí)現(xiàn)政府維穩(wěn)和農(nóng)民維權(quán)的雙贏,不然則會(huì)陷入“越維越不穩(wěn)”的困境。又次,群體維權(quán)作為農(nóng)民實(shí)現(xiàn)群體權(quán)利的一種補(bǔ)救措施,與純粹的聚眾泄憤、社會(huì)騷亂等群體性治安事件有本質(zhì)不同,其實(shí)施過(guò)程可能蘊(yùn)含對(duì)社會(huì)不公的宣泄,采取法外維權(quán)手段還會(huì)增加政府維穩(wěn)壓力,但是其根本目標(biāo)仍然是對(duì)受損權(quán)益進(jìn)行的體制內(nèi)救濟(jì),不具有挑戰(zhàn)現(xiàn)有秩序的政治欲求。總之,農(nóng)民維權(quán)與政府維穩(wěn)并不對(duì)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前者通過(guò)實(shí)現(xiàn)個(gè)體利益訴求進(jìn)而修補(bǔ)被損壞的社會(huì)利益格局;后者通過(guò)排除社會(huì)不穩(wěn)定因素進(jìn)而保障個(gè)體權(quán)益再遭侵害。
基于此,本文以近幾年發(fā)生的農(nóng)地污染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和環(huán)保部門(mén)公布的環(huán)保信息為實(shí)證資料,考察當(dāng)前制約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的三大因素——權(quán)利制度供給不足之困、公力救濟(jì)途徑不暢之困和私力救濟(jì)非法化之困,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破解農(nóng)民維權(quán)和政府維穩(wěn)困境的若干建議。
摘要: 隨著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農(nóng)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發(fā),嚴(yán)重?fù)p害農(nóng)民的群體利益。然而,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行動(dòng)卻經(jīng)常陷入困境:在權(quán)利制度供給不足和公力救濟(jì)渠道不暢的情況,農(nóng)民往往選擇徘徊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私力救濟(jì)手段,由此產(chǎn)生的非理性維權(quán)又常陷入政府剛性維穩(wěn)困局,最終形成維權(quán)與維穩(wěn)相互掣肘、私權(quán)與公權(quán)相互抗衡的局面。解決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之困的關(guān)鍵要從以下幾個(gè)方面消除權(quán)利貧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環(huán)境公正;完善權(quán)利救濟(jì)機(jī)制,提高公力救濟(jì)效能;變非法維權(quán)為依法維權(quán),避免權(quán)利濫用;變剛性維穩(wěn)為韌性維穩(wěn),防止權(quán)力恣肆。
關(guān)鍵詞:農(nóng)地污染;權(quán)利貧困;維權(quán);維穩(wěn)
中圖分類號(hào):F323.2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9-9107(2014)04-0022-10
一、問(wèn)題的提出與理論構(gòu)建
伴隨著我國(guó)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深入發(fā)展,因工業(yè)污染轉(zhuǎn)移引發(fā)的農(nóng)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發(fā),由污染導(dǎo)致的農(nóng)民維權(quán)事件也頻頻發(fā)生,由于農(nóng)地污染往往牽涉眾多農(nóng)民的群體利益,維權(quán)活動(dòng)一般也以群體形式出現(xiàn),有時(shí)還采取過(guò)激行動(dòng),甚至釀成群體性治安事件,具有一定的違法性、危害性[1],因而研究者大多關(guān)注群體性行動(dòng)對(duì)社會(huì)穩(wěn)定的消極影響,并從公共治理或政府維穩(wěn)角度考察其發(fā)生機(jī)理及治理對(duì)策,而忽視其背后的農(nóng)民權(quán)利貧困現(xiàn)象,相應(yīng)地,從權(quán)利救濟(jì)視角研究其積極的意義則相對(duì)遲滯和薄弱。因此,從權(quán)利視角考察群體性事件對(duì)破解政府維穩(wěn)困局,不失為一個(gè)必要可行的研究思路,也頗具現(xiàn)實(shí)意義。
本文的理論建構(gòu)既是對(duì)我國(guó)政府多年維穩(wěn)經(jīng)驗(yàn)的深刻反思,也是法治社會(huì)政府創(chuàng)新社會(huì)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核心問(wèn)題是理順社會(huì)管理與民主法治、公權(quán)力與私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平衡。就農(nóng)地污染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而言,意味著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在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的過(guò)程中,應(yīng)當(dāng)把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與群體性治安事件區(qū)別開(kāi)來(lái),認(rèn)真地對(duì)待農(nóng)民的維權(quán)訴求,努力讓受損的權(quán)利得到充分、有效、便捷的救濟(jì),使權(quán)利的光輝驅(qū)散困擾社會(huì)穩(wěn)定的陰霾。其理論依據(jù)和法治基礎(chǔ)在于:首先,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具有正當(dāng)性基礎(chǔ)。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動(dòng)力機(jī)制雖然復(fù)雜,但最根本的還是被動(dòng)的“壓迫性反應(yīng)”[2],是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環(huán)境權(quán)、生存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等合法權(quán)益被肆意侵害后的無(wú)奈之舉。其次,群體維權(quán)凸顯農(nóng)民權(quán)利意識(shí)的覺(jué)醒,有助于農(nóng)民法律情感的養(yǎng)成和農(nóng)村環(huán)境法治的實(shí)現(xiàn),正如耶林所言,“為權(quán)利而斗爭(zhēng)有助于培養(yǎng)國(guó)民的法感情”,“這種培養(yǎng)……是把正義原則實(shí)際地貫徹于一切生活關(guān)系”[3]。再次,群體維權(quán)暴露農(nóng)民訴求表達(dá)機(jī)制和權(quán)益保障機(jī)制的脆弱,對(duì)社會(huì)穩(wěn)定起到“報(bào)警器”和“減壓閥”作用,社會(huì)能通過(guò)它進(jìn)行適時(shí)調(diào)整[4]。政府倘能以積極維穩(wěn)觀和權(quán)力觀,因勢(shì)利導(dǎo),理性應(yīng)對(duì),便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shí)現(xiàn)政府維穩(wěn)和農(nóng)民維權(quán)的雙贏,不然則會(huì)陷入“越維越不穩(wěn)”的困境。又次,群體維權(quán)作為農(nóng)民實(shí)現(xiàn)群體權(quán)利的一種補(bǔ)救措施,與純粹的聚眾泄憤、社會(huì)騷亂等群體性治安事件有本質(zhì)不同,其實(shí)施過(guò)程可能蘊(yùn)含對(duì)社會(huì)不公的宣泄,采取法外維權(quán)手段還會(huì)增加政府維穩(wěn)壓力,但是其根本目標(biāo)仍然是對(duì)受損權(quán)益進(jìn)行的體制內(nèi)救濟(jì),不具有挑戰(zhàn)現(xiàn)有秩序的政治欲求。總之,農(nóng)民維權(quán)與政府維穩(wěn)并不對(duì)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前者通過(guò)實(shí)現(xiàn)個(gè)體利益訴求進(jìn)而修補(bǔ)被損壞的社會(huì)利益格局;后者通過(guò)排除社會(huì)不穩(wěn)定因素進(jìn)而保障個(gè)體權(quán)益再遭侵害。
基于此,本文以近幾年發(fā)生的農(nóng)地污染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和環(huán)保部門(mén)公布的環(huán)保信息為實(shí)證資料,考察當(dāng)前制約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的三大因素——權(quán)利制度供給不足之困、公力救濟(jì)途徑不暢之困和私力救濟(jì)非法化之困,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破解農(nóng)民維權(quán)和政府維穩(wěn)困境的若干建議。
摘要: 隨著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快速發(fā)展,農(nóng)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發(fā),嚴(yán)重?fù)p害農(nóng)民的群體利益。然而,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行動(dòng)卻經(jīng)常陷入困境:在權(quán)利制度供給不足和公力救濟(jì)渠道不暢的情況,農(nóng)民往往選擇徘徊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私力救濟(jì)手段,由此產(chǎn)生的非理性維權(quán)又常陷入政府剛性維穩(wěn)困局,最終形成維權(quán)與維穩(wěn)相互掣肘、私權(quán)與公權(quán)相互抗衡的局面。解決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之困的關(guān)鍵要從以下幾個(gè)方面消除權(quán)利貧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環(huán)境公正;完善權(quán)利救濟(jì)機(jī)制,提高公力救濟(jì)效能;變非法維權(quán)為依法維權(quán),避免權(quán)利濫用;變剛性維穩(wěn)為韌性維穩(wěn),防止權(quán)力恣肆。
關(guān)鍵詞:農(nóng)地污染;權(quán)利貧困;維權(quán);維穩(wěn)
中圖分類號(hào):F323.2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9-9107(2014)04-0022-10
一、問(wèn)題的提出與理論構(gòu)建
伴隨著我國(guó)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深入發(fā)展,因工業(yè)污染轉(zhuǎn)移引發(fā)的農(nóng)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發(fā),由污染導(dǎo)致的農(nóng)民維權(quán)事件也頻頻發(fā)生,由于農(nóng)地污染往往牽涉眾多農(nóng)民的群體利益,維權(quán)活動(dòng)一般也以群體形式出現(xiàn),有時(shí)還采取過(guò)激行動(dòng),甚至釀成群體性治安事件,具有一定的違法性、危害性[1],因而研究者大多關(guān)注群體性行動(dòng)對(duì)社會(huì)穩(wěn)定的消極影響,并從公共治理或政府維穩(wěn)角度考察其發(fā)生機(jī)理及治理對(duì)策,而忽視其背后的農(nóng)民權(quán)利貧困現(xiàn)象,相應(yīng)地,從權(quán)利救濟(jì)視角研究其積極的意義則相對(duì)遲滯和薄弱。因此,從權(quán)利視角考察群體性事件對(duì)破解政府維穩(wěn)困局,不失為一個(gè)必要可行的研究思路,也頗具現(xiàn)實(shí)意義。
本文的理論建構(gòu)既是對(duì)我國(guó)政府多年維穩(wěn)經(jīng)驗(yàn)的深刻反思,也是法治社會(huì)政府創(chuàng)新社會(huì)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核心問(wèn)題是理順社會(huì)管理與民主法治、公權(quán)力與私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平衡。就農(nóng)地污染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而言,意味著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在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的過(guò)程中,應(yīng)當(dāng)把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與群體性治安事件區(qū)別開(kāi)來(lái),認(rèn)真地對(duì)待農(nóng)民的維權(quán)訴求,努力讓受損的權(quán)利得到充分、有效、便捷的救濟(jì),使權(quán)利的光輝驅(qū)散困擾社會(huì)穩(wěn)定的陰霾。其理論依據(jù)和法治基礎(chǔ)在于:首先,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具有正當(dāng)性基礎(chǔ)。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動(dòng)力機(jī)制雖然復(fù)雜,但最根本的還是被動(dòng)的“壓迫性反應(yīng)”[2],是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環(huán)境權(quán)、生存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等合法權(quán)益被肆意侵害后的無(wú)奈之舉。其次,群體維權(quán)凸顯農(nóng)民權(quán)利意識(shí)的覺(jué)醒,有助于農(nóng)民法律情感的養(yǎng)成和農(nóng)村環(huán)境法治的實(shí)現(xiàn),正如耶林所言,“為權(quán)利而斗爭(zhēng)有助于培養(yǎng)國(guó)民的法感情”,“這種培養(yǎng)……是把正義原則實(shí)際地貫徹于一切生活關(guān)系”[3]。再次,群體維權(quán)暴露農(nóng)民訴求表達(dá)機(jī)制和權(quán)益保障機(jī)制的脆弱,對(duì)社會(huì)穩(wěn)定起到“報(bào)警器”和“減壓閥”作用,社會(huì)能通過(guò)它進(jìn)行適時(shí)調(diào)整[4]。政府倘能以積極維穩(wěn)觀和權(quán)力觀,因勢(shì)利導(dǎo),理性應(yīng)對(duì),便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shí)現(xiàn)政府維穩(wěn)和農(nóng)民維權(quán)的雙贏,不然則會(huì)陷入“越維越不穩(wěn)”的困境。又次,群體維權(quán)作為農(nóng)民實(shí)現(xiàn)群體權(quán)利的一種補(bǔ)救措施,與純粹的聚眾泄憤、社會(huì)騷亂等群體性治安事件有本質(zhì)不同,其實(shí)施過(guò)程可能蘊(yùn)含對(duì)社會(huì)不公的宣泄,采取法外維權(quán)手段還會(huì)增加政府維穩(wěn)壓力,但是其根本目標(biāo)仍然是對(duì)受損權(quán)益進(jìn)行的體制內(nèi)救濟(jì),不具有挑戰(zhàn)現(xiàn)有秩序的政治欲求。總之,農(nóng)民維權(quán)與政府維穩(wěn)并不對(duì)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前者通過(guò)實(shí)現(xiàn)個(gè)體利益訴求進(jìn)而修補(bǔ)被損壞的社會(huì)利益格局;后者通過(guò)排除社會(huì)不穩(wěn)定因素進(jìn)而保障個(gè)體權(quán)益再遭侵害。
基于此,本文以近幾年發(fā)生的農(nóng)地污染群體性維權(quán)事件和環(huán)保部門(mén)公布的環(huán)保信息為實(shí)證資料,考察當(dāng)前制約農(nóng)民群體維權(quán)的三大因素——權(quán)利制度供給不足之困、公力救濟(jì)途徑不暢之困和私力救濟(jì)非法化之困,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破解農(nóng)民維權(quán)和政府維穩(wěn)困境的若干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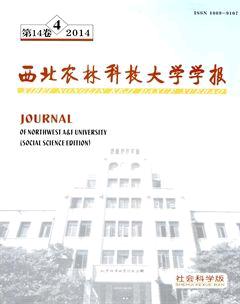 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年4期
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年4期
- 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從生態(tài)學(xué)到人類生態(tài)學(xué):人類生態(tài)覺(jué)醒的歷史考察
- 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流動(dòng)人口環(huán)境健康風(fēng)險(xiǎn)及治理
- 統(tǒng)籌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成就、挑戰(zhàn)及對(duì)策
- 中國(guó)省域節(jié)能減排效率評(píng)價(jià)及其影響因素
- 鄉(xiāng)村旅游:商品化、真實(shí)性及文化生態(tài)發(fā)展策略
- 陜西面花民間鄉(xiāng)土文化的傳承及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