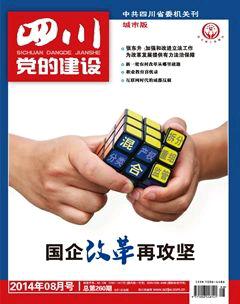職業(yè)教育喜憂錄
雷怡安
7月9日,許多學(xué)校已經(jīng)放暑假,而位于龍泉驛區(qū)同安鎮(zhèn)的成都汽車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里依然聚集著不少前來報(bào)名的新生和家長,因?yàn)槊~只有1000多個(gè),所以從早到晚報(bào)名辦公室就沒有安靜過。
“孩子中考沒考好上不了普通高中,所以選擇職業(yè)學(xué)校上學(xué)。”李芳群的兒子今年中考成績400多分,因?yàn)闆]有達(dá)到普通高中的分?jǐn)?shù)線,所以李芳群決定讓孩子學(xué)一技之長,這種選擇對(duì)于李芳群來講是一種無奈,與現(xiàn)場的人聲鼎沸形成了落差。
報(bào)名現(xiàn)場的家長和孩子臉上,似乎都帶著喜憂參半的神情,這也象征著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現(xiàn)狀。
點(diǎn)“贊”:
學(xué)以致用,就業(yè)率一直在提升
19歲的周永強(qiáng)對(duì)于自己的選擇沒有后悔。去年高考,周永強(qiáng)落榜。于是,他選擇一所離家較近的水利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上學(xué),對(duì)于周永強(qiáng)來講,他看重的是這個(gè)學(xué)校的專業(yè)性和就業(yè)率。
雖然下期開學(xué)才大二,但是學(xué)校已經(jīng)組織學(xué)生開展不定期的實(shí)習(xí)培訓(xùn),學(xué)以致用使他就讀的機(jī)電設(shè)備運(yùn)行與維護(hù)專業(yè)這幾年就業(yè)率都達(dá)到了100%。“讀書就是為了擇業(yè),每年都會(huì)有很多企業(yè)到學(xué)校來現(xiàn)場招人,就業(yè)前景挺不錯(cuò)的。” 周永強(qiáng)認(rèn)為,學(xué)習(xí)知識(shí)和技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學(xué)到對(duì)以后就業(yè)有幫助的東西。
近日,國家大力倡導(dǎo)發(fā)展職業(yè)教育的好消息,周永強(qiáng)并不清楚,但是看到每年學(xué)校的就業(yè)率,他相信兩年后自己畢業(yè)時(shí),找到對(duì)口的工作肯定沒有問題。
給職業(yè)學(xué)校點(diǎn)“贊”的不止是學(xué)生,已經(jīng)當(dāng)了20多年職業(yè)學(xué)校老師的張曉明,對(duì)近年來的變化感觸很多。過去,他所教授的汽車數(shù)控專業(yè)幾乎沒有實(shí)習(xí)的設(shè)備,勉強(qiáng)有幾臺(tái)都只能擺擺樣子,老師和學(xué)生根本無法親自操作,所以絕大多數(shù)知識(shí)只停留在書本上。
這幾年的變化讓他感到很欣慰,隨著成都龍泉驛區(qū)的主產(chǎn)業(yè)定位為汽車制造,學(xué)校的方向緊隨產(chǎn)業(yè)發(fā)展,也將服務(wù)于汽車產(chǎn)業(yè)這一大型鏈條定格為學(xué)校的基本發(fā)展目標(biāo)。于是,更加注重對(duì)數(shù)控技術(shù)應(yīng)用、汽車制造與檢測、汽車運(yùn)用與維修等課程的設(shè)置。張曉明認(rèn)為最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是,政府每年對(duì)他們專業(yè)投入100多萬元,這筆錢都用在新設(shè)備的購買上。
“沒有資金扶持,就沒有設(shè)備,沒有設(shè)備,就沒有條件培訓(xùn),就不可能培養(yǎng)出合格的學(xué)生。”張曉明說。2011年至今,從中央到省市區(qū)各級(jí)財(cái)政對(duì)汽車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的投入達(dá)2000萬元,場地設(shè)備1600萬元,在3年左右的時(shí)間里,政府對(duì)一所職業(yè)學(xué)校的投入將近4000萬元,這個(gè)數(shù)字對(duì)于一所職業(yè)學(xué)校的發(fā)展顯得尤為重要。
老觀念:
若隱若現(xiàn)的失落
2014年的高考過去兩個(gè)月了,大小媒體在爭相報(bào)道各地狀元榜之后,也都會(huì)針對(duì)落榜生這個(gè)群體介紹職業(yè)技術(shù)院校。雖然其中不乏有廣告的嫌疑,但職業(yè)院校的大量存在說明了市場對(duì)其的需求是明顯的。然而,社會(huì)對(duì)職業(yè)院校的看法還是讓人堪憂。
據(jù)一份不完全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顯示,在分?jǐn)?shù)線大致相當(dāng)?shù)那闆r下,選擇本科院校或者職業(yè)院校的人數(shù)比例差很大,其中僅有10%的人選擇就讀職業(yè)院校,而有90%的人選擇普通本科院校。
張曉明介紹,現(xiàn)在學(xué)校里,也只有20%的學(xué)生家長思想轉(zhuǎn)變了,還有80%的學(xué)生家長依然將就讀職業(yè)學(xué)校作為萬般無奈的選擇。已經(jīng)從重慶某職業(yè)學(xué)院畢業(yè)3年的李元偉,記起當(dāng)時(shí)高考結(jié)束后的場景依然五味雜陳。因?yàn)闆]有上本科線,父母對(duì)他很失望,覺得多年的辛苦都白費(fèi)了,而他身邊不少同學(xué)都考上了本科院校,這也讓他多了一份自卑,整個(gè)暑假都很少和同學(xué)來往。
李元偉父母的失望和對(duì)職業(yè)學(xué)校的擔(dān)心不僅僅是個(gè)別情況,中國多數(shù)的家庭依然將能不能進(jìn)入不錯(cuò)的高中和大學(xué),作為衡量一個(gè)孩子成功與否和一個(gè)家庭多年付出后收獲大小的標(biāo)準(zhǔn)。孩子在職業(yè)學(xué)校讀書的家庭似乎總有一種失落感和自卑感。
企業(yè):
要名號(hào)還是要技能
中國家庭對(duì)職業(yè)教育認(rèn)同感低的原因除了對(duì)“功名”的追捧外,還面臨著許多企業(yè)、公司依然崇尚“重點(diǎn)”大學(xué)名號(hào)的困局。李元偉在學(xué)校讀了3年的計(jì)算機(jī)應(yīng)用,當(dāng)他從學(xué)校走出來,并沒有如愿進(jìn)入一家IT公司,許多公司在應(yīng)聘時(shí)聽說他來自職業(yè)學(xué)校,就拒絕了他,甚至有少數(shù)公司直接告訴李元偉,他們要招的是985、211重點(diǎn)大學(xué)的畢業(yè)生。幾經(jīng)挫折后,他不得不考取了導(dǎo)游證,做起了導(dǎo)游。
近幾年,名校名企的聯(lián)合發(fā)展模式備受青睞,重點(diǎn)大學(xué)憑借其優(yōu)秀的學(xué)校資質(zhì)吸引了不少知名企業(yè)來校開講座,學(xué)校也會(huì)提供機(jī)會(huì)讓學(xué)生到企業(yè)去實(shí)習(xí)培訓(xùn),這種模式為學(xué)生鋪設(shè)了不錯(cuò)的就業(yè)道路,也正因?yàn)橛兄@樣的資源,所以促使更多的學(xué)生希望擠進(jìn)重點(diǎn)學(xué)校,因?yàn)檫@意味著自己離名企又近了一步。
曾瑞2007年畢業(yè)于西南交通大學(xué),從2003年進(jìn)校他就同時(shí)參加了北大青鳥職業(yè)課程學(xué)習(xí)。“北大青鳥的課程很有針對(duì)性,對(duì)以后就業(yè)非常有幫助。”曾瑞認(rèn)為這些課程主要是針對(duì)當(dāng)前IT行業(yè)比較熱門的技術(shù)設(shè)計(jì),還會(huì)隨IT行業(yè)的新動(dòng)態(tài)進(jìn)行調(diào)整,比起普通大學(xué)更能及時(shí)的適應(yīng)IT行業(yè)的技術(shù)需求。當(dāng)時(shí)他經(jīng)常上網(wǎng)看IT行業(yè)招聘的條件,發(fā)現(xiàn)有些條件是自己通過學(xué)校學(xué)習(xí)達(dá)不到的。于是他選擇到北大青鳥IT職業(yè)教育學(xué)校學(xué)習(xí)。
在北大青鳥學(xué)習(xí)的3年時(shí)間里,曾瑞先后考取了勞動(dòng)部認(rèn)證的初級(jí)程序員、中級(jí)程序員和軟件工程師,這些對(duì)曾瑞畢業(yè)后找工作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今他已經(jīng)是該公司的一名股東。
如果回過頭來讓曾瑞重新選擇是直接就讀職業(yè)學(xué)校還是重點(diǎn)大學(xué),曾瑞還是選擇重點(diǎn)大學(xué),“直接上職業(yè)學(xué)校也不是不好,但還有很多企業(yè)對(duì)學(xué)校的‘名氣是看中的。”知名企業(yè)對(duì)學(xué)校的偏好也導(dǎo)致了一般性大學(xué)和職業(yè)學(xué)校的差別待遇。
成都汽車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校長助理張興華認(rèn)為,真正的校企合作現(xiàn)在還很不足,不少企業(yè)會(huì)考慮成本、價(jià)值以及培養(yǎng)這些學(xué)生給自身帶來了多少效益的問題。雖然企業(yè)本質(zhì)上應(yīng)該追逐效益,但是在同時(shí)并存的社會(huì)責(zé)任和企業(yè)效益之間,不少企業(yè)放棄了社會(huì)責(zé)任。所以這也導(dǎo)致一些企業(yè)不愿意和職業(yè)學(xué)校合作。endprint
發(fā)展困局:
師資、升學(xué)通道
師資的稀缺也是職業(yè)教育發(fā)展中遇到的不小問題。據(jù)調(diào)查,現(xiàn)在普通中學(xué)的師生比例為1:12.5,而職業(yè)學(xué)校的師生比例還是1:30。由于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緊跟市場發(fā)展的節(jié)奏,所以對(duì)于職校的教師培養(yǎng)任務(wù)顯得更加必要,但是職校教師人少課程多,所以培養(yǎng)計(jì)劃總是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教育部明文要求職校教師每兩年要到企業(yè)去實(shí)習(xí)兩個(gè)月,由于職校教師任務(wù)太重,所以這項(xiàng)措施幾乎沒有實(shí)行過。2014年,成都汽車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獲得了國家、省、市各級(jí)教師培養(yǎng)項(xiàng)目共20個(gè)名額,但培訓(xùn)和教學(xué)任務(wù)相沖突,最終只派了6名教師去“充電”培訓(xùn)。
在師資的培養(yǎng)上,張興華很是為難,一方面學(xué)校特別看重對(duì)教師的專業(yè)知識(shí)培養(yǎng),另一方面如果一名教師出去學(xué)習(xí)了,那他的工作量就會(huì)分?jǐn)偨o其他的教師,相對(duì)于普通中學(xué)一個(gè)教師每周8節(jié)的課程安排,職業(yè)學(xué)校教師每周有18節(jié)課程。高強(qiáng)度的課程設(shè)置讓許多教師都沒有機(jī)會(huì)出去培訓(xùn)。
“如果教育局能夠多給我們職業(yè)學(xué)校一些教師名額,我們就可以多派一些教師出去學(xué)習(xí)。”學(xué)校教師的人數(shù)問題仍然是制約職業(yè)學(xué)校發(fā)展的一個(gè)瓶頸。
現(xiàn)在不少職業(yè)教育似乎走向了一個(gè)死胡同,多數(shù)職高學(xué)生面臨著無法升入大學(xué)的困境,大學(xué)在眼界和思維上能夠給與學(xué)生更多地幫助,幫助他們更好地學(xué)習(xí)知識(shí)技能,同時(shí)打開思維模式,走出既定的技術(shù)套路。然而職高學(xué)生文化課程上的劣勢,導(dǎo)致了多數(shù)學(xué)生無法升入更高一級(jí)的學(xué)校就讀,不能進(jìn)一步提升自己學(xué)習(xí)到的技能知識(shí),就只會(huì)囿于現(xiàn)有的知識(shí),這就大大縮小了他們的就業(yè)前途,因此低端的技術(shù)工作常常是他們畢業(yè)后的工作方向。
變局之年:
讓每個(gè)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jī)會(huì)
6月23日,習(xí)近平總書記專門對(duì)職業(yè)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牢牢把握服務(wù)發(fā)展、促進(jìn)就業(yè)的辦學(xué)方向,深化體制機(jī)制改革,創(chuàng)新各層次各類型職業(yè)教育模式,努力建設(shè)中國特色職業(yè)教育體系,努力讓每個(gè)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jī)會(huì)。這對(duì)于中國的職業(yè)教育發(fā)展可謂意義重大。
同日,李克強(qiáng)總理在人民大會(huì)堂接見了參加全國職業(yè)教育工作會(huì)議的代表。他說:“我們要用大批的技術(shù)人才作為支撐,讓享譽(yù)全球的‘中國制造升級(jí)為‘優(yōu)質(zhì)制造。”
中國有13億人口,9億多的勞動(dòng)人口,要將“中國制造”轉(zhuǎn)變成“優(yōu)質(zhì)制造”是現(xiàn)階段中國產(chǎn)品必須要跨過的一道坎。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憑借著人數(shù)多的優(yōu)勢,“中國制造”以量的投入打進(jìn)國際市場,而現(xiàn)在為了縮小和中等發(fā)達(dá)國家的差距,就必須在質(zhì)上有突破有創(chuàng)新,要將中國的人口壓力轉(zhuǎn)化成人才優(yōu)勢,加大職業(yè)教育的投入,將職業(yè)技能和職業(yè)精神作為發(fā)展的重點(diǎn)。
這一系列的指示意見發(fā)出了一個(gè)信號(hào):國家將大力發(fā)展職業(yè)教育,而這種發(fā)展不再僅僅是針對(duì)單純的學(xué)校教育,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已緊緊地和國民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聯(lián)系在了一起。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顯示,“十一五”以來職業(yè)院校累計(jì)為國家輸送了近8000萬名畢業(yè)生,占新增就業(yè)人口的60%。“十二五”以來,中央財(cái)政每年投入150億元打造職業(yè)教育。
四川在職業(yè)教育的投入上也下了大力氣,據(jù)2011年統(tǒng)計(jì),3年的時(shí)間四川職業(yè)教育基礎(chǔ)場地投入近130個(gè)億,建成一大批國家級(jí)、省級(jí)示范職業(yè)院校。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huì)”,省教育廳副廳長王康更建議將職業(yè)教育融入國家產(chǎn)(事)業(yè)發(fā)展體系建設(shè)和整體布局,政府應(yīng)要求所有用人單位都要主動(dòng)參與人才培育工作,并承擔(dān)一定的責(zé)任和經(jīng)費(fèi)。“用人單位參與人才的培育,或?yàn)槁殬I(yè)學(xué)院提供師資、設(shè)備、實(shí)習(xí)崗位或?qū)嵙?xí)費(fèi)用的,可以折算成相關(guān)的成本,從其承擔(dān)的經(jīng)費(fèi)中扣減。”
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迎來了一個(gè)“春天”。而中國的職業(yè)教育向前一步的發(fā)展步子到底怎樣,多數(shù)人都期待著。
曾在德國學(xué)習(xí)培訓(xùn)兩個(gè)月的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的秦老師深有感觸:“如果中國的職業(yè)教育能打破一次性教育的禁錮,發(fā)展為像德國一樣的終身教育,那么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前景會(huì)很好,整個(gè)市場的發(fā)展和國家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都會(huì)得到很大的提升。”(責(zé)編:賀貴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