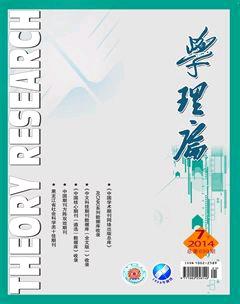量論因明認識論之研究
姜鐵穩
摘 要:量論因明主要包括推理規則和認識論兩部分內容。佛教邏輯之認識論部分有一個自身而展的邏輯過程。古因明時期主張知識之來源是現量、比量和圣教量,而新因明時期則主張知識之來源是現量和比量。試圖對古因明時期之量與當時各哲學派別進行比較,對古因明時期的現量、比量、圣教量進行闡釋,研究新因明時期陳那之二量,最后研究法稱之量與成量,進而得出量論之根本目的在于成就量。
關鍵詞:量論因明;現量;比量;量;成量
中圖分類號:B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1-0043-03
量論因明,亦即佛教邏輯。總的說來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關于推理論證之學問,一是關于認識論之學問。推理論證主要是研究推理中的邏輯規則和邏輯錯誤,其主要包括九句因、因三相、因三十三過等等內容;而認識論主要研究現量和比量。認識論是佛教邏輯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可以說,只有對佛教邏輯認識論有了深刻的認知,我們才能真正地了解佛教邏輯。按照佛教邏輯的發展歷史進程來看,簡要地說,古因明時期以《瑜伽師地論》為代表,新因明時期以陳那《集量論》為集大成者,而佛教邏輯之最高峰則以法稱《釋量論》為標志。佛教邏輯正是一步步從注重論辯的規則發展到以認識論為主,即以量論為主。目前學界主要集中在對佛教邏輯之邏輯規則部分進行研究。因此,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佛教邏輯之認識論部分做一個綜合性研究,以期對佛教邏輯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一、對古因明時期之量與印度哲學各派之量的比較
量論因明之“量”,梵文為PramANA,可譯為量、規則、權威、正確認識之手段、真實之觀念、定量、理、因明等等,可見其意蘊之豐富。量總的說來,既包括邏輯的規則,也包括行為的法則。依其規定,量乃知識確實性之規定,亦即知識種類之問題。從印度哲學的歷史來看,印度的知識確實性之問題,實則是印度各哲學派別學問之核心問題。基于印度哲學各派對于量的認識不盡相同,從現有的文獻可以看到,對量的理解約有十種:
1.現量:在眼前、一目了然、現法。
2.比量:比量謂比類之量也,即是以分別之心,以已知之事比知未知之事。
3.圣教量:又名圣言量。是借助權威而獲得的認識。
4.譬喻量:也譯為“義準量”。是指通過譬喻來顯示的量,根據已知之物與未知物的相似來認識未知物。
5.假設量:又譯為“義準量”,指通過兩概念間的蘊含關系而獲得知識。
6.無體量:是通過觀察某處沒有某種東西,因而產生不存在某物的判斷。
7.世傳量:指有一種傳言,這種傳言不指明它最初是由何處產生的。
8.姿態量:指姿態也能成為一種量,因為姿態能夠表達一種思想感情。
9.外除量:即用排除某類中的分子的方法以獲知識。
10.內包量:指根據包含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的存在來認知這一事物的存在[1]170。
對量的理解如此之多,那么何為正量?大致說來,印度各哲學派別依其教義而對量的理解有所不同。例如,耆那教承認第二種量為正量,順世論承認第一種量為正量,數論派和瑜伽派承認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為正量等等。不過,也有的哲學派別承認上述九種或十種量都是正量。
對于佛教而言,印度五世紀以前,古因明時期,《方便心論》以現見、比知、以喻知、隨經書等四量作為知因。則佛典對現量的表述不一。《方便心論》規定現量為“五根之所知”;五根即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其分別有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的機能。我們的這五根所感知到的即是現量;《瑜伽師地論》規定現量為“現量者。謂有三種。一非不現見。二非已思應思。三非錯亂境界”。現量有三種情況,一是現見;一是當下的思才是現量,過去了的不是現量,還沒有來的也不現量;一是不是錯亂的認知。如有眼病而看到有兩個太陽,如乘船頭暈而覺得天在轉動、地在動搖等等。《大乘阿毗達摩集論》規定現量“自正明了,無迷亂義”。即指能夠正確認知事物,沒有發生任何迷亂之心。古因明時期對現量的規定表述不盡相同,但其共同點是,對現量的定義都強調正確之認知,強調對知識的把握需要本人親自感受,而且隱含只有當下的感知才是最真實的。
古因明時期,對比量之認識也各有差別。《大乘阿毗達摩集論》曰“現量外之信解”。《方便心論》將比量分為前比比量、后比比量、同比比量。其中“前比者,如見小兒有六指頭上有瘡,后見長大聞提婆達,即便憶念本六指者,是今所見。是名前比。后比者。如飲海水得其堿味。知后水者皆悉同堿。是名后比。同比者。如即此人行至于彼。天上日月東出西沒。雖不見其動。而知必行”。《金七十論》分為有前、有余、平等。此與數論派、正理派的有前、有后、共見相當。簡約地說,“有前”即是從現在推知過去,“有后”是指從現在推知未來,“共見”是從現在推知現在。而在《瑜伽師地論》中則云比量乃是“與思擇相共之已思應思之所有境界”,并提出五種比量:1)相比量;2)體比量;3)業比量;4)法比量;5)因果比量。相比量即是類比推理,也含有據因果關系而進行推理;體比量即是根據事物之類進行推理,也含有類比推理的性質;業比量是根據行為的性質進行推理;法比量是根據事物之間屬性的相似性進行推理;因果比量是根據因果關系進行推理。那么這五個比量之分類是否科學?是否據此可以獲得正確之知識呢?有學者認為,從邏輯的推理方法來看,《瑜伽師地論》的比量顯得很幼稚,但從五支作法的角度看,其無疑把因明學推進了一大步[2]51-56。對于《瑜伽師地論》之分類,日本武邑上邦指出,《瑜伽師地論》之因明說,沒有能跳出論證邏輯的限制。其局限于以宗為圣教量,依據比量智而得解脫的正理學之立場,而獲得真知,這是不可能的[3]48-52。
顯然,古因明時期,佛教把圣教量作為宗,對圣教量只需要接受,無需質疑和論證。其信仰容易使人心生疑惑,最終導致人們不能獲得真知。隨著佛教邏輯內在自身的發展,其理論的完備將由陳那建構。
二、對新因明時期現量和比量之認識
大約在公元五、六世紀時,新因明之開創者陳那在《正理門論》曰:“為自開悟,唯有現量與比量。”即認為正確認識的途徑只有兩個:一是現量,一是比量。相應地,人們的知識對象只能有兩個:一是自相,一是共相。自相亦即感性認知,共相亦即理性認知;自相亦即直接認知,共相亦即間接認知。而所謂的圣教量、因果比量、譬喻量等等量,實質上被現量和比量所包含。認知途徑之種類由認知對象所決定。陳那《正理門論》曰:“此中現量除分別者。謂若有智于色等境遠離一切種類名言。假立無異諸門分別。由不共緣現現別轉。故名現量。”
因此,現量就是于色等境中遠離了一切言語。若現見某事物,試圖用言語表達出來,那么所處之境不再是現量境。現量之境實只能體會不可言說。正如《金剛經》所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凈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思想是,試圖使人在現量之認知中,生起對宇宙人生之真確認知。又,陳那將現量分為:一依據五根而得的感覺性的認識,二與此同時生起的意識,三自證,四修定者的無分別心。除第四種現量為定心現量,其余三種都是有錯亂的散心現量。
何為比量?《正理門論》曰:“余所說因生”。即是說比量智之產生是以現量智作為基礎。正確的比量智應遵守三相正因。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門論》曰:“謂藉眾相而觀義”。比量以事物之共相為研究對象,以一定的理由或者事實為推理的依據,在記憶、想象等思維活動的指引下,從而獲得對事物的間接認知。比量有兩種,一是真比量,一是似比量。區別何種為真比量,何種為似比量,其依據是因的正還是不正。如果依據的是正因,則是真比量;如果是不正的因,則是似比量。那么,正因從何而來呢?在公元7世紀,窺基法師的《因明入正理論疏》曰:
智為了因,火、無常等,是所了果。以其因有現、比不同,果亦有兩種,火、無常別。了火從煙,現量因起;了無常等,從所作等,比量因生。
現見“此山有煙”,比知“此山有火”,此因即現量因;現見“聲是所作性”,比知“聲是無常”,此因即比量因。可見,正因之來源為現量因和比量因。又,比量可分為幾種?陳那在《集量論》之《為自比量品》曰:“比量有二種,為自與為他。”為自比量即通過三相因而觀察義,為他比量即是傳達自我觀察所得之物[3]2-10。為自比量以三相因,通過觀察得出結論,已達到對事物的自我開悟。其開悟的過程無須借助于言語。那么,若觀察義之時,觀察者本人也借助了言語,那么還是不是為自比量呢?我以為,在實際的推理過程中,雖然可以不言說,但是借助已有的認知,借助于語言文字在內心處進行推理,此種情形依然屬于為自比量。為他比量則借助于語言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所悟。
古因明時期,無著與世親認為知識之來源為現量、比量和圣教量。《瑜伽師地論》卷十五曰“一切智所說之言教稱為圣教量”。圣教量有三:一是不違圣言,一是能治雜染,一是不違法相。無著在《大乘阿■達摩集論》中主張圣教量和現量、比量并不相違。而后期唯識學派之陳那認為圣教量不是正確知識來源之一。
陳那《集量論》曰:“聲起非離比,而是其他量。由遣他門顯,自義如所作。”[4]110陳那認為聲是比量,言語“聲”僅是遮詮。如說“所作”,遮“非所作”;說“無常”,則詮“非無常”。一切言語都有遮詮作用。由此,聲只能是比量。圣教量依然是聲、言語,所以圣教量也依然是比量。陳那隨之認為,知識的來源只有現量和比量,基于陳那如是之立場,即使是佛陀的言說,也只能通過現量和比量進行認識,不能盲目地信仰。這也是陳那的真理觀。可以說,陳那首先是一位徹底地具有批判主義精神的邏輯學家,然后才是一位虔誠的偉大的佛教徒。取消圣言量,實質上亦是佛陀之本意。佛陀曰:“眾善知識,汝等于我所言,莫唯以彼,敬畏之念,而生執著。博聞強記,成為學者,精進研修,若能如是,善哉善哉!恰如金匠,以火煅之,碎為細片,以石磨之,盡一切法,精打細敲,善哉善哉![3]48-52
知識的來源是現量和比量,這是佛陀本人的認識論。此表明了佛教一開始就具有徹底的批判精神。早期佛教中采取三量之說,實際上是后學誤會了佛陀之本來思想。自陳那以后,佛教邏輯發生了一個根本性地轉向,即從因明學轉向了量論。量論所要構建的是,如何使人走向成佛之路,使人獲得解脫的智慧。
三、對量論之量和成量的認識
量論之“量”,是佛教知識論之總稱,佛學之最終目的是成量,即成為定量。也就是成佛。釋迦牟尼佛本人就是定量士夫。陳那《集量論》歸敬頌“敬禮成量欲利生,大師善逝救護者”。量論因明從知識論的角度而言,就是通過現量和比量,最終達到定量士夫。法稱之《釋量論》專門辟《成量品》一章,講述量之總相為何,世尊為何是正量。《成量品》開篇曰“量謂無欺智”。僧成大師解釋曰“量之總相謂新生無欺智”[5]97。量的定義是無欺智,即是正智。法上論師認為正智是與經驗不相違的知識,如果知識能指引我們達至他所言之境,那么該知識就是正確的。
陳那《正理滴論》曰:“眾人所務,凡得成遂,必以正智為其先導。是故彼智,此論今詳。正智有二。一者現量,二者比量。”[6]24-25陳那和法稱對量的定義,其語言表達方式不相同。陳那對量定義時,是遮“欺”詮“正智”;法稱對量定義時,是遮“欺”詮“無欺”。實質上,法稱是繼承了陳那對量的看法,只不過法稱說得更加細致罷了。法稱認為,量識的性相是新起而非欺誑之智。所謂“新生”,即是指在第一剎那間所生起的認知,以此排除一切非第一剎那間之認知,比如已決智就會被排除掉。當認知不是處在第一剎那間,而是處于第二剎那,甚或第三剎那間等等,那么這就是已決智了。“無欺”是指對所緣境而言。也就是對認識之對象——所知境無欺騙,以此消除一切邪智邪見。這些邪知邪見妨礙了對所知境的真實認知,而只有量才能對所知境如實反映。“智”是佛所說的般若智慧、無上遍正覺,以此避免錯誤的量識。
不欺智是量,則還包括比量。外道則認為不能包括比量,其理由是以比量不以自相為所取境故。法稱反駁道“如通達具煙山上有火之比量,是不欺誑,以是通達安住能燒煮作用之覺故”。即看到此山上有煙,推斷此山上有火。煙與火是不相離的。佛教邏輯要歸到勝義有之真實存在,而這已經不再單純是邏輯問題,而是關于宇宙人生之真相了。佛教邏輯最終已然超越了名相,落實到名相背后之真相。
不欺智是量,則還包括聲。外道以為“若不欺智量相者,不應道理,以不能遍聲起量故”[5]97-98。即是說如果不欺智是量,那么就不應包括聲。法稱對此反駁,認為聲顯示了起聲的人所欲達到境,則聲所生起的量應是無欺。如言說“山”,說者在心中能夠生起真實存在之境,即“山”的真實存在,使其表象在認識主體的內心活動中顯現。此時,對于“山”而言是量。當言說“山”之聲時,說者的心中隨即有了“山”之表象,說“山”的聲是不欺。其量滿足因三相。然而說“瓶”聲時,并不是意味著現見某處有真實之“山”,此不以瓶的現實真實存在為因。
不欺智是量,但不是由根現量里之見分或相分確立量,而依自證現量確立量。在自證現量里,超越了見分和相分,例如面對藍色,當面對藍色之境所新生的第一剎那的認識,這才是正量。之后,當試圖把當下之境用言語表達出來,那就不再是量了,而是后得智。因此,法稱認為境是有次第的,新生也是有次第的。同一個命題有不同次第,每一次第之間都是新生。量永遠只能是生死相續,永遠新生。新生即是無常。按照佛教的觀點,無常有二種:一是剎那間的無常,即是剎那剎那有生住異滅之變化也;一種是相續的無常,即謂一期相續之上有生住異滅之四相。佛陀從“聲是無常”這一現量境里,悟出了塵世間一切之法,都是生滅遷流剎那不住。正如《大智度論》曰:“一切有為法無常者。新新生滅故。屬因緣故。”量,實已隱含了從凡夫位到成佛之所有次第。佛陀以無上菩提心領悟到無上瑜伽現量,從而認識到“聲是無常”這一極其隱秘之境。
佛陀是量,并且佛陀是成量。說明佛陀是通過精進修行而成就量。這樣就遮止了外道無生自然量。佛陀依據意樂圓滿和加行圓滿,而成為定量士夫。正如《大乘起信論》所云“諸佛如來離于見。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眾生所應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因為佛陀只承認知識之源泉是現、比二量,佛陀則具有意樂圓滿和加行圓滿,佛陀所說真實不虛,于是成就了佛陀是正量、定量、量士夫。
四、余論
綜上所述,佛教邏輯從開始的三量說逐步發展到陳那時期的二量說,其過程不得不說有一些漫長。這也說明了佛教理論是一步步走向量論因明之本來意蘊。其實,佛陀早已在其著作中開示,但因為后人的誤解,直到陳那時期,方才揭示量論因明這一認識論之真實意蘊。法稱繼承了并發展了陳那之學,明確提出量即是佛,成量之路即是成佛之路。而法稱之后,藏傳因明很好地繼承發展了陳那法稱之量論學說,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在漢地,陳那之量論沒有受到很好地重視,甚至對于法稱之量論幾乎不曾耳聞,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因此,我以為,如果想要在佛教邏輯中有所作為,那么重視對陳那《量論》和法稱《釋量論》之研究則顯得異常重要了。
參考文獻:
[1]姚衛群.印度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170.
[2]釋水月,許地山.古因明要解·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M].北京:中華書局,2006:51-56.
[3][日]武邑尚邦.佛教邏輯學之研究[M].順真,何放,譯.北京:中華書局,2010:2-10;48-52.
[4][印度]陳那.集量論略解[M].法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110.
[5][印度]法稱.釋量論略解[M].法尊,譯.臺北:佛教出版社1984:95-98.
[6]李潤生.正理滴論解譯[M].香港:密乘佛學會,19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