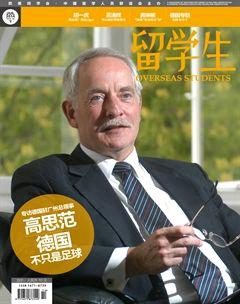拜羅伊特的剛與柔
李鑫
近年來歐盟經濟形勢嚴峻,歐盟本身也頗多困境,歐盟的兩大巨頭德國和法國為此費盡心思。法國自近代以來一直是歐洲的強國,而德意志國家的成形,在整個歐洲都算是非常晚近。但德國也有法國和英國無法與之相比的驕傲,那就是德國的音樂。
也許我們上面的說法對法國有些不公平,畢竟法國巴洛克時期還是有不少音樂大師,但和德國的音樂大師相比,后者的光輝明顯更勝一籌,至少對普通樂迷來說,肯定如此,沒有聽過3B(巴赫Bach、貝多芬Beethoven、勃拉姆斯Brahms)的樂迷恐怕基本沒有,沒有聽過夏爾龐蒂埃(Charpentier)或呂利(Lully)的則大有人在。但德國音樂這個概念本身就很微妙,因為我們欣賞或研究音樂,常常把德奧兩國的音樂放在一起,一說就是“德奧音樂”。
要說在德國最常聽到哪位音樂家的作品,如果是在教堂里,大概是巴赫,我們一般聽到的各種管風琴音樂和合唱音樂,大半出自他的手筆。在教堂里聽這些為教會和信眾寫作的宗教音樂,要比在音樂廳里聆聽震撼得多,哪怕很多時候在音樂廳表演的是更專業的音樂家,但在教堂里,可能是有千百年來信仰之力的環繞,這些時常頗為業余的團體,也能演奏或唱出令人靈魂為之一清的音樂。當然,這可能也和不同的建筑結構所擁有的不同的聲響效果有關,教堂里的混響很大,四壁的吸音又并不是很強,就有一種特別渾厚甚至可說震耳欲聾的聲響。
可要說音樂廳里演奏最多的作曲家,大概要數勃拉姆斯或貝多芬,勃拉姆斯的四部交響曲每年總有機會完整聽上兩遍。貝多芬的各種作品也是音樂廳里常常聽到的,雖然我已經聽過了許多重要樂隊的演繹,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反倒是不萊梅室內樂團這個并不起眼的小樂團。說它小,是因為不萊梅室內樂團的編制不大,更偏室內樂的規模,而非最經典的交響樂的配置。這樣的樂團演奏瓦格納或瓦格納一系的布魯克納和馬勒肯定會力量不足,但演奏莫扎特的那些東西就再適合不過,至于貝多芬,他們的小巧靈動給貝多芬的9部交響曲帶來了全新的質地。整套交響曲停下來,感覺是連貫的,連在一起,而不是聽了9部獨立的交響曲。這樣的感覺,在我的聆聽體驗中,還真是絕無僅有。從那以后,每當有朋友來德國,我的推薦城市里一定有不萊梅,我會建議他們去聽聽這個有意思的樂團,哪怕就為了聽音樂,也值得去這個城市。
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神奇的城市,如果你置身那里,你會發現那里幾乎所有人都是為了聽音樂而來,這個城市就是拜羅伊特。
拜羅伊特可謂音樂史上的一個奇跡,一座專為一位作曲家而建的劇院,一個只演奏一位作曲家作品的音樂節,而這個節日要持續整整一個月。之前一直聽說要提前好幾年訂,否則根本沒位置云云,所以2012年我想去拜羅伊特音樂節的時候,本以為不太可能,只不過是抱著先查查資料看看再說的心態去看他們的官網,后來發現,原來訂滿了的只是《尼伯龍根指環》的套票,單場的票都還可以買到,于是我就買了單場票,把《萊茵的黃金》、《女武神》、《齊格弗里德》和《諸神的黃昏》全部看了一遍,都是從下午一直看到晚上,雖然分了四天,但還是讓人感覺興奮之余非常疲憊。
拜羅伊特劇院是個很特別的演出場地,這里的樂池比通常要深,符合瓦格納“音樂為戲劇服務”的“總體藝術”理念。當然,觀眾也因此可以專心欣賞舞臺上的表演,雖說,現在瓦格納的歌劇還真談不上什么表演,也演不出什么特別賞心悅目的戲來,所以還是好好聽音樂吧。
瓦格納給人印象就是只寫歌劇,其實他也寫過動人的藝術歌曲。那是他寫作《女武神》的時期,他當時因為積極參與1948年革命,被迫流亡瑞士的蘇黎世,他在那里碰上了他的仰慕者奧托·威森東克。威森東克不僅資助瓦格納,還邀請瓦格納夫婦到自家別墅去住住。瓦格納瘋狂愛上了女主人馬蒂爾德·威森東克,他用馬蒂爾德的詩寫出了不朽的藝術歌曲,人稱“威森東克之歌”。這也是瓦格納唯一一次用不是自己寫的文本作曲,對于他這樣自我的人來說,能做到這一步,真是愛神的力量無邊了。
近年來,古樂(早期音樂,包括格里高利圣詠時期或者文藝復興等時期的音樂)大行其道,一時間人們都開始用羽管鍵琴演奏巴赫的《平均律》,用夾腿提琴演奏《無伴奏大提琴》,連握小提琴的琴弓,都要往上握上半尺,據說是更輕柔,更接近巴洛克時期的握法。
這同一座城市除了古樂團,還有最為現代的音樂。隨著西方古典音樂自身的發展,現代派越來越不滿足于原有的聲響效果和樂器,20世紀的作曲家想盡了辦法去制造新的樂器和新的聲音。其中施托克豪森不可不謂是佼佼者,除了比較“傳統”的現代序列音樂、電子音樂、磁帶音樂、隨機音樂、具象音樂,他也是開創性的領軍人物,而他最早創立新音樂實驗班,正是在他于科隆任作曲教授之時。所以在科隆這座城市,你可以從一千年前一直聽到當下。
可音樂也不僅僅是古典音樂,德國的各種“通俗”音樂也毫不遜色,大名鼎鼎的迷幻搖滾(Krautrock)影響了無數熱愛音樂的人們,雖然現在我們基本聽不到這些樂隊的現場演出了,但我們仍然難忘同樣是在科隆組建的樂隊CAN。不過,真要是想看現場,電子音樂這一系的“活化石” 發電站( Kraftwerk)還在頻繁巡演,所以不一定要去杜塞爾多夫,也許哪天他們就會到你所在的城市呢。四位加起來足足有300歲的“老小伙兒”在臺上仍然活力十足,而且特別與時俱進,這些年3D技術盛行,他們就也開始用3D技術做他們的現場演唱會,如果哪天人工智能真能實現,恐怕他們會用四個虛擬人代替他們表演吧。
德國就是這么一個矛盾而富有活力的國家,你在這里可以找到你想要聽的一切,可以聽舒伯特和舒曼美妙動人的藝術歌曲,也可以聽“戰車”(Rammstein)或者“以淚洗面”(Lacrimosa)這樣的暗潮、金屬類音樂。各種哥特音樂更是日耳曼民族的特產,隨便找一個聽聽,都很有意思。可能有人會說這一俗一雅兩種音樂太分裂,我倒覺得,其中有一種暗暗的統一。如果我們去聽舒曼的套曲《詩人之愛》或者舒伯特的套曲《美麗的磨坊女》,我們就會發現,里面既有溫柔的吟唱,也有痛苦、憤怒的咆哮,德意志的血液里,本身就同時包含了溫柔與剛烈。這也是我熱愛德國的原因之一,這片土地有豐富的可能,正如它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