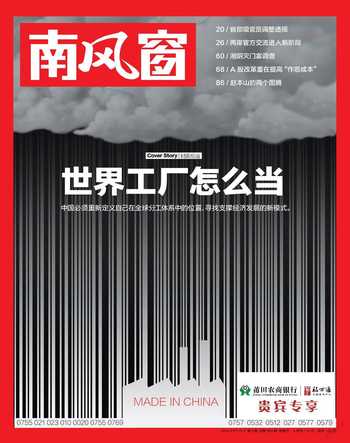為什么爭當貧困縣?
萬海遠
從1986年我國第一次正式確立貧困縣名單以來,關于貧困縣確定標準的質疑從來就沒有間斷過,比如國家級貧困縣同時又是百強縣,中國人均GDP最高的兩個縣(伊金霍洛旗和準格爾旗)都曾是國家級貧困縣。
近年來各種關于貧困縣的戲劇性故事被曝出,比如安徽望江縣大肆興建占地超8個白宮的豪華辦公樓,尤其是2012年1月湖南新邵縣政府掛出宣傳牌,熱烈祝賀其入選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新聞引爆了社會的輿論,再次激起大家對貧困縣評選機制的廣泛質疑。
當新邵縣的炫貧行為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之后,在2012年3月的貧困縣名單上悄然被迅速拿下。在短時間內農民人均收入和新邵縣財政狀況不可能發生大的變化的情況下,新邵縣在貧困縣名單上的一進一出的確反映出貧困縣標準的人為性、可操作性和非定量性。
因此,為什么要設立貧困縣,怎樣可以進入貧困縣名單,入選貧困縣有什么好處等成為了大家最為關注的問題。
1986年我國正式建立起一個具有政府首長統領的實質性扶貧機構—“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政府開始建立一個區域式集中連片式的扶貧開發機制,貧困縣或貧困村的設定由此拉開序幕。
國家級貧困縣的正式審批工作于1986年底開始。由于中央財政資金有限,所以只按1985年人均收入低于150元的標準確立了331個貧困縣,以防止扶貧資金的分散使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再次提高標準,對人均純收入低于400元的全部納入國家級貧困縣的范疇。

從1995年開始,扶貧辦對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定義為扶貧工作重點縣而單獨劃列出來,從此建立了一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簡稱國家級貧困縣,由此財源貧乏、財政自給能力低的貧困地區得到相當規模的財政資金補貼。在此基礎上,國務院扶貧辦也第一次正式提出標準,要求1992年年人均純收入超過700元的,一律退出國家級貧困縣名單。在經歷了這樣一個凈進入過程后,國家級貧困縣的數量也隨之增加到592個。
后來,在2001年貧困縣的進出機制得到進一步明確,重點縣的調整確定也更加定量化。2002年,扶貧辦對外公布了調整標準,即“631指數法”原則,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低占60%權重,人均GDP低占30%和人均財政收入低占10%。之后的調整再也沒有公開公布是根據什么確定原則進行的。研究者從一些文件中的表述推出后來的調整是會參考這些原則來確定的。
迄今為止,貧困縣的調整有3次,分別是1994年、2001年、2011年。調整公布的年份是在下一年的年初。
扶貧辦在2006年進一步確定了592個縣(旗、市)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為簡便,重點縣與貧困縣的概念下文不再區分)。其中將東部33個重點縣指標全部調到中西部,東部不再保留國家級重點縣。
2012年,國務院扶貧辦第一次把貧困縣名單調整的權力下放到省,允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按“高出低進,出一進一,嚴格程序,總量不變”的原則進行調整,從而進一步更新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名單,其中有38個縣區被調出,同時又新調進了38個,所以貧困縣的名單總數仍為592個。
但是,在貧困縣名單調整權力下放到地方后,不同地方對貧困縣的定義和認識都不太一樣,其調整過程也廣受質疑。尤其是在分權負向激勵的刺激下,一些縣市會通過瞞報數據的方式力爭進入貧困縣名單,再加上省級政府在名單調整過程中的隨意性、非確定性和不透明性,從而催生出為進入貧困縣名單而出現的各種戲劇性現象。
爭當貧困縣,算是中國當代政治生態的一景。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只要回顧下在獲得貧困縣稱號后每年單列的財政撥款數額就窺斑知豹。
總的來看,中國針對貧困人口的扶貧專項資金投入逐年增加,規模不斷擴大。而且,財力的不斷增強和重點偏向貧困縣的扶貧策略,也為重點貧困縣提供了巨額的財力補貼。近幾年來,中央財政扶貧專項資金以平均每年超過100億元的速度在增加,這給各縣市入選貧困縣名單提供了最強的激勵。
截至2013年底,全國近3000個縣市區,國家級貧困縣只有592個。2013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投入為406億元,較2008年的197億元,翻了兩倍還多。只要入選,每個縣平均都可以獲得數以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補貼,這些財政補貼往往是一個貧困縣全年財政收入總額的一倍甚至是好幾倍之多。平均來看,光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每個貧困縣每年就可以獲得3000萬~5000萬元的中央補助。同時,一旦入選貧困縣,與之相伴隨的各種附加政策優惠和稅費減免則會更多;而且,這一政策能持續多年,甚至是終身的。因此,在中央、省市各種優惠政策和措施的刺激下,各地都爭先恐后地努力成為貧困縣,這也就是各地爭奪貧困帽的根本原因。
在持續擴大的財政資金幫助下,貧困縣的發展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總體來看,貧困縣的扶貧效果是顯著的。過去的經驗表明,設置國家級貧困縣短期內使扶貧重點縣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得以顯著改善。
新邵縣為什么要不計艱辛地努力申請貧困縣的帽子?其目的在于一旦被列入國家武陵山集中連片扶貧攻堅重點縣,則該縣每年會獲得國家財政下撥的5.6億元資金用于扶貧開發,這一數字為2010年新邵縣每年財政收入的1.4倍。在新邵縣的努力下,一些經濟指標被人為壓低,再加上“大量艱苦細致的銜接協調工作”后,新邵縣如愿以償地獲得了貧困縣的帽子。
既然進入貧困縣的名單能獲得如此多的財政補助,而且入選貧困縣之后對農民脫貧能產生如此顯著的效果,如何設定貧困縣的新標準也就成為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話題。
雖然從1994年以來,貧困縣的名單有所調整,有新進入也有調整出去的,但貧困縣的總數量一直保持在592個不變。當然,最近一次的調整是明確規定,每個地方的貧困縣名單要保證一進一出的平衡,所以貧困縣總數保持不變。但如果貧困縣是根據“631指數法”原則進行精確定量后確定的,那么為什么每次確定的貧困縣名單恰好為不多不少的592個?這樣一種極端的巧合在概率意義上幾乎是不存在的。
我們進一步比較下新進入和退出的國家級貧困縣的發展情況。根據2012年3月扶貧辦新調整的貧困縣,其名單發生變化的省份有河北等9個省,而其他省的貧困縣名單都沒有發生變化。
從調出的貧困縣來看,他們的3項指標普遍要好于那些一直處于貧困縣名單里的縣。尤其是從農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GDP的角度來看,被調出貧困縣名單的那些縣確實在經濟上顯著更好。由此說明,貧困縣的退出機制還算表現良好。然而,在湖南新邵高調炫窮之后,筆者專門赴該地進行了實地調研。我們在計算湖南新邵縣的經濟表現時,發現新邵縣在人均GDP和人均財政收入這兩項指標上都要遠低于其他貧困縣,甚至也要低于新調入的貧困縣。
從調入的貧困縣名單來看,被調入的貧困縣的經濟指標也同樣表現良好,尤其是人均GDP指標甚至要好于那些被調出的貧困縣,也同樣高于那些一直在貧困縣名單的縣。這樣看來,貧困縣名單的進入并沒有完全按照貧窮的標準來執行,有的甚至相反。
而且,我們還按照3個標準,分別計算了2011年592個貧困縣名單的農村人均純收入、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指標,結果發現,有一個縣的3個指標值均遙遙領先于其他縣,而且也要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在新一期的國家級貧困縣名單上,它仍然在列,這顯然與國家最初成立貧困縣的本意是相背離的。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貧困縣的標準不僅沒有徹底按照貧困等級來劃分,甚至被當成某種政治獎勵來激勵或管理地方官員。正是在這種游戲框架下,新邵縣的炫貧行為無疑是給自己斷了退路,所以引起社會爭議的新邵縣隨即就被剝奪了這樣一項政治獎勵。
以縣為瞄準對象的區域式、漸進式扶貧策略,最早是從美國俄亥俄州的扶貧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它是以整個縣為基本單元,以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和增加收入為主要內容,以整合扶貧資源為主要手段的扶貧開發方式。它的瞄準對象在于重點區縣,在推進過程中主要以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社會公益事業、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為重點,通過集中投入、分批實施的方法來進行扶貧開發。
中國政府在扶貧方面推出的最重要措施也是以貧困工作重點縣為基礎的扶貧攻堅戰略。雖然貧困縣的進入和退出過程中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不能否認的是,在財政資源有限且不能覆蓋到所有貧困農戶的大背景下,選擇一些連片特別困難的地區,進行有針對性的重點扶貧正是中國扶貧取得全球矚目成就的最為重要的原因。
然而,這種以縣為重點的瞄準策略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由于貧困人口可能并沒有集中連片居住,所以以貧困縣為主導的扶貧方式并沒有真正有效地減少貧困人口,反而造成資金的嚴重浪費,并且很多有限的資金被投入到耗資巨大的基礎設施中來,減貧資金被嚴重鎖定,從而大量貧困人口無法從貧困陷阱中脫離出來。
而且,這個過程中同樣存在著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沒有從項目中平等受益的問題。首先,是項目實施過程中過度追求項目的數量而導致投入嚴重不足,隨后要求農戶拿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資金。然而,一些真正貧困的人口卻沒有能力配套而不能參與項目。其次,是扶持對象選擇的準確性還有待提高,一些更窮的縣并沒有納入貧困縣,特別是由于缺乏全國的縣級統計資料,貧困縣的確定還存在一定的瞄準誤差。再次,是貧困縣推進的進度過于緩慢,到《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要結束時,已經確定的貧困縣有相當的比例不能納入,而一部分早期的貧困縣因資金量過少根本達不到重點扶貧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勢下,貧困群體的分化現象也愈發突出,貧困分布由區域的、整體性的貧困逐漸過渡到個體性貧困,剩余的貧困人口更為分散,從而以縣為瞄準對象的扶貧模式也遇到越來越多的問題,這需要我們在制度上進行變革,從而更好地適應新形勢下的扶貧工作。
在未來,由于經濟發展的滯后性,極端貧困群體和輕微貧困群體之間的差異性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消除,這需要未來的扶貧制度在承認人群異質性差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出更加有針對性的扶貧方式來增加窮人的發展機會、提高窮人的發展能力,從而對邊緣群體進行更有力的減貧嘗試。在此基礎上,未來的減貧進程也一定會更加細化扶貧目標,由原來的以縣為目標,細化到后來的以村為目標,甚至把扶貧目標落實到戶、到人。最終,以縣為目標的扶貧策略會不斷弱化,貧困縣的問題也會逐漸退出我們的視線。
近期內的問題是,貧困縣的入選需要陽光操作,它的設定標準、申報、初選、入選等都要向大家公示,從而真正接受社會各界監督,這樣才能讓貧困縣發揮應有的政策效應,也才能杜絕假冒偽劣的貧困縣。另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減少貧困縣的數量,激勵貧困縣限時、定期地脫離貧困縣帽子,從根本上杜絕爭當貧困縣的人間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