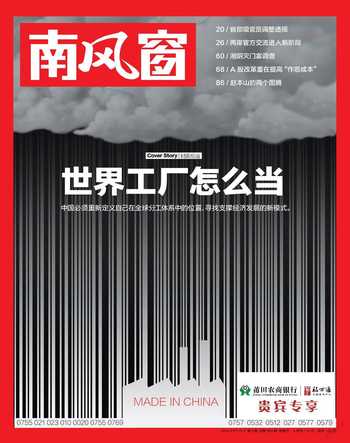“中國藝術(shù)”再定義
河西

輝煌燦爛的中國藝術(shù),從繪畫、書法、瓷器、造像、建筑,乃至物質(zhì)文明中的點點滴滴,都讓人為之顫栗,為之神迷。但如此豐厚的傳統(tǒng)以往并未獲得西方學(xué)者足夠的理解,比如他們多聚焦于歐洲文化所看重的繪畫和雕塑,而忽視了像書法等這類非常重要的藝術(shù)形式。這一情形近來才有所改觀,柯律格的《牛津藝術(shù)史︰中國藝術(shù)》正是該領(lǐng)域突破性的成果。《中國藝術(shù)》是牛津藝術(shù)史叢書的一種,而該叢書是西方藝術(shù)史的權(quán)威著作。
今年1月,英國牛津大學(xué)藝術(shù)史系教授柯律格的這本重要著作《中國藝術(shù)》的中文版出版,柯律格教授也到訪中國并接受了記者采訪。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是享譽世界的中國美術(shù)史及物質(zhì)文明史的研究大家,曾任職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遠(yuǎn)東部研究院兼策展人長達(dá)15年,并自1994年起先后任教于薩塞克斯大學(xué)藝術(shù)史系、倫敦大學(xué)亞非學(xué)院及牛津大學(xué)藝術(shù)史系。2003年,柯律格成為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獲最高榮譽獎的10人之一。2006年,他因在中國文化和藝術(shù)史研究領(lǐng)域中的杰出成就和貢獻(xiàn),被提名英國人文社會科學(xué)院院士。他對于中國傳統(tǒng)典籍亦有深厚的造詣,《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shù)》、《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長物志︰早期現(xiàn)代中國的物質(zhì)文化與社會地位》都是享譽世界的美術(shù)史杰作。
在《中國藝術(shù)》一書中,柯律格指出,任何關(guān)于“中國藝術(shù)”的定義都存在諸多的異常現(xiàn)象和內(nèi)在矛盾。因此,他反對從既定的概念出發(fā),他要追問的是:古代中國的“藝術(shù)”究為何物?它們是在何時,又是怎樣成為“藝術(shù)”的?
柯律格覺得,藝術(shù),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西方概念,而“中國藝術(shù)”其實是個新創(chuàng)造的詞匯,它的出現(xiàn)不足百年,雖然在《中國藝術(shù)》一書中所涉及的紡織品、書法、繪畫、雕塑、陶瓷以及其它藝術(shù)品,都來自于中國5000多年的璀璨文明之中,為世世代代的王公貴族文人雅士所收藏把玩,但對它們分門別類進(jìn)行研究,歷史卻非常短暫。一個簡單的例子,20世紀(jì)之前,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建筑”這個概念,中國第一本建筑史,是日本人伊東忠太寫的《支那建筑史》(1931年),而中國人的開山之作則是1934年之后由樂嘉藻寫作出版的《中國建筑史》。
另一方面,沒有概念,卻發(fā)展出璀璨的文明,就建筑而言,并不表示建筑物在中國沒有發(fā)揚光大,不論是皇家宮殿,還是江南的私家園林,都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輝煌。中國人靠的,不是理論,而是對美的創(chuàng)造力,是對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美的追求。在中國復(fù)雜的藝術(shù)歷史中,不同的藝術(shù)門類,它們的發(fā)展軌跡常常密切交集在一起,有多少是藝術(shù)觀念的影響?柯律格認(rèn)為,更多的,恐怕是由社會和物質(zhì)環(huán)境決定的。在中國古代,藝術(shù),更像是一種設(shè)計,為了增加生活的美感而存在,它們有其非常重要的“功能性”的一面,大至寺觀建筑中的壁畫、小至日常生活中的桌椅、茶具、鍋碗瓢盆,都在滿足功能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美的價值。
這一面,恰恰在之前所有的藝術(shù)史寫作中被忽略。正因于此,柯律格沒有采用傳統(tǒng)以時間為綱的藝術(shù)史寫法,也沒有按照藝術(shù)門類編排,而是將中國藝術(shù)放在一個更為寬廣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劃分為陵墓藝術(shù)、宮廷藝術(shù)、寺觀藝術(shù)、精英分子的藝術(shù),以及在市場中買賣的藝術(shù)等不同形式,基本上以中國人不同的生活空間作為劃分的標(biāo)準(zhǔn),加以多種語境的考察。柯律格說他這樣做“只是希望我能客觀地、基于不同歷史材料—或只是按照中國編年史順序,或以其它方式處理,而不是用人為的概念—來梳理中國藝術(shù)史。有一種明確的劃分方式可以使工作順利一些而已”。
這一方法,在柯律格撰寫《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shù)》時就體現(xiàn)出來了,他從文人社交的角度來審視中國古代畫家的作品,讓人耳目一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文徵明這樣重要的藝術(shù)家,有許多方法可以研究他和他的作品。當(dāng)然,儒家的社交理論強調(diào)血緣關(guān)系和人脈關(guān)系(雖然與此同時,像王陽明這樣的儒家理論家也強調(diào)了個人教養(yǎng)的重要性)。我覺得我們沒必要去懷疑中國明代文人要撤退到更簡樸生活中去的沖動的真實性,我也老想離開這喧囂的都市,走入平靜的田園(正如許多學(xué)者所做的那樣),可是我還是要回email。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有時候,這是一種理想,而非現(xiàn)實性的選擇,也并不意味著就是虛偽。”

雖然這是一本寫給英語世界讀者閱讀的介紹性讀物,但柯律格可不是一個滿足于寫教材的學(xué)者。在這本篇幅不大卻又包羅萬象的著作中,他不斷提供給我們新的視角。
在《墓室藝術(shù)》一章中,他提到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新石器時代玉圭,博物院對它的解釋可能是后人的“構(gòu)想”,而非“真實的意義”。以此類推,如果遠(yuǎn)古藝術(shù)品都是如此,那么中國藝術(shù)史豈不是建立在后人闡釋的基礎(chǔ)上?
這件玉圭,石料呈乳黃色,因年代久遠(yuǎn)而在表皮有一層灰色和赭色的包漿,它被磨成梯形薄片,在較窄的一頭有鉆孔。上面還有精致的淺浮雕,一面雕正在跳躍捕食的鳥,另一面則是一張神秘的程式化的臉。上面有紀(jì)年1786年的銘文(即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皇帝在上面題字,第一次將鳥和神秘的臉解釋為鷹和熊,認(rèn)為這是給古代(商或周)英雄的獎勵。而事實上,據(jù)現(xiàn)代考古證據(jù),這件玉圭可能比乾隆皇帝想象的還要早得多—大概制作于公元前2500~前2000年間,屬于龍山文化的產(chǎn)物,我們知道商朝所處年代在約公元前1500~前1050年,顯然,乾隆皇帝的推測,純屬個人的杜撰,但這個玉圭,因為乾隆皇帝為其題字而變得意義非凡,也就是說因為一個錯誤的判斷而在藝術(shù)史上擁有一席之地的現(xiàn)象,在中國藝術(shù)中,真是層出不窮。

柯律格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個案,“原來在生產(chǎn)過程中并沒有特定意義的物品/藝術(shù)品,隨著時間的推移,發(fā)生了奇妙的變化,改變了意義。”
他對人類學(xué)家伊戈爾·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所說的“物體的傳記”很感興趣,這意味著,事物和人類一樣,也有生活史。“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通過學(xué)術(shù)研究,能夠確定藝術(shù)品意義變化的整個范圍,”柯律格說,“我不認(rèn)為時間太過久遠(yuǎn)的歷史我們就無法研究,就像新石器時代,我們照樣有辦法。不過我也認(rèn)為,人們對一個藝術(shù)品的認(rèn)識在歷史過程中會發(fā)生變化,這些后來人的看法會深刻影響我們的認(rèn)識和判斷—這一點在中國也不足為奇。這里還有個歐洲藝術(shù)的例子:現(xiàn)在我們知道,古希臘和古羅馬大理石雕塑最初的色彩是很鮮艷的,但是當(dāng)我們一想到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我們頭腦中的第一反應(yīng)還是白色的大理石(就像電影《角斗士》中,我們看到的都是白色大理石)。”
臺南藝術(shù)大學(xué)教授徐小虎教授在研究元四家之一的吳鎮(zhèn)時宣稱:現(xiàn)存畫作僅有4幅是真跡,而其余均為偽作,既然吳鎮(zhèn)如此,其他畫家就能免俗?她得出的結(jié)論似乎是:吳鎮(zhèn)之外其它的書畫、文物作品,同樣贗品居多。柯律格對此感到無可奈何:“當(dāng)然有很多贗品還沒有被鑒定出來。在我的《中國藝術(shù)》一書中,圖14是納爾遜-艾金斯博物館的一副著名的石棺,斷代在公元522年,收在許多藝術(shù)史書籍中,但是藝術(shù)史家羅杰·科維(Roger Covey)近期在一篇公開發(fā)表的論文中指出:這是贗品。我覺得他的論述很有說服力,要是我能重寫這本書的話,我就不會再舉這個例子了。”
他說他對明及明以后時期的中國藝術(shù)的判斷和鑒賞還是有一點自信的,但他不敢進(jìn)入非常專業(yè)化的明前時期藝術(shù)的討論:“在這個領(lǐng)域,徐小虎教授已經(jīng)做出了卓越的貢獻(xiàn)。理查德·巴恩哈特(Richard Barnhart)關(guān)于宮廷藝術(shù)和浙派繪畫的著作已經(jīng)論述了,很多之前被認(rèn)為是宋代的作品,實際上是明朝人仿的,這一點我沒有異議。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學(xué)者也論證過,許多著名的宋畫斷代在明朝可能更合適,顯然這是我們必須加以注意的一個問題。”
就像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一樣,在藝術(shù)史的領(lǐng)域,同樣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敘事。這些傳奇虛虛實實,讓藝術(shù)品也蒙上了層層或真或假的光環(huán),需要藝術(shù)史家通過抽絲剝繭的方式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對話
柯律格:所有的藝術(shù)都值得研究
特約記者 河 西
《南風(fēng)窗》 : 謝閣蘭在《偉大的中國雕塑》一書中拒絕涉及中國的佛教雕塑,認(rèn)為它“非真正中國”,在你本書的《寺觀藝術(shù)》一章中,你對佛教藝術(shù)做了深入細(xì)致的研究,那么你不同意謝閣蘭的立場,并且認(rèn)為佛教藝術(shù)是中國藝術(shù)重要的組成部分?
柯律格: 這個問題和我這本書的英文原名—“藝術(shù)在中國”(Art in China)而不是“中國藝術(shù)”(Chinese Art)—有關(guān)。叫“藝術(shù)在中國”更準(zhǔn)確,因為我想概括一種廣義在中國的藝術(shù),而并非對什么是、什么不是“真正在中國”的藝術(shù)做出判斷。謝閣蘭的立場—佛教雕塑不是“真正在中國”的藝術(shù)品—正是我認(rèn)為非常錯誤的觀點的一個例子。我認(rèn)為所有限制的努力,或者說排除所有與原初的“中國性”不符的藝術(shù)品的嘗試都是錯誤的。一方面,我們覺得謝閣蘭荒謬可笑,但另一方面,以他為代表的這種看法現(xiàn)在仍然在我們中間存在,對此,我只能說我不贊同。
《南風(fēng)窗》:中國的佛教藝術(shù)和道教藝術(shù)關(guān)系復(fù)雜,你認(rèn)為是佛教藝術(shù)影響道教藝術(shù),還是反過來,道教藝術(shù)影響佛教藝術(shù)?
柯律格:這是個非常技術(shù)性的問題,我不覺得我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一個原因是寫作這樣一本研究性著作你必須建立在你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上)。但是再考慮一下這個問題的話,認(rèn)真區(qū)分“佛教藝術(shù)”和“道教藝術(shù)”似乎只在東漢時期存在,之后兩者的界限就沒有那么清晰了。這些宗教傳統(tǒng)從一開始就糾纏在一起,共同發(fā)展,所以將它們更多地視作伙伴而不是對手可能更有助于我們理解它們的藝術(shù)。
《南風(fēng)窗》:公元935年,中國首次雕印儒家經(jīng)典,50年后首次雕印佛經(jīng),你覺得印刷技術(shù)的革命對于儒釋道理念的傳播以及中國藝術(shù)的發(fā)展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
柯律格: 正如我之前的很多藝術(shù)史家所指出的,印刷有其對藝術(shù)的貢獻(xiàn)。它能創(chuàng)造同質(zhì)性,在“想象共同體”之間建立聯(lián)系(閱讀相同印刷品的人更容易把他們自己視作同一個團(tuán)體中的個體);這能保存一些事物的意義(事物的意義可能塵封已久,經(jīng)此,又重新浮出水面);在某種意義上,它也能促進(jìn)多樣性和特殊性。印刷對一切都產(chǎn)生了影響,甚至對不閱讀的人群也同樣如此。
《南風(fēng)窗》 : 研究中國藝術(shù),對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其它宗教藝術(shù)的關(guān)注非常不夠,你在書的最后提到了天主教在中國的藝術(shù),你認(rèn)為這些宗教的藝術(shù)是否同樣值得認(rèn)真研究?比如,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其藝術(shù)傳承,影響了中國現(xiàn)代最重要的畫家任伯年、徐悲鴻、雕塑家張充仁、月份牌畫家杭樨英等等,在西方,對中國近代藝術(shù)的研究是否和中國古代藝術(shù)一樣重視?
柯律格: 我覺得對于藝術(shù)史家來說,所有的藝術(shù)都是值得仔細(xì)研究的。有太多我們不了解,或者說還沒有仔細(xì)了解的藝術(shù)品。但這個問題和藝術(shù)批評或者藝術(shù)鑒賞常常被混為一談,我覺得這是和藝術(shù)史完全不同的問題。正如歷史學(xué)家也許需要研究惡人一樣,在我看來,藝術(shù)史家需要認(rèn)真審視那些重要但從美學(xué)角度看算不上最偉大或最有趣的藝術(shù)品,你舉的那些例子就是這樣。土山灣的藝術(shù)是晚清中國最有意思的藝術(shù)?我當(dāng)然會說:不是。但我們需要通過土山灣來了解整個晚清藝術(shù)的發(fā)展史嗎?答案當(dāng)然是:是的。在這里,我同意萬青力教授的觀點,他重要的著作《并非衰落的百年》,其視野就覆蓋了這方面的藝術(shù)。與之類似的,當(dāng)我給我的學(xué)生上 “1911年來的中國藝術(shù)”課程時,我們當(dāng)然提到了月份牌,也許不是在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美術(shù)”概念上來討論它們,但是要了解1911年以后的中國,這一研究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