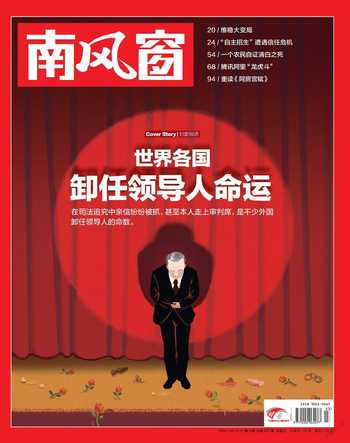“腐敗比興奮劑更難控制”
許春華

2月7日,索契冬奧會就將開幕。各國家和地區的奧委會都厲兵秣馬,組織運動員并爭取賽出優異成績。然而,印度的奧委會卻不得不“置身事外”,因為它被繼續“暫停”著。嚴厲的處罰緣于印度奧委會2012年的換屆選舉遭受政府干預,將烙有貪腐污點的官員“選”為主席和秘書長,并罔顧“警告”,在此后的一年時間里無動于衷,未予“整改”。
對于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去年底有關繼續暫停印度奧委會成員資格的聲明,印度運動員雖然因不能代表國家參加冬奧會表示難過,但普遍認為這是正確的。著名射擊運動員賓德拉說:“再見了,印度奧委會,希望很快能見到你,但希望是一個干凈的你!”
其實,這個所希望的“干凈的你”,不應僅僅是印度奧委會。坦率說,這些年來,國際體壇的腐敗已然不是“病在肌膚”,對此,巴赫坦承:“腐敗比興奮劑更難控制。”
早在2012年12月,印度奧委會就被暫停國際奧委會成員資格。一年下來,由于印度奧委會沒有“限期整改”,國際奧委會原本要“痛下殺手”開除其會籍。巴赫說:“如果開除會籍,意味著印度再也不存在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了。”2013年12月8日,印度奧委會召開緊急會議修改章程,總算才免于“死刑立即執行”。
國際奧委會這次顯然是“忍無可忍”了。印度奧委會換屆后的主席阿沛·辛格、秘書長巴諾特,以及前任主席蘇萊什·卡爾曼迪,均涉嫌在籌備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中貪腐。巴諾特被拘留過11個月,辛格和卡爾曼迪至今還處于保釋中。
國際奧委會官員皮爾·米羅表示:“選舉過程從最開始就被玷污了。”對國際奧委會來說,“既不干涉政治,同時反對政治干涉體育”是其至高法則,印度則是雙重觸碰“紅線”,不僅政治干涉體育,體育的“掌門”還拖著濃重的貪腐陰影。此前,觸碰“紅線”被暫停資格的,已有伊拉克、科威特等國。
印度奧委會一幫官員在籌備英聯邦運動會過程中的貪瀆,這些年來一直是國際體壇最大的丑聞之一。早在運動會召開前,印度媒體就曝光了籌備過程中的嚴重腐敗,迫使政府撤換了各場館建設負責人。運動會后,印度審計署公布了最終審計報告,列出的多種高價采購的物品簡直不可思議,比如,22盧比的衛生卷紙的購買價格高達每卷3751盧比。審計署還稱,63億盧比的運動會建設工程中,至少有10億盧比被組委會“吃”了回扣。
英聯邦運動會組委會主席卡爾曼迪是老政客,擔任國大黨秘書長,同時自1996年以來一直擔任印度奧委會主席。印度奧委會一眾官員之所以“避過風頭”后又毫發無損地坐上了“寶座”,是因為像卡爾曼迪這樣的體壇大佬背后,有一條又長又粗的利益鏈:長期以來,印度體壇的許多人靠體育大發了“橫財”成為巨室豪門后,又“反哺”政客,為盟友“輸血”,或者“加盟”為政客,為政黨“作戰”。于是,體壇大佬便與政客“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印度奧委會的辛格和巴諾特之“巋然不倒”,便也“順理成章”了。
當然,不僅是印度奧委會,國際奧委會也曾陷入腐敗丑聞,最“著名”的當屬美國鹽湖城丑聞。鹽湖城為爭取2002年冬奧會舉辦權,委托律師湯姆·威爾馳和汽車商戴維·喬納森大肆賄賂擁有投票權的國際奧委會官員;花樣滑冰比賽期間,時任法國花樣滑冰協會主席蓋亞格和法國裁判勒古恩與俄羅斯滑協交易,讓對方為自己的冰舞選手打高分,勒古恩則以為俄羅斯雙人滑一對選手打高分作為回報。
不僅僅一個鹽湖城丑聞,曾擔任國際奧委會執委的霍德勒后來自曝家丑,稱此前的1998年長野冬奧會、2000年悉尼奧運會申辦過程中,都存在索賄受賄的行為,其中有1名國際奧委會官員一張選票的“賣價”高達100萬美元。此外,倫敦奧運會期間,希臘、馬耳他和塞爾維亞的奧委會主席,以及立陶宛奧委會秘書長等數人被查實倒賣奧運會門票。
這些年來,國際奧委會從薩馬蘭奇、雅克·羅格到巴赫,都誓言反腐,并重拳出擊。鹽湖城丑聞被揭露后,20名國際奧委會官員被驅逐,薩馬蘭奇還立即改革沿襲了95年的奧運會申辦方式,取消了國際奧委會負責篩選的形式,并縮短“元老”的過長任期,讓運動員委員進入決策層,同時,成立道德委員會,預防權力尋租。羅格在任內著力于嚴肅治理奧運會商業化后帶來的一系列弊病,加強對申辦城市宣傳活動的監管。巴赫2013年9月甫一上任就明確表示“我們必須嚴格執行,確保各國遵守奧委會良好管理的規定”,并維持對印度奧委會的“罰單”。
國際奧委會的“難兄難弟”國際足聯,這些年來陷得更深。曾幾何時,國際足聯的一眾官員,貪腐簡直是明目張膽到“百無禁忌”。
著名球星羅馬里奧多次批評巴西籌備2014年世界杯過程中的“豪奢”之舉,稱“這是巴西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搶劫”,并稱國際足聯秘書長瓦爾克為“敲詐勒索者”,還稱他與前任和現任巴西足協主席特謝拉、馬林三人是一丘之貉的“腐敗分子和強盜”。
這真不是“信口雌黃”。國際足聯的歷史“賬本”上確實是污水橫流,不僅如此,前后兩任主席若·阿維蘭熱和約瑟夫·布拉特都陷入腐敗漩渦。
2012年7月,瑞士聯邦法院公布的一份國際足聯受賄案的文件證實,阿維蘭熱和他當時的女婿—國際足聯執委和巴西足協前主席特謝拉曾收受國際體育休閑集團(ISL)高達1823萬歐元賄賂。文件還顯示,國際足聯知道兩人的受賄情況,主席布拉特甚至公開解釋,當初收錢時,其情節屬于“業務支出”。后來,瑞士檢察官與國際足聯、阿維蘭熱、特謝拉達成協議,特謝拉和阿維蘭熱分別繳納了250萬和50萬瑞士法郎、國際足聯因管理不善被罰250萬瑞郎后,有驚無險地“軟著陸”。
與瑞士的調查同時,BBC記者詹寧斯也對國際足聯進行了10年調查,獲得了ISL公司的一份機密文件—里面列出了175項、涉及約1億美元的支出。節目明確指稱,除特謝拉外,國際足聯副主席哈亞圖、南美足聯主席里奧茲也分別受賄10萬法郎和60萬美元。
布拉特本人多年來也廣受質疑和批評,指他利用手中權力“涉足”商業。2010年5月,網絡媒體公司Mail & Guardian懷疑布拉特和國際足聯其他官員在綠點球場施工中涉嫌不正當牟利,把南非2010年世界杯組織委員會告上法庭,要求其公開相關招標文件。
這確是一塊非常龐大的蛋糕,國際足聯通過2010年南非世界杯獲取的利潤達到32億美元。南非世界杯期間,布拉特入住的是著名的太陽酒店的總統套間,每晚房費3500美元,住宿費用超過70萬元人民幣。他還“肥水不流外人田”,將世界杯的電視轉播代理和市場開發權交給侄子。
由于誘惑實在巨大,許多人都“削尖腦袋”想“上位”,成為國際足聯的“掌門”。輿論稱,每一次的主席選舉都是一場戰爭,都是一次賭局,都是一出無恥的丑劇。
國際足聯2011年的主席選舉就被稱為丑劇。亞足聯主席、卡塔爾人本·哈曼為向布拉特發起挑戰“不惜血本”,專程趕赴國際足聯副主席沃納的家鄉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會見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區25個成員協會主席,并向每名足協主席提供4萬美元現金的“差旅費”。布拉特安排的“臥底”立即告發,哈曼被“暫停”職務,布拉特成功連任。
此案牽涉的國際足聯副主席沃納,是有向黑市倒賣世界杯門票“前科”的人,故“魚死網破”地指稱布拉特也是重金賄選,剛剛在邁阿密舉行的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區足聯大會上送出100萬美元和大量電子產品,“目的是換取選票”。不過,國際足聯認定布拉特不必接受調查。
其實,每一次的主席選舉,每一次的世界杯承辦地競爭,都在重復這樣的故事。早前,在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申辦過程中,國際足聯副主席、塔希提島人雷納-特馬里和尼日利亞人阿達姆就涉嫌選票換金錢的交易。《泰晤士報》記者喬裝為某美國財團代表“約談”兩人,特馬里和阿達姆明碼標價“表決權最低價格50萬英鎊”。此外,英國足總前主席特里斯曼也指控4名執委在申辦2018年世界杯期間向英格蘭索賄。特里斯曼甚至稱,當時國際足聯執委會的24名官員中,至少有13人是“可以收買”的。國際足聯副主席沃納也曝光過卡塔爾收買2022年世界杯舉辦權。
面對腐敗,國際足聯也進行了整治,邀請相關國家的專門人員組成調查組查案,邀請著名人士加入決策委員會,以“制衡”決策。尤其是,世界杯賽承辦地的選舉由原來的24名執委投票擴大到由208個成員投票決定,以此減少“集權”,并增加“游說”成本,遏制賄選。
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組織結構和組織運行機制具有特殊性。它們都屬于松散的國際組織,就像是“世外桃源”,不隸屬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主權機構,不接受任何主權機構監管。比如國際足聯,雖然是臺超級“吸金器”,但作為非營利性組織,總部所在地瑞士的《反腐敗法》對其沒有約束力,除非國際足聯內部提供證據,才能觸發瑞士聯邦相關機構對其經營狀況進行調查。
同時,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的委員和主要工作人員來自各個國家,對這些人,沒有非常有力的限制或控制機制。比如,國際奧委會某些官員貪腐,從司法的角度講,已觸犯了法律,然而,由于每名官員隸屬不同國家,而不同國家的法律又各各不同,國際奧委會就很難給予法律制裁。就如羅格說的,“根據國際奧委會倫理守則規定的職權范圍,可以對這些國家的奧委會采取措施,但是對于那些參與涉黑、倒票的官員個人,并沒有權力作出懲罰措施”。這種“先天性的缺陷”,無疑使那些貪欲膨脹的體壇官員有恃無恐,敢鋌而走險。
當然,也與其故意“自絕于”國際社會的法律體系、基本規范有關。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都自有“游戲規則”。國際奧委會擯棄市場機制,獨家壟斷門票發售權。國際足聯甚至強硬規定,足壇問題只能在內部解決,不得提交當地司法機構,許多執委的貪腐最后僅是“家法”處置。它甚至利用足球的巨大影響力,威逼試圖制裁腐敗的主權國家體壇官員。
這樣“無法無天”,腐敗就是必然的了。要想治本,就必須改變“游戲規則”,加強國際體育機構內部管理,改革選舉制度,公開透明地行使權力,允許并創造條件讓主權國家的法律通過一定的途徑介入。同時,為了防微杜漸,還必須對各國各地區的體育機構實施嚴厲的懲戒和嚴密的監督,防止體育官員濫權謀私,并杜絕政治干預體育,絕不允許政客在體壇橫行無忌、渾水摸魚。
印度奧委會被“命懸一線”,實在是一樁得人心之舉。它不僅表明了國際奧委會堅定反腐敗的決心,更讓國際社會看到了希望—能出現更多“干凈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