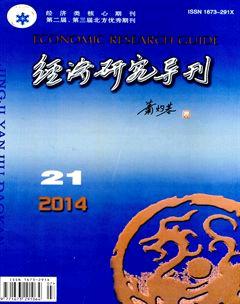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財稅問題探析
林柔桑
摘 要: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中國社會也出現了公共服務供需不均衡、農村轉移人口缺保障及環境承載壓力劇增等一系列問題。作為宏觀調控主要手段,財稅政策沒有發揮出應有作用。中央財政需解決財政資金需求與減稅訴求的矛盾,地方財政則受制于資金保障不足,土地財政及支出不規范等問題。針對城鎮化中的財稅問題,提出通過進行區域性統籌規劃,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培育資質專業機構,多方面激活資本等方式,改善和解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問題。
關鍵詞:城鎮化;財稅區域;統籌規劃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1-0091-02
城鎮化是一個客觀的社會經濟過程,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都無法回避。這既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也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城鎮化建設是中國城鄉發展的重點目標,而財稅政策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關鍵在于政府合理運用財稅政策保證城鎮化建設的高質量與高效率。從新中國剛成立時到現在,關于城鎮化的研究從城鎮化理論、經濟城鎮化等方面,轉向小城鎮問題、民工潮問題等領域,但是已有成果中很少從財稅困局的角度來討論城鎮化。本文嘗試從城鎮化過程的問題入手,分析財稅措施在其中的困惑以及今后如何改進,以使城鎮化能夠平穩推進。
一、中國城鎮化變遷概況
從1949年至今,城鎮化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1949—1957年的城鎮化起步和發展階段,1958—1965年的城鎮化劇烈波動階段,1966—1978年的城鎮化徘徊停滯階段,1979—1992年的城鎮化的恢復發展階段,1993—2002年的城鎮化穩步增長期和2003年至今的城鄉矛盾顯現的高速發展期。隨著城鎮化各階段進程,中國城鎮化水平已達52.57%。
在政府部門的積極努力和主導下,中國新時期的城鎮化進程得到了快速推進。但是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的不匹配關系導致許多社會矛盾開始凸顯。較為突出的有如下幾方面:
一是公共服務提供不足。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過程中在公共交通,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投入不足,使得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跟不上城鎮化步伐,供需矛盾日益嚴峻。同時公共服務的城鄉差異日趨加大,鄉鎮各方面基礎設施都落后于大城市。
二是農村轉移人口問題嚴峻。農民變市民的身份轉換是城鎮化的核心問題,但在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國累積近2億生活在城鎮卻未享受城鎮居民待遇的農民工。補償水平低,保障不到位,就業無助力是失地農民的普遍境況。
三是資源浪費和環境承載壓力劇增。在政府壟斷經營、財政投資為主的體制下,城鎮化建設缺乏市場調節與反饋,導致城鎮化中的無效率與重復建設,一則城市空間,耕地等土地資源閑置、浪費,二則水土資源過度開發,生態環境惡化。
二、城鎮化過程中的財稅困局
從中央和地方的角度,中國財政收入與支出都面臨極大壓力。財政供給能力已經成為制約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因素。有人粗略計算過,要在2030年前實現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財政資金每年至少要投入兩萬億。盡管2013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為12.9萬億,要對接這筆支出依然不輕松。但中國全口徑宏觀稅負高達31.7%,社會對于減稅的呼聲也日益高漲。這種社會共識與財政收入需求的矛盾使得中央財政陷入困局。
從地方財政來看,在中國施行的分稅制度下,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力不匹配。從三個方面來看地方財政的問題:(1)資金支撐不充足。財政資金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導致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對城鎮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不夠,許多地方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脫節,沒法滿足所處城鎮化階段的需求;(2)資金來源不正常。地方政府追求城鎮化目標,但又迫于財政壓力,于是尋求預算外資金收入,大量征用耕地和集體土地。依靠轉讓土地獲取收益,不僅導致城鎮化建設資金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益,而且變相刺激“土地財政”現象愈演愈烈,使地方財政存在巨大的隱患;(3)資金支出非重點。盡管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需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依然沒有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投入到這些公共產品的攻擊上,而是追求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項目。財政資金支出的重心錯位,使得把農村轉移人口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保體系的目標成為空談。地方政府回避社保體系的建設,而不斷將新增建設用地使用費挪用于城市開發,無異于繼續惡化地方財政的困局。
三、城鎮化進程中的財稅對策
針對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財稅困局,今后要在城鎮化過程避免和改善這些問題,以實現和諧社會目標,我們可以從如下幾點加以改進。
一是規劃先行,區域性統籌規劃設計。繼續推行城鎮化并保證新建城鎮發展的速度和質量,最理想的方式是進行全面深化稅收制度改革。由于稅制改革耗時而城鎮化需求又十分迫切,可以通過合理的區域性統籌規劃,中央以轉移支付方式將部分事權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來支撐關鍵階段的城鎮化。區域性統籌規劃,是指以市、縣為轉移支付主體進行小城鎮建設,結合當地現有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明確城鎮化建設目標,使城鎮化的安排切合當地實際情況。原先以鄉鎮為單位建設的模式,因追求政績或者財政乏力,把區域協調及總體發展效率置于腦后,使得區域內部出現嚴重的重復建設。區域性統籌規劃與地方稅、中央轉移支付及地方投融資等方式,共同保證資金來源及資金的高效利用。統籌規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鄉鎮政府的短視和局限,不僅使財政資金投入更具方向性和高效率,而且為今后整治“以土地出讓金支撐城鎮化建設”的模式鋪平道路。
同時,生態上充分考慮區域資源優勢確定整體目標,并且根據生態及資源內部分布細化建設目標,力求城鎮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最大程度降低,尤其是對能源、水、土地等資源實現節約集約使用,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
二是降低成本,政府財政支出有重點。中國提出要將農村人口市民化,其根本意義在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政府向市場放權,由市場主導資源配置,而政府職能應轉變為構建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因此財政支出重點應放在改善基礎設施,增加民生支出上,以降低農村轉移人口的城鎮化成本。完善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所追求的是實現剩余索取的權力公平,剩余積累的機會公平及等價交換的規則公平。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正是保證剩余積累的機會公平的重要路徑。增加民生支出,通過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最大程度降低農民負擔成本;同時促進社會保障資源在城鄉、區域間的平等分配,實現生產和再生產條件的公平。endprint
農村人口進入城鎮,醫療和教育是最為迫切的問題。社會發展的目標是實現每一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只有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公平,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推動社會發展。政府應重點在醫療衛生設施、教育投入、及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為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打下了堅實基礎,使稅收真正起到惠及人民的作用。
三是合理評估,培育有資質專門機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得到的補償低已成為普遍現象。地方政府在預算外通過土地出讓收入與征地收入的巨額差值獲得財力,無疑是強行從失地農民手中分走僅有的一杯羹的行為。通過圈占耕地和操縱一級土地市場價格等方式進行城鎮化是危險的和病態的。十八界三中全會決議中明確提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縮小征地范圍,規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范、多元保障機制。”可以看出,新一屆政府放開政策,支持農村土地流轉目的是保障集體土地所有權,也就是保障失地農民的利益不受侵犯。
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僅僅放開政策是不夠的。首先,農民在土地市場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相對開發單位或個體的議價能力弱;其次,是農村土地剛剛進入建設用地市場,各方面政策和匹配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所以農村土地即使實現入市流轉,農民也極可能得不到完全的補償;但也不排除出現部分釘子戶漫天要價的情況。為了避免和克服兩種情況,政府應培育一些有資質的專業機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機構作為第三方機構,以公允價值為標準,在農民和開發商之間平衡利益,真正實現由市場配置資源。
四是盤活資產,多面激活資本高效率。農民作為城鎮化中的重要主體,其財產權利應得到尊重和考慮。中國要推行社會主義公平保障體系,由市場主導資源配置,則應遵循等價交換這一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律。等價交換包括交易主體,交易客體及交易方式三方面的平等。隨著城鎮化進程,農民應該被納入市場的重要交易主體中并且享有在各個要素市場平等進行交易的權力。然而農民在土地市場上的交易權力缺失,交易公平更無從談起,有悖市場經濟規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提到應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體現了對農民財產權力的高度關注,表明保證農民在土地等要素市場中享有與城鎮居民平等的權力的重要性。
決議中明確提到,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部分可以入市,允許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推進農民住房產權抵押,保障宅基地用益物權等政策,不僅僅是對農民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權力的肯定,同時也是對集體土地作為交易客體的確認,進一步保障農民權力,使農民財產權有渠道實現在市場中應實現的收益,體現了政府與市場職責合理分配,促進社會公平。另外,可以鼓勵外出打工農民資金回流,培育愛國愛鄉的有識之士回鄉創業,使之成為城鎮化的生力軍甚至主力軍。
參考文獻:
[1] 高培勇.城鎮化進程:全面考量中國稅收[N].中國財經報,2010-09-28(006).
[2] 溫來成.城鎮化稅收政策與城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J].稅務研究,2005,(4):9-12.
[3] 鄭濤.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利益訴求問題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3.
[4] 余雁剛.促進中國城鎮化健康發展的財稅政策思考[J].中國城市經濟,2008,(3):75-77.
[5] 賀雪峰.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財政問題思考[J].人民論壇,2012,(29):18-19.
[責任編輯 陳丹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