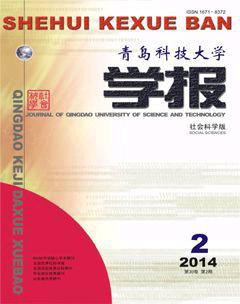追續權制度的幾個基本問題探析
戴哲
[摘要]正在修訂過程中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在我國首次規定了追續權制度。在正式引入追續權制度之前,有必要對追續權的性質、主體、客體、權利內容進行研究。從性質上看,追續權不屬于著作權的一項具體權能,但考慮到追續權與“作品”的聯系,應將追續權納入《著作權法》中。從主體上看,追續權的權利主體應為作者或者其繼承人、受遺贈人,追續權的義務主體應為作品原件出售人,參與作品原件交易的受讓人或中間人承擔不真正連帶責任;從客體上看,追續權客體應限于美術作品原件和建筑作品設計圖、模型的原件。此外,追續權的權利內容包含了精神權利和財產權利兩種權能。
[關鍵詞]追續權;《著作權法》;基本問題
[中圖分類號]D92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372(2014)02-0115-06
On several fundamental issues of Droit de Suite
—as an opportunity to the amendment of Copyright Law
DAI Zhe
(School of Graduate Educ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Chinas Copyright Law, which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revised, first stipulates the system of Droit de Suite. Before the formal introduction of Droit de Suite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nature, subject, object and right content. In terms of its nature, Droit de Suite is not a specific right of the copyright, but according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roit de Suite and “work”,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opyright Law. In terms of its subject, its right subject should be the author or his successor or legatee, and its duty subject should be the seller who sells the works, while assignee or middlemen shall not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ies. From the view of its object, the object of Droit de Suite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original works of fine art, architecture design, the original model. In addition, the right of Droit de Suite contains the spirit right and property right.
Key words:Droit de Suite; Copyright Law;fundamental issues
正在修訂過程中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在我國首次規定了追續權制度。《著作權法》修改草案送審稿第十二條規定:“美術、攝影作品的原件或者文字、音樂作品的手稿首次轉讓后,作者或者其繼承人、受遺贈人對原件或者手稿的所有人通過拍賣方式轉售該原件或者手稿所獲得的增值部分,享有分享收益的權利”。追續權制度起源于法國,這與法國長久以來屬于世界藝術中心的社會背景有關,大量的藝術家云集法國,一些作家一貧如洗,而他們的作品卻在轉售中賣出天價。基于此,法國國會于1920年5月20日通過了由Andre Hesse起草的追續權制度,以允許藝術家參與藝術品轉售的利益分配。為了進一步完善《著作權法》修改草案中的追續權制度,我們有必要對追續權的性質、主體、客體、權利內容進行研究,由于上述研究對象涉及追續權制度的核心,所以本文將其歸為追續權制度的基本問題。
一、追續權的性質
關于追續權的性質,目前并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有的國家將追續權歸入著作權的范疇內;而有的國家則認為追續權“只是一種報酬權”,“目的是對一些不公正的情況給予補償,使藝術作品的作者在其絕對利用權范圍之外出現將其作品用于商業目的的情況時,能夠從這種使用所獲得的好處中收取合理報酬”[1]。目前我國理論界多將追續權歸入著作權范疇,并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即著作人身權說、著作財產權說和綜合權利說。
著作人身權說認為追續權是著作人身權的一種,追續權是為保護作者的利益而創設的權利,其只能由作者本人或其繼承人所享有,并且追續權不可轉讓、不可放棄、不可剝奪,可以認為追續權是對作者精神利益的保護。相較于一般財產權,追續權主要體現的是權利的人身依附性。原《澳門著作權法》第五十七條第一款中規定:“追續權不可轉讓、也不受時效限制”,并且將該追續權歸入著作人身權一節。我國持該觀點的學者不多,如楊立新教授認為,“追續權表面上看起來是著作財產權,但實質上是著作人身權,其立法本意是保護作者的權利,其他任何人不享有這種權利,因而,追續權是不得轉讓的人身權”[2]。又如王遷教授認為,“追續權總體來看更接近于著作人身權”[3]116,所以他將追續權歸入著作人身權的范疇。
著作財產權說認為追續權是對作者經濟利益的補償,旨在消除藝術品市場交易存在的不公正現象;而作者從追續權中所能獲得的,是財產性的期待利益,這不同于精神權利的利益屬性,所以追續權應受著作財產權制度的規制。持此觀點的如吳漢東教授將追續權歸入著作財產權的框架內[4],李明德教授也將追續權歸入著作經濟權利中[5]。
綜合權利說認為追續權兼具精神屬性與經濟屬性的特點,但又不屬于著作權的一種,而是獨立于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身權而存在,屬于著作權的下位概念。持該觀點的如鄭成思教授在其專著中,把追續權列為與著作經濟權利、著作精神權利相并列的一種權利[6]89。丁麗瑛教授在其專著中,把追續權列入了區別于著作人身權與著作財產權的著作權人的其他權利[7]。
筆者認為,界定追續權的性質應當首先考慮追續權與著作權的關系,再判斷追續權到底屬于著作人身權、著作財產權抑或是獨立權利。那么追續權是否屬于著作權呢?分析這一問題應當從著作權的立法目的和立法體系展開。
從立法目的上看,現代著作權法的立法目的有兩個方面:一是旨在維護作者的著作人身權與著作財產權利,以激勵作者進行創作;二是由于作品的社會性來源于公共效應,《著作權法》亦考慮社會公眾對作品的使用與利用。這種立法目的體現了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而且《著作權法》自始至終就在來回找平衡,按下一頭起另一頭,永無休止,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完善,以達到新的平衡。追續權制度最初創設的背景在于藝術家的窮困與轉售商獲取巨額回報之間存在的實質性不公正。為了扭轉這一不公正的現象,以維護作者的經濟利益,法國作為當時的世界藝術中心,首先引入了追續權制度。可以看出,追續權與著作權在立法目的上存在巨大差別,追續權體現的是作者的私人利益,欠缺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點,若強行將追續權納入著作權權利體系,將對著作權體系的內在利益平衡造成沖擊。
從立法體系上看,著作權的權利體系緊緊圍繞對“作品”的利用展開。研究著作權的立法史,可以看出,無論是最初隨印刷術的發明而創設的復制權,還是今天隨著互聯網絡的興起而產生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每一次著作權體系的變化都圍繞著“作品”利用方式的更新換代。而追續權制度則緊緊圍繞著“作品原件”而展開,“作品原件”雖然與“作品”相關,但從其本質上看,“作品原件”只是“作品”的載體,是物的一種,若將追續權歸入著作權范疇,勢必造成著作權權利體系的內在邏輯混亂。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美國于1990年制定《視覺藝術家權利法》時,雖然在最初的草案中對追續權做出了規定,但美國國會經過討論后,還是最終刪去了有關追續權的規定,因為追續權不屬于“版權”范疇[8]。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追續權不應屬于著作權權利體系范疇,那么應當如何界定追續權的性質?應當明確的是,追續權雖不屬于著作權的一種,但追續權又與“作品”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作者能享有追續權,主要是因為其創作出了“作品”,他人購買“作品原件”,不僅僅是為了購買畫布、紙張等“作品載體”,而是因為這些載體與所承載的“作品”有關。相較于文字作品和音樂作品能夠不斷復制并形成新的“作品載體”,追續權所規則的“作品”在“作品載體”上具有單一性、獨特性。好的藝術作品往往是很難或無法復制的,因此造成“作品”與“作品載體”的不可分性,當然了,這種不可分性主要是基于作品價值角度的考量。從《著作權法》角度分析,“作品”與“作品載體”是可以分割的。由此可見,追續權是一項與作者和“作品”密切相關的權利。正如歐共體《追續權指令重述》所指:“追續權屬于作者的一種特權”[9]。
基于此,筆者認為,雖然追續權不屬于著作權權利體系范疇,但考慮到追續權與“作品”的聯系,以及目前世界各國的知識產權框架,宜將追續權納入著作權法律框架中。但追續權并不屬于著作權的一種,不應將追續權納入著作權的權利體系內,宜將其歸入《著作權法》框架下的“其他權利”。正如A·德爾加多·波拉斯認為,西班牙法之所以選擇將追續權的規定放在“其他權利”一節中,原因在于“這一節不直接涉及有關作品,只涉及含有有關作品的物質資產(孤本);因此,從這項權利的被動主體(即因獲得有關作品實物而與作者有義務關系者)的角度來看,他所獲得的是變賣活動中的流通的具體作品,而不是該作品的任何使用權”[10]。在我國此次《著作權法》修正過程中,修正草案第一稿將追續權歸入著作財產權權利范疇,明顯未認清追續權與著作權之關系。值得肯定的是,立法機關在征求意見后,在修正草案第二、三稿將追續權單獨列明,并歸為《著作權法》第十二條,與著作權并列設置,厘清了追續權在著作權法體系安排中存在的問題。
同時,從權利外延上看,追續權既具有財產權利的特征,又具有精神權利的特征。首先,追續權是作者對其作品轉售所享有的利益分配權,并且追續權具有明確的保護期限,如《伯爾尼公約》規定了追續權的保護期為作者的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11]62,由此可見,追續權具有財產權利的特征。其次,《伯爾尼公約》第十四條之三明確規定了追續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權利”[11]72-73,我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送審稿中亦規定了追續權“不得轉讓或者放棄、不可剝奪”,由此可見追續權具有精神權利的特征。
二、追續權主體
追續權主體包括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兩者為相對概念,目前各國在追續權主體上的規定并不一致,我國應考慮追續權制度的目的和內涵,對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進行明確規定。
(一)權利主體
大多數國家將追續權的權利主體限定為作者及其繼承人。有的國家明確排除了受遺贈人作為權利主體的資格,如法國[12]73;有的國家則將受遺贈人包含在內,如德國[12]153、意大利[12]323。我國此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送審稿中規定追續權權利主體為作者或者其繼承人、受遺贈人,但目前各國關于受遺贈人是否有資格成為追續權主體尚存分歧,我國應如何確定追續權的權利主體呢?解答這一問題,應當考慮到追續權制度的兩方面內涵:第一個內涵是實質性的直接補償,即作者有權對其藝術作品轉售的增值部分獲得直接補償;第二個內涵是安慰性的間接補償,指藝術作品原件不斷升值,作者去世后,為安慰離世的作者,給予作者以外的人以補償[13]。因此,從直接補償上看,作者作為權利主體是無可置疑的;從間接補償上看,追續權的權利主體應包括作者的繼承人,亦應包括受遺贈人,因為作者對其追續權享有處分權,作者可以在去世前約定其死后將其追續權中的財產利益轉讓給受遺贈人。這也體現了追續權對作者安慰性的補償,法律應當予以尊重。
此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中仍保留了關于法人作者的規定,作為追續權權利主體的作者僅指自然人作者,不包含法人作者。首先,追續權制度起源于大陸法系國家,大陸法系國家的作者僅指自然人作者,法人或單位無法成為作者。其次,我國在借鑒兩大法系立法時,不但仿照英美版權法規定了視法人為作者的情形,還根據大陸法系著作權法,規定了不視法人為作者,而僅將法人視為原始著作權人的情形[3]163,這兩種同時存在于我國《著作權法》中的互不相容的機制也導致了我國關于作者的規定存在爭議。總的來看,追續權制度應主要考慮大陸法系立法規定,而我國追續權權利主體的作者僅指自然人作者。
依據《伯爾尼公約》,將追續權權利主體規定為作者或作者死后由國家法律授權的人或機構[11]72-73,若作者去世后,沒有繼承人、受遺贈人時,筆者認為追續權可由國家享有,由國家指定的機構行使。
(二)義務主體
追續權義務主體是承擔支付追續金義務的民事主體,關系到追續權權利主體能否有效實現追續權,在追續權立法中占據重要地位。目前各國的追續權制度中一般都將藝術作品原件的出售人規定為義務主體,如歐盟《追續權指令》[14]《法國知識產權法典》[12]73的規定。同時,為了保障作者追續權的有效實現,部分國家還規定參與交易的受讓人或者中間人負連帶責任,如《德國著作權法》[12]153《意大利著作權法》[12]323的規定。
我國此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中并未對追續權義務主體做出規定,筆者認為,參照目前各國的一般規定,應將出售人規定為義務主體。此外,在藝術市場實踐中,藝術作品出售人可能并不是本國人,出售人在完成藝術作品交易后便離開本國,在這種情況下,若藝術作品原件的轉售符合追續權的要件,作者也難以向出售人請求支付追續金,即便出售人為本國人,其亦可能擔心暴露身份而委托中間人進行交易,最終導致作者難以確定出售人身份而無法獲得追續金。因此,為了保障作者追續權的有效實現,還應當規定參與藝術作品交易的受讓人或中間人向追續權權利人承擔連帶責任,這種連帶責任應當是不真正連帶責任,受讓人或中間人在向作者支付追續金后應有權向出售人追償。
三、追續權的客體
關于追續權客體的規定,各國存在巨大的差異,目前在各國追續權立法中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采用歸納的形式,如《伯爾尼公約》規定追續權適用于“藝術作品原件和作家與作曲家的手稿”[11]72-73。《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則規定追續權客體為“藝術家親自創作的平面及立體作品原件,亦包括由藝術家親自或者在其指導下完成的限量版作品”[12]73。這種方式將追續權客體范圍擴大化,有利于保障藝術家的追續權,但由于不對客體的外延加以明確,也容易引發爭議。第二種是采用列舉的形式明確追續權的客體,如《德國著作權法》將追續權客體的范圍限定于美術作品,并明確排除了建筑作品和實用藝術品[12]153。英國追續權制度針對的是“繪畫、攝影及雕塑作品原件”[15]。這種方式有利于追續權制度的有效實施,但若欲增加新形式的作品為追續權客體,只能通過立法加以規定,從而缺乏解釋的可能。第三種方式則結合了前兩種方式,既列舉又歸納了追續權客體,如《意大利著作權法》規定追續權制度的客體包括了“繪畫、雕塑、陶瓷、玻璃作品、照片、原始手稿,以及所有作者本人和原創作品和其他被認為是原件的藝術作品的樣品”[12]323。目前使用這種方式的國家較少,在規定追續權制度的國家中大多數采用的是第二種方式。
考慮到我國的法律實踐,不宜在立法中模糊界定相關概念,我國追續權立法應采用第二種方式,明確追續權的客體,以防止后續不必要的爭議。同時,在采用第二種立法模式的基礎上,我國立法者應當結合追續權的立法目的、客體屬性進行綜合考量。第一,追續權的客體應為藝術作品原件。追續權設立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護藝術作品原件轉售時藝術家的收益權利,這種權利基于的是藝術作品原件的唯一性,并由此產生的藝術家與藝術作品原件之間的聯系,若藝術作品原件可被大量復制,這將破壞該作品受保護的權利基礎,因此追續權所保護的作品原件應當具備稀缺性和獨一無二性。第二,追續權的客體應當是特殊的。相較于文字作品、音樂作品的主要經濟收益來源于作者對外的復制許可,而藝術家一般只能通過出售藝術作品原件實現獲利,倘若藝術家亦可以大量許可他人復制其作品而獲利,那么即便不存在追續權制度,藝術家仍可以獲取與普通作品相對應的回報。在這種情況下,追續權將為藝術家提供新的收益渠道,這對于其他作品作者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由于藝術作品載體的唯一有限性,藝術作品無法像普通作品那樣能夠通過大量復制獲利,立法者正是認識到了藝術作品的特殊性后才創設了以藝術作品原件為客體的追續權制度,而將其他能夠通過大量復制許可獲益的作品排除在外。
綜合考慮上述要求,追續權的客體應當限于具有特殊性的藝術作品原件,但由于我國對藝術作品沒有進行界定,所以應當區分作品屬性并進行分析。
首先,作為藝術作品原件核心的美術作品原件應為追續權客體。客觀地說,追續權制度創設之初保護的作品類型只限于美術作品,后來才逐步擴大至其他作品類型,我國《著作權法》將美術作品規定為繪畫、書法、雕塑等以線條、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或者立體的造型藝術作品,這已經構成了藝術作品的主要外延。
其次,建筑作品設計圖、模型的原件也應當納入追續權客體范圍內。建筑作品完整體現了設計的藝術美感,理應將其歸為藝術作品的范圍。我國2001年修法之前的《著作權法》中,建筑作品一直屬于美術作品的范疇,這也證明了其藝術特性,需要注意的是,2001年修改后的《著作權法》將建筑作品與美術作品并列列舉,該建筑作品僅指以建筑物或者構筑物形式表現的有審美意義的作品,而建筑設計圖、模型被納入圖形作品和模型作品的范圍。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文件,建筑作品應當包括:1.建筑物本身(僅指外觀、裝飾或設計上含有獨創性成分的建筑物),2.建筑設計圖與模型[6]154。我國的《著作權法》中的建筑作品只規定了第一種情形,這造成了我國建筑作品的外延與傳統意義上的建筑作品存在差別。值得肯定的是,本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將建筑作品規定為以建筑物或者構筑物形式表現的有審美意義的作品,這包括作為其施工基礎的平面圖、設計圖、草圖和模型。因此,建筑作品設計圖、模型的原件應當成為追續權的客體。
再次,實用藝術作品原件不應納入追續權客體的范圍。我國此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將實用藝術作品獨立規定為作品的類型之一,但保護實用藝術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滿足工業生產的需要,其藝術價值不及實用價值,并且實用藝術作品的作者一般可通過大量許可復制獲益,其載體不具有唯一性,不符合追續權客體特殊性的要求。因此,追續權的客體應當排除實用藝術作品原件。
最后,我國立法者在此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中將攝影作品原件,文字、音樂作品的手稿包含在追續權客體的范圍內;但這幾類作品不符合追續權客體特殊性的要求,作者可以通過大量復制作品獲得相應利益回報,不需要追續權制度對其進行額外保護。同時,世界各國目前基本沒有采用《伯爾尼公約》的規定,將文字、音樂作品納為追續權保護范圍。因此,筆者認為,追續權的客體應當排除攝影作品原件和文字、音樂作品的手稿。綜合上述,我國的追續權客體應限于美術作品原件和建筑作品設計圖、模型的原件。
四、追續權的權利內容
(一)追續精神權利
追續權具有精神權利的特征,本文將這種精神權利稱為追續人身權。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都規定追續權不得轉讓、不可放棄,如《德國著作權法》[12]153《意大利著作權法》[16]等追續權制度的規定,《伯爾尼公約》也規定追續權不可剝奪[11]72-73,我國《著作權法》修正案中亦規定了追續權不得轉讓或者放棄,不可剝奪。那么追續權的精神權利特征從何而來?這實質上與追續權客體有關:作為追續權客體的藝術作品原件,是藝術作品的唯一載體,若藝術作品原件滅失,則相當于作品不復存在。可以認為,追續人身權體現的是作者與作品原件的聯系,這種聯系基于作者創作作品之事實行為而產生,并且這種聯系不因藝術作品原件的轉讓而中斷。具體來說,作者與作品原件的聯系體現在:原件在后續的每一次轉售中,都應標明原件作者的姓名,不得偽造或篡改,在未經作者同意的情況下,也不得對原件的內容進行“實質性”刪除[17]。由此可見,追續人身權實質上包含了作品原件的署名權和保持作品原件的完整權,這兩項權利來源于著作人身權中的作品署名權與保護作品完整權,這是因為作品原件雖然不同于作品,但當作品只有唯一的載體即作品原件時,作品原件與作品具有滅失和毀損上的一致性,保護作品原件的完整性可以認為是維護作品的利益,由此便產生了追續人身權的必要;同時,追續權人身權與著作人身權不同,追續人身權的客體是作品原件,為物的一種,而著作人身權的客體為作品,是智力成果,兩者并不相同,著作人身權不能規制針對作品原件的篡改、毀損等行為,而這正屬于追續人身權所規制的范圍。基于此,追續人身權具有存在的獨立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此次《著作權法》修正草案送審稿中第二十條亦體現了追續人身權的存在,該條之四規定:陳列于公共場所的美術作品的原件為該作品的唯一載體的,原件所有人對其進行拆除、損毀等事實處分前,應當在合理的期限內通知作者,作者可以通過回購、復制等方式保護其著作權;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二)追續財產權利
追續權財產權指的是作者對追續權客體的利益分享權,即作者對任何轉售其創作的藝術作品原件所得收益享有不可剝奪的分享權。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此次《著作權法》修改草案送審稿中規定追續權“不得轉讓或者放棄、不可剝奪”,并且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都規定追續權“不可轉讓、不得放棄”,一般人認為“不可轉讓、不得放棄”是基于追續人身權的性質所產生的,那么追續財產權可否進行轉讓?筆者認為,追續權制度應由追續權的權利主體享有。前面已經論述,追續權權利主體為作者、作者繼承人和受遺贈人,作為第一種權利主體的作者是基于創作的事實行為而產生的,后兩類權利主體只能在作者去世的情況下通過繼承或遺贈獲得追續權。若對轉讓從狹義角度進行分析,追續財產權不能轉讓,但從廣義的角度對轉讓進行理解,作者去世后追續財產權發生了權利主體的變更,屬于廣義上的權利轉讓。因此,筆者認為,追續財產權原則上不能轉讓,但在作者去世的情況下,追續財產權可通過繼承轉讓給繼承人,或通過遺贈轉讓給受遺贈人。同時,為了更好地保障追續財產權的實施,權利主體可以委托他人如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追續財產權。
五、結語
在正式引入追續權制度之前,本文對追續權的性質、主體、客體、權利內容進行探析。從性質上看,目前共有著作人身權說、著作財產權說、綜合權利說三種學說。從著作權的立法目的和立法體系分析,追續權既不屬于著作人身權,也不屬于著作財產權,但考慮到追續權與“作品”的聯系,應將追續權納入《著作權法》中。從主體上看,追續權的權利主體應為作者或者其繼承人、受遺贈人,追續權的義務主體為作品原件出售人,參與作品原件交易的受讓人或中間人承擔不真正連帶責任。從客體上看,我國《著作權法》應采用列舉的方法規定追續權的客體,以防止后續不必要的爭議。同時,根據追續權客體的特殊性要求,應將追續權客體限于美術作品原件和建筑作品設計圖、模型的原件。此外,追續權的權利內容包含了精神權利和財產權利兩種權能。當然,任何制度的性質、主體、客體等基本內容都伴隨著法律實踐而不斷發展,本文更意在拋磚引玉,喚起更多人對追續權制度的基本問題進行關注。
[參考文獻]
[1]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與鄰接權[M].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163.
[2]楊立新.人身權法專論[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896.
[3]王遷.知識產權法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吳漢東.知識產權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85.
[5]李明德,許超.著作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6.
[6]鄭成思.版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7]丁麗瑛.知識產權法[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124.
[8]Paul Goldstein.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and Related State Doctrines[M].Minnesota:Foundation Press, 1997:801.
[9]Recitals 9,Resale Right Directive[EB/OL].[2014-01-23].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ALL/?uri=CELEX:32001L0084.
[10] A 德爾加多·波拉斯.Panoramica de la Proteccion Civily Penal en Material de Propriedad Intellectual[M].London: Civitas Press, 1988:26.轉引自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與鄰接權[M].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163.
[11] 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M].劉波
林,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12] 十二國著作權法[M].《十二國著作權法》翻譯組,譯.北京:清華大
學出版社,2011.
[13] 劉輝.追續權的幾個理論問題研究[J].西部法學評論,2011(3):
70.
[14] 李明德,閆文軍,黃暉,邰中林.歐洲知識產權法[M].北京:法律出
版社,2010:272.
[15] 洪偉典.國際作曲者協會亞太地區主管洪偉典先生在2012年12月舉
辦的中歐著作權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記錄[EB/OL].[2013-10-
23].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2-11/21/
content_3999322.htm?node=20737.
[16] 吳漢東,曹新明,王毅,胡開忠.西方諸國著作權制度研究[M].北
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42.
[17] 丁麗瑛,鄒國雄.追續權的理論基礎和制度構建[J].法律科學,
2005(3):38.
[責任編輯祁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