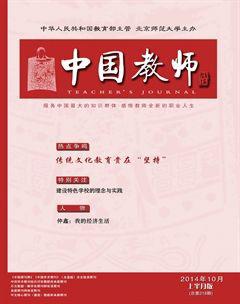王玫:傳統文化教育應當是潛移默化的
《中國教師》: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各種思想文化與觀念形態的歷史積淀,一脈相承,具有一定的延續性,理應在各個時期都得到重視,但為什么當前我們要突出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您認為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么?
王玫:我認為這與當今網絡文化、快餐文化、影視文化、科技文化等的廣泛流行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隨著科技的進步,教學手段與工具不斷更新換代,而且這一速度越來越快,使得孩子們的視野被打開,他們可以快速地篩選出自己喜歡的文化信息。我們不得不承認,與中華傳統文化相比,影視、游戲、網絡趣聞、娛樂體育等信息以及其他各種吸引人們眼球的獵奇消息更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在有限的時間內,如同樣是一個小時的時間,除非是個別的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有興趣的孩子,我想大部分的孩子還是更愿意把這一小時的時間花在瀏覽更有意思的新聞消息或玩各種游戲上。這并不是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不重要或是沒有魅力,但讓年齡比較小、社會經驗比較少的年輕學生去明白、去懂得它的魅力,并在內心接受,進而排斥其他更輕松、更刺激的信息,這顯然是不太可能的。總體而言,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比較安靜深沉的,它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傳承,需要我們安靜地品讀、仔細地感受。這與當今快節奏的學習、生活模式相比,還是相去甚遠,所以如果我們單單依靠所謂的自然傳承,那一定會導致傳統文化的邊緣化。
我一向認為,對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尚不成熟的中小學生而言,一方面我們要尊重他們的選擇權,另一方面我們也一定要干預、引導他們,如果一味地隨著他們的興趣,那么肯定會導致教育的膚淺和簡單。因此,我們應當在中小學教育中突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實,孩子是很單純的,他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會伴隨他們的一生。我認為在他們年輕時,讓他們去感性地感知中華傳統文化的精彩和魅力,一定會強化他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每個國家都會美化自己的歷史,宣揚自己的英雄。中國這樣一個能夠以歷史自豪的國家,就更應當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優勢,讓“愛國”體現在孩子們身上,所以我非常贊成在中小學教育中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國教師》:您認為我國傳統文化應如何體現其在教育領域的價值?
王玫:作為一名教師,我常會聽到孩子的家長對我說“這孩子只聽教師的話,您說的話他一定聽”。其實,我自己的孩子也是這樣。我想,這就是教育的價值。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們所引導的東西必然會對學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所謂“親其師,信其道”。由此可見,要想體現傳統文化在教育領域中的價值,我認為首先要從教育工作者入手。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那么,我們的孩子也就會從教師的身上學會,開始身體力行地重視中華傳統文化。其次,我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并不是所有的內容都適合中小學生,這需要這一領域的教育專業人員對其內容進行認真的篩選和歸類,把對中小學生有用的部分總結出來,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就好像如果國家沒有統一的課程標準或是規范的教材,勢必會導致教育領域的混亂,也會加重孩子們的負擔。中國的很多教育內容的出發點都非常好,但就是因為缺乏統一的規范和管理,最終變成壞事,如奧數。因此,從一線教師的角度來看,如果能夠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統一規劃,或者制訂出統一的課程標準,會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再次,我們一定要關注青少年的接受能力,要想辦法將枯燥、復雜的傳統文化形象化與趣味化。按照受教育者的年齡和心理,我們要有層次地改造傳統文化的面貌,這樣才會更好地體現其在教育領域中的價值。
《中國教師》:當前社會上出現了一些“經典誦讀”的培訓班與“讀經”活動,您是怎樣看待它們對學校教育工作產生的影響的?
王玫:對社會上出現的“經典誦讀”或者是“讀經”活動,我既不反對也不提倡。對一些在這方面特別有興趣的孩子而言,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趕鴨子上架,強制所有的孩子都參加就沒有什么意思了。如果只是單純的“經典誦讀”或者“讀經”,我認為這對學校的教育工作恐怕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只是有可能會對孩子的氣質或是素養有所影響。
我之所以說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是因為:其一,“經典誦讀”本身是與這個時代是脫節的,很多人說人家古人從小不學別的,就背《三字經》,背那些儒家經典,那不是都挺成才的嗎?這樣的說法實在是脫離實際的想當然,古代的語言習慣與現在的大不相同,而且古人想學生物、化學、物理也不可能,所以那時的孩子沒有別的課業負擔。再者能為今人津津樂道的古人都是古人中的佼佼者,他們能名垂千古絕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從小會背誦經典,他們也不具代表性。
其二,讓我們靜下心來想一個問題,什么才能對學校教育產生影響?我們每個人都接受過學校教育,想必大家都明白,真正能夠影響學校教育的絕對不是復古,而是當下。社會的需求才能對學校教育產生真正的影響。所謂的“經典誦讀”或是“讀經”活動,說到底是一種興趣的培養。我相信,即使是在今天這樣的時代,一定也會有對古代經典非常感興趣的孩子或是成年人,但憑心而論,這些人肯定是少數。
我們必須承認,教育有其功利性的一面。雖然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以人為本的興趣教育,但當興趣不能成為主導時,勢必需要功利的一面來強化,甚至是逼迫孩子來順從這種教育。在當今這樣的教育背景下,“讀經”顯然不能滿足教育的功利性,既不能迎合大部分學生的興趣,又不能滿足孩子學習的功利性,當然也就不會對學校教育工作產生什么影響。例如,一個小學生,他根本就弄不懂什么是古文,我們讓他去背經典,那顯然只能是死背。這種死背既占時間,又對現實的學校學習產生不了什么影響,這對好動、愛玩的孩子而言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除非我們能將那些枯燥的經典兒童化、簡單化,但這顯然又是對經典的一種篡改。我記得我年輕時流行過一套漫畫書,是蔡志忠畫的,全都是根據一些古代的經典或是古詩詞改編的。當時覺得真有意思,但長大后才發現他為了方便繪畫,將經典簡化了很多。所以我不認為誦讀經典會對學校教育有什么影響。當然,什么事情堅持下去后,總會對孩子有影響。我相信如果一個孩子堅持讀經很多年,那么總有一天他會顯露出與眾不同的人文氣質,問題在于在學校教育帶給學生的負擔已經很重的今天,有多少人能堅持下去。
我想,傳統文化教育應當是潛移默化的。比如,走在大街上,如果孩子抬頭看到的不再是滿眼的廣告,而是幾句有意境或是應景的古詩;我們的電影、電視劇都能尊重中國歷史,不再隨便“演義”、“戲說”;演藝明星們的言談舉止能夠再多些傳統文化的底蘊;我們的媒體能夠多關注對文化遺產的宣傳或解讀;我們的博物館能有意識地走進學校……我想,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不再是簡單刻意的“讀經”教育,而變成一種很隨意的社會行為時,才能對學校教育產生真正有意義的影響。
《中國教師》:一些學校會將《四書五經》、《弟子規》等國學經典帶進課堂,您是如何看待“國學經典進課堂”這一現象的,您認為學校的這些活動會給學生產生怎樣的影響?
王玫:在這里,我特別希望大家能夠將國學經典與儒家經典做一個明確的區分,國學并不等于儒學。正如我前面所說的,任何經典都是復雜的,并不是說全盤地“端”給學生就是好事,更何況如果將國學等同于儒學,這就太形式主義了。我同意“國學經典進課堂”,這絕對是好事,但我更希望能夠走進課堂的是真正的國學,是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那么多有意思、有內涵、有哲理的經典作品,這些都可以走進課堂,而不僅僅是一些形式化的《四書五經》、《弟子規》。我女兒從小學一年級就將《弟子規》背得很熟,但過兩年之后,就全忘了,而且對這些書籍中的內容并不理解,所以在我看來對她的國學教育并沒有產生任何作用,只是強化、練習了她的記憶力。我想,如果學校將“國學經典進課堂”簡單地理解為背誦《四書五經》、《弟子規》等內容,這樣的“國學經典進課堂”未免太過形式化。因此,我希望學校不要搞形式化的“國學經典進課堂”,這樣產生的影響只能是負面的,還會讓學生錯誤地理解國學,甚至是排斥國學。
北師大二附中非常重視人文教育,我們每個學期都會有一些涉及傳統文化理念的講座或社會實踐,而且這些教育都會盡量與我們的課堂教學相結合。比如,在講詩歌單元時,我們會請大學里專門研究古典詩或現代詩的教授來給學生們講解古典詩歌的意境之美,或是如何讀懂中國現代詩歌;在講關于北京文化的課文時,我們會舉辦類似“北京‘絕活進校園”的活動,請一些有絕活的北京藝人到學校來給學生表演。再比如,我們的文科實驗班每一學年都會有專門的特色課程,高一是《古文觀止》專題,高二是魯迅作品專題,社會實踐的保留節目是參觀故宮博物院和中國國家博物館,而且每年都會走出北京,去文化底蘊非常濃厚的城市,例如蘇州、杭州、安徽、紹興、曲阜、泰山、黃山……我們的社團里有專門的國學社,每年參加全國的國學比賽都能拿到大獎。此外,我們學校還專門設立了“素書樓獎學金”,以獎勵在國學方面有興趣、有造詣的優秀學生。我覺得,這其實都是對國學經典的一種弘揚,是“國學經典進課堂”的一種表現。可見“國學經典進課堂”完全可以進行得有聲有色、生動活潑,沒有必要只揪住幾個儒家經典來做文章。
《中國教師》:您認為學校應怎樣將學校校本課程的開展與傳統文化教育結合起來?
王玫: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太好回答,因為校本課程與傳統文化教育的內涵豐富,概念太大,要真說起來,我們每一堂的古文課、古詩課、文學作品分析課都會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比如,我們在講蘇軾的《赤壁賦》時,會講到“賦”這種文體,會介紹文章產生的歷史背景,會講到蘇軾其人,會講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月”這個意象的內涵,再往深里講還會涉及中國傳統文化中人生觀、生死觀的對比和傳承……這些都是將校本課程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相結合的表現。而且語文本身就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相關,語文教師只要稍微上點兒心,不就課文講課文,就能把這二者結合起來。至于學校層面,我們會辦一些講座,設立各種社團,有各類獎學金……此外,我們還有專門的校本教材,比如《誦讀詩文集》、《文言揭蒙》等,初中每年還要舉辦“誦讀詩文大賽”,高中每年都有“人文知識競賽”等,這些教材以及活動其實就是一種導向,讓學生們明白我們很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我們的選修課還開設了茶藝、書法、國畫等。我認為這些都是課堂教學與學校活動和傳統文化教育結合起來的表現,并不僅僅限于在校本課程開發中結合傳統文化教育。
《中國教師》:語文教學是傳播傳統文化的主渠道,您認為語文教師在開展傳統文化教育方面應該注意什么問題?應推薦學生閱讀哪些書籍,怎么讀?
王玫:語文教師在開展傳統文化教育方面有著當仁不讓的責任,這需要教育工作者有長遠的教育眼光,而非僅僅地盯著眼前的分數。其實,傳統文化教育不需要我們花費專門的時間刻意地去教,可以將其融入到日常的教學當中,在教學活動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就可以實現。
比如,我們在講老舍的《想北平》時,就可以在文章講授的過程中將北京的傳統文化加進去,讓學生找一找老北京的方言以及這些方言背后傳遞出的北京人的性格特點。在講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時,讓學生去找關于北京胡同的資料,或是每人介紹一個北京有名的小吃,感受一下老北京特有的帝都文化。
又如,我們在講《竇娥冤》時,可以將中國傳統戲劇文化,如戲劇角色的分類、劇本寫作的基本格式、演員程式化表現的特點等內容加進去,讓學生了解中國的傳統戲劇文化。
再如,我們講古詩時,就可以將中國傳統的對聯文化、詩詞文化、韻文文化甚至是書法藝術、繪畫藝術、中國傳統的審美情趣等都加進去。我們在講古文時,可以加入的傳統文化會更多,如我國官史制度的發展、帝王稱謂的發展變化……
教師在課文內容的講授過程中過多地滲透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會占用大量的課時,這就需要教師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教學設計,熱情滿滿地去備課,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教師的備課量。但現在,我們語文教師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時,還是缺乏一種統一的條理性,就如我前面所說的,如果能從國家教育部門的角度統一規范出有關傳統文化教學的一整套的教育教材或課程標準,可能會更適合于操作。我們拭目以待。
在有關傳統文化方面可以閱讀的書籍,我認為當前已經有很多了,我會推薦學生讀一些文化論著類的圖書,如王力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圖典》、《中國文學史》等。今年暑假時,我們推薦學生讀的三本書是老舍的《四世同堂》、余秋雨的《尋覓中華》和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一般會在開學之后辦讀書交流會或是用寫小論文的方式來督促學生完成閱讀。
《中國教師》:您對我國傳統文化教育有哪些寄語?
王玫:余秋雨說:“我們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經成了家長,卻未必知道這個家的來歷。小家庭這樣,大家庭也是這樣。”我想說,懂“家”、愛“家”方能顧“家”、興“家”!對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也是如此,只有我們真正地了解其內涵,懂得其真諦,才能真正地踐行,才能對我們的言行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而將其發揚光大。
(責任編輯:孫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