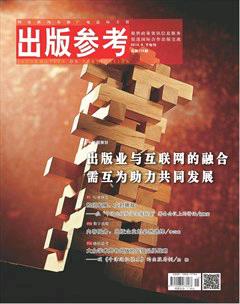溝通融合發展中的現實問題
劉旭明+邸榮芬
2014年的數字出版年會,最大的創新點莫過于讓傳統出版人和互聯網巨頭坐在一起,共同就各自關心的問題展開對話。7月15日的對話由新聞出版總署信息中心副主任劉成勇主持,嘉賓是百度新聞主編陳磊、騰訊文學高級副總裁張蓉、高等教育出版社數字出版中心總監張澤、人民郵電出版社音像電子與網絡出版部主任安達、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數字出版事業部總監彭彥。
一直以來,在很多傳統出版人的心目中,數字出版就是把傳統出版的內容數字化,放在網上去賣或者直接賣給技術公司。傳統企業想做互聯網的事情,原以為是窗戶紙一捅就破,殊不知這里是一層透明的天花板,很難摸得著。
互聯網公司是以經營用戶和平臺為主,對傳統出版的改造頗為順手,數字出版對于他們盡在掌控。傳統出版單位在互聯網環境下,存在著極大的困惑:原有的價值如何體現?傳統出版的內容放到互聯網的平臺上是不是被貶值?傳統出版如何借助互聯網商業模式?互聯網公司做數字閱讀是抱著怎樣的目的?僅僅是引流的手段還是致力于數字閱讀產業發展?對話現場的交鋒激烈,言語中透著急切和懇切。
傳統出版的內容放在互聯網的平臺上是不是被貶值?
對于傳統出版人在互聯網時代自身價值如何體現,傳統出版的內容放在互聯網的平臺上是不是被貶值的困惑,張蓉認為,像騰訊這樣的公司,的確擁有一些用戶資源,同時擁有數據基礎,但是傳統出版社擁有很多有價值的知識版權,能夠滿足用戶學習、閱讀等方面的需求。對互聯網公司來講,與傳統出版最大的不同是,用戶決策決定傳播的方向。
張蓉進一步解釋,互聯網公司每天都在看用戶的反饋,看用戶提出的建議,分析用戶行為,分析用戶閱讀屬性,分析用戶的年齡層,分析用戶對每種書閱讀的偏好,這是傳統出版與互聯網公司的最大不同。
張蓉認為,出版社一定要保護自己的著作權,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價值。有價值的內容,用戶需求的內容,最終用戶的選擇會更大。他舉例說,教育的內容,教材、教輔,傳統的出版行業份額很大,為什么在觸網之后反而份額變得比較小?對于騰訊來講,那么多的用戶在教育方面肯定有很大的需求,教育類的書籍排版方式比較復雜,因此,數字化推進起來比較慢。
隨著技術的發展,教育類的優質內容逐漸數字化之后,一定能找到在互聯網用戶當中應有的價值。
互聯網時代,如何提升版權價值?傳統出版是不是被邊緣化了?
很多傳統出版社的內容,在互聯網上被低價使用。對此,張澤認為,在數字時代提升內容產品價值,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但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曾經做過很多的嘗試,一年有3000多個品種做電子書,一年收益才100萬。現在互聯網習慣低價甚至是免費的模式,如果說把傳統產品變成電子化是縮小了市場份額,那么傳統出版社在互聯網上的價值如何體現?
對此,陳磊認為,互聯網的發展對所有傳統行業帶來了影響,更多的傳統行業會覺得是危機的到來,其實身處在互聯網行業里,我們認為這帶來的是更大的機遇。出版行業中,圖書發5萬冊、10萬冊算是很暢銷的,但如果把這個書的內容放在互聯網上,其面臨潛在的用戶將是百萬級,千萬級,上億的級別。互聯網的趨勢是全世界的趨勢。
張蓉補充道,在互聯網企業內容價值被貶值,這一點我不是很認同。在騰訊平臺上一本小說要全讀完可能花200到300塊錢,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很多用戶在看,你滿足用戶需求,用戶就愿意付費。
互聯網公司是想做數字閱讀還是引流的一種手段?
互聯網時代核心就是“用戶”。不管百度、阿里還是騰訊前年都在做數字閱讀市場,很多人認為,這個市場一定能做得很大。安達則提出,互聯網巨頭真的是想做數字閱讀,還是把數字閱讀作為抓手和手段,來提高用戶的流量和黏性,當流量和黏性達到一定程度再做其他的事情,值得大家密切關注。
對此,陳磊認為,對平臺型的互聯網公司,用戶是基礎。公司一切行為都是為用戶著想,這是肯定的。百度的使命就是讓用戶平等,便捷地獲取信息。發現用戶需求,就盡最大力量滿足用戶的需求,這就是百度堅守的用戶至上的原則。這確實是為了增加用戶的黏性,對平臺的依賴度,這樣我們才會有更多拓展的空間。當然你說我們拿到更多,獲得更多用戶會不會有其他附加值的產品出現,我覺得這是共性的問題,任何一個行業都會這么做。比如說去餐館吃飯,你餐做得好吃,用戶來了,你也會賣酒。我們圖書做得很好,書賣的很多,就可能會附著加頁的廣告,這都是很正常的附加手段。它是一個手段,目的是提高用戶的黏性,最終是為了滿足用戶的需求。
互聯網為數字出版開辟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傳統出版與互聯網公司未來將是怎樣的關系?
互聯網時代,擁有內容的傳統出版單位越來越被動。對此,張澤認為,傳統出版單位的內容,被互聯網公司拿過去,匯集了流量,黏住了用戶,而傳統出版卻成為了附屬品。面對這樣的問題,張蓉介紹,騰訊為了做數字出版,單獨成立了一家公司,這些員工放到新的公司里。為什么呢?我們看到了數字出版業有很大的空間,用戶有很大的需求在這里。我們覺得數字出版這個行業應該剛開始,希望在這個領域有更多的發展,無論是培育市場,還是教育用戶,我們都有決心,或者有信心把這塊業務做大。我們希望出版社看到騰訊這樣的決心,更加主動地觸網。傳統的傳播方式已經不足以滿足用戶,對于移動閱讀的需求,機會應該更大。
對于傳統出版與互聯網公司的關系,陳磊認為,傳統出版與互聯網公司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關系。我們努力經營用戶和平臺,我們與內容生產企業,是共生的關系,是共同的生態,是生態鏈上不同的環節。互聯網公司是在用戶環節上,出版單位是在內容生產環節上,當然還有消費的環節,里面還有服務的環節。我們在不同鏈條,不同的環節上。我覺得互聯網帶來更大的變化是,加速了社會結構的改變,更多元,也會加速社會化的分工。
傳統出版單位能否分享到數字閱讀生態里的用戶和數據?
很長時間以來,互聯網公司與出版社的合作僅僅是就閱讀付費部分分成,而由閱讀帶來的其他收益,出版社基本拿不到。張澤介紹,高教社和中移動合作,拿到的是電子書售賣的分成,但是,移動是流量掙錢,書帶來的流量不給出版社分成。假設高教社的圖書放在百度上,圖書賣多少錢沒關系,圖書帶來其他的增值服務是不是能分成,能分成才是公平的游戲。
對此,陳磊介紹,百度百家就是這樣的合作模式。現在比較流行自媒體,每個人可以在這里注冊,可以在這里寫作。對于好的內容,我們有相應的機制推送到用戶面前,用戶在閱讀內容的同時,總有一部分用戶點擊廣告。對于這部分廣告收入目前為了推廣,是百分之百回饋給作者。移動互聯時代,手機是人的一部分,手機上可以更精準找到適合內容的用戶。我們正在嘗試做開放的生態,與出版單位會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安達對此有不同的觀點:我看過百度和騰訊,百度收購了熊貓讀書,騰訊組建自己的數字出版公司,在前面內容生產、中間研發到推送,各種附加產品是比較完整的生態系,這里沒有出版商的位置。雖然百度、騰訊會有出版的欄目,但只是插進去的小環節,是單項流入的內容,這個是比較封閉的。我關心的是,除了內容本身融合外,用戶數據的分享和共享出版商能否享受得到?在互聯網模式中,數字內容本身的售價變得不重要,數字內容變成了平臺,在上面可以跑授權,倒廣告,跑流量,這樣對我們傳統出版來講,難以接受。
互聯網公司對傳統出版的改造很順手,為什么傳統出版在與互聯網的融合中,卻難以找到突破口?
說到融合中如何找到突破點的話題,從傳統出版單位轉戰到互聯網企業的陳磊最有發言權。他最大的感受是,互聯網的核心是效率,提高效率,是從互聯網里感知到的最大收益。同時,他認為出版單位是有價值的,核心是有專業價值。比如說文字表達效率,優美程度,知識結構的再梳理,或者是對于作者作品的再升華,更極端的個例是化腐朽為神奇,這就是傳統出版的價值所在。
我們能夠看到,很多互聯網上的東西質量不高,反映出來就是閱讀流量不高。對此,陳磊介紹,我們在做百家,大家說做C2C,可以越過中介。其實,在做C2C的過程中,你會發現越高品質的內容帶來收益越大,做到最后會回到類似出版。傳統出版已經具備相當專業的流程,來做這樣的事情,順理成章。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傳統出版怎么理解互聯網,這是核心的問題。相互之間的了解才是融合的開始和基礎。
對于融合和了解,陳蓉認為,互聯網公司具備的能力是對數據的挖掘和對用戶的理解。閱讀的需求非常多樣化,每個人閱讀的需求都不同,在這樣的場景下,我可能5秒鐘就決定你是否留在這兒,或者去看別的。怎么在第一時間讓用戶覺得這個內容能夠吸引他,我們每天都在做這方面的運算,這個數據是共享給傳統出版的,可以讓其快速地了解現在的行為是否合理,如何更有效。
從此次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統出版業與互聯網企業相互之間更多的是索取所求,或者是不了解。由此也說明雙方的溝通還是太少。
(作者單位:劉旭明,廣西大學體育學院;邸榮芬,出版參考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