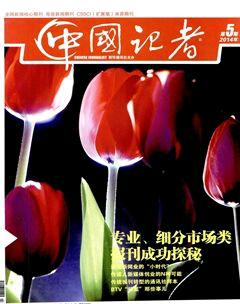BTV“檔案”那些事兒——制作團(tuán)隊(duì)漫談“檔案”
□ 文/李 成
采訪呂軍后,《中國記者》雜志記者與幾位主創(chuàng)進(jìn)行了1小時(shí)的圓桌對話。從定位、價(jià)值觀,到操作、方法論,從節(jié)目形態(tài),到從業(yè)故事……隨著話題逐漸展開,氣氛也活躍起來,他們流露出的職業(yè)自豪感和成就感感染著我:這種精氣神,也是媒體從業(yè)者越來越稀缺的狀態(tài)。
目前,“檔案”欄目組已經(jīng)由初始的不到十個(gè)人發(fā)展為八十多人、六個(gè)制作小組的大團(tuán)隊(duì)。你可能像我一樣意外:以中老年人為主要受眾的“檔案”欄目,制作者竟是80后和90后為主、女性占大半邊天的年輕團(tuán)隊(duì)。
這個(gè)團(tuán)隊(duì)還有一個(gè)特點(diǎn),呂軍稱之為“多國部隊(duì)”,主要是指成員中多元的語種構(gòu)成,英語、德語、意大利語、日語、俄語……
很多沒有趕上圓桌座談的“檔案”成員,后來通過email向本刊記者講述了他們和“檔案”結(jié)緣的故事,他們對“檔案”的認(rèn)識。
他們的言談和文字間,充滿銳氣和激情,富于娛樂精神和文藝氣質(zhì)。看到他們就知道,制作“檔案”欄目一定是一件很酷很好玩的事兒;透過他們的所思所想,或許能找到“檔案”的文化基因和成功密碼。
資料先行、電影手法:制作過程不一般
:“檔案”制作過程有何特點(diǎn)?
王紅(“檔案”欄目副制片人):“檔案”制作過程最大的特點(diǎn)就是資料先行。 我們一般是先有檔案,如照片、音視頻材料、書信等,才去做選題。節(jié)目的宗旨是給觀眾看得見、聽得到、摸得著的故事。所以不會按照時(shí)間線索或簡單的歷史框架去找選題。比如黃煒做的新中國封閉妓院改造妓女的選題,就是先找到了一些檔案,覺得很有意思才去做的。因?yàn)楹芏嗍聝捍蠹铱赡芏贾溃侵赖脹]那么多沒那么細(xì),也還有很多不知道的細(xì)節(jié)和側(cè)面。
找線索需要多看書、多跑檔案館,如書籍里面的一些回憶錄、日記、書信等線索。《偉大的抗美援朝》里面有秦基偉將軍的日記,線索只是書里的一句話,我們就要去找到原始檔案。其實(shí)最好是當(dāng)事人或其后人能給我們提供一些資料,觀眾也沒見過。
我們會根據(jù)選題需要去找專家,比如做西沙海戰(zhàn),會去找海軍方面的專家,做“清宮”會找清史專家。史實(shí)一定要沒問題,目前還沒有史實(shí)有誤的批評。
劉曉彤(“檔案”欄目主編):每次都有拍電影的感覺,是“檔案”與其它電視欄目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檔案”的攝影棚巨大空曠,黑暗無邊,深入其中能夠滿足你所有的想象。你可以把它變成二戰(zhàn)的現(xiàn)場、索馬里的海灣、香港回歸時(shí)的中英談判桌,也可以變成慈禧的后宮、張國榮的演唱會現(xiàn)場、泰坦尼克號的甲板……這些如同電影場景的設(shè)計(jì)生動形象,不僅為我們的現(xiàn)場講述增添樂趣,還可以帶領(lǐng)觀眾回到某一歷史瞬間、某一特殊場景。
摸索、衍生、當(dāng)下關(guān)注:選題三部曲
:選題如何確定?
王紅:做選題,主要是看:一是有沒有新的發(fā)現(xiàn),二是到底要跟觀眾說什么。我們不是全景式地講歷史,關(guān)鍵不是發(fā)生了什么,而是想通過這些跟觀眾說什么。
黃煒(“檔案”欄目副制片人):“檔案”創(chuàng)立五年以來,選題方法經(jīng)過了三個(gè)階段,也可以說是做選題的三個(gè)關(guān)鍵詞。
第一個(gè)是摸索階段。一開始我們所挑選的“誰盜走了北京人的頭蓋骨”“珍珠港”系列、“諾曼底”系列等,這些耳熟能詳?shù)拇髿v史史料很豐富,也是比較現(xiàn)成的選題,但我們要做的是從中找出新選題、新資料,給大家一個(gè)新視角。
第二階段是從第一個(gè)階段中衍生出選題。例如,我們做過的《誰是真正的007》,就是在關(guān)注上述重大歷史題材時(shí)衍生出來的。從日俄戰(zhàn)爭、二戰(zhàn),到國際間諜史,在這些大選題的搜尋之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一些“有故事”的人物。就是這樣慢慢鎖定達(dá)斯科·波波夫,他被譽(yù)為真正的007。這樣切入,這個(gè)人物與當(dāng)代的一些影視作品就有了有機(jī)結(jié)合。在傳統(tǒng)紀(jì)錄片中,多全景式地關(guān)注一場戰(zhàn)爭,或者某一段歷史時(shí)期,但很少能具體到某一個(gè)人物。將具體歷史人物掛靠在宏大歷史事件或背景中的做法就是從007這類題材開始的。在經(jīng)過了很長時(shí)間的積累后,為周播改日播奠定了基礎(chǔ)。
第三個(gè)階段,也就是最近嘗試跟新聞、熱點(diǎn)關(guān)聯(lián)。如反恐、馬航飛機(jī)失聯(lián)等,我們會從歷史中尋找相關(guān)的事件、人物凸顯出來。
合理想象和情緒性:一種解讀方式
:主觀性(如合理想象、情緒性、細(xì)節(jié)打碎重組)對“檔案”的歷史敘事有什么影響?
王紅:“檔案”喜歡從細(xì)節(jié)出發(fā),去尋找懸念,給大家構(gòu)造一個(gè)講故事的場景,并把情緒傳達(dá)給觀眾。“檔案”最有意思的是細(xì)節(jié)拆解。一份檔案,一般的紀(jì)錄片就是拿來當(dāng)證據(jù)說一下,而我們會圍繞這個(gè)檔案做得更充分,告訴觀眾這是一個(gè)4A級的檔案,從哪發(fā)到哪,當(dāng)時(shí)的背景是什么。
黃煒:所謂的合理想象,我更傾向于認(rèn)為這是欄目組和導(dǎo)演對這些資料的解讀。在這一點(diǎn)上,尤其關(guān)于人物的,不管是大的政治軍事人物還是明星,拿到資料后,編導(dǎo)在寫臺本時(shí)會帶有強(qiáng)烈的情緒性。這種情緒是個(gè)人對這個(gè)題材的理解及其延伸。其實(shí)這也是“檔案”的特色:有觀點(diǎn)、有思想、有理解。我們經(jīng)常也有這樣的表述:當(dāng)時(shí)某某到底怎么想的無從考據(jù),但是我們的理解是……
吳志勇(“檔案”欄目主編):其實(shí)很多合理想象,是合理的有依據(jù)的推測,通過檔案的細(xì)節(jié)來展現(xiàn),而不是憑空想象。比如邁克爾·杰克遜在法院的判決書上簽字時(shí),他的簽名比以往都要大,從心理學(xué)上說,只有在極端憤怒的情況下才會這樣。再比如毛澤東在某個(gè)電報(bào)上圈圈鉤鉤、改改劃劃,也體現(xiàn)了他當(dāng)時(shí)復(fù)雜的心情,為什么這么改?這就需要一個(gè)解讀。
劉曉彤:很多人小時(shí)候都有“聽外婆講故事”的經(jīng)歷吧?夏日的夜里,外婆搖著蒲扇講著神話、童話,小伙伴們?nèi)宄扇海3B牭媚康煽诖簟F鋵?shí),“檔案”就是一個(gè)給你好好講故事的欄目。故事里有細(xì)節(jié)有推敲,有懸念有疑惑,還很有趣味。
愛故事,愛講故事,有故事:BTV“檔案”人的共同基因
:為什么做“檔案”?你眼中的“檔案”是什么樣子?
許璐(“檔案”欄目編導(dǎo)組組長):“檔案”之前,我大概從沒見過哪個(gè)歷史節(jié)目能把故事講得如此生動感人,對這個(gè)節(jié)目產(chǎn)生了一種帶著神秘色彩的仰視。大學(xué)畢業(yè)后機(jī)緣巧合地進(jìn)入到“檔案”的集體后,才發(fā)現(xiàn)許多故事并非神秘莫測,正是每一個(gè)撰稿、導(dǎo)演渴望將一個(gè)故事、一個(gè)人、一份檔案講給你聽的那份熱情和沖動,使得那些生硬枯燥的歷史有了鮮活的靈性。漸漸地,我發(fā)現(xiàn)我也可以通過自己的文字、畫面,把辛亥革命、解放戰(zhàn)爭、中共代表大會、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意義重大而又看似刻板的歷史講得引人入勝、充滿情懷。
夏欣(“檔案”欄目編導(dǎo)):我是個(gè)生活很獨(dú)立的女生,從高中起就自己住,一直靠電話和國外的父母聯(lián)系。但自從畢業(yè)后加入“檔案”,每次播出我制作的節(jié)目,他們就會上網(wǎng)去找。雖然那行寫著“導(dǎo)演 夏欣”的字很小很短,他們?nèi)詴荛_心地截圖拍照,還會跟我探討節(jié)目內(nèi)容。 最近一年,他們可以從“檔案”中看到我的樣子,看到我客串扮演的徐志摩老婆、墨索里尼女兒、各種小媳婦、小宮女。他們看到片子的時(shí)候會為我驕傲,這是我現(xiàn)在最在乎的事。
劉曉彤:是呂軍老師把我領(lǐng)進(jìn)“檔案”門的。我從創(chuàng)辦那天一直呆到現(xiàn)在。“檔案”的原創(chuàng)是我最喜歡的一點(diǎn),節(jié)目的形態(tài)、講訴人的選擇、臺本的要求、拍攝的角度等等,都有團(tuán)隊(duì)獨(dú)特的設(shè)計(jì)和創(chuàng)造,而不是隨便找?guī)讬n節(jié)目拿來抄襲一下。“檔案”的團(tuán)隊(duì)是一個(gè)有活力有追求的團(tuán)隊(duì),始終不忘原創(chuàng)的初衷。
吳志勇:上學(xué)的時(shí)候不是特別喜歡歷史課,教科書上的歷史似乎總是枯燥乏味的,考試也無非是死記硬背。“檔案”節(jié)目讓我第一次感到歷史可以這樣生動有趣。作為節(jié)目的導(dǎo)演,在操作每一期選題時(shí),對歷史細(xì)節(jié)的探索能激發(fā)我強(qiáng)烈的好奇心。可以說,每解開一個(gè)歷史疑問的過程,都是一次奇妙的時(shí)光旅行,而旅行歸來,又總能帶給我對現(xiàn)實(shí)和未來的思考。我想,這就是這檔節(jié)目的魅力所在吧。
郝霖(“檔案”欄目編導(dǎo)):我曾經(jīng)在“檔案”欄目中負(fù)責(zé)相關(guān)的檔案搜集工作,尤其是在和中央檔案館合作方面。其中包括《從一大到十八大》《偉大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等廣受好評的大歷史題材。從中央檔案館借來的檔案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檔案是“檔案”欄目的靈魂。也許你可以用最華麗的辭藻去修飾一段故事,也許你會用昂貴攝影器材去拍攝、再現(xiàn)一個(gè)歷史片段,也許你會用一段最抑揚(yáng)頓挫的解說去描繪一段情節(jié)。但一個(gè)有分量的、恰到好處的檔案比這一切都重要。
由于“檔案”欄目和中央檔案館之間多次合作,了解了對方的運(yùn)作模式,也建立很深厚的友誼和信任。但是當(dāng)剛開始合作時(shí),“檔案”的運(yùn)作效率和要求就讓中央檔案館吃驚不小。以往中央檔案館調(diào)檔對調(diào)閱檔案數(shù)量的限制很嚴(yán)格,周期也很長。但“檔案”欄目經(jīng)常是一次就索要數(shù)十份檔案,兩周之內(nèi)就要弄齊。這讓檔案館的工作人員甚至有些“焦頭爛額”。面對“檔案”欄目的“無理”要求,中央檔案館給予了很大的理解和支持。在《從一大到十八大》的檔案搜集過程中,時(shí)間就非常緊迫。在最后一天,中央檔案館檔案資料利用部的工作人員們一直干到很晚都沒有回家,甚至錯(cuò)過了回市區(qū)的班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