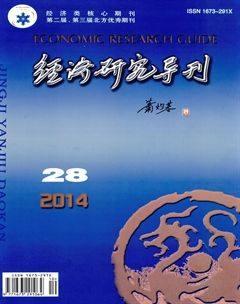從歐洲法院最新判例透視《羅馬公約》第6條對勞動者的保護
楊赟
摘 要:《羅馬公約》第6條對涉外勞動合同的法律適用進行了統(tǒng)一規(guī)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國家間的差異。不論是適用慣常工作地的法律、主要營業(yè)所所在地的法律,還是依照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確定的法律,都要以具體的個案為基礎裁量取舍。通過對勞動者提供保護的可能緣由和保護問題的特殊性分析,認為法律的可預見性與個案的公正審理是貫穿沖突規(guī)則的始終,在一般情況下即體現與涉外勞動合同的最密切聯(lián)系性,適應羅馬公約的法治特征。
關鍵詞:Schlecker案;羅馬公約;勞動者保護;歐洲法院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8-0320-05
隨著歐盟境內國際勞工流動的日益頻繁,涉外勞動合同糾紛也逐漸增多,而歐盟境內各成員國法院針對這一現象所采取的不同做法,也使得問題的合法處理日趨復雜。《羅馬公約》[1]第6條對涉外勞動合同的法律適用進行了統(tǒng)一規(guī)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國家間的差異,但隨著全球化、區(qū)域化、信息化經濟的發(fā)展,案件時而呈現出特殊的個性特點,對該條的解讀也應隨之變化而變化,適應羅馬公約的法治特征。2013年9月12日,經荷蘭最高法院申請,歐洲法院[2]對Schlecker訴Boedeker一案(以下簡稱Schlecker案)做出先決裁定,解釋《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3]的具體適用。根據《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規(guī)定,在涉外勞動合同中,如果當事人沒有選擇應當適用的法律,則應適用勞動者慣常工作地的法律(a項),或勞動者受雇的營業(yè)所所在地的法律(b項)。但隨后的“例外條款”規(guī)定,從整體情況來看,如果合同與另一國有更密切的聯(lián)系,則合同應當適用該國法律。Schlecker案是歐洲法院依據《羅馬公約》第6條審理的第三起雇傭合同糾紛,與前兩個案例(Koelzsch[4],Voogsgeerd[5])不同的是,Schelecker案首次明確提出了第6條第2款中“例外條款”[6]的具體適用問題。
一、案情簡介和相應特征的相關法律分析
(一)案情事實與過程慨要
Schlecker是一家經營化妝品與保健品的德國公司,總部在德國,同時在歐盟的成員國境內有許多分公司。根據最初的雇傭合同,Boedeker女士,德國公民且居住在德國,被Schlecker公司雇傭,工作地點在德國,雇傭期限為1979年12月1日至1994年1月1日。
根據1994年11月30日達成的第二份合同,Boedeker女士被Schlecker任命為荷蘭全境的銷售經理,任期為1995年3月1日至2006年的夏天。Boedeker女士在此期間在荷蘭工作。2006年6月19日,Schlecker去函通知Boedeker女士,其荷蘭全境的銷售經理職務被取消,自2006年6月30日起生效。同時Schlecker邀請其自2006年7月1日起擔任德國多特蒙德的財務主管。
盡管Boedeker女士于2006年7月4日對工作調動通知表示了反對,但其隨即前往多特蒙德,并擔任地區(qū)經理。2006年7月5日,Boedeker女士以身體不適為由聲稱不再適宜工作,并在此后向荷蘭法院提起訴訟。
(二)主要訴訟程序
一審蒂爾州法院(the Kantonrechter te Tiel)依據案情作出判決,支持了Boedeker女士的訴訟請求,認定第二份雇傭合同應適用荷蘭的法律,并于2007年12月15日終止了該合同,判決Boedeker女士獲得557 651.52歐元的賠償。
Schlecker公司不服判決,上訴到阿納姆地區(qū)上訴法院(the Gerechtshof te Arnhem)。依據2009年12月15日的判決,上訴法院維持了蒂爾州法院關于法律適用的判決。其根據《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a項的規(guī)定,認定Schelecker公司和Boedeker女士之間的雇傭合同應適用勞動者慣常工作地的法律,即荷蘭的法律,Schelecker公司提出的諸多證據,如養(yǎng)老金、健康保險都在德國,并不足以證明德國法律與雇傭合同存在更密切的聯(lián)系。
Schelecker公司根據上訴法院的最終判決上訴到荷蘭最高法院(the Hoge Raad der Nederlanden)。荷蘭最高法院認為,關于《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中“例外條款”的適用需要進一步進行解釋,因為當合同與另一個國家從總體來看存在更密切的聯(lián)系時,依據第6條第2款a項和b項明確指向的法律將可能得不到適用。
據此,荷蘭最高法院向歐洲法院就兩個問題提出先決裁定的申請。問題有:
1.《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是否能解讀為,如果一個雇員為履行合同而在同一個國家慣常地、長期地、不間斷地工作,那么在所有情況下,合同都應適用該國的法律,即使所有的其他條件都表明合同與另一國家存在更為密切的聯(lián)系。
2.如果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是否要求在訂立合同時,至少在開始工作時,雇員和雇主已經達成共識,或至少知道這個事實,工作將在同一個國家長期地、不間斷地展開。
(三)歐洲法院的裁決與分析
歐洲法院認為,針對第一個問題,關鍵點是《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具體內容的適用層級,即a項和b項[7]與“例外條款”[8]的適用層級。在Voogsgeerd案中,法院已經闡明a項與b項的適用層級,依據對第6條第2款的合理解讀,法院必須首先確定勞動者是否在某一國家慣常地進行工作(a項),只有在不能確定慣常工作地的情況下才會考慮營業(yè)所所在地(b項)的適用[9]。針對Schlecker案,慣常工作地的確定并無爭議,因此具體爭議即為“慣常工作地”的法律與“與合同有更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的適用層級。
《羅馬公約》中第6條針對雇傭合同的規(guī)定與《羅馬公約》第3條、第4條規(guī)定的總體原則有所不同,因為第6條的有其特殊目標——對勞動者提供“適當的保護”。根據Giuliano和Lagarde對《羅馬公約》的報告[10],《羅馬公約》第6條旨在為合同一方當事人提供一種適當的保護。該當事人,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被認為是合同關系中的弱勢方[11]。
歐洲法院進一步指出,既然第6條的目標是對勞動者提供適當的保護,則其必須保證勞動合同適用的法律是與合同有最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12]。但需要注意的是,依據本案法律顧問的觀點,依該解釋適用法律,與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并不必然是對勞動者最有利的法律[13]。
在判斷哪一國家的法律與合同存在更密切聯(lián)系時,歐洲法院指出,法院必須考慮所有與勞動合同相關的因素,并從中挑選出最重要的因素。但這并不意味著法院在審理某一具體案件時,僅僅因為其他因素的數量多就排除經a項指引的法律的適用。在考慮眾多可能成為連接點的因素時,應重點考慮勞動者依其收入繳納稅款的國家、享受社會保險的國家、享受養(yǎng)老金的國家。另外,法院還應考慮到與案件相關的所有情況,例如工資形成標準以及其他工作情況[14]。
據此,歐洲法院得出結論,在考慮《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的適用時,即使勞動者依合同慣常地、長期地、不間斷地在同一個國家展開工作,法院也可以依據第2款最后一段的規(guī)定排除該國家法律的適用,只要整體情況表明合同與其他國家存在更密切的聯(lián)系。同時,由于對第一個問題給予了否定的答復,第二個問題也沒有回答的必要。
因此,即使Boedeker女士在荷蘭進行了長達11年的、未間斷的工作,同時荷蘭法律針對雇主單方改變工作地點對雇員提供了更強的保護,但法院仍依照上述論證,認定德國法律與該雇傭合同存在更密切的聯(lián)系,而認定應當適用德國法。
二、對《羅馬公約》第6條的解讀
Schlecker一案的判決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看似塵埃落定的對《羅馬公約》第6條的解讀與適用又重新引起熱議。其中對勞動者的保護與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之間存在的沖突是這場爭議的焦點。因此我們有必要根據相關案例對歐洲法院對《羅馬公約》第6條的適用做一下梳理。
依據《羅馬公約》,作為合同法律適用總體原則的第3條與第4條為合同的法律適用提供了總的標準。第3條規(guī)定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第4條規(guī)定了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第4條的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體體現在第2、3、4款的規(guī)定中,第5款則規(guī)定了“例外條款”。“例外條款”稱,從整體來看,若合同與另一國家存在更密切的聯(lián)系,則第2、3、4款的推定不得適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羅馬公約》第3條和第4條的規(guī)定是抽象的、中性的,因為它們設立的目標并不是為合同一方當事人提供保護,也就是說,在選擇適用的法律時,其實體內容并不被考慮在內。但《羅馬公約》第6條針對涉外勞動合同提出了特別的法律選擇規(guī)則。根據《羅馬公約》起草者的立法意圖[15],與作為總體原則的第3條、第4條不同,第6條的設立并不應當完全“中性”,而應體現出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適當保護。下面由此進行詳細分析第6條的具體適用。
(一)第6條第1款的具體適用
本款規(guī)定了當事人約定了法律適用時對其意思自治的限制。與第3條不同,本款規(guī)定當事人的法律選擇不得剝奪勞動者由法律的強制性規(guī)定給予的保護,該強制性規(guī)定來自于當事人未做選擇時應適用的法律,即來自于勞動者慣常工作地或營業(yè)所所在地的法律。在處理當事人明示選擇適用法律的涉外勞動合同糾紛時,法院應當首先根據第2款的規(guī)定,確定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時應當適用的法律;然后,判斷該法律中是否包含保護勞動者的強制性規(guī)定;最后,從當事人選擇的法律與前述的強制性規(guī)定中選擇對勞動者更有利的法律[16]。也就是說,該強制性規(guī)定為勞動者提供了最低的保護標準,當事人選擇的法律不得低于這個標準。
(二)第6條第2款的具體適用
本款規(guī)定了在當事人未做選擇時的法律適用問題。其中a項規(guī)定應當適用勞動者“慣常工作地”的國家的法律,在慣常工作地無法確定的情況下,則適用b項規(guī)定的勞動者“受雇的營業(yè)所所在地”國家的法律。同時,“例外條款”,規(guī)定,從總體來看,若合同與另一國存在更密切的聯(lián)系,則應當適用該另一國法。
針對如何確定a項的勞動者的“慣常工作地”這一問題,根據以往案例,難點在于當勞動者在多個成員國進行工作時,“慣常工作地”該如何確定。在Koelzsch案中,法院認為以下連接點都值得考慮[17],勞動者向雇主履行其主要合同義務的地點[18];勞動者展開其工作活動的有效中心(如辦公室所在地)[19];在無法確定辦公地點的情況下,勞動者完成其大部分工作的地點[20]。
針對如何確定b項的勞動者“受雇的營業(yè)所所在地”這一問題,Voogsgeerd案中的法官認為,“受雇的”(營業(yè)所所在地)一詞應當被嚴格解釋成“簽訂勞動合同的”(營業(yè)所所在地),即產生勞動關系的事實發(fā)生地,而非勞動者執(zhí)行其勞動合同的實際發(fā)生地[21]。
(三)適用層級的確認與判斷
針對a項與b項的適用層級,《羅馬公約》第6條旨在“為合同利益不對等的雙方設定一個更為合理的安排……為從社會經濟學角度被認定為弱勢的一方提供更適當的保護。”[22]為了實現“適當的保護”這一目標,對6條的理解應為保證勞動者工作地而非雇主所在地的法律得到適用。勞動者的工作地即為勞動者履行其經濟、社會職責的所在地,經濟政治環(huán)境對勞動行為產生影響的所在地。因此,應當在最大限度上遵循該所在地國家的法律對勞動者提供的保護。因此,應當對a項的“慣常工作地”進行擴大解釋,b項的“受雇的營業(yè)所所在地”應當在法院無法確定慣常工作地時才能得到適用。
而針對“例外條款”的適用,歐洲法院之前的判例并沒有就此展開詳細的論述。我們可以由此推論,a、b項與例外條款的關系一直被認定為“原則和例外”的關系,即只有在適用經連接點指引的法律導致極不公正的結果時,才應考慮適用 “與合同存在更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
三、Schlecker案的特殊性及其必要分析
與歐洲法院之前的案例不同,Schlecker案著重討論了《羅馬公約》第6條中“例外條款”的適用。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已經得知,之前的案例重點關注的是對勞動者“慣常工作地”的確認,以及“慣常工作地”與“受雇的營業(yè)地”的法律的適用層級。法院對于“例外條款”的態(tài)度,如對該條款的稱呼一樣,是在適用前述法律會導致極不公正結果時的例外。但Schlecker案中,法律顧問Walh在其法律意見中進行了洋洋灑灑的論述,其中心思想就是,《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的a、b項與“例外條款”之間并不是“原則與例外”的關系,他們之間 “并不存在適用層級關系,而應當由法院根據自由裁量權來確定與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法律”[23]。同時,Wahl在法律意見中反復強調,對勞動者應當提供“適當的保護”,而不是為其選擇“最有利的法律”。由此引出兩個問題:第一,如果勞動合同也適用“與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法律”,那么勞動合同與普通合同有何區(qū)別,即勞動合同的保護性如何體現?第二,如果“適當的保護”不等于對勞動者“最有利的法律”,那么“適當的保護”的具體含義包含那些內容。為了解答上述兩個問題,可進行如下分析。
(一)對勞動者提供有效保護的可能與緣由
在Sayer[24]案之前,對勞動者的保護多體現在各國的實體法規(guī)范中,通過沖突規(guī)范指引的準據法或本國的強制性規(guī)定實現。但Sayer一案暴露了只有實體法保護的缺陷,勞動者很有可能處于“法律的真空”而得不到任何保護。受到Sayer案的啟發(fā),如今歐盟的許多有關國際私法的法律文件都包含了勞動者保護條款,例如《布魯塞爾規(guī)則I》第18~21條和《羅馬規(guī)則I》第8條,其設立都是為了實現對勞動者的保護,而勞動者作為合同弱勢方的地位已經被歐洲法院的多起案例明確證實。與傳統(tǒng)的國際私法更多地強調“沖突正義”不同,對勞動者的保護更多地強調“實體正義”。誠然,當事人自由選擇法律是合同領域的首要原則,但在涉外勞動合同中,支持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三個主要原因都很難得到實現,即契約自由、經濟效益、法律的確定性。
1.契約自由的需求。國際私法中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就來自于契約自由這一古老的原則。19世紀后半葉,即自由主義和不干涉主義的全盛期,當事人在涉外交往中選擇準據法的自由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得到承認。當事人可以自由地約定合同的權利義務,換句話說,他們是合同關系的“立法者”[25]。因此更不消說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合同應當適用的法律。幾乎整個19世紀,勞動合同的權利義務也是由一般的合同規(guī)則調整的。然而在法律面前被視為地位平等的勞動者和雇主,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并不平等。雇主在社會經濟地位中的優(yōu)勢使得其可以將合同條款強加在勞動者身上。因此在二者的從屬關系之中,絕對的契約自由是對勞動者利益的極大損害。
2.經濟效益的驅動。當事人意思自治可以極大地節(jié)約經濟成本,這是學者們通過經濟分析得出的結論。但這一結論有其自身的前提,即合同的當事人是理智的,不存在額外的交易成本、不完整的信息以及其他外部因素。但涉外勞動合同的典型特征就是其高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的不對等。涉外勞動合同中,雇主需要勞動法專家或律師來比較各國法律的不同以減少合同風險,節(jié)約經濟成本,實現規(guī)模經濟。對于雇主來說,其雇傭的勞動者越多,花費在每個勞動者身上的法律咨詢費用就越少。但對于勞動者來說,其缺少雇主所擁有的龐大資源,其所簽訂的合同對其本身來說只是一個單獨發(fā)生的事件。而這種資源上的不平等進一步導致了信息上的不對等。同時,法律選擇條款多數包含在復雜的格式合同中,勞動者很難注意,即使注意了因缺乏專業(yè)知識也很難理解,即使意識到存在的風險也因還是失去這份工作而很難反對。同時,在存在所謂“社會傾銷”的情況下,雇主在勞動成本很低的國家選擇勞動者并與其簽訂合同,在那里勞動者有可能在不安全的環(huán)境下超時工作,領取極低的薪水,同時沒有工作保險,沒有結社的自由和集體談判的權利。如果雇主將該國的法律強加于勞動者,從合同本身來看的確更加高效,但如果將社會成本考慮在內,例如對失業(yè)員工的救濟、對受傷員工的補償,這一選擇可能導致更高的成本。
3.法律的確定性。一般來說,當事人如果事先約定了合同適用的法律,法律的確定性將大大增強。但是,基于涉外勞動合同背后隱藏的政策利益,許多國家并不愿意承認當事人在合同中的法律選擇條款。如果當事人選擇適用的法律不存在調整該合同的合法利益,不涉及該合同引起的特殊糾紛,與合同沒有足夠密切的聯(lián)系,則該選擇可能會導致更大程度的不確定性。
綜上可以看出,勞動者與雇主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導致意思自治原則在涉外勞動合同中存在缺陷,因此需要特殊的規(guī)則對該原則加以限制,以實現對勞動者的保護。
(二)對勞動者如何提供有效保護的法律問題
這就回到我們在最初討論Schlecker案的特殊性時提到的兩個問題,在當事人沒有選擇適用法律的前提下該如何實現對勞動者的保護?一些學者認為,法院應當考慮和勞動合同存在聯(lián)系的所有國家的法律,然后適用對勞動者“最有利的法律”。有一些學者認為應當將比較的范圍縮小到勞動者工作地的國家的法律和雇主營業(yè)所所在地的國家的法律。但不論范圍大小,尋找對勞動者“最有利的法律”這一出發(fā)點本身就存在極大的問題。首先,考察的國家的法律在具體案件中可能和勞動合同的聯(lián)系很微弱。其次,如此龐雜的比較工作無論對于法官還是當事人來說,都是極大的負擔。再次,“最有利”的標準過于抽象,不同國家的標準不同,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標準也可能存在不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從事涉外勞動的勞動者沒有理由受到比普通的內國勞動者更多的保護。
對從事涉外勞動的勞動者的保護不應該“過度”,是我們探討的問題的核心。“最有利的法律”就是“過度的保護”,與勞動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才是“適當的保護”。Schlecker案的特殊之處就在于,其忽略《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第a、b項的連接點的指引,直奔“例外條款”,以“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確定了涉外勞動合同應當適用的法律。打破了a、b項與例外條款之間“原則與例外”的關系,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涉外勞動合同的法律適用如何利用“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體現對勞動者的保護問題。
在討論為何要對勞動者提供保護時我們得出結論,因為勞動者和雇主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導致絕對的遵從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將會損害作為弱勢方的勞動者的利益。那么,如果不存在意思自治,即當事人沒有事先選擇勞動合同應適用的法律,對勞動者提供保護的主要原因不再存在,那么此時只要選擇與勞動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就能得到公平正義的結果。也就是說,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前提下,涉外勞動合同的法律適用和普通合同的法律適用沒有實質上的區(qū)別。但這不等于勞動者在這種情況下得不到任何保護,畢竟勞動者的弱勢地位是客觀存在的。但此時對勞動者的保護將體現在與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的實體法上,勞動者將得到與該國家保護其本國勞動者的相同程度的實體法的保護。
從另一個角度,a、b項與例外條款之間“原則與例外”的關系認定本身存在著邏輯上的漏洞。正如荷蘭政府在Schlecker案中指出的那樣,相較于勞動慣常工作地的法律,涉外勞動合同與另一國家存在更密切的聯(lián)系,那么存在更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就應得到適用,否則例外條款將形同虛設[26]。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處理涉外勞動合同糾紛時,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情況下,法官應當對涉案的法律與事實情況進行總體考量,選出與該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
四、對Schlecker案的批判性分析和功能實現
雖然Schlecker案頗具爭議,但筆者支持歐洲法院對該案所持的觀點。但對于本案中與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確定,即德國法的確定,筆者卻存在疑問。這涉及到更細節(jié)的問題,如果法院應當利用自由裁量權選擇與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那么《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第a、b項的功能如何實現?首先應當承認,根據特征性履行在涉外勞動合同中的具體體現,a、b項的連接點的設定,即勞動者的慣常工作地與雇主的營業(yè)所所在地,在一般情況下即體現了與涉外勞動合同的最密切聯(lián)系。因此,通過對連接點的具體分析,可以得出適用a、b項的具體情形。
(一)慣常工作地的適用性
慣常工作地一般適用勞動者在某地固定工作的情形,同時雇主的主要營業(yè)地也在該地。在這種情況下,該勞動者有權受到和當地勞動者一樣的待遇,而雇主也避免了適用外國法律的風險。一般來說,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就表明其了解并認可在某地工作的現實,對于適用該地的法律調整其勞動合同關系至少有所預見。因此適用慣常工作地的法律調整涉外勞動合同是一個合理的前提性假設,符合勞動者對法律適用的合理期待。
(二)主要營業(yè)所所在地的確認性
但現實中涉外勞動合同的情況卻多種多樣。例如從事跨國業(yè)務的雇主經常將其管理人員、專家顧問派往業(yè)務所在地或者國外的子公司、分支機構等。這時適用主要營業(yè)所所在地的法律調整勞動合同對于雇主來說是極為有利的,因為其避免了每一次派遣可能引發(fā)的不同國家的法律的適用。同時,雇主的主要營業(yè)所所在地一般來說也是勞動者訂立合同、領取工資、接受指令的所在地。因此,在勞動者被頻繁派往各地的情況下,其雇主主要營業(yè)所所在地的法律應當得到適用。尤其是在勞動者和雇主享有相同國籍的情況下,適用上述法律更是無可厚非。
(三)法律與勞動合同內在關聯(lián)性
Schlecker案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案例。一般來說,雇員在荷蘭工作十一年,荷蘭作為勞動者的慣常工作地并不會引起太大爭議。但歐洲法院向前進了一步,仔細分析了與該勞動合同相關的各個因素,如雇員是德國人,雇主是德國公司,在德國簽訂合同、領取工資、繳納稅款,從而認定德國的法律與勞動合同存在更密切的聯(lián)系。
(四)歐洲法院對此解釋的特定性
歐洲法院對此的解釋為,法院必須考察與雇傭關系相關的因素,并從中選出對重要的一個或多個因素,在這些最重要的因素所指向的國家中,應當尤其關注勞動者依其收入繳納稅款的國家、勞動者享有社會保險、養(yǎng)老金即醫(yī)療保險的國家。因此,即使勞動者在一個國家慣常地、長時間地、不間斷地履行其義務,法院也可以依據《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的例外條款,選擇適用與勞動合同存在更密切聯(lián)系的國家的法律[27]。依照法院的意見,不論該德國雇員在荷蘭工作了多久,與其存在更密切聯(lián)系的還是德國的法律。進一步說,德國雇主不論將本國雇員派往哪里,派去多久,在沒有約定的情況下都將適用德國的法律。
(五)約定合同適用法律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歐洲法院之前的案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針對涉外勞動合同的法律適用規(guī)則。Voogsgeerd案和Koelzsch案分別解決了兩個問題,勞動者有多個工作地點時如何確定慣常工作地以及a項和b項的適用層級。可以說,《羅馬公約》第6條的適用已經非常的清晰、明確和程序化。但Schlecker案推翻了上述程序,將法律重新置于不確定的境地,讓我們不禁有些疑惑,重要體現在這種對傳統(tǒng)沖突規(guī)則的背離原因和程度。而Schlecker案的另一特殊性在于當事人并沒有約定合同適用的法律,即雇主并沒有利用雙方的不平等地位將法律條款強加于處于弱勢的勞動者,沒有當事人意思自治在勞動合同中的缺陷,也就不需要啟動旨在限制當事人意思自治的保護機制。因此勞動合同被當做普通合同一樣看待,適用的法律是與勞動合同存在最密切聯(lián)系的法律。根據《羅馬公約》第6條第2款的規(guī)定,適用荷蘭法律本應爭議不大,但法院以其推論選擇適用德國法律,似乎在傳遞一個信息,相較于人員的自由流動,法院更傾向于支持服務的自由流動,雇主可以將本國員工送往任何地方,由于各國勞工標準不同導致的沖突,不應僅僅依靠法院去解決,也應由市場進行調節(jié)。而只要勞動者和本國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其就應當能預見到本國法律對其的約束。
總之,不論是適用慣常工作地的法律、主要營業(yè)所所在地的法律,還是其他依照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確定的法律,都要以具體的個案為基礎,依據法官的自由裁量進行判斷和取舍。由于其中的區(qū)別更多地來自于方法論的不同,體現是法官對于人員自由流動與服務自由流動的不同態(tài)度。因此,對Schlecker案的判斷需要未來更多的案例加以證實。未來涉外勞動合同糾紛的審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會依賴傳統(tǒng)的沖突規(guī)則。而法律的可預見性與個案的公正審理是貫穿沖突規(guī)則始終的永恒的矛盾,但也正是由于這種內部矛盾,使得國際私法才能不斷地完善,而持續(xù)不斷地向前發(fā)展。
參考文獻:
[1] 全稱為“(歐共體)關于合同債務的法律適用公約(1980年)”.
[2]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
[3] 第6條第2款稱:“二、盡管有第四條的規(guī)定,雇傭合同未按第三條規(guī)定作出法律選擇時應依:(一)履行合同時受雇人慣常進
行其工作地的國家的法律,即使他僅系暫時受雇于另一國家;或(二)如受雇人并不慣常于任何一個國家進行工作,則為他所
受雇的營業(yè)所所在地國家的法律。但如從整個情況看,合同與另一國有更密切的關系,則此合同應依該另一國法。”
[4] Case C-29/10[2011]ECR I-1595.
[5] Case C-384/10[2011]ECR I-0000.
[6] 系指“但如從整個情況看,合同與另一國有更密切的關系,則此合同應依該另一國法。”
[7] 系指“盡管有第四條的規(guī)定,雇傭合同未按第三條規(guī)定作出法律選擇時應依:(一)履行合同時受雇人慣常進行其工作地的國
家的法律,即使他僅系暫時受雇于另一國家;或(二)如受雇人并不慣常于任何一個國家進行工作,則為他所受雇的營業(yè)所所
在地國家的法律。”
[8] 系指“但如從整個情況看,合同與另一國有更密切的關系,則此合同應依該另一國法。”
[9] Voogsgeerd,paragraph 41.
[10] OJ 1980 C 282,p.1.
[11] See Koelzsch,paragraphs 40 and 42,and Voogsgeerd,paragraph 35.
[12] See Schlecker,paragraph 34.
[13] See Opinion by Walh,paragraph 36.
[14] See schlecker,paragraphs 41 and 42.
[15] See Giuliano Lagarde Report,p.25.
[16] See Schlecker,paragraph 24.
[17] See Koelzsch,paragraph 39.
[18] See Mulox IBC,paragraph 21-23.
[19] See Case C-383/95 Rutten[1997]ECR I-57,paragraph 23.
[20] See Case C-37/00 Weber[2002]ECR I-2013,paragraph 42.
[21] See Voogsgeerd,paragraph 46.
[22] See Giuliano Lagarde Report,p.1.
[23] See Opinion of Schlecker,paragraph 40.
[24] 該案中,合同約定適用荷蘭法律,法院地為英國,勞動者工作地為尼日利亞。若適用合同履行地法,荷蘭法與英國法將得不到
適用。本應適用尼日利亞法,但又被法院判定為與合同不存在足夠密切的聯(lián)系。
[25] P.S.Atiyah,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Oxford,1979)402-408.
[26] See Schlecker case,paragraph 21.
[27] See Schlecker case,paragraph 40,41 and 42.
[責任編輯 陳 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