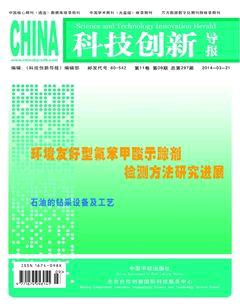淺談樹立物證鑒定文化的必要性
趙欣
摘 要:我國司法鑒定制度建立相對較晚,司法鑒定人也是一個新興的職業,司法鑒定文化并不會相伴而生,該文為了能夠在認知層面樹立起鑒定文化的必要性,從鑒定文化缺失的現實狀況出發,談論樹立鑒定文化的基礎即有限性,最后以四類人的認知為突破口來探索樹立鑒定文化的必經之路。
關鍵詞:鑒定文化 有限性 突破 認知
中圖分類號:U491.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4)03(c)-0235-02
不可否認地,司法作為社會“平衡器”的作用日益凸顯。在求助于公力救濟以實現正義的過程中,“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打證據就是打鑒定”已經不言而喻,鑒定意見這種具有科學含量與專家判斷的證據對于幫助法官認定事實、理清證據關系、明確責任歸屬、宣判案件結果有重大的影響。所以,在老百姓的心中,物證鑒定、鑒定意見理應具有權威性,理應使訴訟的終結沒有疑問,理應使公力救濟更有力道,理應在法治的發展中人們漸漸融入并感受著正面的物證鑒定文化。
但是現實不會是理應如此,所以該文就對樹立物證鑒定文化的必要性進行探討。希望在文化氛圍的理解中,讓司法鑒定制度健康的發展,成為人人認可并尊重的公正司法的左右手。
1 必要性的提起——鑒定文化的缺失
1.1 鑒定文化所為何物
有人會問,鑒定文化是什么呢?我們又需要樹立怎樣的鑒定文化呢?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司法鑒定的本質屬性說起。司法鑒定無疑在訴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重要。“它能夠在案件事實認定過程中甄別物證真偽、揭示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的內在聯系,補強或者減弱其他證據的證明力,甚至可以澄清人證的證明能力,對其他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方面有很大幫助。”正如湯瑪斯.摩伊特在《訴訟技巧》中所說的“訴訟需要這些具有專門知識的鑒定人解釋事情如何或為何發生,或者事情如何或為何沒有如此發生。”[1]
所以,鑒定本是一項具有正面能量的活動,鑒定文化也應該是一種反映著司法鑒定人的崇高的職業信仰和精神追求,并有一套支撐此精神追求并能調整利益關系、化解矛盾糾紛的規章制度和體制機制,且最終在實踐中真真切切的做出維持社會秩序、為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提供證據支持、技術保障和技術服務[2]的一種獨特的行業文化與觀念形式。
1.2 鑒定文化現實狀況
這種積極向上的文化才是真正的鑒定文化,所以與鑒定打過交道或正在打交道的人們亦或是即使是對鑒定只有概念上認識的人們應該是認同鑒定文化并堅定相信鑒定文化為公力救濟所做的卓越貢獻。但是以我國目前的情況看來,我國并不具有這種國人廣泛認同的鑒定文化,可以說,我國并未形成鑒定文化。
從一個老生常談的“黃靜案”1說起,其死亡原因做了5次尸檢、6次死亡鑒定,而每次的鑒定結果都不盡相同,這不僅僅給審判帶來極大的困難,也給當事人、被害人家屬帶來雪上加霜的心靈創傷,更讓社會對“鑒定”打上一個問號。誠然,在此案件中,不談案情本身,僅是因鑒定體制的松散給訴訟實踐又運送了一個更大更難的問題,成為了此案的爭執對象。重復鑒定、久鑒不決、虛假鑒定等鑒定機構本身出現的問題嚴重影響了訴訟的正常秩序,甚至出現了因鑒定問題上訪的事件。
換言之,“法院之判決幾乎以各鑒定機構之鑒定結果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故鑒定制度設計是否周全,直接影響司法機關之審判品質,并可深刻強化對人民訴訟權利之保障。”[3]可以說我國目前的鑒定現狀以及鑒定氛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審判品質,人們對以鑒定意見為依據的審判結果這種公立救濟的最終判決不甚認同,從而引發了各種“纏訟”“信訪”等既耗資源又耗人力的社會現象,這樣反過來使得職能部門的司法鑒定失去了應有的權威性,而不斷遭到質疑,鑒定文化就無從談起了。
2 必要性的基礎——對鑒定“有限性”文化的認可
司法鑒定體制現階段的病態現狀,以及人們普遍對司法鑒定不正確的認知狀況(主要是對其最基本的鑒定常識理解缺位),還有審判檢察等司法人員對司法鑒定本身所能做到的鑒定程度及相關結果的過分推崇和過分依賴,不僅阻礙了司法公正及人民權利的維護,而且不利于樹立鑒定的正面氛圍和文化。
要改變這種大眾認知層面對鑒定文化的負面影響,就需要從基礎做起,將鑒定文化之所以能夠不斷建立發展起來的“根本”即“鑒定有限性”旗幟鮮明的表述出來,改變人們的過度崇拜或不良認知,為鑒定文化營造良好的生長空間,直到在專業人員和人民大眾心中接受認同并放心的在鑒定文化中訴訟。
從現場發現、找到的物才存在,倘若偵查人員沒有發現,“存在”也“不在”,而這其中的發現又與訴訟中的時間緊密聯系這是鑒定及鑒定文化存在的基礎,也是實用主義有限的發現的存在。之所以這樣的“存在”是只能被我們有限的發現,是受到以下因素的想象。
2.1 發現的技術、方法有限
物可以被發現、提取、固定、保管直至鑒定意見的作出都與發現所用的技術、方法有關,并與此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有關。我們技術方法的發展進步可以解決越來越多的鑒定問題,使得發現率不斷提高,但是不得不承認發現的技術方法永遠是有限的,發現的實施過程及程序要求也需要不斷的適應鑒定的需要來完善。比如從橫向的訪問到立體的視頻、電子信息來獲取、存儲、利用信息,現場的發現率因技術不斷提高,但發現永遠是有限的,現場中的足跡、血跡、指紋,尸體中的病理、毒理始終會因技術或人為原因而不被發現。
2.2 發現的條件、環境限制
物證的發現會受到技術設施、設備條件的限制,也會受到物證存在的狀況條件的限制(如處于水中、油中的發現提取),還會受到存在的環境條件的限制(如氣候、交通或者人的活動的影響),這些都是客觀的限制,永遠無法回避或忽視其對堅定發現的限制,所以發現的“物”不具備鑒定的條件,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確定,那也不能成為“證”。endprint
3 有限的可知
發現“物”后,是否可知?能知?也存在有限性問題的探討。
3.1 作為物證的“物”的范圍的有限性
關于可做物證的“物”的范圍,至今沒有一個嚴謹的科學定論,而事實上,犯罪現場千變萬化,也不能下一個范圍的限定,物證鑒定專家一般是從經驗出發大概的限制了物證的種類范圍及物的數量質量范圍。比如形象痕跡即:指紋、相貌、足跡的一部分是不具備鑒定條件的,亦或者筆跡鑒定檢材的一個短“1”的出現,數量少也無法做鑒定,更無法做重新鑒定。這些便是科學之不能、客觀之不能的有限性可知。
3.2 確定可知與能知對象特性及特征的有限性
無非是用辨認或者鑒定的方法來確定可知與能知的對象的具體特征(量化的描述)及特性(概括描述),即通過對物在運動變化中的相對靜止統一的固有規律進行歸納總結。但是倘若鑒定人員無法找出并確定物所蘊含的固有規定性,便不能出鑒定報告,此“物”便不能為“證”。
3.3 對特性、特征確定的程度及層次的客觀有限性
鑒定意見分為肯定或否定的確定性意見和可能是或不是的不確定性意見,這便是對物的特性及特征確定的程度及層次的不同所得出的不同意見,無論是確定性的鑒定意見還是不確定性的鑒定意見都應是客觀科學的即具有客觀科學的態度的結論,不應因結論的不確定性而質疑鑒定意見不科學不嚴謹。
4 有限的關聯
事件或者案件都存在必備的結構要素,哪些人或物在何時何地因為什么原因經歷了怎樣的犯案過程而最終又造成怎樣的結果,這是我們想找出的物的關聯,以物質交換理②和信息交換與轉移理論為基礎,可以從人的記憶,物質、物品、痕跡,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些反映體中搜尋供述與辯解、證人證言、陳述,物證、書證,視聽資料證據和電子數據證據,再通過同一認定理論回到事實本身,最大程度的接近案件事實得出鑒定意見。這當然是最理想的物與其他證的關聯模式。
但是由于發現和可知的有限性使得案件形式要素的時間關聯、空間關聯、方式手法關聯和轉移物及結果關聯常常不會像鎖鏈般展現在我們面前。也就是說在鑒定中信息轉移交換直接來源于案件的直接關聯,如像鑒定DNA般的唯一性、排他性是比較少的,關聯的有限性,促使鑒定人員從各種間接關聯中找到物與證的聯系,是指互相得到印證形成系統關聯。
所以如果我們的民族認知接受這些最基本的鑒定“有限性”文化,那么就為我國的鑒定文化氛圍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但目前鑒定文化在大眾認知層面還存在以下問題有待突破。
5 必要性的探索——鑒定文化在認知層面的突破口
5.1 公眾百姓需引導
時下,公力救濟訴訟中老百姓會想到用鑒定的方式尋求有利于自己的證據或者明確責任的歸屬,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至少鑒定的有效性與科學性得到了認可,但是一旦當不利于自己的鑒定意見出現時,重復鑒定的要求便頻繁出現,不僅如此更有甚者還會找到鑒定機構大吵大鬧“討回公道”,或采用“纏訟”和“信訪”的私力救濟方式來表示對鑒定意見的抗議和不滿。這就表明鑒定文化在公眾百姓心中的缺失,大眾百姓會選擇鑒定的方式,但大多是“利己”主義的驅使,一旦鑒定意見不符合預期,便采取各種方式試圖改變鑒定意見。
事實上科學客觀的鑒定是經得起考驗的,無理蠻鬧最終會在客觀公正的鑒定意見面前偃旗息鼓,鑒定文化也最終會在這股公正客觀的力量引導下發芽成長被大眾所認可。公眾百姓的需要對鑒定有限性的文化的認知,也需要被引導。應“廣泛開展群眾性文體活動,整合文化資源,突出行業特色,大力推進群眾性文化活動的開展,創造健康向上、獨具特色的司法鑒定行業文化,以先進、健康、優質的文化形式和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活動感染人、熏陶人、影響人”[4]并以鑒定人員在鑒定工作中的實際行動引導大眾參與到鑒定文化中來。
5.2 媒體視聽需負責
現在的某些新聞傳媒常常以不負責任的態度來報道事件以博取眼球,抓住一點無限放大、混淆視聽,報紙網絡等媒介關于鑒定方面的報道大多是傳播負面新聞及批駁,而我國全年有多少重大案件是靠鑒定取得的突破卻現有宣傳,這樣無疑會放大鑒定文化缺失時的制度漏洞,將鑒定工作推向一個需要不斷認錯、改錯的尷尬境地,使整個大眾視聽在對鑒定的價值選擇上偏向質疑。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在技術上無論是普通大眾還是媒體人都是不精通鑒定知識的,對于有異議的鑒定意見可以申請重新鑒定,但針對判決結果,個別“纏訟者”一味將敗訴責任歸結給鑒定人、辦案人,拿起媒體的力量來對付某些鑒定人或者鑒定機構,當然正確的使用媒體曝光的方式是公民的權利,但是作為媒體人對于報道的真實性和評論的內容的權衡應該有更加負責人的態度,不能枉聽一方對于“敗訴結果”難以平復的控訴,更應該實地考察、探索發現,運用媒體人的權利,拿出公正鮮明的態度按事實報道,以正視聽,促使積極正面的鑒定文化以傳媒的方式廣泛傳播。
5.3 司法人員需自省
還有一個不容小視的問題,就是目前司法辦案人員的執法水平和執法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使案件處理不當引發受害人纏訟,而且對鑒定文化的形成產生消極作用。“鑒定意見作為案件證據的一部分,應當和其他證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并沒有高出其它證據的任何理由,必須經司法人員嚴格審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然而,目前司法人員普遍存在一個誤區,認為鑒定意見是專門人才依據其專門知識并借助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對專門性問題所作出的客觀鑒別和判斷,當然具有科學性和客觀性,而不進行嚴格審查,或者根本不審查,不結合其他證據材料,直接將鑒定結論作為定案的依據,導致案件處理不當,引發當事人強烈不滿。”[5]
除此之外,司法人員經常試圖忽略或者說是不認可鑒定意見中本應正常存在的不確定意見,當拿到不確定意見時,總是已案件不好判為由要求鑒定人員給出確定的結論,即“是或不是”,這就給鑒定活動的依法公正進行帶來很大困擾。由司法干擾的鑒定意見當然是不客觀不科學的,只能像毒樹之果一樣埋下“壞因”,假若重新鑒定或者進入二審程序,被不客觀的鑒定意見被推翻自然會讓鑒定人員惹禍上身,又何談鑒定文化健康的成長并融入每個人的心中呢?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司法人員應該自省。endprint
5.4 鑒定人員需努力
所謂掃凈自家門前雪,欣賞的人兒自會來。鑒定文化至今沒有在我國正式形成和鑒定人員自身有很大關聯。本文在這里不談鑒定體制本身還有不完善的缺陷,只說鑒定人員確實還有一條布滿荊棘的征程需要一步一個腳印用實際的行動來見行鑒定文化的感染力。去掉那層神秘的專家色彩,用更貼近大眾的論理來描述檢驗鑒定過程,使結論更容易讓當事人雙方和司法人員接受;在實際工作中司法鑒定人員應與時俱進,注重培訓,定期了解相關法律知識和司法鑒定規則以及新技術的應用,提升鑒定人員的專業能力;除此之外司法鑒定人應嚴于律己,遵守職業道德,在司法鑒定的過程中,會遇到說情,要求鑒定中給予照顧。作為鑒定人一定要堅守職業道德,不受委托單位、上級領導、熟人說情的干擾,客觀公正科學嚴謹做出符合事實的鑒定結論,是鑒定結論經得起審查,雙方當事人對鑒定結論的公正性得到認可,遏制雙方當事人因鑒定結論不公而投訴上訪[6]。
只有這樣,再配合鑒定體制不斷的改革完善,我國的鑒定文化會因司法鑒定制度在服務訴訟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中發揮的功能和作用而日益形成,社會大眾也最終會認識到鑒定文化的必要性,而從認知方面摒棄民族認知對鑒定文化的劣根性影響,最終成為推動鑒定文化的一份子。
參考文獻
[1] 湯瑪斯.摩伊特.訴訟技巧[M].蔡秋明,譯.臺灣:商周出版社,2002.
[2] 李凌云.關于加強司法鑒定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J].中國司法,2009(3):19-21.
[3] 朱富美.科學鑒定與刑事偵查[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8.
[4] 金興民,劉一石.司法鑒定文化核心價值初探[J].中國司法鑒定,2011(2):39.
[5] 徐紅星.論“纏訟”案件產生的原因[J].中國法醫學會法醫臨床學學術研討會,2011(6):141.
[6] 王萍.高作香.司法鑒定引起投訴的原因及對策[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2(3):55.
注釋
① 黃靜案是2003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省湘潭市發生的一起案件。此案的離奇之處在于,多次鑒定結果不同。
② 如汗液會轉移到杯子上,而玻璃中的元素卻不可能轉移到手上。物質交換原理解釋了許多物證的形成機理,對具體的檢驗方法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