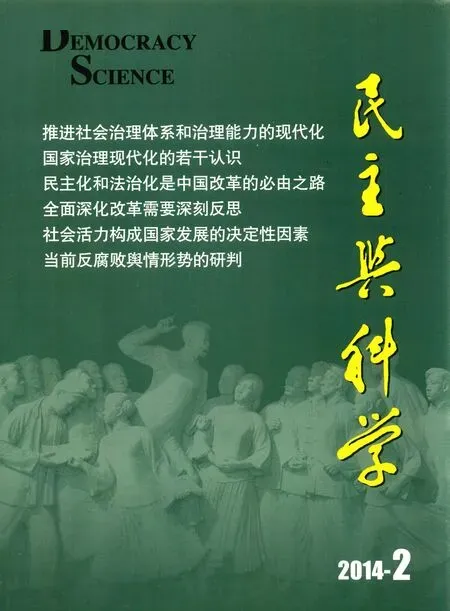回到“五四”的原點
■陳占彪
一
距離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的學生愛國運動已經九十五周年了,我們照例得紀念,論理得大紀念。
可是,什么是“五四運動”呢?
“五四運動”之名自然得自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為反對日本強占我山東權益的愛國游行。然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五四運動”的范圍和意義要遠大于此。
這突出地表現在“五四”數年前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游行”緊密地捆綁在一起。1931年,羅家倫在口述五四運動時,就從蔡元培掌校時期的北大所引領的“新文化運動”談起,稱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思想變化的結果”。后來羅家倫又深切地指出,“五四運動是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新文化運動也廣泛地澎湃地由五四運動而擴大。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一貫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國現代化”。
今天我們所說的“五四運動”不再只是指1919年5月4日引爆的以反對日本強占我山東權益的學生愛國運動,而是如羅家倫、俞平伯所說的那樣,是包含了此前此后的思想革命、文化反省、社會變革、政治改良、經濟自立等內容在內的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
后來,五四運動研究者周策縱先生對“五四運動”下了一個類似的定義。他稱,“它是一種復雜的現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種種社會和政治活動。這一切都是由以下兩方面因素促發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條和巴黎和會的山東決議所激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種學習西方、試圖從科學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國的傳統以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企望”。他將五四運動的時段限定在1917年到1921年。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所說的“五四運動”和最初所說的僅僅指5月4日學生游行示威的“五四運動”時間跨度更長,所涉范圍更廣,意義更重大,影響更深遠。基于“五四運動”這個詞已被普遍地認為是一個包括5月4日愛國游行事件在內的一個更為廣義的概念,在這里,我們將從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生游行示威反對巴黎和會上列強同意日本強據山東始,到6月28日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簽對德和約止,在此期間全國范圍發生的、社會各階層積極響應的一系列游行、演說、抗議、辭職、逮捕、罷課、罷市、罷工、成立組織、抵制日貨等事件,統稱為“五四事件”。
在“五四事件”發生的幾乎同時,與其表兄蔡曉舟一同搜集編撰五四資料的楊亮功先生后來這樣說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自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天安門游行趙家樓縱火起,至六月十日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并明令準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辭職止,為時共一個月零十日左右。此一運動初由北京幾個大學發動,蔓延至全國各省市各級學校暨各工商業人民團體。其傳播之速,范圍之廣,可以說是史無前例。”他這里所說的“五四運動”與我們今天所說的“五四運動”就是兩個概念。如果我們用“五四事件”這個詞的話,便可以將他之所謂的“五四運動”與今天所說的“五四運動”區分開來。
可以說,今天的“五四運動”這個概念是以當年的“五四事件”為原點,不斷豐富,不斷拓展起來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時又因為其無所不包,就難免顯得龐雜模糊,以致一談起五四運動都有些叫人“不知從何處說起”之感。
今天,我們普遍認同的是一個更為廣義的“五四運動”,可是,要知道,在當年很多當事人的心目中,“五四運動是一個簡單的、純粹與明朗的事件”。陶希圣甚至明確地說“五四”與新文化運動關系不大,就是新文化運動對當時的學生影響也不大,“五四運動的起因與白話文或文學革命沒有什么關系”,“新青年與每周評論在學生們的中間,亦有流行。但白話文,或文學革命,或新文化運動,還未發生多大的影響”。田炯錦則稱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是“兩碼事”,參與其中的也是“兩撥人”,“五四運動努力的人,對新文化運動,甚少參預,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們,亦很少參加五四的行動”。在他們看來,“五四”沒那么復雜,沒那么“含混”,而今天這個廣義的“五四運動”簡直就是“胡說八道”。
更有當時的參與者稱,“如果說是文化人激動起五四愛國運動,這功績應歸之于當時的新聞記者,而不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這當然是從“五四事件”,而不是從“五四運動”的角度而論的。而田炯錦則說,人們在談“五四”的時候,有的是指五月四日當天;有的是指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這一段期間;有的是指文學改良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很長期間的許多事象。
可見,將“五四運動”與“五四事件”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就可以避免這些含混,以及由含混造成的贊美或批評。
二
自然,對于“五四運動”的史料整理和全面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滿坑滿谷。但在編者看來,撇開更為廣義的“五四運動”,既便對“五四事件”,甚至對“5月4日那天在北京的學生游行示威”,還有相當一批材料為我們,特別是大陸的讀者,所鮮見,而這部分材料正是本書的主要內容。
本書主要著眼于對“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的愛國游行”這一事件進行“事實描述”的“稀見材料”進行收集整理。也就是說,我們試圖通過媒體現場報道、親歷者回憶,當事人書信、日記、公文、密件等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性質材料,來告訴我們當天發生了什么事,又是如何發生的。因為這一天發生的這件事是“五四運動”的原點。可以說,本書旨在通過對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更好地“退到五四的原點”。
于是,本書區別于已有的“五四”參考資料有以下兩點:一、除與“五四事件”直接相關以外,“五四”前后一些專論思想文化、罷工罷市、社會活動、政治外交的材料不予收入。二、除北京之外的,全國其他省市的“五四事件”不予收入。并不是說這些材料不重要,而是因為一方面本書所關注的是最基本的“五四事件”,而非更廣大的“五四運動”。另一方面這些資料我們在已有的出版物中可以參考。
要問的是,對五四事件的回憶材料難道就缺乏嗎?當然不。1979年,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之際出版的《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下、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可以說是“五四”回憶的集大成者,其中就包括一些當事人對當時事件的回憶(此書所指五四運動當然更多的是廣義上的“五四運動”,因此就包含了更為豐富的內容)。可以說,正是這些材料成為日后我們了解5月4日這一天學生游行示威情形的重要材料(凡此書收錄的內容,本書一概避免收錄,我們將此書和其他書籍中一些與五四事件相關的文章附錄列出,以備有興趣者參考),此后出版的一些“五四回憶”之類的書,多是從此套書中選錄。
可是,除過這些親歷者的回憶之外,還有沒有與五四事件相關的材料?事實上,還有一批由于種種原因我們不便看到,不易看到,進而被忽視的文字存在。而這些文字正是本書的基本內容。本書的資料來源大概有以下兩種:
其一,居留臺灣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憶。
長期以來的國共對抗,陸臺對峙,使得我們很難看到“另一方”對五四事件的記述。正是這種對立,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幾乎全是留在大陸一方的“五四青年”對“五四”的敘述,如許德珩、周予同、匡互生、楊明軒、楊東莼、楊晦、霍玉厚、俞勁等人的回憶,可是,我們要知道,還有相當一批的“五四青年”日后都居留臺灣,有的還是臺灣社會的精英和中堅,而他們也有一些關于五四事件的,有相當分量的敘述,比如陶希圣、楊亮功、田炯錦、王撫洲、毛子水等人的回憶,羅光對陸徵祥的訪問,馬星野對羅家倫的訪問,傅斯年侄子傅樂成對蔣復璁先生的訪問,秦賢次對楊亮功的訪問,陳其樵的日記等,而這顯然是全面了解五四事件不可或缺的寶貴材料。“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大陸臺灣兩地在各個層面已經不斷融合、走向統一,兩岸文化學術共享互補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那么,我們有理由、有義務將這一部分材料嵬集整理出來。可以說,居留臺灣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憶是本書的一部分主要內容。
其二,建國前報刊檔案中的五四事件敘述。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多是建國后的五四事件敘述。由于建國前民國報刊檔案紛繁蕪雜,不易接觸,不易檢閱,對建國前關于五四事件的回憶和敘述就不易見到。這次我們從民國報紙、期刊(包括內部刊物,地方刊物)、日記、書信、密電、公文、報告,甚至小說創作中爬梳出對五四事件的敘述材料。網撒得很大,撈到的魚卻不多,每有些微收獲,都十分激動,因此也就顯得彌足珍貴。
比如在編者看來,1919年5月5日《晨報》上登載的在中央公園游覽的該報記者的現場目擊文字,記述生動,細節豐富,可謂是最早最生動的五四學生游行現場報道,論理這個文章并不難找,可是這個文章卻似未加整理,也較少為研究者所重視。再如,1941年《城固青年》上登載的陸懋德的演講《五四運動之經過及其意義》亦是作者親身親歷“五四”的文字。城固系吾省名不見經傳小縣城,《城固青年》亦是名不見經傳小刊物,恐怕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這類文字的存在。再如,周瘦鵑于1919年5月9日寫的《賣國奴之日記》更是以曹汝霖的口吻寫其“末路之窘促”,“冷嘲與熱罵俱備”,“窮極酣暢”,卻因“語多激烈,無出版社敢印”,只得自費出版。此小說是五四事件的藝術反映,其反應之迅速亦是讓人驚嘆。
可以說,通過本書搜集的“民國時期”和“臺灣地區”對五四事件的敘述,再加上我們能夠看到的“大陸建國后”對五四事件的敘述,大概能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五四事件敘述。
本書的基本內容包括六部分。
(1)“和會秘辛”通過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伍朝樞、西園寺侯爵、重光葵等巴黎和會參與者,以及當初在法國發動同胞阻止中國代表團簽字的李宗侗的文章,讓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巴黎和會上中國所處的困境,是為北京學生五四游行的直接動因。(2)“現場存真”是從當時的書信、日記、密電、呈文、報紙中將“五四”當時游行的現場呈現出來。(3)“親歷者憶”收錄了日后臺灣地區“五四青年”的回憶,民國報刊中關于五四事件的敘述,這些親歷者的五四回憶,也是本書最主要的內容。(4)“日本五四”收錄的關于1919年5月7日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游行示威,并被日本警察和民眾阻撓、毆打、鎮壓的記述,這個事件向為人忽略,但也是五四事件的一個向度。(5)“五四演義”收錄了蔡東藩、薔薇園主、周瘦鵑、程生、汪靜之等人數篇關于五四事件的“文藝創作”(通俗小說,話劇,詩),從這部分內容中可以看出一個“創作中的五四事件”。需要強調的是,幾乎就在“五四”發生的同時,以“文藝”的形式對五四事件進行創作并不少見,但這個角度似乎鮮為人注意,但這些材料尚未能整理出來,就只好留待以后了。(6)“告日人書”輯錄了當初各界人士,如北京學生、林長民、張繼、何天炯、戴季陶、李大釗等人,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勸說日本放棄侵略的“講理”之辭。這些文字在今天日本竊據釣魚島的背景下來看,似乎也并不過時。
由“事件背景”到“現場實錄”到“事后回憶”到“文學演義”到“當下警示”,是本書的大致脈絡。
最后,本書還增加了兩個附錄。一個是編者輯錄了其他書籍中與五四事件相關的文章的題目,以方便有興趣的讀者參考。另一個是編者于六年前寫的一個與五四事件相關的文章。這個文章主要從五四事件中一些不為人注意的細節論及以下四點內容:五四事件與當時的天氣狀況和星期休息是有關的;“五四”中軍警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曹、陸、章的“賣國賊”稱號是值得商榷的;火燒趙家樓是經過事先謀劃的。這個文章曾拆分為若干部分分別在《新文學史料》、《歷史學家茶座》、《世紀》、《南方都市報》等報刊發表過。這次結合新看到的若干史料,對該文有所補充和修訂。
三
或曰:你收集的這些東西到底有什么意義?
有時我們覺得要弄清一個歷史事件似乎并不覺得困難,那往往是因為我們接觸到的只是一面之詞的原因。須知“明白”并不意味著“正確”,要對一件事情形成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和合理的判斷應當是建立在“多面之辭”的基礎上。“多面之辭”,公說婆說,雖然會讓我們有“你不說我倒明白,你越說我越糊涂”之感,但卻更易接近真實的歷史,更易形成正確的看法。
我們常會感到,一件事情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是很難說得清、道得明的。這是因為事實雖然是曾經客觀發生過的,惟此一個,但呈現事實和認識事實的方式卻是主觀的,眾說紛紜。然而,事件的最大真實性正是在這眾說紛紜的互相補正之中呈現出來的。
對五四事件的敘述同樣如此。由于客觀條件(記憶力、感受力等),更是由于主觀條件(喜好、利益、立場等)的制約,對不同時代、不同身份、不同人物對同一件事情自然有著多種的,有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認識。
比如對于火燒趙家樓這一五四事件的高潮,通行的敘述會稱此舉為英雄壯舉。可是即便在當時,人們也不全這樣認為。當初一同到趙家樓的毛子水就稱:“后來看到火從曹家燒起來,又見到有人打了駐日本公使章宗祥,我覺得做得有點過火了。還沒有法律定罪的事,怎么可以先訴諸武力?”“五四”后的第二天,為學生教授刑法課的總檢查廳檢查官張孝簃則稱學生行為是“法無可恕,情有可原”。梁漱溟更是在《國民公報》上發文稱,“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縱然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他說:“最好我們到檢廳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領受。”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有人便以“政治訴求的合理性完全遮蔽了暴力行為的殘忍性與犯罪特征”來評價學生當初的放火行為。在這些不同的敘述中,火燒趙家樓就呈現出了一個復雜的面目。
就是對曹、陸、章這三個“賣國賊”,人們的看法也不全相同。對絕大部分人來說,此三公實乃不折不扣、鐵板釘釘、恨不得人人得而誅之、食肉寢皮的賣國賊,可是在他們本人看來卻是“冤比竇娥”。“五四”第二天,曹汝霖在辭呈中說,當年簽訂“二十一條”時的“經過事實,我大總統(按:指徐世昌)在國務卿任內,知之甚詳。不敢言功,何緣見罪”?1964年,89歲高齡的曹汝霖在為自己的回憶錄寫的序文中還長吁短嘆,喊冤不已,“國人既懷恨日本,遂益遷怒于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二十一條由我簽字;其后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此!清夜捫心,俯仰無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然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就是對政府來說,當時也為曹、章、陸三人洗刷前愆,稱“曹汝霖迭任外交財政,陸宗輿、章宗祥等,先后任駐日公使,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案牘具在,無難復按”。在這些不同的敘述中,“暴打賣國賊”就呈現出了一個復雜的面目。
就是對“參加五四運動”一事,各人性情不同,參與的熱情亦不同。比如,對王統照來說,可謂熱血沸騰,他說:“我第一次感到群眾力量的重大,也是第一次沸騰起向沒有那么高度的血流。”但對那個比有的學生還年輕的梁漱溟老師來說,卻是冷眼旁觀,梁稱:“我沒有一種很激昂的情緒,沒有跟著大家跑。”
甚至曹宅門墻到底是高是低,也是人言言殊。當時在墻外的周予同說:“我們打算爬墻進去,礙于宅子的圍墻相當高,沒有成功。”而另一個學生田炯錦則稱“曹宅坐北向南,墻壁很高”。陶希圣回憶也稱“曹宅的墻很高,大門緊閉”。可是,對曹汝霖來說,他家的院墻并不高啊,曹稱“我家向無警衛,墻不高,門又不堅”。這其實不難理解的,不同的人,立場不同,感受不同,敘述也不同,對要越墻而入的學生來說,再低的墻也都會覺得高,而對祈禱平安的曹汝霖來說,再高的墻都會覺得低。
至于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場來論“五四”,其觀點更是截然相反,針鋒相對。
朱維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常用“實相”,而不是“真相”這樣的詞,在他看來,“真相是絕對的”,而“你看到的只能是一個方面”。可以說,幾乎在五四事件的每一個環節,我們都能找出或互相補充,或互相矛盾的不同敘述,而正是這些不同的敘述不斷地修正著我們的認識,以便達到最大限度的真實。以上所舉只是數例而已。
這也是我們收集材料不厭其多、不厭其全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