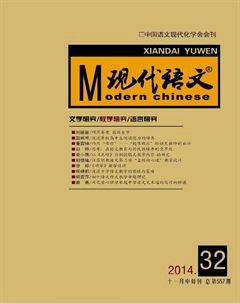略談語文的建構
語文的建構包括課程、教材、教學、考試等,這里略為言說。作為課程,自然要有所界定,包括課程性質、課程要素、課程目標等。課程性質,定位于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工具性側重于語言文字的運用,人文性則講人文養成,但或許還可增加一個操作性,更便于二者的結合,而不是各執一端。從課程要素來看,包括知識、能力及修養。語文知識有語言知識、文章及讀寫知識、文學文化知識等,這些知識雖并列在一起,卻屬于不同層面。能力有聽、說、讀、寫之分,其中聽與說屬于口語運用,讀與寫則為書面能力。聽與讀是吸收,說與寫為傳導。語文修養,有文學審美、文化傳承及人文養成等。這些要素既各有所指,又要有機配合,三位一體,才有助于語文的學習或教學。課程要素包括知識、能力及修養,相應地,課程目標就可定位為掌握語文知識、提高語文能力及增進語文修養。又有三維目標之說,即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大致也是對應的。其中過程與方法,就是講操作性的。語文作為一門課程,其目標還可分解為不同層次,且不同層次的目標都應當盡可能地明確。像描寫之類,作為手法之一,小學就接觸了,但由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這描寫有何區別,卻不清楚。語文學習中其它不明確的層面,可依此類推。而從實際來看,是有一些區別的。就課堂教學來說,像描寫之類,聽來都耳熟能詳,但因為不加區別,就變成了老生常談。在學生那一面看來,則缺乏新鮮,如此課堂效率就不可期待了。
教材,是最主要的課程資源。現行教材或課本的設計主要有“閱讀鑒賞”“表達交流”“梳理探究”“名著導讀”等。比起先前那種只有單一文選型的課本來,顯然是進步了。教材中突出“閱讀與鑒賞”“表達與交流”兩個板塊,自是讀寫并重的,另外也兼顧了口語交際、語言知識、名著閱讀等。各科教材都按單元來設計,出于橫向比較,語文教材也不例外。但語文教材的單元設計不能只是便于按文體編排課文,還要有文本內容方面的考慮,于是有的便改為主題編排。但將不同體裁的文本混編在一起,殊不可取。或許可調整為專題編排,既擴大容量,又顯得更為緊湊。此種專題設計,大可參照文學史的做法。比如詩歌方面,有《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唐詩、宋詞、元曲等,散文方面有諸子散文、歷史散文、辭賦駢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等,小說方面有白話小說(話本與擬話本)、文言小說(傳奇與筆記體)、章回小說等,戲曲方面主要是雜劇與傳奇。然后是現代詩歌、現代散文、現代小說、現代戲劇及外國文學等等。這些名稱可綱舉目張,大致能反映出文化及人文的傳承。現行教材中,將現代文放在前面,文言文放在后面,這是顧及了五四以來白話文的傳統。但白話與文言之爭,早已告一段落。而今看來,大可將文言文放回到前面,更能體現文化的長河從古流到今。且實際的教學中,也常有將文言文或古詩文提前的。專題的設計,理當從古到今,由中及外,更能體現出教材的條理性。而今教材又分必修與選修,選修教材多是專題化的,只不過容量更大,削減一些,必修與選修仍可合二為一。閱讀專題的選文,多以名家名作為主。這與作文的寫作是有距離的,則作文及寫作板塊,還可編選一些時文。時文方面自不乏佳作,對作文寫作不無參照。作文及寫作專題里,可講知識,可舉例文或范文,但更重要的是得分開層次要求來設計。作文在不同的學齡,其要求應當有所區分,更便于達成目標。至于教學參考書,本是配合教材或課本的,即有為教學提供參考之義。但語文教參,卻成了許多教師手上的法寶,過于依賴。嚴重的,可以說脫開了教參就不會教。而照搬教參的做法,如同照本宣科一樣,又會使操作簡單化。教參自有其體例的設計,包括課文研討,主要是整體把握與問題探究;關于練習,就是提供一些答案;教學建議,即有若干條建議;有關資料,多是提供相關背景及鑒賞文章。教參的內容不無豐富,但若按體例遷移到教學中,仍就是千篇一律的。傳統的做法,是與文本對照,有注解有章句有評點,而今不妨合理地加以繼承。換言之,教參的設計大可在課本的基礎上形成,而不必另編一冊。盡管多一本書少一本書不是問題所在,但在課本的基礎上形成教參,合二為一,可使教學更專注于課文。配合課本,還可有讀本,大致與課本平行。但由課內到課外,多有延伸及拓展。
教學,即課程實施。其中教是對教師而言的,學是對學生而言的,可以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教與學相聯,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需要雙方的配合或合作。教有教法,傳統的有章句和評點。章句,就是分章析句,從段落結構到語句層面來解讀文本內涵。評點有眉批、旁批及總評,眉批與旁批用于文中局部,而總評則著眼于全文。在熟讀全文的基礎上,即可試作評點。章句和評點,也可謂過去的閱讀教學和寫作教學。常用的教法還有讀、背、講、練等。朗讀要讀得熟,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有的篇章,則要背誦。講解是主要的手段,所要做的仍就是疏通文意,進而把握重點難點。講練結合,就是講解了,還得有一些練習來鞏固配合。語文的教,是教一些可教的。對應于學習來看,又可根據學情來教。學情,即學習的情況,包括學習興趣、學習狀態、學習程度等。至于學生的學,還要加強自主性,而不可過于依賴教。所謂自主性,不只是自覺學習一些新的,還得整理或盤點教過的或已學的。“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既溫習舊知識,又吸取新知識,就可以做教師了。“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不到想明白而不得,不去開導;不到想說而說不出來,不去啟發。不能舉一反三,不再重復。溫故知新和舉一反三,對語文教學來說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禮記·學記》中又說:“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所以通過學習,然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通過教別人,然后知道其中的困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然后能加強學習;感到了困惑,然后能自己發憤圖強。所以說教與學是互相促進的。
讀與寫,是語文學習或教學的兩個重點。先說讀,讀什么,教材或課本自然是要精讀的,但不能囿于課本,而要向課外延伸。課外讀什么,最好是與課內有些關聯,即由課內向課外延伸。比如課內讀了某一名家的作品,覺得喜歡,便可延伸閱讀。多讀一些,才有可能增加印象,或者改變看法。再就是從選本入手,為人所公認的優良選本,也是很好的讀物。再由選本涉獵開去,就可拓開閱讀的視野。由課內而課外,最起碼的是比課本內容多了一些。至于拓展開去,無有窮盡,因語文的課內與課外就是有限與無限的關系。課外閱讀,可拓展閱讀的視野。怎么讀,是方法問題,如朗讀、精讀、慢讀、復讀、熟讀等,是較為重要的。再說寫,寫什么,無非是自己的經驗、想象和思考。怎么寫,先說基礎訓練,包括仿寫、擴寫、縮寫、改寫、續寫等,都是很能體現讀寫結合的方式。片斷訓練,相對于整篇的大作文來說,片斷訓練也就是小作文。能力訓練,包括觀察力、感受力、記憶力、想象力、思維力及表達力等。文體訓練,作文的文體主要是由表達方式來界定的。即以記敘為主的是記敘文,以說明為主的是說明文,以議論為主的是議論文。此種設計著眼于練筆,可謂練筆文體或基礎文體。過程訓練,一篇作文的完成,包括審題、立意、選材、構思、表達及修改等,在這些環節上有所落實,便可體現出操作的有序性來。
考試,是主要的課程評價。語文試卷本于穩中求變來設計,自然是方向明確。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與教材的對接不夠。一份試卷中,除了幾句默寫,盡是課外的,這對語文教學來說不無尷尬。再說所學非所考,所考非所學,也不是個事。雖說能力可以遷移,但此種遷移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達成,并不分明。長此以往,語文教學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下降。考試雖有選拔之義,但此種選拔是基于基礎之上的選拔,切不可一下子拔得太高。就語文學習或教學的兩個綱領性文件來看,考試大綱理當配合課程標準,而不可高踞其上。考試作為一種檢測,本就是配合教學的。或許,考試設計仍要回歸教材。當然,前提是教材的編排要合理一些。比如增加古詩文的比重,文言文考試可以鞏固課內所學為主。一方面是回歸教材,另一方面則可保持開放,比如現代文就可選課外的,較少閱讀上的障礙。語文考試就回歸教材而言,由于所讀過的課文是熟悉的,則選擇題、填空題、簡答題、論述題都可考。這些本是考試中較普遍的題型,再考慮到語文的學科特點,則選擇題可以少一些,總體上仍要以文字表達為主。
(吳永福 福建省長汀一中 3663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