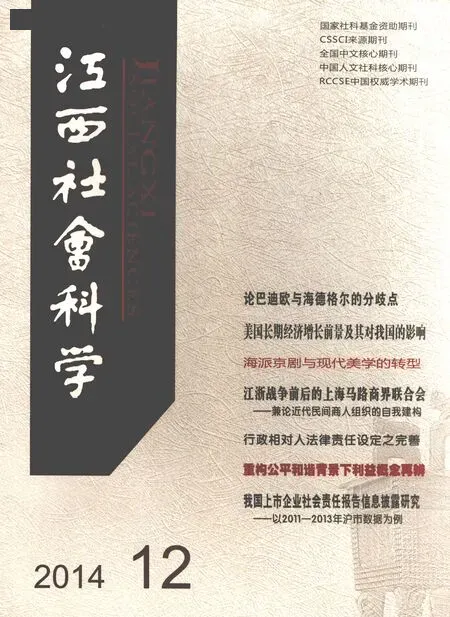論楊憲益文學翻譯思想
■歐陽友珍
20 世紀是西方文論空前繁榮的時期。大量的國外理論引入我國翻譯界,使我國譯評界的理論意識以及批評方法科學化,我國翻譯理論建設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語言文字是最具有民族性的,翻譯理論也應植根于民族自身的歷史結構和文化土壤之中。我們既要辯證地借鑒和吸收西方理論成果,也要立足于民族自身特定的歷史文化,對我國本土翻譯思想進行系統化整理和現代詮釋。
楊憲益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文學翻譯大師,成績斐然,尤其在中國古典文學的英譯方面影響甚為深遠。學界稱其翻譯了整個中國。他于2009 年獲得中國翻譯協會“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楊憲益譯作豐厚,卻沒有專門的理論著作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翻譯思想。筆者擬從他的翻譯實踐入手,對散見于其譯作的前言后序以及翻譯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涉及的翻譯思想進行梳理、整合,以期對這位翻譯家有更全面、客觀的認識。
一、翻譯之“道”及釋“道”之難
(一)翻譯本質之“道”
翻譯有“器”的一面,也有“道”的一面。自古以來中西方學者都有從這兩方面來研究翻譯的。從形而上的層面研究翻譯,有助于我們深刻地理解翻譯的本質。關于翻譯的哲學基礎,哲學家賀麟1940 年在《論翻譯》中指出:“翻譯的哲學基礎,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處,才是人類的真實本性和文化創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處亦為人類可以相通、翻譯之處,即可用無限多的語言去發揮、表達之處。”[1](P48)就翻譯的可行性和翻譯的本質,楊憲益在不同場合談過自己的看法。“翻譯是溝通不同民族語言的工具。不同地區或國家的人都是人,人類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什么東西應該都可以翻譯,不然的話,人類就只可以閉關守國,老死不相往來了。”[2](P82-83)既然人類的思想感情是可以互通的,那么翻譯也就成為可能。這與賀麟指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翻譯哲學基礎同出一轍。就是說,人類思維是同一的,人類的思想感情有其普遍性,語言形式的差異不會影響到思維的內容。人性的共同性是翻譯之“道”的哲學基礎。人類可以用多種語言去表達同一思想,譯文與原文本的關系即是一意與兩語的關系。
此外,楊憲益指出,翻譯活動的時空距離也不是問題,是可以彌合的。在他看來,“我們大可不必擔心時間相隔久遠的問題”,比如《詩經》,現代人還是很欣賞這些詩歌的,“原因是它們都是杰出的詩篇,將作品翻譯成外語,也應該是這種情況”[3](P89)。楊憲益強調的是,文學藝術的內涵和審美具有超時空性,可以在全人類心中引起共鳴。這是翻譯可行性和翻譯本質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如果要翻譯幾百年前的文學作品,楊憲益指出:“譯者就得把自己置身于那一時期,設法體會當時人們所要表達的思想;然后,在翻譯成英文時,再把自己放在今天讀者的地位,這樣才能使讀者讀懂那時候人們的思想。”[3](P83)時空距離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要想彌合翻譯活動的時空距離,譯者就必須“入乎其中”把自己融入原文,感知原文,然后又“出乎其外”,設身處地為讀者考慮,這樣原作與譯作之間的時空距離才能消除,譯作才有可能在異域文化語境中被接受和產生影響力。基于此,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產品才得以傳播和交流,并成為人類公共的財產。
(二)翻譯的釋“道”之難
一方面,楊憲益堅信一切都是可譯的,因為人類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文學藝術的內涵和審美具有超時空性的特質。但同時,他又認為在文學翻譯過程中存在不可譯的問題,因為在文學中有許多其他的因素構成原文的某些含義,而要把這些含義傳達給文化不同的人則是根本不可能的。[3](P85)世界上的事物極其復雜,語言的表述和意蘊也是如此。總體上我們可以說所思是普遍的,同一事物可以由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達,即“意一言多”,但有時也可能是“言一意多”,比如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蘊的雙關語、典故、俗語、文化負載詞以及蘊意豐富的詩句。這些都是翻譯的難處。在楊憲益看來,由于“人類自從分成許多國家和地區,形成不同文化和語言幾千萬年以來,各個民族的文化積累又各自形成不同特點,每個民族對其周圍事物的看法又會有各自不同的聯想”[2](P83)。民族性、地方性色彩濃厚的語言形式的翻譯就面臨這樣的困境,其中蘊含的文化意象很難準確、有效地傳達給目的語讀者群。
這里提出了某些文化意味不可譯的問題,即譯作與原作的文化距離問題。翻譯涉及各種類型的距離: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心理的、審美的以及更多的派生類別,由文化差異造成的文化距離是與翻譯相關的最常見的距離。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各自的文化心態、閱讀體驗、審美感知等都會影響其對譯作的閱讀反應和接受效果,因而文化距離也就成了翻譯活動中繞不過去的核心問題,同時也是“不可譯”的主要原因。翻譯傳遞的不僅僅是基本意義,其本身還需跨越各種距離。兩種語言以及兩種文化之間的部分可通約性和不可通約性,勢必產生部分可譯和不可譯的問題。翻譯之難就在于如何合理地協調原作與譯作之間的各種距離。
在詩歌的不可譯方面,楊憲益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翻譯《奧德修紀》時,他曾在散文體和詩體之間舉棋不定,最后還是將其譯成了散文,“因為原文的音樂性和節奏在譯文中反正是無法表達出來的,用散文翻譯也許還可以更好地使人欣賞古代藝人講故事的本領”[4](P170)。與此相關的是中國古詩詞的英譯問題:是保留古體還是用現代體,抑或是另尋途徑,采用散文體?楊憲益曾多次嘗試用英詩格律譯中國詩歌,但通過長期的翻譯實踐摸索,他發現,如果一定要遵循原詩的音韻格律,那么原詩的內容必然受到損傷。“每國文字不同,詩歌規律自然也不同。追求詩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內容上的不夠‘信’。”[2](P84)“字有其音”,文字傳神還要靠聲音節奏,這點在詩歌、散文體中尤為凸顯。中英文在語音上有很大的差異,英文每個字一個音節或多個音節,音節還有輕重之分,如果一定要按照原詩的音韻格律來翻譯,原詩的內容必然有損失。語言距離給詩歌翻譯帶來巨大的挑戰。楊憲益認為用外國的格律詩譯中國詩歌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以詩譯詩當然好,但須在不損害原詩內容的前提下,為了忠實原文的內容,楊憲益多采用散文體來翻譯詩歌。
二、翻譯之“器”的傳承與發展
“信、達、雅”作為重要的翻譯之“器”法則最早出現在三國時期支謙的《法句經序》中,但將這三個字按翻譯的內在規律如此排列組合,并明確將它們作為翻譯標準的當屬嚴復。嚴復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指出:“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5](P85)這正是我國傳統翻譯理論的特色之一:扎根于自身傳統文化土壤之中,從我國傳統哲學與美學思想中汲取營養以自用。
對于“信、達、雅”的標準,后人都是認可的,但具體翻譯實踐中如何把握尺寸,還是人言人殊。楊憲益有著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在四十多年的翻譯生涯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不斷探索,印證“信、達、雅”翻譯標準的解釋力和影響力,并結合自身的翻譯實踐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考量和踐行這一標準。
(一)譯文“信”內涵的豐富
1.忠實原文,譯者克制
談到楊憲益翻譯風格時,譯界普遍認為是異化為主,歸化為輔。他的代表譯作《紅樓夢》就是極好的例證。楊憲益本人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翻譯必須忠實于原文內容,不增不減。“過分強調創造性是不對的,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是在翻譯,而是在改寫文章了。”[3](P84)并且,他還認為翻譯的時候譯者不能作過多的解釋,譯者的職責就是把原文的信息盡可能忠實地傳遞給目的語讀者,譯文中不應夾雜太多譯者自身的觀點。“我們不應過多地把自己的觀點放進去,否則我們就不是在翻譯而是在創作了。”[3](P89)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譯者職責重大,翻譯活動自始至終必須通過譯者主體意識和主導作用才能完成。從文本選擇到譯本生成,譯者總會出于意識形態或詩學的考慮來操縱原文。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楊憲益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角色定位。他認為翻譯就是翻譯,不是對原作的改寫,譯者應以翻譯倫理來規范自我,自重自律,合理發揮譯者的主體性,強調譯者應隱形和克制。
多年來的翻譯實踐中,楊憲益堅守自己的翻譯理念,強調譯者克制,忠實傳達原文內容,盡量讓譯文讀者像原文讀者一樣接收到原文傳達的信息,反對對原作的改寫和操縱。翻譯《紅樓夢》時,他盡量忠實地把中國文化信息和內涵保留下來,對原文中具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詞語進行異化處理,不做改動,也不做過多的解釋。相比之下,霍克斯傾向于交際翻譯,自我定位為文化的協調者,充分發揮了譯者的主體性。為了順應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心理期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進行了適當的改寫、替換甚至省略。
我們來看看楊譯和霍譯對詞語“紅”的處理情況。“紅”是《紅樓夢》作品中的一個中心詞,總共出現了664次。在中西文化中“紅”有著不同的文化意味,因而兩個譯者各自采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楊譯用其一貫的直譯,把原文的內容和形式同時傳入譯文,而霍譯則采取多種方式來處理這些“紅”字。[6](P110)比如:書名《紅樓夢》楊譯本譯為“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而霍譯本則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怡紅公子”楊譯“the Happy Red Prince”,霍譯為“Green boy”;“悼紅軒”則分別譯為“Mourning-the-Red Studio”和“Nostalgia Studio”;等等。
2.內容至上,形式次之
中國翻譯始于佛經翻譯,經文重義,自是理所當然。重義也成了中國歷代翻譯家共同的座右銘。楊憲益繼承了這一傳統,尤其體現在詩歌翻譯上。關于詩歌翻譯,前文已經提到楊憲益認為用外國的格律詩譯中國詩歌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由于中英文在語音上的差異,譯文很難把原詩中的音樂性和節奏體現出來,所以翻譯時如果一定要嚴格遵循原詩的音韻格律,那么原詩的內容必定受到損失。因此,為了忠實原文的內容,形式暫且放在第二位。
這種內容重于形式的詩歌翻譯理念與另一位翻譯大師許淵沖的理念大相徑庭。兩位大師在中國古典詩詞英譯方面頗有建樹,但兩人翻譯理念差異較大,主要在于對“信”字有不同的理解。許淵沖主張譯詩除了要傳達原詩內容外,還要盡可能傳達原詩的形式和音韻,做到“意美、音美和形美”,翻譯的忠實應包括內容、形式和風格三方面。楊憲益則認為追求詩歌格律上的“信”,必然造成內容上的不夠“信”,故其多采用散文體翻譯中外詩歌。[7](P40)
3.文化精神,“信”之核心
文化具有民族性、時代性和地域性等特征,翻譯產生的根源來自于文化間交流的需要。楊憲益曾說:“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文字翻譯成另一種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習俗和思想內涵,因為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都有差別。”[8](P2)這就是說,翻譯不只是語言層面的轉換,更是語言背后的兩種文化的交流和對話。文化移位對文學翻譯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認為在兩種文化接觸的地方存在一個“第三空間”,文化間的差異在這個空間內發生作用。這一空間的產物即為文化雜合體,兼具兩種文化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講,譯文都是文化雜合體,是翻譯過程中歸化和異化相互交融的產物。[9](P242)當然譯文中異化和歸化的比例會隨著歷史和社會的變遷不斷變化和調整。
翻譯策略的選擇受主、客觀多重因素的影響。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意識形態、主流詩學,以及譯者本人的文化態度和譯者職責定位都與翻譯策略的選擇密切相關。就楊憲益而言,他擁有深厚的國學素養,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熱愛,秉承“忠實原文”的翻譯理念,以及中國文化傳播者的自我定位,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他在翻譯實踐中必定重視對中國文化信息的保留,較多采用異化處理,如有需要,還附上腳注以彌補譯文中的文化缺失。任生名教授認為,楊憲益在其翻譯生涯中以忠實的翻譯“信”于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文明的精神,希望通過翻譯向譯入語讀者忠實傳達中國文化的價值和靈魂,傳達中國人的人生和他們的喜怒哀樂。[10](P34)
(二)譯文基于“信”的可“達”
楊憲益說:“‘信’和‘達’,在翻譯則是缺一不可。‘寧順而不信’和‘寧信而不順’都是極端的做法。要做到‘信’‘達’兼備不是容易的事。”[8](P2)在翻譯蕭伯納戲劇《凱撒和克麗奧佩特拉》時,他覺得書名譯成《凱撒和克麗奧佩特拉》不夠通俗,但又認為不能為了通俗化而將其譯成《霸王別姬》,因為擔心如此一來,中國讀者會有錯誤的聯想,以為這是關于西楚霸王相遇虞姬的故事。由此我們可以解讀到這點:“達”不僅意味著語言流暢,通俗易懂,還指文化的傳達,即“達”意味著語言和文化的可達性,譯作的可達性應該在保留原作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實現。
由于楊憲益自身的語言水平、文化修養,以及得天獨厚的優勢(夫人戴乃迭的出生背景和學術背景),其譯文語言優雅正統、自然流暢,帶有濃厚的純正英國英語味。夫人戴乃迭是一個強有力的翻譯伙伴,楊曾提起過,翻譯《紅樓夢》時,每遇到晦澀的文字時,夫人總是能流暢地找到英文對應詞。這種中西合璧的翻譯伙伴模式令人羨慕,同時翻譯效果也能得到保證。在充分理解原作意義,尊重原語和目的語各自的語言規范的前提下,楊氏夫婦能夠突破英漢兩種語言表層結構的束縛,用流暢地道的語言再現原作的語體風格,滿足目的語讀者的心理期待和語言習慣,使其譯文具有可接受性和可達性。
(三)譯文“雅”的時代性解讀
關于“雅”的標準,楊憲益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在嚴復時代,用文言翻譯西方作品,算是“雅”。但在今天,用文言而不用白話翻譯外國作品,就是太怪了。也就是說,譯者應該把自己放在今天讀者的地位,設身處地考慮當代讀者的接受反應和心理期待,盡量合理縮短譯作與原作的時空距離、譯作與讀者的心理距離。理論只是社會當時的價值觀反映,后人應該也必須結合時代的發展,賦予其新的解讀視角和內容。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前人的理論思想,才是真正尊重前人,正確理解前輩的思想。我們知道在嚴復時代,士大夫文學潮流占主體文化中的主流地位,“用漢以前的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5](P85)。因此,為了迎合封建士大夫的審美心理,勸導他們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和人文思想,嚴復著意使譯文合乎中國古文傳統的體式,即順應當時讀者的接受心理與期待,以便達到自己的翻譯目的。
翻譯既然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必然遵循一定的社會習俗和規范,要想被讀者接受,譯作必定與當時社會主體文化中的主流詩學保持一致。在嚴復時代,“雅”意味著用文言翻譯西方作品,那么今日的“雅”,當然應有新的所指。楊憲益認為“雅”只是“達”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原文是用極俚俗的話,翻譯人偏偏要用極文雅的話來表達,這恐怕也說不上是好的翻譯”[2](P83)。至此,筆者認為,對楊憲益來說,雅并非指某種特定的文體,而是指語言風格層面上的“文雅”,與“俚俗”相對,且與達緊密相連,在語言形式上表現為生動流暢、富有文采。
三、翻譯:民族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在一次座談會上,談到英國翻譯家亞瑟·威利的《詩經》英譯本時,楊憲益認為它學術水平很高,稱得上是一部翻譯杰作,但同時也指出:“有弄得過分像英國詩歌的弊病:比如他把中國周朝的農民塑造成田園詩中描述的歐洲中世紀農民的形象。”[3](P85)這樣一來,譯文讀起來不像反映中國情況的詩歌,倒更像英國中世紀的民謠。在這里楊憲益表達了對翻譯的價值和社會功能的理解:翻譯不是機械的語言轉碼,而是傳遞文化信息的媒介,是兩種語言所承載的不同文化的交流與溝通。忠實原作,準確傳達原作的文化精神是楊憲益翻譯生涯中一直堅守的翻譯理念。好的譯作應該尊重原作的文化特色和風貌,采用異化策略,盡量保留原作的文化習俗和精神內涵。
在后結構主義視域下,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活動,還是一種文化政治實踐,是社會精英層的一種有目的的行為,翻譯的目的本身往往超越技術層面的所指意義的傳遞。德國哲學家、翻譯思想家施萊爾馬赫認為翻譯有兩種途徑,即在實施翻譯活動之前,譯者就面臨一種選擇:是站在原作的立場,保留原作的異國情調,讓目的語讀者走向原作;還是站在讀者的立場,對原作進行改寫,讓原作走向讀者。為了讓英美讀者真正感受到其他民族人民的所思、所想和所言,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呼吁在翻譯與英美主流價值觀有差異的外語文本時使用阻抗式異化翻譯,尊重文化差異,保留原文的異國情調,而不應肆意改寫,對原作實施文化暴力。在文化策略翻譯選擇上,楊憲益與韋努蒂是英雄所見略同。采用異化策略,才能真正實現翻譯的主要社會功能價值:維護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促進民族文化間的交流與溝通。
四、結語
通過從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三方面對其翻譯思想進行系統而客觀的梳理和整合,我們認識到楊憲益深受我國傳統哲學與美學的影響,繼承并豐富了中國傳統譯論內涵,從翻譯的形而上本質和形而下標準、方法和策略層面來看,其翻譯思想蘊含著道與器的辯證統一關系。
當前西方理論大量地引入我國翻譯界,我們應該抱著客觀而理性的態度,既要大膽拿來為我所用,也要對其進行合理反思。盲目跟風于西方翻譯理論的大潮,否定或忽視我國本土的翻譯思想都是不理性的行為。立足于我國本土翻譯思想,加強自身翻譯理論建設,合理地運用西方理論,才有助于我國典籍對外譯介模式的探索和構建,對當前中國文化“走出去”提供積極有益的借鑒和指導。
[1]柯飛.關于翻譯的哲學思考[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4).
[2]楊憲益.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歷與體會[A].因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C].金圣華,等.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
[3]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
[4]禹一奇.東西方思維模式的交融[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09.
[5]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3.
[6]馮慶華.母語文化下的譯者風格[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7]陳麗麗.從《琵琶行》英譯試論許淵沖與楊憲益翻譯思想的差異[J].考試周刊,2011,(28).
[8]楊憲益.我與英譯本《紅樓夢》[A].一本書和一個世界(第二集)[C].鄭魯南,主編.北京:昆侖出版社,2008.
[9]賴祎華,歐陽友珍.跨文化語境下的中國典籍外譯策略研究——以《紅樓夢》英譯本為例[J].江西社會科學,2012,(12).
[10]任生名.楊憲益的文學翻譯思想散記[J].中國翻譯,19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