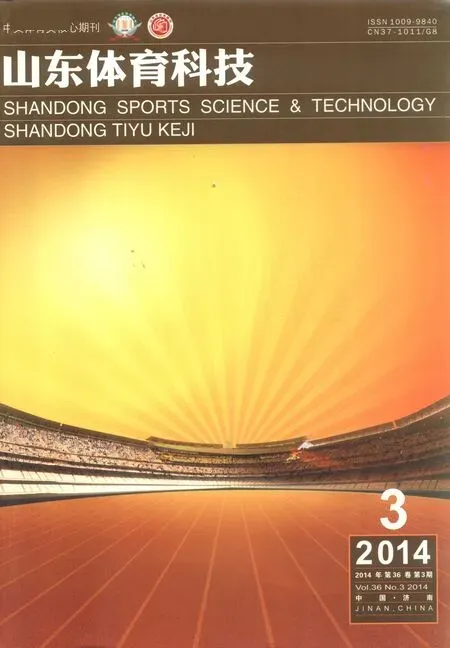俞大猷探訪少林寺重要意義略探
李 磊
(韶關學院體育學院,廣東韶關 512005)
明朝中后期,由于政治的逐步腐敗,相應地使得海疆軍事防務出現廢弛局面。在日本封建主的縱容下,一部分日本武士和中國沿海一帶的漢奸亂民相互勾結,形成海盜勢力,在中國東南沿海一帶肆意搶掠,極大地擾亂了中國東南沿海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并嚴重危及到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再加上邊疆不斷爆發少數民族的起義,成為明朝統治階級的內憂和外患。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打起精神,組織軍事力量進行平定倭寇的戰爭。這一系列的抗倭和“平叛”戰爭,不僅不能使處于清靜之地的少林寺置身事外,派出少林武僧力量參加抗倭戰爭,同時也使抗倭將領關注到少林寺。正是通過抗倭戰爭,也使得少林寺武功得到交流和提高。明朝著名軍事將領和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探訪少林寺,就是少林武術史,乃至中華武術史上極具意義的一段佳話。
俞大猷,字志輔,又字遜堯,號虛江,福建泉州北郊濠市濠格頭村人,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俞大猷不僅是明代著名抗倭名將,還是一個著名的武術家。他歷任明代三朝將官,一生坎坷。戎馬倥傯47年,時而受到朝廷重用,名聲顯赫;時而受到貶責,淪為囚徒,一生中曾經四為參將,六為總兵,累官至都督。在明朝倭寇屢犯海疆的多事之秋,率領所部俞家軍轉戰于蘇、浙、閩、粵之間,身經百戰,戰功顯赫,因而與戚繼光并稱“俞龍戚虎”。《明史》有《俞大猷傳》,對他蓋棺定論地評價認為:“大猷為將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勛。”《明史》還稱贊他:“世宗朝,老成宿將以俞大猷為稱首,而數奇屢躓。以內外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眾也。”。嘉靖四十年(1561),著名抗倭英雄俞大猷從云中奉命南征途中,親自取道嵩山,來到少林寺進行了一次專門探訪。這次探訪對少林寺發生了較大影響。對于這次探訪,由于史籍記載比較簡略,對于它在少林寺和少林武術發展史的作用和意義,中華武術史界還缺乏全面的認識和專題研究,有待于進一步系統深入探討。
俞大猷探訪少林寺,在他的《正氣堂續集》中有明確記載:“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長劍技。嘉靖辛已歲,自北云中奉命南征,取道至寺。僧負其技之精者,皆出見呈之,予告其住持小山上人曰:‘此寺以劍技名天下,乃傳久而訛,真決皆失矣。’復著芒鞋,扶竹杖,游本山大小庵場,歷達摩面壁石洞,遍覽金乘珠藏、龍步虎音之區。見寺前一山地,其形勢更奇,又告小山上人曰:‘此地可見一小院,以增此寺之勝。’小山而慨然曰:‘建院之責,愚僧任之,即平治其基以經始也。劍訣失傳,示以真訣,是有望于名公。’予謂:‘是,非旦夕可授而使悟也。’”俞大猷在《詩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中也說:“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擊劍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負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見呈之。予視其技已失古人真訣,明告眾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積之歲月而后得也。’”俞大猷探訪少林寺的兩處記載,內容大致相同,但也有差別:一是說自負有精湛少林棍藝的武僧,給俞大猷進行了演練;二是又說,有自負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見呈之。少林武僧在朝廷高級將領到來之際出面給進行表演或者演示,應該是正常的,也是一種慣例和禮節。河南巡撫視察少林寺就觀摩了少林武僧表演,并賦詩以記。到少林寺參訪的人,古往今來,可謂很多,唯獨俞大猷探訪少林寺,目的明確,意義深遠,對少林寺和少林武術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值得回味。
1 通過交流印證了俞家棍法的價值,指出少林武術的缺失
俞大猷探訪少林寺前,已經胸有成竹,創作完成了《劍經》。俞大猷是一個一身而二任的軍事家和武術家。他出生的福建泉州是中國著名的武學重鎮。泉州地區不僅是武術的發源地,也是各種技擊之術得以廣泛傳播的地區。這里的棍術等就曾被時人所稱道。明末大臣黃景昉就自詡地說:“吾溫陵(泉州)棍棒手撲妙天下,蓋俞都督集古今棍法而大成之,身與士卒相角斗。余所接善棍者,皆言其父、其大父承都護所指教”[1],將福建省武風的形成歸功于俞大猷等。嘉靖三十六年(1557),《續武經總要》(八卷)付梓,前七卷為俞大猷之師趙本學所著“韜鈐內外篇”,后一卷為俞大猷所著《韜鈐續篇》。俞大猷通過學習趙氏陣法多有體會,進而推演陣法并講述兵器使用要領而成《劍經》。主要是將所練“俞家棍法”編寫成武功秘籍,亦即《劍經》。書中不僅深刻地闡發了俞家棍法要義,還總結了棍法練習和實戰的真訣。《劍經》完成后,不僅對泉州的南少林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為當時俞大猷組建俞家軍發揮了重要作用。
俞大猷在探訪少林寺前的抗倭實踐中,已經把俞家棍法用于練兵和實戰。俞大猷曾采取了自己的選將練兵方法:平時在鄉村民間開始培養訓練民兵骨干,戰時迅速擴充為能打仗的軍隊。他先從千戶、百戶和兵營中挑選30名有組織才能者任甲長,讓他們到鄉村各挑選25歲以下、乖覺勇健、力挽300斛、能管束10人、將來可做甲長的義士9名,每名給銀5錢,令自備藤牌、刀槍,日給工食四分,平時首先教習武藝,其次教練營陣,務必使他們知道其中深意。要求義士每人自募親鄰10人,給安家銀三錢、工食三分,聽此義士管束。平時一遇小警,即督甲長及義士共300人出面抵擋;如遇大警,則將270名義士升為甲長,各自帶領自募新兵10名,原甲長升為哨長,管9名新甲長和90名新兵。這樣就可以迅速擴建成一支數干人的戰斗軍隊,就可以用來抵御較大規模的的倭寇入侵[2]。俞大猷在福建地方曾訓練出數千名民兵,把俞家棍傳授給他們,隨時可以用來抗倭自保。俞家棍在平定倭寇、海盜的戰爭中,發揮了極大的威力。
在探訪少林寺時,俞大猷通過觀看少林武僧演練,直接指出少林棍法的缺失。俞家棍法在武術史界又被有的學者稱為南少林棍法。在俞大猷探訪少林寺前,俞大猷已經有了兩種準備:一是有了一部集俞家棍法大成和真訣的《劍經》;二是還有了在抗倭御虜戰爭中運用俞家棍法的實踐經驗。俞大猷之師趙本學是宋太祖趙匡胤后人,宋太祖是少林派外家開山始祖,趙本學是宋太祖的第十八世嫡孫。有人進一步認為,俞大猷師事趙本學,自然可以把俞視為少林俗家弟子。俞大猷師承趙氏太祖拳棍,而后發展成俞家棍,是和少林武術具有一脈傳承的歷史淵源關系。不管俞大猷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俞大猷對少林寺原本是仰慕的。要不他不會一再說到“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長劍技”,而在軍務繁忙之際,還專門親自取道探訪。俞大猷的探訪,首要的目的和作用在于通過用自己的俞家棍法和少林棍法進行驗證和切磋交流,一探少林棍法虛實。由于俞家棍法是俞大猷通過長期在南方抗倭前線演練和實戰應用的武術,和少林寺偏重防守、注重功夫、禪武合一的少林棍法相比,自然會感到“真訣皆失”。少林寺的棍法練習,主要是為了修禪和健身自衛;而俞大猷的俞家棍主要是為了抗倭戰爭,二者真訣自然也不會一樣。至于當時的少林寺住持小山上人是否認同俞大猷的看法,也感到少林棍法久傳失卻了真訣。但是,少林寺為了發展自己,為了落實俞大猷創建十方禪院的動議,對他這個朝廷命官、抗倭名將還是很尊重的。當即答應籌建十方禪院,并委派年少且有勇力的少林武僧精英宗擎和普從,跟隨俞大猷進入俞家軍中,為解決少林棍法“真訣皆失”的問題做準備。發現少林寺棍法“真訣皆失”,是俞大猷探訪少林寺的首要重大意義。
2 探訪后少林武僧進入俞家軍,為“少林真訣”回傳做了準備
發現問題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問題。委派兩個年少有勇力的少林武術到俞家軍跟隨俞大猷領受俞家棍法真訣,就是小山上人和俞大猷達成的默契。宗擎和普從在俞家軍效力3年,出入于營陣,并有俞大猷隨“時授以陰陽變化真訣,復教以智慧覺照之戒”[3]。通過俞大猷的諄諄教誨,2人都得到了俞家棍的真訣,雖然他們還不能達到得心應手、出神入化的境界,但也幾乎是達到了“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地步了。經過俞大猷培訓的兩個少林武僧又返回了少林寺,用俞大猷所教真訣轉授給少林武僧,以便使真訣得以永傳。13年后,少林寺弟子宗擎到北京神機營前來叩見俞大猷。問到宗擎在少林寺傳授《劍經》真訣的情況,得知少林寺已有近百人得到了傳授,真訣可以在少林寺永遠傳承。俞很高興,又把《劍經》授予宗擎,鼓勵他能夠精益求精地進行傳授。這樣,俞大猷探訪少林寺的目的達到了,不僅使得俞家棍得到驗證,又反向傳播回到了少林寺。這也是俞大猷探訪少林寺的最終的、也是最大的意義所在。
3 少林武僧再次從軍,使俞家軍提高了聲譽,增強了戰斗力
俞大猷探訪少林寺之時,正是俞大猷得到朝廷任用奉命南征之際。他對少林寺自然也有居高臨下之感。明說是認為少林棍法“真訣皆失”,實際上少林棍法是少林武術傳承的正宗,而且也曾經在東南沿海接受過實戰檢驗、立過大功、聲威顯赫的武藝,月空等參加沿海抗倭就是實例。宗擎和普從被推選到俞家軍效力,也是俞大猷過過眼的。二人作為少林武僧到軍中效力,作用不是單一的去接受俞大猷傳授“真訣”,他們作為少林寺的正宗武僧代表和象征,同樣參與訓練俞家軍隊。無論使用俞家棍或者是用少林棍來訓練軍隊,都可以名正言順地說用的是少林棍。盡管俞大猷對俞家棍也很有自信,畢竟,少林棍法和俞家棍比較起來更加正宗,也曾在沿海一帶的抗倭戰爭中大顯過神威。因此,實際上,俞大猷探訪少林寺并帶領少林武僧進入俞家軍,他和少林寺至少是雙贏的。俞大猷和俞家棍通過認祖歸宗得到了印證,也進一步用回傳真訣的名義幫助訓練了俞家軍,提高了俞家軍的抗倭平虜的戰斗力。通過探訪少林寺,俞大猷至少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是用少林棍法印證了俞家棍,提高了俞家棍的聲譽和地位;二是探訪后進一步強化了俞家軍的少林武術訓練,提高了軍隊的戰斗力。這對俞大猷和少林寺方面,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4 通過“認祖歸宗”,提高了少林寺的聲譽和地位
俞大猷在奉命南征途中,取道嵩山親自探訪少林寺,也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還了他的一個夙愿。他一再說出“予昔聞河南少林寺,有神傳長劍技”之類的話來,就是明證。說明少林寺武功在此前,已經是聞名天下。對于少林寺來說,俞大猷畢竟不是一般的參訪者,而他是具有朝廷命官、抗倭名將、少林俗家弟子、武術家多重身份集一身的重要人物,自然要認真接待。少林寺本身雖然練武,但原本就是通過武術切磋交流,善于吸納天下中華武術精華,來提高自身武藝。少林寺和俞大猷雙方應該都是這種情況,雙方仰慕已久,都有吸納對方、提高自己的意愿。俞大猷雖然是一個名聲顯赫的人物,但他的俞家棍法及其本身,都是有傳承的,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離不開天下聞名的禪宗少林。俞大猷雖然幼讀儒家經典,通過武科進入仕途,但他處在南少林崛起的泉州一帶,也是禪宗傳播發展的重鎮,因此他對佛教禪宗也有比較虔誠的信仰。或許是因為他師從趙文學,擬或是師從李良欽學習過荊楚長劍、齊眉棍法武藝,此2人又都和佛教禪宗具有天然的聯系。無怪乎有人把他當做少林俗家弟子來看待。他的參訪,正可以了卻自己認祖歸宗的一個夙愿。少林寺在發展過程中,也不是能夠一帆風順的。尤其是到了明代,也面臨著修禪和武功的重大中興任務。俞大猷的到來,也算是找到了一個契機。送出兩個少年武僧精英隨俞大猷到抗倭的俞家軍中歷練,學得南少林棍法真訣,再在少林寺進行反向傳播,是中興少林武術的一個很好機會。俞大猷探訪少林寺,還有系列的后續舉動,諸如通過巡游少林寺龍步虎音之區,提出創建十方禪院的意見,對發展少林禪宗叢林,都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從整體上看,俞大猷探訪少林寺,進一步提高了少林寺的地位,擴大了少林寺和少林武術的聲譽,也給少林中興提供了契機,探訪的意義深遠而且廣大。
5 俞大猷為十方禪院選址、題寫碑記,促進了少林叢林的發展
嘉靖四十年(1561),俞大猷奉命從山西大同南征,專門取道嵩山,探訪了少林寺。由于他特殊的多重身份,少林寺住持小山上人熱情接待了他的參訪。少林寺武僧還專門為他進行了棍術表演,然后又換了方便爬山的芒鞋,拄了竹杖,巡游了少林寺的大小庵場。不僅到了達摩面壁的石洞,還觀賞了少林寺的金乘珠藏、龍步虎音之區。俞大猷看到少林寺對面有一片山地,其形勢奇偉,便給小山上人建議:此地可建一小院,以增少林寺之勝。小山慨然答應:建禪院的責任,就由愚僧小山來擔任了,立即進行地基平整就可以開工建造;劍訣失傳,示以真訣,這是要拜托名公(俞大猷)來實施了。這時的俞大猷,已經年近花甲,到了58歲年紀,但仍躊躇滿志,奉了朝廷之命,準備南下粵閩贛一帶,在平定倭患和匪亂中一展身手。宗擎、普從2人,跟隨俞大猷在俞家軍中,效力3年后,又回了少林寺。等到13年后宗擎再到北京神機營拜望俞大猷時,普從已經化為異物,只能由宗擎一人來向俞師匯報回傳少林武功真訣的情況了。盡管如此,俞大猷也是很高興的。興之所至,揮筆題詩贈給了宗擎:“學成伏虎劍,洞悟降龍禪。杯渡游南粵,錫飛入北燕。能行深海底,更陟高山巔。莫訝物難舍,回頭是岸邊。”俞大猷在他的《正氣堂續集》中記述了此事。此后,少林寺僧普明來見俞大猷,說明為少林寺新建十方禪院在得到了少林無空大師的俗家弟子御馬監太監張暹、盧鼎、高才輸俸資助后得以落成,特請求俞大猷題寫禪院碑文,作為永久紀念。俞大猷欣然應諾。碑文之中,還專列一條,祝愿宗擎所學劍法再得廣傳。俞大猷把探訪少林寺引發的宗擎回傳《劍經》真訣和新建十方禪院聯系起來加以認識,可見二者在俞大猷眼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印象。俞大猷探訪少林寺的又一意義,就在于他不僅為十方禪院的肇建,不僅有創意之功,還有選址、題寫碑文的貢獻。俞大猷探訪少林寺,在少林寺叢林發展史上,意義是重大的。
[1]向愷然,俞大猷《子母三十六棍對習之法(一)》[J].精武,2007,(07):39 -43.
[2]蔡金星,俞大猷與少林武術的的淵源關系[A].蔣夏雨主編,俞大猷研究[c].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104—110.
[3][明]俞大猷,正氣堂續集.詩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A].周焜民編,五祖門研究[A].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