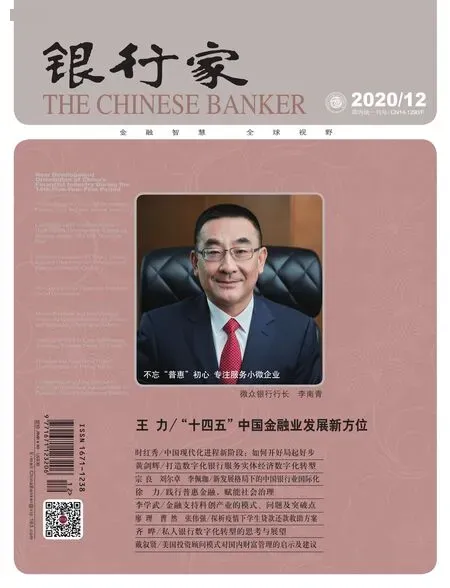共生哲學—科學精神與中國之道的共融體①
高續增
各位學者,尊敬的主席先生,很高興有機會在這里闡述我對共生哲學的看法,并借此機會就相關的認識教于各位老師和朋友。
我以為,共生哲學是當代時事政治的實踐與關于公共社會管理的學術實行探索相結合而產生的一個新的思想觀念,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實踐問題。它產生于21世紀的中國不是偶然的,它的最根本的核心,是堅持認為人對客觀世界的積極進取的精神也應當深入到對社會組織進行管理的實踐中。
當前西方那些最發達的國家都在社會管理的實踐中遇到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要不要對實行已久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進行突變型的變革,我以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有待于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和理念,把中國人在幾千年來在治國實踐中所積累下來的自信心移植到西方政治理論中來。
由西方人創新出來的科學精神讓人類獲得了空前的文化成就,這與它的社會映像——民主政治的密切跟進分不開,但是實踐已經證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完美無缺的,在當前世界各個民族文化大融合和人類科技爆發性的飛躍的情況下,它已經到了對自己文化進行反省的時候了,就像中國人從一百年前開始做的一樣。
中國人在歷史上因為過分執著地堅持施政者的主觀意志,雖然創造出社會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但是始終沒有解決好從根本上化解掉社會各個層面之間的時緊張時緩和的矛盾,使得中國一直未能把社會管理的水平和有效性提升到西方國家最近200年來的成功程度,反而從18世紀開始陷入了深重的災難。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自漢唐以降,儒家經典成為中國人的治國《圣經》以后,所有有志于治平的鴻鵠大才,莫不以孟子的天下己任精神自勵自詡,這樣的一種自信,構成了中國歷代朝廷的官僚體制機構的大無畏的主動施政的源動力。這是中國兩千年來中國大體維持穩定的重要基石。官員們施政時所依據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法規,更多的是他們依據儒家學說的經典言說再經過自己的理解和判斷所作出的決策。除了朱明王朝先期的過分掌控、后期的荒唐放縱以外,所有大的朝代(漢、唐、宋、清)的吏治都是可圈可點的,這是留給我們后人的中國政治歷史的正面經驗。我將這種主動施政的精神,稱為“大政府哲學”。然而,這樣的治國理念雖然能在一定時間段讓中國富庶,卻總也無法讓中國擺脫“治世——亂世”相互交替的周期性困擾。
民國初年,中國學者中的多數(除了梁濟、王國維)都一致拜倒在西方人發明的議會制度理論前,后來的歷史證明了梁濟和王國維的悲觀并非杞人之憂。上個世紀前半葉民國政府施政的挫折證明了,中國這樣的有著老大帝國底子的巨型國家直接實行西式民主是不妥當的。
世事滄桑,又一個甲子過去了,中國在經濟上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的巨大改變。但是實行權威政治的中國現在仍然堅持拒絕西方的民主政治,所依據的,我看還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天下觀,只不過執政者用的是另一套語言來進行解釋。我以為,就是因為中國人固執地堅持大政府的做法,才在經濟上獲得了令西方人歆羨的成果,究其原因,是中國人的治國倫理中蘊含著西方人政治倫理中應當有而恰恰欠缺的內容。中國人現實的成就越來越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冷靜的西方學者的注意。
英國《金融時報》2014年10月22日刊載了馬丁-雅克(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時》的作者)的文章“西方對中國經濟崛起的短視看法”,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國治理國家比西方更成功。”他認為,中國的成功是因為中國的政府模式使得施政者更能“戰略性地思考問題”。這不禁讓我想起一件發生在20多年前的事。
1988年1月,75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齊聚巴黎發表宣言:“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鄧啟銅:《中國傳統文化經典讀本·第一輯·論語》)
但是在1988年,當時的中國人沒有幾個會把這樣的一段話語當一回事的,這段話只在極少數的中國人之間傳遞,因為那時的中國正在被自身的社會問題所困擾。
那么那75位智者為什么會有這樣“怪異”的言論呢?
——因為他們比別人更早地看到了西方文明再進一步往前發展時必然會遇到的障礙,這就是所有現行的民主社會的社會管理機能的缺陷——政府理念的先天性不足——政府功能主動性的缺失,這個毛病在以往的時期里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未能充分暴露,或者沒有機會對社會的進步造成影響,但是從1990年代起這個缺陷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來。
引起大家普遍注意的先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大潮,襲擊了包括韓國在內的十幾個東南亞和東亞國家,后是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性的金融動蕩,緊接著一兩年后是歐洲金融危機,其實,還應當加上日本從1990年代初開始直到今天的長期經濟衰退,把這些一連串的事件打包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我有所發現,這一連串危機的內部都隱藏著讓這些國家發病的同一個病原體,是它使得那些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患上了這樣一種通病,——我給出的診斷是,它們都患上了“非獲得性政府機能缺失綜合癥”,這些“病夫”在風平浪靜的年代里不會有什么癥狀,而當一旦社會生活發生劇烈變化時,癥狀就會顯現出來。
首先說說我給出的病名。說它是“非獲得性”,是因為這是西方社會的政府從胚胎里就沒有生成那樣功能的基因,是先天的功能缺失,而不是受外界感染后而得的流行病,這個病癥的原由是西方人文化理念的某種不足造成的。
16世紀,西方人引進了中國人的文官政府管理方式,而后不斷加以制度創新,最后發展成由議會政治所主導和控制的“有限責任政府制度”。一直以來,西方人的政府形態一直如此,200多年來略無變化。這樣的一個制度創新讓西方人獲益匪淺,也對這樣一個制度的生命力和合法性引以為自豪,它也確實取得了世界范圍內的巨大成功,引領世界走進了現代社會的門檻。
但是時代在變遷,他們的政府所充當的一直是主持社會管理的“不完全角色”(除了特殊時期如世界大戰期間)在最近幾十年在經濟領域和社會治理領域都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煩,我是這樣分析其中的原因的。
那個政府是由一群“仆人”所演化而來的,干好了,再多干四年五年,干不好立馬卷鋪蓋走人。這樣的政府組成很像是一個臨時拼湊起來的打工者小集團,盡管他們是從社會精英中選拔出來的,但是“主人們”一直對他們懷有戒心,始終不愿意給以太大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權力。趕上太平年月,不遇到大風大浪,還算平安無事,一遇到“史無前例”的大事件,這個辦事的機構就會因為決策權力的限制變得無所措手足。例如,冷戰的終結,互聯網科技等一系列新技術新觀念的產生,
最近30年,中國人在頑固堅守“大政府政治”的同時又引入市場經濟法則,于是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引起了世界所有國家所有學人的關注。這是個不符合“慣例”的現象,不但西方人看不懂了,大多數信守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也一直不打算從心眼里接受這個怪異的現實。這30年中,人們或是從西方人的角度研究它,或是從中國的執政者的角度研究它,很少有人從更加超脫的視野客觀地對它的文化淵源與實踐效果兩方面綜合對它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已有的解釋只是用了一個新詞——“中國模式”來對它進行一個大略的概括,它生成的機制是什么,它內部的機理是什么,其實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論題。我以為,在共生研究院旗下集合起來的一群“好奇的思想者”現在所要做的工作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我很欣賞錢宏先生的如下主張:超越傳統觀念中“道不同不相與謀”的封閉狹隘的局限,提倡道不同亦相與謀。
從歷史上看,中國盛唐文化就是在中國儒家傳統與外來的佛教文化之后產生的。儒家與佛家,從思維方式和關注要點來看都是迥異的,但是它們之間的熔融卻在中國人后來的社會生活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彌補了中華文化關于人的生活意義方面的不足和盲點。而開啟人類文化輝煌一頁的文藝復興則是基督教新教倫理與古希臘美學哲學邏輯學相互雜交后才得以產生的。
從現實情況看,中國當代社會的管理模式雖然有效地維持了社會穩定,但是無論以西方人的眼光看還是考察中國人的切身體驗,社會中還充滿了許多不和諧之處。許多弊病就來自大政府哲學。西方社會文化上述社會問題,依照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恰恰缺少的就是中國人的“大政府”理念。我相信,如果這兩種不同的文化能夠相互交融,互相汲取、互相學習,那么一定會是的雙方都能在今后克服自己的困難,并創新出行的社會管理模式,以造福人類,造福千秋。
我相信,有關共生哲學的理論和實踐一定會引起越來越大的社會關注,并在今后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進程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西人科學不知道②
中國之道不科學
他日世界成一統
必是二者相提攜
謝謝大家。
注:①本文是作者在第三屆全球共生論壇會議上的講話稿。
②荀子曰:治之,要在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