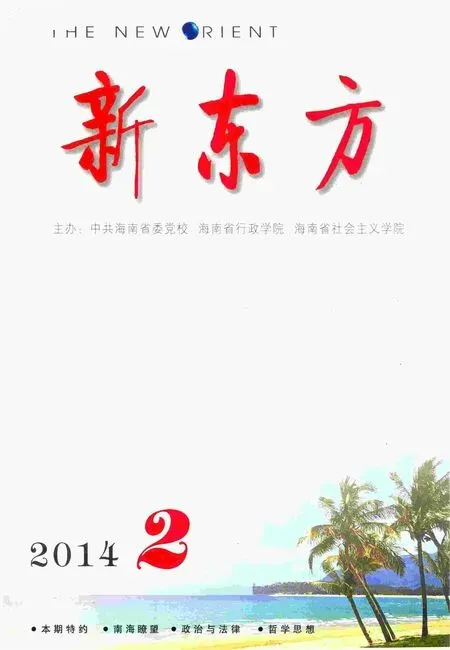淺談中國古典人文精神同現代性的摩擦和碰撞
李 原
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其人文精神在近現代受到西方文明的碰撞顯現其優勢與不足,如何能在這種碰撞之中充分發揮其固有優勢并充分認識和克服自身缺陷,從而完善東方人文精神的“創造性轉化”,是個值得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探討的問題。
一、現代性視角下看東西方人文主義文化的差異
中國古典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自然人性的人文主義,中國古典人文主義強調的是“文”對于“人”的教化影響,在邏輯形式上是修身—治國—平天下的主體人文修養,在人文主體同人文對象的主客體相互融合的基礎上,所呈現出的是一種“內圣外王”的人文理念。這種人文觀念在其發展歷程上經歷了由自給自足的建構,到近代中西人文背景的相互摩擦,而被視作以西方自然人性的人文主義為參照的“遠東的人文主義”,在此之后又有梁啟超等人以新康德主義文化價值派的人文科學觀念,對東方文化的人文主義的張揚,和“五四”時期胡適依照自由主義個人本位的“人文主義”的視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在這種中西文化的比較之中,可以把中國人文主義判斷為教化自然人欲的“人文”教化主義。這種教化人文主義由于身處“反封建的現代化與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兩個不同目標解構相關”環境[1],因而其內在現代性矛盾顯得“尖銳而復雜”,反映出了中國文化自身的矛盾。因此,在這種前提下以中國現代人文主義對以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現代性批判,在全球化時代往往轉化為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批判。然而這種批判忽略了中西方所共有的古代社會及文化形式,因而這種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批判比較就轉化為“古代”與“現代”的比較,由此陷入一種封閉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之中,因而“具有執迷與蒙蔽的特點”。“前現代傳統的人文主義傾向只有在與現代唯科學主義相抗衡的現代性矛盾格局中,才有從其現代眼光看來明晰確定的人文主義”[1]。
現代性是“由現代化而形成的文化心里及其結構,是關于現代人的自身屬性”[2]。對于西方人來說,現代化的發展和形成過程中無論其社會面貌還是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而其文化心理及結構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也包含著某些東方社會所不具備的因素。西方社會,在現代化的發展建設的同時還保持著同古代社會文化的連續性,是在保守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形成的對立統一中進行的,它經歷了現代化過程發展所呈現出的每一個歷程,這與多數東方社會從長久處于古老封建制度下的社會形態在外來文明的沖擊下造成的突飛猛進的現代化發展形式是不盡相同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東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對傳統和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沖擊也更為突然和猛烈,并且因為具有被迫接受的性質而缺乏自主性,因而其現代性存在著某種結構上的斷帶,這樣的差異導致東西人文主義在對現代性的理解視域的不同,無論是出于自身所面臨的,還是對于對方的分析性觀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這樣的差異在東方還因為被迫和缺乏獨立性而造成其人文主義思想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下缺乏自信心,反而更加強烈地表現出一種狹隘并自大的民族主義特質,使得東西方人文主義在文化對比上存在著自我封閉的傾向,并在以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進行批判的時候缺乏獨立的社會學與人類學意義上的建構性根據。基于中國古典人文精神具有人文教化的特質,而“教化”作為一種具有人文方法論意義的實踐方式,出于其自身特質和要求同樣表現出某種特異性,這種特異性體現在吸納西方人理想主義和具有集體主義性質的理想主義的采納上。因此,要從現代性視角對中國古典人文精神進行觀察分析,首先需立足于中國現代性的特質,從人文理想與人文方法的角度出發,對教化、理想主義等概念進行分析。
二、對中國古典人文精神中人文教化特質的分析
中國古典人文精神具有人文教化的特質,教化作為一種人文形式主要通過指導、傳授和運用環境影響、教育感化和民俗風化等方式,感化人的心靈,并對其行為和處事態度產生修正性質的改變。這里面包含三個方面的因素,即教化過程當中受教化的對象,教化形式的本體性參照(教條)和教化實踐者(施教主體)。在中國主流傳統意識形態當中,這三方面的因素分別是人民群眾、“禮”和由君子、圣賢構成的精英道德團體。教化作為一種手段,出于其本質屬性對于這三個方面是有要求的。首先,它斷定受教對象在行為上不能夠很好地符合教條,在品性上是蒙昧弱勢的,因而需要被感化和引領;其次,要求教條本身是卓越的和絕對的,因而施教主體對于受教者在價值的詮釋學意義上擁有全權代理權;最后,需要有一個有道的資深人士(內圣外王)組成的精英群體作為楷模對整個社會進行引導并實施治理。可以認為,教化形式要求精英群體即道德楷模因為其知識結構內本體性教條的絕對性和優越性而對于受教主體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因而具有管理和規范他人行為思想的資格和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社會具有“人治”的特性,并且在政治文化結構上是精英本位的,帶有集體主義的性質。由此形成的民族心理結構和文化氣質基于傳統情感所形成的性格,也與之相一致。因此,以梁漱溟等思想家為代表的新儒家出于現代性危機在對西方文化進行批判的時候,在意識上就具有了這種東方文化優越性的特征,卻由于沒有注意到這種優越性乃是依照自身文化背景而在邏輯上作出的假設性斷言,而缺乏對于這種優越性本身更為深入的沉思。這種假設由于缺乏具備近現代科學性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建構,因而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下往往陷入一種剛愎自用的態勢,在這種態勢之下,對于西方人文理想和人文精神的詮釋上甚至存在著某種曲解和負面意義的采納和運用。
三、立足于現代性的特質對中國人文精神中理想主義概念的分析
人文理想作為一種具有超越性質和終極意義的人類理想,不談普世價值與意義!它超越于差異性之上,是比文化多元主義的人文理念更為本源的,其形式是理想主義的,并帶有集體主義的色彩,它的終極要求是科學公正,要求每一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全面發展的機會。這當中包含一個前提,即人文理想是基于人文科學的,而人文科學作為科學具有科學性。海德格爾在《黑格爾的經驗概念》一文中對于知識成為一種科學做了深入的分析,認為科學達到其絕對性是通過“對認識的無條件的自我認識”而得以實現的,即科學出于自身的要求而不斷地對自身進行反思和修正,以使得自身不斷地接近絕對,甚至于最終發展為同初始狀態全然不同的面貌,甚至于相對立。海德格爾借黑格爾原話稱這個過程為“陳述”。因此,“作為絕對認識的哲學(知識)之所以是科學,絕對不是它力求使它的方法精確化,使它的結果具有強制性”“科學絕對不會以斷言的方式把自己展現出來,并因此完全把它自己確立起來,……也不可能一下就達到絕對認識”[1]。也就是說,現代意義的知識出于其科學性的自我要求,是因為“陳述”體現出絕對性的(而不是在一開始斷言絕對)。知識具有科學性,意味著對于當下的超越。因此,這里的絕對并不是靜態且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動態的變化的不斷自我擴充、自我完善之中的,運動與變化乃是絕對之絕對性。由此可見,人文科學作為一種科學,其理想絕對不是停滯的、形式固定的“教條”,其理想形式之所以是理想主義的,恰恰是因為這是一種出于不斷自我擴充之中的終極理念。因此,教化作為一種人文手段在整個人文理想的某一具體環節之中能夠發揮建設性意義,但這并不意味著某種獨斷的教條就是歷史性的和絕對的。正因如此,中國古典人文精神,尤其是以儒家意識作為主流影響下產生的文化心理及其解構,在與西方文化進行碰撞的過程中試圖以古代文化形式超越現代性,帶有對人文終極理念在解讀上的片面化和歪曲,這尤其體現在將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兩種對立形式的解讀上。如前所述,人文教化主義出于其自身特質同樣是帶有集體主義色彩的,但這種集體主義色彩基于東方文化在現代性上所出現的斷帶效應而缺乏發展的環節和內容,因而是古老而樸實的,但也同樣是蒙昧和原始的。它和人文理想下的帶有終極性的集體主義色彩不可同日而語。在東西文化的碰撞下,中國古典人文主義把對現代性的批判首先轉變為東方文化對于西方文化的批判,進而化作古代文明對近現代文明的批判,顯然不僅對新康德主義存在著扭曲運用,對于集體主義和理想主義的解讀和運用同樣存在著偏差。況且,我們知道源自于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想主義自身也是帶有缺陷的,這種缺陷在海德格爾看來就是過分依賴知識的可靠性。因此,源自于文藝復興的理想主義,不可避免地也帶有著這種對個體的消解和遮蔽。盡管這種理想主義出于一種集體主義功利價值觀而承認個體的權利,但因為過分相信知識的可靠性忽略了個體的自發性,由此造成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立和社會主義同自由主義的對立。盡管自由主義下的個人主義具有無限和慫恿放大自然人欲,以及滋生利己主義的危險,但其強調個體自發性的意義和自發機制的發展模式,以及強調“知識的可靠性”在認識論意義上本身具有片面性,也有其合理的成份。這一點與人文性的終極理想對于人的發展的肯定并不相沖突。在中國“教化”人文主義受民族主義的支持下進行的對于集體主義的解讀,顯然是站在教化模式自身集體主義性質的原始視域下對人文主義終極理想進行理解的,這不僅造成了對一些意義的曲解,還放大了本身源自于西方的理想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負面因素,從而為社會帶來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人文精神本身出于理想而對個體自由、自覺、自發的承認,在這里被遮蔽得毫無蹤影,以至于出現一種絕對化的“集體大于個人”的話語模式。比如,假設問愛迪生為什么要發明電燈泡,出于自然和自發的角度,顯然是出于一種個人興趣愛好和對自身理想的追求,但在集體主義話語模式之下,就有可能轉變為“為了我的人民都能夠享受到電氣照明”,或者是“為了人類的科學事業發展”。這些回答盡管都符合邏輯,符合理想性,卻缺乏個體的自我決斷性,忽略了人們能夠產生“享受電氣照明”的概念。恰恰是因為先有人自發地產生這方面的興趣并進行科學實踐,進而發明了電燈泡,而不是為了發明電燈泡,或者因為燈具有世俗的利用價值而發明了電燈泡,更不是因為受圣人語錄教化而進行科學實踐。盡管效用價值的評價機制有利于作為一種外在誘因刺激促進人類創造性活動,但這取代不了人的自發性和出于自愿而進行的活動。在這里,人的探索欲作為深層次的誘因要比依照文化背景所制定出的理想更為本源。同樣的,集體的權利也不能取代個人的權利,相反,集體的設立是為了更充分地保障個人享有應得的權利。日本軍國主義基于文化傳統通過文化習慣設立一個被認為是崇高的使命和目標(如為天皇犧牲自我),就可以因為這種崇高的使命去剝奪每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往往以一些抽象的集體主義概念為理由,一些人就可以剝奪他人的尊嚴權利,而不把這些權利看作是每一個人所固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而這種民族心理結構,不能不說是長期受到教化的影響所導致的,這些行為意識是違背科學的。
海德格爾將科學的對立面稱作“自然的意識”,海德格爾提出這類意識的用意在于批判笛卡爾現代性危機。而筆者認為,我們的傳統文化意識當中同樣帶有“自然的意識”色彩。當然,如今我們不能站在現代理論的高度上對以往提出要求和進行指責,但同樣不應該因為現代性危機就退回古代,然后反過來在思想體系尚缺乏獨立完善的發展歷程的情況下,就不加反思地借鑒古代來反對現代性。這樣做不僅無法解決現代性危機,反而將唯科學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因素變本加厲地放大出來,以至于總是宣揚終極卻從來不在創造性實踐上下功夫,總是以終極的圣人觀來對世俗生活做終極價值評判,處于一種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生活態度中而錯過了對當下生存意義的捕捉和把握,甚至因為“理想”而失去了一顆平常心,丟掉了創造力。
因此,只有從人文科學的立場出發,借鑒現代性闡釋學背景,以一種科學的態度對我們的傳統進行解讀和建構,就像李澤厚先生所說的,進行一種“創造性轉化”[3],才能真正發揮出傳統智慧的真諦,也才能使這種建構和發展本身上升成為一種人文科學,從而為人類發展做出歷史性的貢獻。
[1]尤西林.人文科學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海德格爾.林中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3]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M].北京:三聯書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