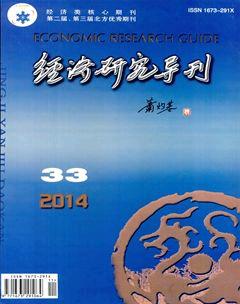基于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的視角: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化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
韋統(tǒng)義++宋胤
摘 要: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是以屯墾戍邊為基本職能的黨政軍企合一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組織。兵團(tuán)發(fā)展的歷史就是兵團(tuán)工業(yè)化發(fā)展的歷史,就是探索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chǔ),工業(yè)為農(nóng)業(yè)服務(wù),農(nóng)業(yè)工業(yè)化的發(fā)展歷史。這是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自立的需要,也是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經(jīng)濟(jì)積累的需要。回顧兵團(tuán)從成立到當(dāng)前大力發(fā)展新型工業(yè)化三個(gè)階段的歷史和經(jīng)驗(yàn),對(duì)于兵團(tuán)和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推進(jìn)新型工業(yè)化建設(shè)、實(shí)現(xiàn)二次創(chuàng)業(yè)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guān)鍵詞: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發(fā)展歷程;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
中圖分類號(hào):F320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673-291X(2014)33-0059-03
引論
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以下簡(jiǎn)稱兵團(tuán))是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家借鑒中國(guó)古代西域屯田的歷史經(jīng)驗(yàn),結(jié)合建國(guó)初期新疆特殊的省情、民情,為實(shí)現(xiàn)屯墾戍邊的基本職能而進(jìn)行的組織制度創(chuàng)新。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是兵團(tuán)兵、師、團(tuán)三級(jí)組織的基本生產(chǎn)單位和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成插花狀地分布于新疆各大綠洲和邊境地區(qū),忠實(shí)地履行著黨和國(guó)家賦予的屯墾戍邊的歷史職責(zé)。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黨政軍企合一的組織體制、“飛地”的區(qū)位因素和自我積累的發(fā)展路徑,是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大力發(fā)展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的必然選擇[1]。這既是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在亙古荒原開荒拓土自立的需要,也是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實(shí)現(xiàn)農(nóng)產(chǎn)品的轉(zhuǎn)化和獲得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積累的需要。這一實(shí)踐有力地支持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發(fā)展。
進(jìn)入新世紀(jì),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雖然相比較兵團(tuán)創(chuàng)立初期已獲得了巨大的發(fā)展,但當(dāng)前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又一次面臨著新的“自立”的挑戰(zhàn)。從兵團(tuán)范圍來看,突出的體現(xiàn)為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畸高資產(chǎn)負(fù)債率,目前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平均資產(chǎn)負(fù)債率達(dá)到了2008年的91.7%,部分團(tuán)場(chǎng)負(fù)債率超過100%,已經(jīng)資不抵債[2];從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層次來看,部分團(tuán)場(chǎng)長(zhǎng)期虧損以及團(tuán)場(chǎng)虧損面長(zhǎng)期居高不下。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如何走出困局,這不僅關(guān)系到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是否可持續(xù)發(fā)展,更關(guān)系到屯墾戍邊事業(yè)是否可持續(xù)以及基于其上的中國(guó)西部邊疆的國(guó)家戰(zhàn)略安全是否可持續(xù)?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企業(yè)的組織屬性和公共財(cái)政的缺位,決定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只能以自身的經(jīng)濟(jì)剩余來化解這些財(cái)務(wù)風(fēng)險(xiǎn),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現(xiàn)實(shí)的財(cái)務(wù)壓力以及初級(jí)農(nóng)產(chǎn)品比較利益的下降,對(duì)于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來說僅僅具有原料優(yōu)勢(shì)并不能有效克服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長(zhǎng)期發(fā)展的困境,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的根本出路在于按照市場(chǎng)化原則,大力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工業(yè)化和農(nóng)產(chǎn)品的深加工,延伸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的產(chǎn)業(yè)鏈和價(jià)值鏈獲取較高的比較利益。大力發(fā)展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對(duì)于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來說已成為新一次“自立”的需要。總結(jié)兵團(tuán)及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過往工業(yè)化的歷史實(shí)踐,對(duì)于推進(jì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新型工業(yè)化,實(shí)現(xiàn)二次創(chuàng)業(yè)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意義。
一、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發(fā)展的歷程
第一階段(1954—1966年):兵團(tuán)工業(yè)大發(fā)展時(shí)期。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成立時(shí),按照當(dāng)時(shí)領(lǐng)導(dǎo)人的設(shè)想應(yīng)該是工農(nóng)兵學(xué)商統(tǒng)一聯(lián)合的組織。在實(shí)踐中,兵團(tuán) 也在一定的層面踐行了當(dāng)時(shí)領(lǐng)導(dǎo)人的設(shè)想。早在兵團(tuán)成立之前的1950年開始,當(dāng)時(shí)進(jìn)軍新疆的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就通過內(nèi)部的指戰(zhàn)員集資和節(jié)省下來的菜金、復(fù)員費(fèi)以及軍裝被服費(fèi)用興辦工業(yè),及至兵團(tuán)建立后進(jìn)一步通過生產(chǎn)積累和生活節(jié)約大規(guī)模地進(jìn)行工業(yè)化建設(shè)。先后興建了在新疆具有時(shí)代標(biāo)志的一系列工業(yè)項(xiàng)目,如八一鋼鐵廠、新疆水泥廠、六道灣露天煤礦、新疆機(jī)械廠等。兵團(tuán)工業(yè)化建設(shè)不僅迅速地壯大了兵團(tuán)的經(jīng)濟(jì),也有力地推動(dòng)了新疆地方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和進(jìn)步,這些項(xiàng)目在后來無償劃歸地方后,構(gòu)成了新疆地方工業(yè)發(fā)展的骨架。應(yīng)該說兵團(tuán)層次的工業(yè)化建設(shè),是服務(wù)于整個(gè)新疆工業(yè)化發(fā)展需要的,而且也推動(dòng)了新疆工業(yè)化的發(fā)展進(jìn)程。兵團(tuán)在兵團(tuán)層次進(jìn)行工業(yè)化建設(shè)的同時(shí)也在師、團(tuán)層次進(jìn)行了小型工業(yè)項(xiàng)目的建設(shè),以滿足各墾區(qū)和團(tuán)場(chǎng)生產(chǎn)、生活的需要,建設(shè)了一大批磨面、榨油、小型發(fā)電、被服、磚瓦等生產(chǎn)單位。這些具有自給屬性生產(chǎn)的工業(yè)項(xiàng)目,堅(jiān)持了為農(nóng)業(yè)服務(wù),走以農(nóng)業(yè)為中心的工業(yè)發(fā)展道路。這是兵團(tuán)成立的組織初衷和兵團(tuán)早期工業(yè)發(fā)展所堅(jiān)持的基本方針,集中體現(xiàn)為自立的需要。對(duì)此,時(shí)任兵團(tuán)司令員的陶峙岳強(qiáng)調(diào)“工業(yè)生產(chǎn),都要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chǔ)。我們工業(yè)的發(fā)展,必須面向農(nóng)業(yè),為農(nóng)業(yè)服務(wù),把支援農(nóng)業(yè)放在第一位。工業(yè)的發(fā)展,必須建立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逐步擴(kuò)大、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逐步提高的基礎(chǔ)上”[3]。這些項(xiàng)目從建設(shè)的導(dǎo)向來看,是為農(nóng)業(yè)服務(wù)而不是作為帶動(dòng)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農(nóng)產(chǎn)品深加工龍頭出現(xiàn)的,并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加工企業(yè)龍頭。因而,從本質(zhì)意義上說,這些企業(yè)并不是以商品化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yíng)為目的,它只是整個(gè)團(tuán)場(chǎng)生產(chǎn)車間中的工具車間和消費(fèi)資料車間,它也必然會(huì)在整個(gè)兵團(tuán)范圍內(nèi)呈現(xiàn)結(jié)構(gòu)趨同、產(chǎn)品趨同和規(guī)模狹小的特征。
第二階段(1966—1981年):兵團(tuán)工業(yè)處于停滯增長(zhǎng)時(shí)期。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以及兵團(tuán)大中型工業(yè)項(xiàng)目劃歸地方,兵團(tuán)層次的大中型重化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量迅速減少,保留的基本是以輕紡、造紙和制糖等以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為主的輕工業(yè)企業(yè),兵團(tuán)工業(yè)生產(chǎn)迅速下滑,兵團(tuán)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遭遇嚴(yán)重的困難。此時(shí),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的小型工業(yè)項(xiàng)目在這一時(shí)期雖然得以保留,但在整個(gè)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秩序紊亂的背景下也沒有得到更好的發(fā)展,期間為了解決兵團(tuán)長(zhǎng)期存在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單一、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脫節(jié)、二三產(chǎn)業(yè)發(fā)展滯后、經(jīng)濟(jì)效益不高、農(nóng)工收入增加緩慢等問題,根據(jù)國(guó)務(wù)院和農(nóng)業(yè)部的安排,借鑒前歐洲、南斯拉夫等國(guó)農(nóng)工商聯(lián)合體發(fā)展經(jīng)驗(yàn);在全兵團(tuán)進(jìn)行農(nóng)工商綜合經(jīng)營(yíng)試點(diǎn)和全面推廣,在一定程度上推動(dòng)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農(nóng)、工、商、交、建等行業(yè)企業(yè)的發(fā)展[4]。
第三階段(1981年至今):兵團(tuán)工業(yè)處于迅速恢復(fù)和大發(fā)展的時(shí)期。這一階段實(shí)際上可分為兵團(tuán)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大發(fā)展時(shí)期和新型工業(yè)化發(fā)展時(shí)期,以黨的十六大為分界。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和兵團(tuán)的回復(fù)為兵團(tuán)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新的歷史機(jī)遇,也帶來了兵團(tuán)工業(yè)化發(fā)展的新高潮。從兵團(tuán)層次上看,兵團(tuán)工業(yè)化的發(fā)展有力提升 了兵團(tuán)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總量,優(yōu)化了兵團(tuán)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機(jī)構(gòu),使兵團(tuán)工業(yè)生產(chǎn)總值從1985年的5.80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148.70億元,三次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由1982年的44.6∶38.2∶16.2調(diào)整為2009年33.5∶33.8∶32.7。同期,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的工業(yè)發(fā)展經(jīng)過了兩個(gè)顯著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分別是以發(fā)展團(tuán)場(chǎng)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新型工業(yè)化團(tuán)場(chǎng)為目標(biāo)的階段。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全國(guó)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熱潮,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也大量舉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使團(tuán)場(chǎng)經(jīng)濟(jì)得到了比較快速的發(fā)展。到1992年底,全兵團(tuán)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總產(chǎn)值由1988年的8 998.6萬元增加到1992年的38 847.6萬元,年平均遞增44%;其中工業(yè)產(chǎn)值由4 522萬元增加到25 885.6萬元,年平均遞增54.7%;1992年全兵團(tuán)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已發(fā)展到1.4萬個(gè),從業(yè)人數(shù)3.3萬人,實(shí)現(xiàn)利潤(rùn)3 552.3萬元,上交國(guó)家稅金1 080.7萬元[5]。由于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出資額的很大一部分來自團(tuán)場(chǎng)以及企業(yè)定位不夠準(zhǔn)確、經(jīng)營(yíng)管理水平不高、資產(chǎn)擴(kuò)張速度過快和產(chǎn)權(quán)不夠明晰等原因,團(tuán)場(chǎng)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九十年代后期遇到了較大的發(fā)展困難,導(dǎo)致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負(fù)債水平迅速提高和財(cái)務(wù)壓力驟增。如農(nóng)六師102團(tuán)高峰時(shí)期有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幾十家,年盈利額在千萬元以上,但由于上述原因,從1993年兵團(tuán)農(nóng)六師102團(tuán)資產(chǎn)負(fù)債率達(dá)到87.5%,當(dāng)年虧損246萬元,1996年資產(chǎn)負(fù)債率87%,虧損進(jìn)一步擴(kuò)大到450萬元,此后若干年基本連續(xù)虧損,2008年虧損更是達(dá)到了2 321萬元[6]。從整體上看兵團(tuán)的負(fù)債率也從1980年的23.63[7~8]。黨的十六大以后,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貫徹國(guó)家和兵團(tuán)上級(jí)機(jī)關(guān)大力發(fā)展新型工業(yè)化的指示,大力推進(jìn)新型工業(yè)化團(tuán)場(chǎng)建設(shè),這期間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的工業(yè)化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和發(fā)展,涌現(xiàn)了一批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量較多,實(shí)力較強(qiáng)和營(yíng)業(yè)規(guī)模較大的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如農(nóng)八師石河子總場(chǎng)、121團(tuán)、143團(tuán)、152團(tuán),農(nóng)七師130團(tuán),農(nóng)十師184團(tuán),農(nóng)二師22團(tuán)以及農(nóng)六師芳草湖等團(tuán)場(chǎng)。endprint
二、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化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
新型工業(yè)化是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長(zhǎng)期以農(nóng)為主,工業(yè)服務(wù)農(nóng)業(yè),初級(jí)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逐步走低的趨勢(shì)下,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財(cái)務(wù)壓力和債務(wù)水平逐步增高的背景下,以及中國(gu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領(lǐng)域逐步向集中化、集團(tuán)化和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方向發(fā)展的新形勢(shì)下做出的歷史選擇。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過往的工業(yè)化實(shí)踐表明以農(nóng)帶工、以支農(nóng)、扶農(nóng)為中心的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并不是市場(chǎng)化和產(chǎn)業(yè)化的農(nóng)業(yè),也沒有真正延伸農(nóng)業(yè)的產(chǎn)業(yè)鏈和獲得農(nóng)產(chǎn)品附加值。因而,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新型工業(yè)化必須要以市場(chǎng)為導(dǎo)向,開展深入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經(jīng)營(yíng),獲取農(nóng)產(chǎn)品附加利益。總結(jié)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化的過往經(jīng)驗(yàn)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價(jià)值。
第一,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深化不足,產(chǎn)業(yè)帶動(dòng)能力不強(qiáng)。兵團(tuán)成立之初,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風(fēng)頭水尾遠(yuǎn)離中心城市且呈插花狀的地域分布,決定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要以農(nóng)業(yè)為中心,以實(shí)現(xiàn)生產(chǎn)自給為基礎(chǔ)。按照當(dāng)時(shí)領(lǐng)導(dǎo)人的設(shè)想,就是兵團(tuán)建立工農(nóng)兵學(xué)商聯(lián)合的組織,實(shí)現(xiàn)自立。因而,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基本堅(jiān)持了以農(nóng)業(yè)為中心,以服務(wù)農(nóng)業(yè)為主旨的方針,具有較強(qiáng)的自給性和自我服務(wù)性質(zhì)。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規(guī)模小、技術(shù)水平低、結(jié)構(gòu)趨同、產(chǎn)品檔次低是當(dāng)時(shí)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的共同特征。這一時(shí)期,在農(nóng)業(yè)實(shí)現(xiàn)較快發(fā)展的同時(shí),工業(yè)雖然也得到了較大的發(fā)展,但這種以內(nèi)向服務(wù)為導(dǎo)向的發(fā)展目標(biāo)以及團(tuán)場(chǎng)的區(qū)位因素,還是會(huì)從根本上限制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發(fā)展的空間和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的服務(wù)對(duì)象,導(dǎo)致一、二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不均衡,工業(yè)帶動(dòng)能力不強(qiáng),兵團(tuán)農(nóng)業(yè)資源優(yōu)勢(shì)沒有得到更好的體現(xiàn)和發(fā)揮。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后,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商品性和市場(chǎng)化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兵團(tuán)成為中國(guó)最為重要的商品棉、糖、糧、油的基地之一,但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并沒有依靠這些優(yōu)勢(shì)得到很快的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jì),從1998—2006年,兵團(tuán)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業(yè)產(chǎn)值從55.11億元增加到97.86億元,增長(zhǎng)了77.6%,但同期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業(yè)產(chǎn)值占兵團(tuán)工業(yè)產(chǎn)值的比例卻由62%降到45.3%,2008年兵團(tuán)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比率僅為0.36∶1[2]。這遠(yuǎn)低于中國(guó)內(nèi)地農(nóng)業(yè)發(fā)達(dá)地區(qū)和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水平,這也體現(xiàn)了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水平不高,帶動(dòng)能力不強(qiáng)。
第二,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發(fā)展體制環(huán)境不佳。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公共財(cái)政缺失導(dǎo)致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的空心化和“工占農(nóng)利”的制度設(shè)計(jì),影響了其他經(jīng)濟(jì)形式在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布局,弱化了企業(yè)間的競(jìng)爭(zhēng),阻礙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化的發(fā)展水平和進(jìn)度。兵團(tuán)目前除石河子、五家渠、阿拉爾和圖木舒克等兵團(tuán)單位因采用師市合一體制,其所轄單位部分擁有公共財(cái)政外,其他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并沒有建立公共財(cái)政。即使這四個(gè)城市有公共財(cái)政也僅限制在師市管轄范圍內(nèi),并不能覆蓋整個(gè)墾區(qū)。為了確保稅收不致流失,兵師兩級(jí)組織都是盡可能地把團(tuán)場(chǎng)招商引資的大項(xiàng)目、帶動(dòng)力強(qiáng)的項(xiàng)目安排到師市轄區(qū)內(nèi),影響到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招商引資的力度和積極性,一些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處于無項(xiàng)目、無投資的空心化狀況。這也是當(dāng)前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農(nóng)業(yè)增加值在三次產(chǎn)業(yè)構(gòu)成中比重超過50%的農(nóng)牧團(tuán)場(chǎng)占全部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總數(shù)的79.4%,個(gè)別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最高達(dá)87%(農(nóng)二師34團(tuán))的重要原因(《兵團(tuán)統(tǒng)計(jì)年鑒》2010)。農(nóng)業(yè)比較利益的低下、沉重的社會(huì)成本和財(cái)務(wù)壓力嚴(yán)重影響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的持續(xù)經(jīng)營(yíng),為緩解這種經(jīng)營(yíng)困境在兵團(tuán)的許多植棉團(tuán)場(chǎng)以及其他團(tuán)場(chǎng)紛紛建設(shè)團(tuán)辦軋花廠及相類似的初級(jí)加工企業(yè),強(qiáng)行要求農(nóng)工繳售農(nóng)產(chǎn)品給團(tuán)辦企業(yè),不僅繳售價(jià)格低,而且壓級(jí)壓價(jià)現(xiàn)象普遍,嚴(yán)重影響了農(nóng)工土地承包產(chǎn)權(quán)的完整和經(jīng)濟(jì)利益的實(shí)現(xiàn)。這些類似“特許經(jīng)營(yíng)”的企業(yè)由于規(guī)模小、技術(shù)水平低以及加工數(shù)量不足,只能季節(jié)性地開工,導(dǎo)致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成本高企、競(jìng)爭(zhēng)能力低下,難以在激烈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中立足。這些原本為“工占農(nóng)利”而建立的企業(yè)不僅沒有起到壯大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效果,反而進(jìn)一步惡化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的資產(chǎn)狀況和經(jīng)營(yíng)狀況。據(jù)筆者調(diào)查,在前些年的棉花種植高峰期,兵團(tuán)農(nóng)六師所屬團(tuán)場(chǎng)中幾乎所有植棉團(tuán)場(chǎng)都建有自己的軋花廠,隨著該師近兩年種植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植棉面積的下降以及兩費(fèi)自理的推進(jìn),許多軋花廠吃不飽,開機(jī)時(shí)間越來越短,經(jīng)營(yíng)狀況日趨惡化,個(gè)別團(tuán)場(chǎng)的軋花廠已經(jīng)停工歇業(yè)。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空心化和遍地“軋花廠”這一看似矛盾的現(xiàn)實(shí),從本質(zhì)上說是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事權(quán)范圍廣泛和公共財(cái)政缺位這一內(nèi)在矛盾的兩種不同外在表現(xiàn),它們具有獲取經(jīng)濟(jì)利益的共同出發(fā)點(diǎn),但卻導(dǎo)致了團(tuán)場(chǎng)經(jīng)濟(jì)行為的扭曲和產(chǎn)業(yè)空間分布的惡化,影響了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發(fā)展的環(huán)境和水平。
第三,投資主體單一。兵團(tuán)和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投資的主體單一,主要是兵團(tuán)和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而且又以國(guó)有經(jīng)濟(jì)為主要實(shí)現(xiàn)形式,這種格局基本保持到了20世紀(jì)90年代。兵團(tuán)工業(yè)投資主體的單一性,從兵團(tuán)成立時(shí)就已有所體現(xiàn),而到了大躍進(jìn)時(shí)期,這種主體結(jié)構(gòu)達(dá)到了極致。大躍進(jìn)中,兵團(tuán)工業(yè)建設(shè)資金基本上都是自籌的,三年中用于基本建設(shè)的投資6.0292億元,其中國(guó)家投資只占14.8%,其余85.2%[9]都是由兵團(tuán)自籌,自籌資金為5.1374億元;1961年兵團(tuán)基建投資又近2億元,國(guó)家撥款卻只有75萬元。90年代后,隨著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國(guó)家開放政策的深化,兵團(tuán)工業(yè)投資來源出現(xiàn)了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shì),外資、民營(yíng)資本在兵團(tuán)工業(yè)的投資力度開始加大,企業(yè)資產(chǎn)和經(jīng)營(yíng)規(guī)模都有了比較大的發(fā)展。但回顧兵團(tuán)工業(yè)發(fā)展的歷史,兵團(tuán)和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仍然是兵團(tuán)工業(yè)的最主要的投資主體(2009年國(guó)有經(jīng)濟(jì)在兵團(tuán)社會(huì)固定資產(chǎn)投資的比重仍高達(dá)64.1%),國(guó)有和國(guó)有控股企業(yè)仍然是兵團(tuán)工業(yè)總量中最為重要的一塊。從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以來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實(shí)踐和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發(fā)展實(shí)踐來看,兵團(tuán)工業(yè)投資主體多元化和資金來源多元化都有待進(jìn)一步提高,總結(jié)限制和制約兵團(tuán)工業(yè)投資主體多元化的內(nèi)外在因素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四,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城鎮(zhèn)化水平較低,城鎮(zhèn)化和工業(yè)化互促機(jī)制沒有形成,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發(fā)展缺乏良好的區(qū)位環(huán)境。從發(fā)達(dá)國(guó)家和中國(guó)城鎮(zhèn)化的實(shí)踐來看,城鎮(zhèn)化總是伴隨著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不斷升級(jí)而實(shí)現(xiàn)的,城鎮(zhèn)化和工業(yè)化具有互促的作用。目前,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城鎮(zhèn)化發(fā)展水平較低既是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工商業(yè)發(fā)展水平較低的現(xiàn)實(shí)反映,也凸顯了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城鎮(zhèn)化和工業(yè)化互促作用的不足。農(nóng)業(yè)是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的基礎(chǔ)和主導(dǎo)產(chǎn)業(yè),也是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最具比較優(yōu)勢(shì)的產(chǎn)業(yè),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現(xiàn)代化水平、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水平、土地產(chǎn)出率的水平和商品化率水平都居全國(guó)前列,棉、油等農(nóng)產(chǎn)品的人均產(chǎn)量和商品率甚至在全國(guó)獨(dú)占鰲頭。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如何實(shí)現(xiàn)從資源比較優(yōu)勢(shì)到產(chǎn)業(yè)比較優(yōu)勢(shì)的升華,其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發(fā)展就是關(guān)鍵的促媒介質(zhì)。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風(fēng)頭水尾的區(qū)位劣勢(shì)以及公共財(cái)政的缺乏導(dǎo)致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在招商引資方面具有先天的自然、稅收環(huán)境和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不足的劣勢(shì),而“工占農(nóng)利”限制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料和農(nóng)產(chǎn)品自由交易的制度設(shè)計(jì)又進(jìn)一步影響了團(tuán)場(chǎng)工商業(yè)的活躍和發(fā)展。因而,團(tuán)場(chǎng)工商業(yè)要發(fā)展首先要進(jìn)行政策和體制松綁,大力推動(dòng)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的發(fā)展,促進(jìn)農(nóng)資交流和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的順暢,以活躍的市場(chǎng)形成產(chǎn)業(yè)升級(jí)和深化的動(dòng)力,以產(chǎn)業(yè)驅(qū)動(dòng)帶動(dòng)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進(jìn)一步形成產(chǎn)業(yè)的集聚和分工,提高團(tuán)場(chǎng)工業(yè)投資密度,達(dá)到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的互促。
參考文獻(xiàn):
[1] 韋統(tǒng)義.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農(nóng)墾團(tuán)場(chǎng)社會(huì)成本分析[J].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社版),2012,(3):64-68.
[2] 劉以雷,孫法臣,孫鵬.新形勢(shì)下新疆兵團(tuán)經(jīng)濟(jì)改革發(fā)展大思路[M].北京:社科文獻(xiàn)出版社,2010:41-56.
[3] 兵團(tuán)工業(yè)史資料匯編(內(nèi)部資料)第2輯[Z].1985:153.
[4] 金勇鋼.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實(shí)踐與探索[J].新疆農(nóng)墾經(jīng)濟(jì),2008,(2):16.
[5] 胡兆璋.全國(guó)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蓬勃發(fā)展兵團(tuán)怎么辦?[J].新疆農(nóng)墾經(jīng)濟(jì),1994,(1):2.
[6] 根據(jù)《兵團(tuán)統(tǒng)計(jì)年鑒》1994年、1997年、2009年數(shù)據(jù)計(jì)算得出.
[7] 楊景江,楊虹.試論企業(yè)負(fù)債經(jīng)營(yíng)的量度[J].新疆農(nóng)墾經(jīng)濟(jì),1994,(4):61.
[8] 馬松利,茍玉玲.農(nóng)牧團(tuán)場(chǎng)高負(fù)債率成因及對(duì)策[J].中國(guó)農(nóng)墾經(jīng)濟(jì),2000,(7):28.
[9] 李福生.新疆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簡(jiǎn)史[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43-145.
[責(zé)任編輯 陳丹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