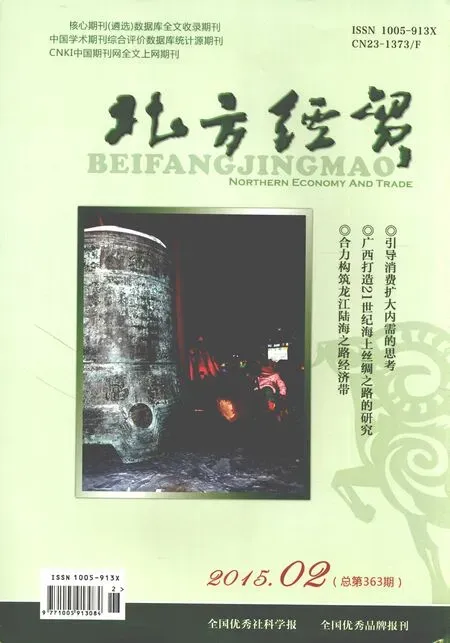淺析網絡民意的概念
許 鑫
(哈爾濱商業大學,哈爾濱 150028)
從古至今,“民主”一直是人類不懈追求的目標,而網絡時代的降臨,改變了民主參與的成本,使民意有了新的傳輸渠道。網絡民意就此產生,它對于民主法治毫無疑問起到了促進的作用,同時,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如何規避它的消極影響亦是一個問題。由此,對于網絡民意概念的研究、網絡民意的界定范圍等問題,都應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分析,才能真正發揮網絡民意的優勢。
一、民意的內涵
“要很精確地來談民意,與了解圣靈的工作沒有兩樣。”在歷史長河中,許多心理學、精神病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均對民意提出了許多進步的概念,但是看法各不一致。其中最為通用的解釋是:民意是個人意見的合集。直到公共領域的出現,對于民意又有了新的認知。在18世紀時公共論壇的興起,引得人們聚集討論,并對一些政治事件提出主張,這促使民意呈現出大眾的聲音。同時報紙的出現使得這種聲音并不局限在特定空間內,它引發了另一種公眾領域的概念,即公開性。這種公開性應理解成有聯絡、多元對話的的涵義,這時的民意就不只是個人意見的總和,還應該是公眾討論及辯論下的共同性。
民意概念雖難以確定,但其構成應包含以下要素:一是議題。民意至少要隱含一個議題,必須是對一項特殊問題所表達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可以是不同的。二是民眾。民眾是指對議題感興趣并參與討論的人。一個人可以參與多個議題的討論,各個議題的民眾并不是壁壘分明的。三是公眾偏好。這是指民眾對于議題意見的總和,它包含了意見方向上(如贊成或反對)及強度上(如強烈反對或稍微反對)兩個方面。四是意見表達。可以公開表達,也可以隱藏于心,這種又稱為“內在的民意”。五是參與人數。民意的目標就是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所以只有在參與人數上達到某種有效的或潛在有效的影響力,才稱得上民意。當然這種影響,是有意見的強度和持有意見的組織,加上參與人數共同產生的,而并非僅由參與人數而決定。
二、網絡民意概念的界定
(一)網絡民意為民意表達的新方式
網絡平臺使得民眾表達的內容也更為廣泛、直接,這些言論是否屬于民意,筆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證明網絡民意屬于民意,是民意的一種新形式。
1.議題發布。從技術上講網絡是有內部連接的節點組成,這些節點遍布網絡所能觸及的每個角落,既可以是一臺電腦,也可以是一部手機。這種開放性,使得參與者可以無障礙地互動與發布自己所關注的議題。網絡為廣泛的參與者提供了技術支持,使得更多自媒體平臺如雨后春筍般涌出。由最開始的論壇、社區到博客,再到微博,媒體變得越來越個性化、個人化,每個人發言的自由空間越來越大。議題出現與更迭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內容也越來越具多樣性,所以在網絡的平臺上不缺少議題,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被遺忘的議題在特定情況下也具有可追溯性。
2.參與主體。網絡具有隱匿性,這一特性使得網絡中的社交行為不同于現實生活中社會等級和身份地位帶來的差別。任何人利用網絡獲取和傳遞信息的權利是平等的,并在網絡中形成一種橫向的新人際關系組織。這種組織結構突破了傳統的社會權力分配機制,使人們在平等的基礎上重塑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使個體能夠完全平等地擁有獲取信息與表達自由的權利。因縱向的權力結構被網絡的獨特性打破,使得趨向于橫向水平化的個人力量被加強,這就初步形成了網絡上的“公共領域”。在此基礎上,網民可以自由選擇網絡發布平臺,參與其感興趣的議題,積極主動地在網絡社區中尋找同盟軍。
3.網民參與程度與意見流向。據統計,截至2013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到6.18億,手機網民達5億。其中男女比例56:44;農村網民占總網民數的28.6%,規模已達1.77億;網民年齡雖然以20-29歲占比最大,但低齡、高齡的網民也呈上升趨勢;小學及小學以下學歷人群的比例也保持增長趨勢。互聯網的興起與快速普及,使得民眾也迅速參與其中。網絡無空間、時間的特性還打破了地域間的文化障礙,使得議題在多種意見討論中可以顯現出共識的部分。且網絡的隱匿性、開放性的特點弱化了“沉默的螺旋”理論,促使網民更為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又因網絡資源的共享性及即時性,網民可以在獲取信息的同時就發表見解,直接參與到事件的討論之中,并能與其相關的政府部門形成“無知之幕”下的對話互動。以鄧玉嬌案為例,鄧玉嬌案的聲音來源于網絡,其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犯罪,怎樣處罰等話題于各大論壇展開激烈的討論。大多數網友從弱勢群體的角度出發認為鄧玉嬌并不構成犯罪,隨著網民意見的呼聲愈演愈烈,引起了上級部門的重視,最后判決鄧玉嬌構成故意傷害罪,但由于其行為屬于防衛過當,以及具有自首、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等因素,免于刑事處罰。由此可見,在網絡上對于某一社會熱點議題,網民好不吝惜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立場。
綜上所述,網絡民意符合民意的構成要素,它其實就是在網絡技術的支持下,為民意表達新添的一種表達途徑。同時,網絡民意還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網絡技術,它是傳輸信息的手段和工具;另一個就是傳輸的內容,也即是民意。因此,可以將網絡民意定義為:以網絡技術為基礎,通過網絡平臺自由地發表個人的見解或評論,集合公眾某種共同的愿望或訴求,從而形成的民意流向。
(二)網絡民意與輿論的區別
對于網絡上言論的“眾生喧嘩”,有兩種態度。一種認為,網絡保障了公民的表達權;另一種認為網上充斥著不實言論,誤導公眾。這就要區分網絡民意與輿論的界限,并非所有網絡上的言論表達均屬于民意。
從廣義上看,輿論是指“公眾意見”,等同于民意,但“廣義的輿論研究為了應付解釋民意的需要,不斷地發明和借用了一些相關概念……使得廣義的輿論研究在范圍上變得越來越廣泛,有時候甚至會出現把輿論研究學者與民意研究學者之間劃等號的現象。”而輿論的狹義概念更能突出其特點,即總是將輿論與媒體的關系放置于第一位,強調輿論是無法離開媒體的一種“公開意見”(而非“公眾意見”)。并且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新聞傳媒對輿論有反應、影響、引導甚至組織的功能,所以,媒體與輿論才是最為契合的關系。因此民意同輿論不應混同使用,其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民意不一定依靠媒體進行發布,它可以是公開的,也可以是不公開的“內在民意”,而輿論則必須是“公開的意見”,并且更加倚重媒體的思想和意見。第二,民意的突出特點是非表層性和相對穩定性,一旦形成,在一段時間內不宜變動。而輿論,則缺乏穩定性,難以預測。同時,民意還包含意見流向和行為后果,在一定時域、地域多數民眾對某些公共事件、公共政策等形成相同的評價或相似社會情緒,這種社會評價及社會情緒還可能伴隨著相當規模的群體性活動。而輿論并不強調它本身所帶來的社會心理以及意見傾向和行為后果。第三,民意側重于人們對社會具體事物真實的情緒、意見、價值判斷等,是民眾內心的呼聲。而輿論則被區分為國家和公眾等不同的輿論,其中既有民眾的聲音,也有國家的聲音。并且由于輿論與傳媒的不可分性,為達到吸引大眾眼球的目的,輿論本身即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虛假的。如“秦火火”案件,秦火火所發表的微博造成了輿論風暴,但其輿論本身就是虛假的、不真實的。我們就不能將這種虛假的輿論歸為民意。
三、網絡語境下言論表達限度的規制
(一)鼓勵網絡民意表達自由
網絡為民眾行使知情、表達、參與、監督四大民主權利提供了新的平臺,在這里可以將權力放置于陽光下,將我國法律運行機制中的不完善之處暴露在民眾的視野內。民眾可以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去監督立法、執法與司法中的不足或腐敗等現象,這就形成了一股推動中國法律良性運行的強大動力。所以政府部門應當做到廣開言路,鼓勵網民的表達自由,真正傾聽網絡民意,從而達到相互溝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妥協和合作,尤其應認真對待理性的網絡民意。這樣,網絡民意必能成為推動我國法律良性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引導與疏導網絡民意表達
網民對于一個議題發表的評論盡管只是代表個人見解,但是網絡的神奇就在于,它的分散組織結構使信息資源得以自由流動,還可以將分散的意見聯結。這使得網民與網民的意見不斷交匯、分散、擴大到再聚集,從而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民意流,倘若政府部門置之不理,并且對此不及時地進行正確地引導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則有可能引發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導致出現“網絡暴力”事件。所以,政府部門在“網絡暴力”形成之前,應當采取有效的對應措施,疏導民眾的情緒。而這種網絡暴力產生的原因部分歸咎于信息不對稱,網民在無法得知全部事件真相的前提下,又被網絡上所謂的“意見權威”所引導、煽動。此時,政府部門應及時發布信息,與公眾通過網絡進行相互對話及理性協商,消減網民的感性情緒,引導理性網絡民意的表達,從而在網絡上建立一個“協商型正義”的互動模式。
(三)過格網絡輿論的法律限度規制
如霍姆斯所言,如果受到合理限制,言論自由是自由政府無可估量的優惠;但如果缺乏這類限制,它就可能成為共和國的災難。但限制也不能過分地侵蝕公民權利,甚至取消了此項權利。所以要區別對待網絡民意與非民意表達的過格網絡輿論,對于網絡民意,政府應持有寬宥的情懷,做到耐心傾聽與認真解答;對非網絡民意的過格言論,則應將其置于法律之中,持有謹慎的態度。
“過格”的網絡輿論,即是其行為本身已經超越憲法所賦予言論自由的限度,已經觸及其他相關法律構成違法或犯罪的網絡言論。對于這樣的過格網絡輿論應適用相關法律進行懲戒。其中《計算機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對于限制網絡輿論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其第5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國際聯網制作、復制、查閱和傳播下列信息:煽動抗拒、破壞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煽動分裂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的;捏造或者歪曲事實,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宣揚封建迷信、淫穢、色情、賭博、暴力、兇殺、恐怖,教唆犯罪的;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損害國家機關信譽的;其他違反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的。”
由此可歸納出,我國受規制的過格網絡輿論可分為三類:一是政治性言論;二是淫穢色情和賭博暴力;三是違背社會規范和侵犯私權(包括盜版、誹謗、惡搞等)。這三類言論對與國家政權及社會穩定的威脅逐次遞減:政治性言論首當其沖,其次是淫穢色情和賭博暴力,它們是典型的網絡犯罪,宣傳者大都借此進行牟利,國家也應持嚴厲打擊的態度。最后是違背社會規范和侵犯私權的言論,這類內容主要是靠社會規范和司法事后約束,但是網絡平臺提供了強大的信息收集和聚合機制,使得原來并不突出的問題也變得嚴重,所以國家對于此類行為謹慎待之。
四、結語
自互聯網的出現,民意在網絡社會中有了最充分的表達空間。當然,這也為披著民意外衣進行偽裝的虛假言論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對網絡民意與網絡輿論的概念的混同,更使得網絡民意也變得不可靠,變得雜亂無章,所以對于網絡民意的概念界定就顯得尤為重要。雖然網絡民意會由于信息不對稱或激情參與等情況,引起的民意表達的不真實或者偏頗。但這成為促進國家加強政府的信息公開,建立透明型政府,及時傾聽民眾呼聲,進行協商互動的動力。而對于過格的網絡輿論,則要抱著嚴肅的態度進行相應懲治。不應讓表象的網絡輿論,掩蓋真正的民意訴求;不要用對待虛假言論的態度,去束縛民眾說話的權利。
[1] 彭懷恩.政治傳播與溝通[M].臺北:風云論壇出版社,2002:103.
[2]楊意菁.“民意理論與研究取向——一個微觀與巨觀多元層級觀點的整合”[J].民意研究,1998(209).
[3]Bernard C.Hennessy.民意[M].趙雅麗,張同瑩,曾慧琦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0:11-17.
[4]張歐陽.網絡民主的核心要素及現實效應理論分析[D].長春:吉林大學,2013.
[5] 王來華,林 竹,畢宏音.對輿情、民意、和輿論三概念異同的初步辨析[J].新視野,2004(5).
[6] 郭衛華.網絡輿論與法院審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99.